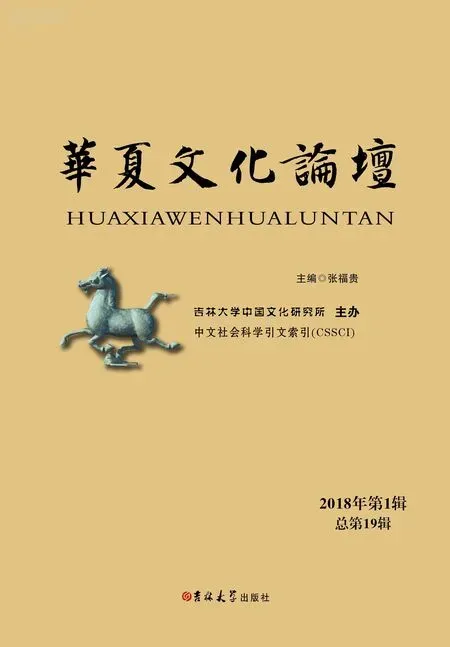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民国文学”还是“现代文学”?
——关于民国文学发展的思考
黄 健
【内容提要】在中国文学由“旧”向“新”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民国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忽视这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文学现象,或简单地用“新”或“现代”“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替代,既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也不能真正地认识和掌握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相反是遮蔽了民国文学发展的丰富价值与意义的内涵,不能全面地展现民国文学的独特性、多样性和多元性价值形态。采用“民国文学”的概念来撰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并非简单地用“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也不是要急于撇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另起炉灶,而是在与现在通用的“现代文学”的相互关联当中,使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能够更加显示出文学发展的原生态,展现出其独特的历史空间场域和发展进程的规律特征。
关于“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争鸣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提出“民国文学”将会冲击现有的“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实属多此一举,甚至是在替后人担忧。一些学者认为“民国文学”框架实际上无法容纳很多重要的文学现象,而且有些问题不好处理,例如,解放区(即民国时期为共产党实际管辖的地区,如井冈山、瑞金等“红色苏维埃区”,抗战期间的“陕甘宁边区”等),虽然属于民国时代,却又不归民国政府管辖的部分,其文学又怎么写?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还在持续“中华民国”名号,又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的现象,所谓“民国文学”,到底是时间概念,还是意义概念?等等。网络上也曾有人提出“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史整体面貌的认识”的问题,有人则解答道:“不是已经有了吗,就是现代文学呀,如果是“中华民国”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提出来,那段屈辱的历史会刺痛很多中国人的心,现在的划分不会影响对中国文学史整体面貌的认识。”温儒敏教授在博客中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指出:
“民国”曾经是一个国家实体,是历史事实,所以“民国文学”应该研究。以“民国”为研究角度,也许会发现某些过去文学史所有意无意遮蔽了的现象。但如果写一本民国文学史,肯定会碰到很多麻烦。我主张这个问题不必再争议不休,能不能写?怎样写?最好在实践中去摸索,拿出“干货”来,那时再讨论,才有眉目。但无论如何,“民国文学”只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不能也不应以“民国文学史”取代“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研究应当拓宽视野,但不能丢失价值尺度去做大拼盘的文学史,要防止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与相对论。
的确,采用“民国文学”的概念来撰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首先要做的工作不是急于简单地将“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也不是要急于撇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另起炉灶,而是在与现在通用的“现代文学”的相互关联当中,使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能够更加显示出文学发展的原生态,展现出其独特的历史空间场域和发展进程的规律特征。
就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如果说1840年是相对封闭而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开始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性标志,那么,自这之后的中国社会便逐渐地进入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为意义重建范畴的“现代”“现代性”一类概念,也开始为人们所青睐。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就对“民国”与“现代”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与解说,解释了为什么采用“现代”而弃“民国”的缘由。他说:
吾书之所以题为“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提“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系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造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皆甚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命之世,言文学必限于民国,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治国闻者,倘有取焉。
虽然钱基博先生当时主要考量的是由于民国时间较短,且许多文学上有名气者,皆与晚清有着紧密的联系,故在当时采用“民国文学”概念,时机未必成熟,而采用“现代”之说,主要是要将民国文学与以往的文学作一个时间上的区分。应该说,钱先生的这种认识理念,对后世认识民国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现代”置于“中国文学史”之前,而非“中国”之后,也即并非后人所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绝不是搞文字游戏,其用意还主要是从历史的发展维度来界说民国文学,也即他所采用的“现代”,更多的还是基于历史时空的考量,并不是像后人那样更多的是基于“现代”“现代性”的意义考量。因此,虽然说钱先生采用“现代”之说,对后世影响也甚大,但后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的真正用意所在。
对于民国文学而言,“现代”“现代性”等意义的含义,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内核。晚清以降,“现代性”(modernity)就成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历史进程之后挥之不去的主导元素。就现代中国发展境况而言,渴望摆脱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内涵的唯一价值标记,由此生成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也就一直都在为现代文学重构现代性,构筑最基本的认知空间。这就是后来的学者之所以坚持把民国以来的文学,称之为“现代文学”的最主要的理据。然而,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还是从文学发展的维度来看,这个理据虽然有较充分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并不全面,也不够细致,甚至也有失客观公允。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一定的程度上,都遮蔽了民国时期文学发展的许多价值与意义的内涵,许多曾经活跃在民国文坛上的鲜活的文学现象,不能全面地展现民国时期文学的独特性、多样性和多元性价值构建的历史发展境况。
众所周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相对应、相制约的时代要素。以时间维度而言,当整个中国社会自晚清被迫进入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以来,“现代”“现代性”的要素就开始植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进入民国之后,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开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民国的建立,一种与新的共和体制相对应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观念、意识也随之而诞生。和以往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体制相适配的观念不同,民国时期所诞生的观念、意识,则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发展相适配的全新观念,全新意识。它势必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文学发展而言,它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类型、样式将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换言之,也就是说进入民国之后,随着社会观念、意识和文化生态发生根本的变化,一种与之相适配的文学也就随之诞生了。尽管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民国时期诞生的新文学与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潮有密切的关联,但民国文学自身无论是在观念、意识上,还是在结构、体制上都是全新的。这是由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体制结构所决定的。特别是受现代文化的自由观念和意识影响,它自身的形态也是呈多样性状态的,价值是呈多元取向的,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现代”“现代性”的唯一尺度。如果撇开民国建立的这些要素,只仅仅用单纯的“现代”“现代性”等意义性的概念来统筹民国时期的文学,就势必会将与民国体制相适应、相匹配的诸多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特点等,都会有意或无意的遮蔽或忽略,造成对民国文学生态多样性,价值取向多元性的忽视或消解。以民国社会变迁为例,日常生活习俗的变革,人生礼仪的变迁,社会节日的演变,新的生活方式的确立,都不只是一种表象的变化,而是具有开新风气之先,其背后深含着鲜明的现代社会价值理念,这些都将导致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形成新的文学理想,促使文学的现代转型。如果忽视民国社会变迁、文化转型、观念变革、意识创新等要素对文学的深刻影响,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观和史识态度,也无法让后人看到民国文学的真面目。
以空间维度而言,当整个中国进入以共和制度为主体的民国宪政体制之后,民国宪政无论是在创作思想观念方面,还是在写作机制方面,都为现代作家从事相对独立的文学写作,提供了一种保障,一种空间。具体地说,就是民国的创立,为包括文化和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民国宪政体制使现代作家开始脱离原先的依附关系,使写作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行为,而不再为“代圣人言”“代帝王言”,在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从事着活跃思想,传播文化的独立写作,或借文学发动“思想革命”,或直接参与“革命斗争”,或从事自由的写作活动,特别是当民国宪政成为文学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理想时,整个国民都能清晰地感知到文学的力量、文学的精神,文学的理想,从而使诞生于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学,就与古代文学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与民国宪政相关联,民国经济、教育、文化等体制的新构建,也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以为传播新文化、新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新闻出版传播业为例,从中就可以看到民国经济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民国的现代经济基础,仅靠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成不了民国文学通过现代传播出版的范式,以一种崭新的形态替代旧文学的气势和实力,也展现不出民国文学独有的现代文明精神气质。民国的教育提倡教育权的平等,宣传平民主义教育,也即民主主义教育,注重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而依照现代教育制度建立起了各种类型的大中学校,也为民国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对民国新文学形态的生成,构筑民国文学整体框架所起到的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在民国时期,对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的崇尚,乃是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使民国文化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都无不处处体现出一种现代文明的精神特质。民国文化的深刻变革,为新文学的崛起,创作出与现代文明精神相吻合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保障和有力的支撑。
以文学自身发展维度而言,虽然民国文学依然有着承上启下的特点,诸多的文学理念、文学思想、审美取向、艺术手法等也承继着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又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纪元。这是因为受民国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政体的影响,民国文学较为完整地体现了自身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新的品格、新的价值和新的审美理想,陈独秀称它是“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正是这种以现代的审美标准而建立的新文学,与“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划清了界限。同时,它也深刻地表明,中国文学在进入民国时代至少是在两个方面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是超越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政治、伦理层面,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通过新的文学方式来对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等进行深刻的文化观照与把握;二是在文化反省与批判中,促使文学审美理想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探寻新文学的观念、性质、功能、价值等相关的时代意义的建构。在使文学成为民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中,也使文学成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花”,成为“引领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因此,民国之后的新文学,就不再是对文学进行局部的改良,而是善于从文化审美的高度,对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进行整体性的反省、批判、革新,并进行新的意义的重构,对文学的自身范式、观念和审美理想进行重大的革新,对文学审美价值与审美意义进行现代性质的整体转换。它打破了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规约,提出要在意义重构的视阈和范畴中,在更为深入,更为广阔的文化审美层次和高度,使新生成的文学能够充分地体现对历史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整体把握,体现对现代人建构新的人生意义的高度关注,体现新的文学对于自身艺术特性的审美回归。如同陈独秀指出的那样,旧的文学“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而“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国文学诞生于民国新的文化兴起时代,以充当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急先锋”面目出现,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当中,就能够以一种新型的文学观念、形式、语言、创作机制,迅速地替代日趋僵化的古典文学,以新的文学范式,在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充分展示迈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历史命运,传达现代中国人渴望自由,摆脱困境,迈向富强,重构意义的伟大心声,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标准的建构理念和思想。由此,民国文学获得了一种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和开阔的创作视野,使它对于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审美观照与把握,不再局限在某一个单纯的领域,某一个层面或某一个角度,而是善于在文化审美的综合而广阔的层面上,开辟文学创作的新天地、新领域,展现新的文学的多样性,多元价值取向,以及新的审美活力。从总体上说,民国文学表现出了一种从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心理内涵的高度,探寻民族文化精神内核和症结,发掘民族心理特征,重构人生意义的审美风采。不论是“为人生”的文学,还是“为艺术”的文学,也不论是何种流派、政治立场是相同还是相异,民国文学都突破了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局限,突破了单一的文学之于政治、经济、伦理、社会等“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局限。民国文学创作的那些鲜活的文字,以及蕴藉在文字背后的性灵,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充满着民国时期的文化反省、批判,意义探寻和重构的思想活力。
以历史发展维度而言,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描绘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状况时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视阈上来看,处于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民国文学,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先锋文学”(avant-garde Literature),虽然整体上还显得年轻、稚嫩,但却充满着青春朝气的创造活力其价值取向也具有一种开拓性质的先锋性,所充当的是中国新文化的“历史先锋”(historic avant-garde)角色,它为整个中国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意义重构,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之声,同时也在为整个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开辟出一个新的发展天地。正如圣西门在谈论艺术的“先锋性”时所宣称的那样:“是我们,艺术家们,将充当你们的先锋。因为实际上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里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先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我们诉诸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因而总是要采取最活泼、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为此,圣西门还强调指出:“……在这伟大事业中,艺术家们,那些想象的人,将开始进军:他们将从过去选取黄金时代,并将其作为礼物赠于将来的世代;他们将使社会满怀热望地追求其安乐程度的上升,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将描绘新繁荣的图景,将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意识到,他们可以分享迄今为止只是一个极小阶级的特权的享乐;他们将歌颂文明的福祉,为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将运用一切艺术、雄辩、诗歌、绘画和音乐手段。一句话,他们将揭示新制度诗意的方面。”尽管民国时期的社会还存在着转型时期诸多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但文学的发展却在展现新的历史时代新的面貌当中,展现出来的却是现代中国人迈向现代文明的诗意精神。作为现代中国人重构新的人生意义的新文学,民国文学始终都将文化审美当作了衡量新文学意义建构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胡适就曾以诗歌创作为例说:“如果诗不表达人类痛苦遭遇的呼喊,而只以做美女圣贤的传声筒自满,那么诗便忽略了其应负的神圣任务之一了。”民国文学受民国时期新的文化观念的制约,在将新的意义重构作为自身生成与发展的一条主线时,对于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如文学对道德的关注,对宗教的关注,对信仰的关注,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对个性、自我、主观性的关注,对人生观的关注、对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关注,等等,都体现了一种向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结构深处开掘的总体走向。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特定语境中,民国文学能够自觉地在宽广的文化审美视野中,把文学对于意义重构的努力,引向文化审美的深层领域,使新的文学能够具有一种探寻人的存在意义和高度关注人的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进而能够最终摆脱“文以载道”的观念制约,获得超越传统审美束缚的一种新的审美自由,使现代中国人在进入民国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中,能够充分地领悟到与此相匹配、相适应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审美关怀。
以回归历史本位,寻求历史真相为原则,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民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种追求历史正义的价值体现。历史发展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程序的,无论人们怎样认识历史,阐释历史,都不可能回避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对历史正义的维护。因为历史不能被用来为人们刻意造成事态的工具,更不能为意识形态所任意的左右。用诺齐克的观点来说,对历史关注的“目的状态”或“模式化”的正义理论核心特征,就在于它认为历史正义并不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特性,而是某些“事态”或历史(社会)过程的“结果”的一种特性。保持对历史发展的客观审视态度,并非完全排斥人的主观能动认识性。相反,则是在尊重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当中,最大限度地发掘蕴含在历史原生态中的那些本质性的特征,以便为后人在认识历史当中,能够真正地从历史发展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推动历史在当代社会的深入发展。因此,以学术研究维度而言,用“中华民国文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来替代“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更不是替后人担忧,而是以尊重历史为尺度,来厘清历史时间和空间的体积和容量、现象和本质、广度和深度,体现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历史逻辑的正义性,还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尤其是把原本遮蔽和忽视的历史客观地展现出来,让后人在历史的客观进程与原生态中,真正地把握到历史的发展发脉搏和发展轨迹。就文学发展而言,民国文学所开辟的中国文学新的历史,只是分别在中华共和体制的两个重要时段与场域中进行和发展的不同态势,这本身不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障碍。所以,致力于正确的历史观建设,尤其是文学史观的建设,编撰一部吻合历史发展境况和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特征的民国文学史,将会使历代文学史的时序线索得以完整的无缝链接,进而能够更加有力地促进中国文学谱系的完整化,有效地避免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称谓及其内涵的纷争所带来的干扰,消除以往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研究的渗透,造成挤兑文学史真相的弊端。这对于廓清研究对象,梳理出清晰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境况和版图,建构起完整的中华民国文学史体系,或者说完整的中华共和体制的文学史体系,都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它将使人们能够在民国文学的历史风云中,真正领略到民国文学的筚路蓝缕之功和开新风气之先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