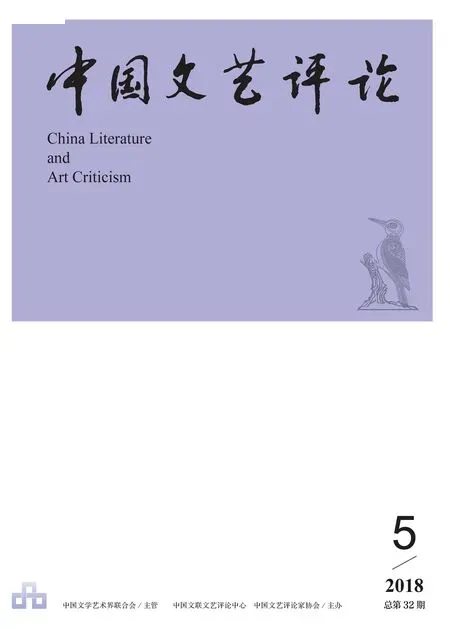金耀基艺术三部曲
长 北
2017年金秋,“金耀基八十书法展”在上海政协展厅拉开序幕。这是继去年香港中环“金耀基八十书法作品展”之后,金耀基先生第二回书法个展。金先生是蜚声中英语文化圈的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版学术著作百万余言。上海展开幕式后,金先生以“我的书写人生”为题作精彩讲座。他将八十余年游历中西方的生涯归纳为“学术书写”“文学书写”“艺术书写”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志向所在、生死以之;第二部曲是兴趣所在,用文字艺术化地表达学术主张;第三部曲是性之所至,一生所历所见所想都化入纯艺术化的书写——书法创作之中。笔者镜头由近及远,对金先生艺术书写——书法创作先行评述。
我是2013年由金先生赠送墨宝初识金先生书法的。金先生自云其书得力于二王,兼采宋代苏、黄、米、赵诸家,对郑板桥、何绍基字也时有临习。我感觉其书法确如逸少“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也得益于黄庭坚中宫紧凑,四出放逸,又并不似黄庭坚四放如剑戟,而是放中有收,回锋蕴藉;也得益于郑板桥撇捺之中有魏碑意味;再看骨肉像何绍基融帖学与碑学,融分书、行书为一体;若论运笔劲俏,颇有些赵佶“瘦金体”意味,却绝非“天下一人”般地瘦劲孤标榨干肉汁;写到兴会之处,则天机自露,潇洒中见腴厚,简直如坡翁米颠回世,一派宋人意趣了。如果用坡翁自云其书“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形容“金体书”,我以为大致应合,“金体书”又比坡翁书见江南名士的潇洒俊逸。
从2013年到2017年,金先生书法一变,诸家影子淡出,自身风貌凸显,劲俏中见腴厚,有法度又洒脱,有逸少的风神俊逸,却绝无逸少的“女郎气”。金先生自云“师法多家而不知归宗何家”,董桥先生称金先生书法为“金体书”。香港“金耀基八十书法作品展”上,展品被拍卖一空。《金耀基八十书法集•序》中随手捻来笔者《中国艺术史纲》中对书法气韵的评述形容自己书法;窃以为,“金体书”更得晋人、宋人之“神韵”,才情、气格、学养、性情,丈夫气、名士气和儒家仁厚之美,皆在点画流动之中。
2017年上海展和上海版《金耀基八十书法作品集》,全部为金先生今年作品。看原作和看香港图册,果然大有不同,金先生书法益发光彩照眼、洒脱灵动了!《短歌行》《归园田居》线条粗细长短强烈律动,可见先生书写时心境极其轻松;《登高》中“禾”“长”等字,如风摆杨柳;《梦中作》末句“家”字笔笔如刀斧凿出,落款“千禧十七年金耀基”虚灵飘逸,一片化机,书写时快意甚至不无得意的情状,一一如在字中。金先生自云“受到敦煌榆林窟‘文殊变’与‘普贤变’二图笔法的启示……是用‘铁线描’和‘兰叶描’来书写”。只要亲临上海展看作品,便可知“金体书”融入“铁线描”“兰叶描”绝非虚语,而是金先生独家创造。
金先生自云书法少时得其父耳提面命,14岁到24岁每日临池未曾间断。从第二次去美国留学直到退休,37年中基本没用毛笔,中文大学就职34年之间,“读帖是我业余最大的乐趣之一”,所以,书法不但没有退步,偶然提笔,还“常有不虞之誉”,如20世纪70年代为王云五先生铜像书200字,90年代为中文大学迎宾馆题“见龙阁”等。退休之后,他在“第一时间拿起了毛笔,并立意定时书写,有时一写就是六七个小时,欲罢不能,‘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居然乐此不疲”。其书法不但在新亚书院成立60周年等纪念活动中十分抢眼,亦因此与大陆、台湾及港澳书家广结书缘,如书法为其继任者——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竞拍、与余光中合书一幅、被《明月》杂志选作封面、为余英时新著《中国文化史通释》题签……由是佳话不断。
再说金先生文学书写。金先生自云“最称心如意者是我教学休假期间撰写的《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及退休后的《敦煌语丝》三本散文集”,香港董桥先生戏称其为“金体文”。三本中我最先读的是《剑桥语丝》。金先生以亲身访学见闻,对欧美学院精神进行了深度解读。他指出大学与学院的不同在于,“大学……是上课、研究的场所,比较是‘智’性的,而学院却是老者安之、少者来之的居息论‘道’之所,比较是‘感’性的”,“英人之重视学院,是由于英人相信大学教育非职业教育,认为师生之不拘形式接触以及学生们共食同宿,具有道德教育之后果”。金先生介绍说,“剑桥学院之谈天,意不在求专精(专精的功夫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做),而在求旁通……重要的是使你对本行之外的东西有所闻见,养成你一种对不同学问只同情与欣赏的心态……剑桥堂在这种环境中,日积月累,自能扩大知识之视野,自能养成一种全面的文化气质”。他对牛津、剑桥的对比,活脱脱写出了两校之“神”,“如果说牛津是天城,则剑桥必是仙乡了!……剑河流过的无数古老剑桥学院的后园,嗅不到一些儿尘烟,见不着丁点儿俗物,云飘水流,万物自得,蓦地里出现一裙裾飘逸的仙子,突然间送来一片箫声琴音,你都不会有半点惊讶!牛津的美阳刚,剑桥的美阴柔,牛津男性化,剑桥女性化”。当读到“原来不敢想象还有比绿玉的绿更美的草坪,此刻却发现白雪之白更冷艳琼绝!还有那一排排的枯树,那一座座孤冷的桥影,那冰河上不出声的一群群有点像鸳鸯的鸭子……而在难得一现的阳光下,残而未凋的柳丝更映射出千万条熠熠的金黄……”我的心已经在欢呼;再读到“心教是每个人对景物的孤寂中的悟对,是每个人对永恒的刹那间的捕捉”,“人的真正成长必须来自自我心灵的跃越”时,我的心简直是在雀跃了!读罢,拿起再读,涵咏吟哦,仿佛与先生共游了剑桥、牛津、海大与哈佛。读后键入电脑,导入手机,一读,再读,每读都感觉如沐甘霖,如坐春风。
剑桥访学之后,金先生为研究社会学家韦伯,重访海德堡并在海德堡大学待了半年,写出《海德堡语丝》。在海德堡,他读韦伯书,寻访韦伯遗迹,自然联想到“韦伯圈”,放而联想到巴黎“杜凯圈”、维也纳“弗洛伊德圈”。他从60万年前“海德堡人”跳到中古,想到歌德、荷尔德林对海德堡的歌赞,想到透纳画海德堡,甚至亲身体验,盖上马克•吐温奇笔所写的“六寸厚的羽毛被”;在“大学广场”,他想到“推开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就在广场的‘狮井’旁主持过一场波涛汹涌的辩论”;在嘉洛斯广场附近,他想起这里“曾是歌德于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两度做客的地方”;到“市墟广场”,他又想起“莫扎特六岁时还在这里演奏过”;重访古堡,他想起中古一个个歌咏海德堡的诗人、剧作家。他写海德堡大学,从1386年卢柏特创立写到“中古宗教世界的大地震、大分裂”,写到“海城从天主教完全转到路德教”,奥多汉尼克“把上帝与恺撒的事清楚地分开来……大学因之得以容忍不同的思想与理论,一个雏形的现代大学于焉出世”,写到承继者的徘徊换班,写到天主教与基督教之战,写到拿破仑称雄、日耳曼小国割据到俾斯麦统一德国再到纳粹入侵,回放了一部海大校史,写活了跨越六个世纪却“长永青春”的海大,文末,先生以轻松之笔写道:“(海大)今日已从宗教、政治的无知、偏执与狂热造成的灾难中走出来了。今日海大已经是一开放、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学府”。他说国外,常常倏地将镜头转向长期供职的香港中文大学,转向童年时期的台湾,转向自己出生地大陆,思绪如天马行空却无一句虚言。这需要对德国文化史学术史乃至对欧洲历史何等地熟谙!在金先生笔下,历史弹跳自如伸缩有致,于是,金先生成了“在历史中漫步的人”(董桥言),其旅行“恍惚行走在历史的隧道中”。由追寻历史追寻韦伯进而追寻自己,他写韦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中的呼吁”。这不仅是写韦伯,也是写韦伯的后继者自己,金先生说,“在小城闲步闲思,最能发现自己”。读此我不免又联想起《剑桥语丝》中的话,“人的真正成长必须来自自我心灵的跃越”。
金先生在海德堡访学半年,其实又是以海德堡为据点游学西欧半年。他写巴黎说,“如果说罗马是西方的精神之乡……巴黎的特殊就在于她具有绝对的国际性格,却又是绝对的法兰西”;他游柏林,从1862年俾斯麦创立的第二帝国,写到希特勒创立第三帝国的野心,写到1948年“柏林解围战”再写到柏林墙,他看到的“不只是德人对‘政治的过去’的冷漠,也是他们对‘文化的过去’的热爱”,从而以宽容仁爱之笔感喟,“在战争中,人不是全疯,就是半疯;不是全盲,就是半盲。有多少人能不疯不盲的呢?”他写弗莱堡说,“传统与现代细针密缝地结合,竟是那么地和谐……人不能活在过去,但也不能不活在历史中……真正的现代化正是应该让现代与传统接榫的呀!”“一个民族没有历史的智慧是长不大的,再豪华的物质也堆不起一寸的历史智慧”。金先生陈情说事,从没有强加于人的态势,话无法说尽,也无须说尽,听者自听。这些边游边想的议论,自然引发人们对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思考。
金先生酷爱秋景。他从海市出发而游周边斯特拉斯堡、巴黎、日内瓦、波恩、科隆、汉堡、弗得里箫乃至柏林的“秋之旅”;仅德国小城,他就游了蓝得勃、曼海姆、斯派亚、法兰斯福、巴登巴登、弗莱堡、蒂宾根。面对落叶纷纷,他以为“只是脱去了秋装,不是与世告别的泪雨”;他写海德堡秋山秋树说,“一树树的菊黄,一树树的蟹红……这不是国画的秋,是西画的秋,是印象派的杰作!”他从秋游到冬,游到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已是冬日,看到“萨城四十几个伸入苍穹的教堂的塔尖,有哥特式的,罗马式的,洛可可式的,就像一组鸣奏天乐的琴键!”他写欧洲小城,倏地跳到北美落基山,我不免又联想起《剑桥语丝》中的话来,“犹记去夏游北美落基山,但见群山排空,气吞斗牛,苍岭负雪,烛照万峰。那种大自然生命的原始跃动,惊心慑魂而幽谷寂寂,山水依偎之态,却又有一种从未沾过人间烟火的天地灵气!”呵,只有沉浸在自然生命原始跃动中的人,才能够洞察大自然微妙的心灵,自己的心灵也就同时得到了自然的过滤与净化。
呀,我已经不遑再写《敦煌语丝》。我看“三语丝”,感觉金先生下笔纵横,思绪飞越,边记事边写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自然生发出感想议论。用“胸中波澜,笔底温情”八个字来概括“金体文”,庶几乎能摄其魂。“胸中波澜”来自好读书、广游历,胸中有万卷书万里路作为铺垫;“笔底温情”来自他良好家教而得的良知教养以及对自然、对社会、对苍生的仁爱。在金先生眼里,到处天清地灵,充满着灵秀之气,到处值得他多情呢喃一番,天地自然与他达到了灵魂深处的契合,正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
金先生自云学术书写“生死以之”,本文不作重点却不可不提一二。他从读法律到改念政治,硕士论文为难度极高的《中国民本思想史》,重回匹兹堡大学又改念社会学博士,31岁出版成名作《从传统到现代》,提出“器物层次技能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思想行为的现代化”三阶段,一版再版影响数代,刘小枫先生评为“汉语现代学的先驱性理论建构……至今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其后出版了《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大学之理念》等影响一代一代学人的学术名著。我受赠的《大学之理念》已是第十二版。书中,金先生回放了一部世界大学教育理念变化史。我特别赞同金先生对博雅教育的赞赏,特别赞同金先生对“象牙塔与服务站”的取舍,特别感动于金先生对大学生的提醒,“大学生的热情与‘直接责任观’常不自觉地纠缠在现实的泥淖中。许多国家的大学生的激烈行动,并没有推倒心目中腐败的权力机构,却反而常湮没了大学的理性与道德的声音,甚于焉者,有些且被驱入骨狱血渊而不可自拔,卒落为假革命者的祭品。许多大学生的运动常以理性始,而以悲剧终……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要等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而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备地掉进险污的现实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必须有待知性的磨练、理性的沉潜,那是在学业告一阶段以后,是在更能判断、更有能力行动的时候”,蔼然仁者,语重心长,慈爱诚恳,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引以为警钟长鸣。金先生将自己《从传统到现代》《大学之理念》《再思大学之道》中警句书为长卷,如书《再思大学之道》“有知性之知,有德性之知,有审美之知,从而大学将不止可卓越,也可有灵魂矣!”我在长卷前立定思索其中微言大义,窃以为翰墨写学术情感受拘,金先生书长卷警句略逊其书横披。
我与金先生交往,源自2013年他来东南大学讲学,我得以陪同活动并且互赠书籍,感觉金先生望之俨然,即之则温,一派宽容仁爱的长者之风。未料金先生回港以后,竟然将我几本浅陋著作读了下去并且十分赏识,陆续赠我“三语丝”、《大学之理念》、自书墨宝和书法作品集。其赠我墨宝书我自传中明志诗“忽忽桑梓风物谙,安居曾不让江南。生当万里留鸿爪,更作鲲鹏越海山”。不由得想起,正是因为此诗与沈鹏先生次韵,我与沈先生有30年的信函交往,意欲将沈先生信函与金先生书我明志诗合为一轴以传永远,金先生表示“很乐意”,立即于酷暑挥汗又书一幅,并且亲自跑到邮局去寄特快专递。手卷裱成以后,恰逢金先生来上海办展,展前为此手卷写成引首“书法缘”。两位大家书法因此诗结缘,于此书坛又续佳话。
金先生能够八十余年先后错综地演奏“三部曲”,源于真性情加读书游历。他自云八十年来“很用功”,“不但看跟社会学有关的东西,社会哲学我也看,文学我也看,我到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看的都是古诗词”。他以整个身心拥抱社会拥抱自然,永远兴致勃勃,永远对世界抱有新鲜的、求知的、逞能的快感。读他的学术著作,感觉情感真挚文采斐然;读他的书集前言《我的书法缘》,如读《世说新语》,真情真性尽在行间。峭拔秀劲又含千种风情的“金体书”,与笔下有情有识见令人击赏情感温文细腻的“金体文”灵魂相通。文,人也;字,人也。金先生达到了孙过庭所说“人书俱老”“通会”“兼通”的境界。董桥先生称其“老得非常漂亮”,余英时评价他“艺术精神贯穿在耀基兄的全部生命之中,书法不过是其中的一环而已。事实上,不仅他以《语丝》为名的所有散文是艺术的化身,而且他在百万言的学术论述中,也时时流露出艺术的光芒”。正因为“金体书”“金体文”是艺术化身,其学术书写也常常带有艺术化表达,研究艺术的我才会与研究社会的金先生如此投缘,“只有在一个心灵与一个心灵真诚相遇时,才能彼此发生感染力”。
金先生书法展还将在北京展出。祝艺术书写给“老得漂亮”的金先生带来更多快乐,祝金先生永葆艺术家般的童心!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吴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