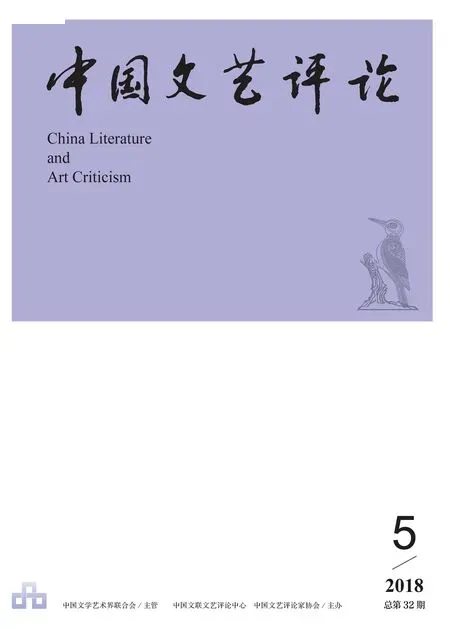“限制”与艺术跨界的尺度
宋生贵
在通常所见的认知判断与语言表述中,“限制”多属于贬义或消极的。不过,在有的领域及某些特有的情境中,必要的限制性不仅是合乎规律的,而且通常会有特别潜质与张力效应,艺术领域就不乏其例。
用历史的、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去,即使不涉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而只要与时间、空间有关系,则可以发现,其实世上的任何存在都是有限制性的——可以说,限制或无限制都是相对而在的。艺术当然也不例外。若落实到众多具体的艺术作品与艺术现象来看,其各自的限制性可谓形形色色,千差万别,难以一一评说。我们在此将着重探讨的是,各艺术种类因彼此间的界限而自然带来的限制,及其在“限制”中实现超越、创造佳作,甚至达到极致的特殊表现力。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创作者在特定情境中没有某种艺术表现上的限制性要求,就没有堪称独绝的艺术性;而独绝的艺术常常表现为“限制”中的突破,在自我要求里获得更大自由。现在的问题是,某些艺术表现凭借外在技术手段通过包装与所谓转换等方式,貌似可以摆脱“限制”,事实上则是放弃了在规定情境中实现超越的艺术追求。如今,各传统艺术门类中“绝活”稀有,不能说与此无关。我们现在之所以讨论“限制”在艺术表现中的必要性及意义,除了学理上的考虑之外,还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也可以说,这的确是因当下某些艺术现象而引发出来的话题。
一
按照现在通行而且有普遍共识的艺术原理,认为自人类开始有艺术创造的自觉意识以来,已形成的艺术种类有:舞蹈、音乐、绘画、雕刻、文学、戏剧、摄影、电影、电视艺术、网络艺术等,还有的将建筑、园林、设计等也列入其中。显然,这主要是依据表现介质与表现形式的不同而确定的。当然这是大类上的区分,有些大类之中还可以继续划分一层,如绘画艺术,根据运用材料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油画、水墨画、版画、水粉画等。
笔者在展开本话题讨论之前,首先表明一点,以上各类艺术就其同为艺术而言,它们是有诸多共同点的,对此,已有成论颇多,而且笔者对其并无存疑——尤其深信各类艺术的美学指向的融通性与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故在此不作赘述。本文所着重论及的,是各艺术种类的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限制”问题。
从上述这些艺术大类来看,可以说,每一类艺术都拥有其独特的优长之所在,但同时也存在自身的一定的限制性。譬如,绘画艺术可以在二维空间之内展现出直观可视的艺术形象,同时却存在难以表现时间流程与声音形态的局限;同理,音乐艺术长于通过有组织的乐音在时间上的流动而传情达意,但却无法描绘出具体空间内直观可见的艺术形象。再如,文学艺术有不受时空限制的描写上的充分自由,但其落在纸面上的只能是文字符号;摄影艺术有直接捕捉表现对象的极大便利,但其可以展现的只能是瞬间的情景。如此等等,如若将其置放在比较的视野中来看,即可见出,各类艺术之间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此类艺术的优长之处,恰是其他艺术中的短缺之所在;反之,此类艺术的短缺,恰可以在别类艺术中得到发挥。或许正因为如此,便有了艺术的分门别类,有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或曰“边界”),同时也便有了各类艺术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以至各自特有的魅力。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特别考虑到人们很容易提出的一个疑问,那就是对所谓“综合艺术”如何解释。我们知道,如今通行的 “艺术原理”类教科书(包括众多版本)中的“艺术分类”,几乎都将“综合艺术”单列一类,其中包括戏剧(含戏曲)、电影、电视。这些教科书对于作为类型化的“综合艺术”的主要特征的趋同性解释是:综合艺术吸取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的长处,获得了多种手段和方式的艺术表现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它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特点融会到一起,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论者认为,“这种综合性体现为各种艺术元素一旦进入综合艺术之后,就具有自己崭新的意义,产生出一种新的特质。例如,电影中的音乐,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电影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艺术规律和美学价值。”毫无疑问,这样的分类,至少从教学所需和讲解的便利方面看是可行的,而且与所谓“造型艺术”“表情艺术”“语言艺术”几个大类平行并列,其划分的逻辑层面与种属关系也是恰当的。而本文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其一,这里的“综合”仅只是一个为了便于讲解的大类上的用语而已,因为事实上同为所谓“综合艺术”中的戏剧(含戏曲)、电影、电视,分别作为独立存在的艺术门类,既各有其独立性,同时又有其限制性(含边界性);其二,上述所谓“各种艺术元素一旦进入综合艺术之后,就具有自己崭新的意义,产生出一种新的特质”,应该说也仅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情况存在,即某一种艺术进入综合艺术之后,其独立性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容易失去其独立存在的魅力。苏珊•朗格指出:“每一种艺术品,都只能属于某一特定种类的艺术,而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又很不容易被简单地混合为一体。然而,一旦不同种类的艺术品结合为一体之后,除了其中的某一种个别艺术品之外,其余的艺术品都会失去原来的独立性,不再保留原来的样子。”同样也是以音乐为例,“一首歌曲,当把它放在一幕优秀的剧中演唱时,它就不再是一首独立的歌曲,而变成了一件戏剧事件。如果我们在观看这一戏剧时,真的把这首歌曲像欣赏独立的音乐那样去欣赏,这场戏剧就必然变成了一个大杂烩,它就会像是一场普通的时事讽刺剧一样,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艺术,而是由许多微不足道的艺术品串在一起而形成的某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毋庸讳言,在当下一些舞台上,如此“不伦不类”的拼盘式的东西,确实并不鲜见。
二
我们知道,关于不同种类艺术之间存在界限,并直接关系到创作差异方面,较早做出明确指认,并进行比较研究的,是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美学家莱辛。莱辛在美学及艺术学领域有两方面的突出贡献:一者是他通过《拉奥孔》这部学术专著,指出并明确阐述了诗与画的界限;再者即是与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相呼应,建立了市民戏剧的理论和一般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主要见诸他的《文学书简》《汉堡剧评》等著作。莱辛关于诗画界限的分析,正是以在他之前的理论家文克尔曼提出的“诗画一致说”为起因的。文克尔曼认为:“有一点似乎无可否认,绘画可以和诗有同样宽广的界限,因此画家可以追随诗人,正如音乐家可以追随诗人一样。”而莱辛在《拉奥孔》中通过分析诗与画的异同,明确指出其界限所在。他认为:首先从媒介来看,绘画用颜色和线条为媒介,而颜色和线条的各部分是在空间中并列的,是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诗则以语言为媒介,语言的各部分在时间表达上有先后顺序与接续关系,是线性发展的。其次,从题材表现来看,绘画的媒介适合于表现静止的物体,诗的媒介更适合于表现流动的动作。再次,从观赏者的感受来看,绘画是通过视觉来感受的,在视觉感受中,眼睛可以将呈现于大范围内的并列的事物同时摄入视野;诗是通过听觉来接受的,其间,耳朵在时间的一点上只能听到声音之流中的一点,声音稍纵即逝,所以耳朵对听到过的声音只能依靠记忆追溯印象。将上述莱辛分析的诗与画的根本界限的关键点扩展开了看,即可归结到德国美学家们一般所说的“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的区别及界限上来。这属于大而言之的整合。其实,再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可以明晰地见出,即使是同为“时间艺术”或“空间艺术”的不同种类艺术之间,依然存在区别与界限,而且恰恰也正是因为这界限,才使得各类艺术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别有意味。
基于此,本文无意再去继续讨论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区别与界限的有无及其差异之所在,而是着重探究其界限的存在、特别是由此而带来的“限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直言之,笔者认为其“限制”是必要的,其意义在于除了有助于突出不同门类艺术的独特性之外,还可以因其限制性所在而使艺术家练出“绝活”,创造匠心独运的力作,甚至可以达到某种极致。诚如法国画家马蒂斯所说:“如果我拿来一张一定尺寸的纸,我就画一幅与纸大小相适的画……如果我必须在一张十倍于它的纸上重复它,那我决不限于放大它:一幅画必须具有一种展开的能力,它能使包围着它的空间获得生命。”
前面提到,不同门类的艺术之所以有区别,主要取决于它们所使用的材料不同以及因此而制约的技术上和表现形式(包括规定情境)的不同。就中国画而论,其主要材料和工具是绢(帛)、宣纸、水墨、颜料、毛笔;绘画者在一张幅面有限的薄薄的素绢或宣纸上,用这几样简单的材料和工具进行创作——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这样的材料与工具在使用和携带上是相对便利的,但其受限制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恰恰就是因画纸的二维空间平面和尺幅大小有限这一“限制”,使相关的创作智慧生发而出。这首先体现在立意、写形、置陈布势等有关构图方面。中国画构图讲究“以大观小,以小显大”,以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南朝宋画论家宗炳在《画山水叙》中讲:“今张绢素以远映,则崑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同为南朝的画论家王微在《叙画》中讲:“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制躯之状,画寸眸之明。”他们都在强调以确定的材料和工具,在限定的纸(或绢)上表现“无限”的境界,如南北朝时期画论家姚最在《续画品录》中评价肖贲的扇面画时所讲到的那样,“雅性精密,后来难尚,含毫命素,动必依真。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学不为人,自娱而已,虽有好事,罕见其迹”。画家能在小小的团扇之中创造出以“咫尺”而观“万里”,以“方寸”可辨“千寻之峻”的艺术境界,非有精心构思、苦心“经营”与高超的表现力而不可得。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从中国画就画面布局方面的处理,来看艺术家面对“限制”的创造智慧。在中国画的构图及艺术境界创造中,讲究“留白”及计白为墨,以达到无笔墨处蕴涵万千气象,为观画者留下很大的审美想象空间,使之感到画外有画,意味无穷。譬如,有的在画面上留有一定的素白之纸,但这“素白”并非无物可画的缺空,也不是表示什么“虚无”,而是合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要求的“计白”——“计白为墨”,墨出形、白藏象,是计划之白,艺术之白,它与画幅所展示出的主体形象之间,虚实相生,和谐统一,即所谓无画处皆成妙境。我们如今可以看到的八大山人的多幅作品可谓在此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这些作品有的是以虚而藏境,以弥散着的淡淡的烟霭雾气等,以显示其景深意远之境。宋代画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即讲:“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正因如此,画家黄宾虹先生曾特别指出:看画,不但要看画之实处,还要看画之空白处。
恰当的空白之处,是整幅画的一部分,它给人以驰骋想象的空间,也给人以“再创造”的更大自由。看画人既受有墨的实处点醒,又在无墨的空白处迁思渺虑,那么,其对画的理解自然会深永而入微,所得美感必然不同一般。如读宋代画家马远那空间感突出、大部分画面留作空白或勾勒远水平野的作品,人们只有不忽视对于空白处的蕴含之物的玩索,才可能领略到其清新隽永的意境之美。
源于西方的油画无“空白”之说,而是只讲空间。作为所谓“空间艺术”的绘画,可否表现在时间性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及相关内容呢?这就又回到了如何面对“限制”的问题上了。莱辛认为,绘画也可以叙述故事和表现动作,但是只能通过画面上的物体暗示,只能选取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顷刻”来实现。莱辛认为,艺术由于材料的限制,只能把它的全部摹仿局限于某一顷刻。因为是以静态而表现动作,而且暗示毕竟不同明示那样直接和容易,至于以“某一顷刻”来叙述一个事件或一个动作的来龙去脉,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说,这同样是对艺术家创作智慧与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逼”其在“限制”面前实现创造性超越。譬如仅就如何“暗示”方可有效,选择哪一“顷刻”最有表现力,这关系到创作立意的确定方面,对艺术家而言即可见出高下。关于这一点,莱辛的见解是明确并且富有启发性的。他说:“既然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顷刻;既然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选择上述某一顷刻以及观察它的某一个角度,就要看它能否产生最大效果了。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狄德罗曾经以画与诗相比较讲过一个例子,他说,诗人在诗歌中写自己或他人赢得爱情,可以用“身中爱神之箭”作比喻,画家如果照实画来,真的画出画中人物身上中箭后的情状,那不仅是意味全无,而且已完全有悖意旨了;画里应该画爱神向他张弓瞄准的动作及神情。应该说,这里的“张弓瞄准”,就是让人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这样,对于审美者而言,便可以达到所谓“我们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们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也就一定愈相信自己看到了这些东西”的效果了。我们不难想到,艺术家用自己的画笔,在一块平而静的画布上准确而生动地将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那一刻”呈现出来,并能够激活观赏者张开想象的双翼,在广阔的时空中自由飞翔,那是何等的精彩!
三
在“限制”中另辟蹊径,以独特的方式实现对有关限制的超越,以作品的精彩而确证对一种艺术形式的自信,当然并非只是绘画,应该说所有艺术门类及成熟的艺术形式都是如此。如中国的传统戏曲演出,舞台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可是我们所见到的戏剧舞台,无一例外都是有限制的——空间的限制、格局的限制,艺术家们只能在这有限制的舞台上完成演出。还有时间上的限制,就单本戏而论,一般应该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演完,这便要求剧作家和导演在题材取舍、情节设置、角色调度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和巧妙安排,以期达到剧情的完整性和具有最佳效果的表现力。
这里主要谈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如何在舞台空间限制中,以高超的艺术智慧创造精彩。在中国传统戏曲演出中,我们所见比较多的舞台呈现,如:舞台上放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就表示一个房间;演员手中摇一支木桨,就表示在江河之上荡舟而行;演员将手中马鞭一挥,在舞台上走几圈,就表示行程千里万里,等等。这是中国戏曲艺术家的智慧与创造,专业上称之为“虚拟化”剧情空间表现。如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讲述了萧何星夜兼程跋涉追回韩信的故事,演员在舞台上跑几个圆场就表示赶了几十里路程。再如京剧《三岔口》,本是同一个舞台,但要完成先后发生于城外与客店两个不同场景的戏,这两处的空间转换,即以演员一系列虚拟动作表现出来。这种在规定的舞台空间之内,通过简便的置景与道具运用,配合演员虚拟式表演的暗示,达到化实景为虚境,求得“不似之似”的表现效果,形成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一个突出的美学特征。
这样的舞台安排,实际上将好多东西“藏”在了实景之外的“空白”空间中,虚拟于演员的表演中。比如,真实的房屋面貌,滔滔江河,遥遥旅途,萋萋荒郊等,都是所藏之“境”。那么,这些“藏”而不见的景物,怎样与实景呼应而现,以至收到艺术真实的特有效果呢?简言之,即,充分激发和调动观众的想象力。有人说,中国戏剧的“景”不在观众眼前,而在观众心里,在演员与观众的内心交流中。譬如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十八相送”一场,剧情中梁祝别离,依依不舍,所以送了一程又一程,其间有许多场景转换,但又只能在限定了的舞台空间内完成,对于这个限制性的“难题”,艺术家们同样予以智慧的解决,即,以演员的唱词和表演,调动观众的想象配合,而将转换的场景“展现出来”。演员唱:“前面到了凤凰山,凤凰山上百花开”,唱词引起观众相应的表象联想,想到百花吐艳、蜂飞蝶舞的景色,并仿佛觉得此时此刻,这景致正在舞台上展现;演员唱:“荷叶青青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观众则又觉眼前似有绿柳垂条、荷叶田田,一对鸳鸯在水中游戏……观众和演员很好地配合下去,便可逐步“看到”独木桥、村庄、古庙等景致,景随情动,美不胜收。当然,这便要求观赏者,不光要目见、耳闻,更要“神”到,去感受,去体味,从“空白”处看出景象,从情思中想象到妙境,方可见出其美。现在有人看不懂中国的传统戏剧,当然这也许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不懂戏剧舞台的假定性,看不出戏中的“虚境”及虚拟性表演,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四
至此,笔者将特别说明,我们现在讨论“限制”在艺术表现中的必要性及意义,除了学理上的考虑之外,同时也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也可以说,是因当下某些艺术现象而引发出来的话题。我们上面讲到了戏剧舞台“限制”的特殊意义,可是如今的戏剧舞台上,凭借现代科技手段的“神通”之能而无视“限制”的情况则所见颇多。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本身的属性是中性的,而如何运用及运用到什么程度则会关系到其效果的指向。显而易见,声光电等为现代舞台美术设计所运用,为舞台场景的变换、拓展等方面的调度与展现,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与可实现的便利。问题是,许多戏剧表演过分依赖于现代舞台美术技术手段的烘托和造势,以至于或者是达到了因过度包装而明显“抢戏”的程度,或者是有“戏不足,舞美凑”的敷衍。这样的呈现状态,貌似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上述那种舞台“限制”,可是观众看后感受会如何呢?往往是感官娱乐大于心灵的启迪或净化。即,观众觉得当时的场面很吸引眼球,看起来很花哨,或者很新鲜,可待离开剧场后,不仅很少有可回味的东西,甚至脑子里连人物形象都难以留下清晰的印象。所谓“看戏”,并非只满足眼球之需,更主要的是用心灵去体味,并且伴随着想象和联想,为剧中人物的命运而情牵意动,进而真正达到一种心领神会的审美境界,这便需要能够沉浸其中。而过分依靠舞台美术的技术而扩容和造势的戏剧表演,绝对不可能产生如此效果。作家肖复兴曾针对时下某些话剧演出热衷包装,并形成奢靡浮华之风的现象指出:“好的话剧,从来都是朴素的,古希腊悲剧的演出都没有如此奢华过,莎士比亚戏剧演出的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舞台的布景道具也是简陋的,双方激战的军队不过用两个人代表,再浩浩荡荡的群众也不过用四个人表演,从来没有如我们现在动员上百个民工充斥整个舞台。中国话剧走过百年历史,我们前辈导演的那些经典名作,有一出算一出,也从来没有这样奢华过。”这种丢掉了必要的限制性依靠现代舞美技术和人数众多的伴演之类的过度包装,主要与三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迎合当下勃兴的“眼球文化”时尚,以突出卖点,其中包括俯就与媚俗;二是艺术表达泡沫化,其中不乏以小充大、以少充多、以次充优等造作意图,形式大于内容——借外在形式的扩容与造势而企求升值;三是有庸俗的攀比之风和不计成本、不合规律的投资方式起着推助作用。凭借如此不符合艺术规律的“运作”催生的作品,多半是人力物力投入巨大,但艺术感染力却很小,至于艺术生命力,则更谈不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 “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很精辟,虽着墨不多,却指出了有关艺术精品的几个关键点,其中即包括内涵充实、厚积薄发。与我们讨论的话题联系起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那些凡是在内容上兑水卖酒式的无节制拖延、在形式上故弄玄虚式的超限度包装,或在展现上拼盘叠加式的多重性借势的作品,都是与精品创作背道而行的。而此类现象恰恰在当下的多个艺术门类中皆有,除了上面提及的戏剧表演的那种舞台现象外,还有常常看到的尺幅巨大而缺乏意味的绘画,场面宏大、人数众多、服装奢华而鲜有艺术个性的舞蹈(有的甚至如赶集一般成群结伙地跑来跑去),至于某些电视连续剧无限制地拖延,以致演到后面越来越差、越来越“水”,几乎已成习见。
五
接下来再以欣赏歌曲演唱为例,简略论及艺术表现方面必要的限制与接受者的审美体认的关系。笔者曾多次听人们讲到过这样的感受:对于同一位歌唱演员所唱的同一首歌,听录音往往比收看电视演播,或者看那种配有太多包装性画面——音画同期呈现的演唱光碟要可意动人得多,而且也容易随着歌声进入情境,展开联想。对此,我也颇有同感。原因何在呢?显然,这主要是与审美心理活动中的审美注意有关。审美实践表明,人在有限的时空之内面对客观对象时,不可能将所有信息全都接受过来,而是通过自觉或非自觉的选择或“过滤”,将某一点作为注意中心,其他方面在感知中便会显得相对模糊,处于注意的边缘或注意的范围之外。就审美中视听感受间的关系而言,当画面作用于审美者的视觉并成为注意中心时,传入耳中的声音便相对模糊,甚至会听而不闻;而当声音激活了审美者的听觉并成为注意中心时,映入眼帘的画面则会相对模糊,甚至是视而不见。这就是审美注意的指向性与集中性的体现。由此可见,客观对象只有成为审美者的注意中心时,才可能与接受者建立起审美关系,并生发情趣意味,产生美感。
我们知道,音乐的基本活动是“听”,这可谓是一个常识,同时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最突出的方面。音乐接受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具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在虚幻时空中对形式的认识,其中即需要有关各方共同营造并走进一个“听的世界”。苏珊•朗格认为:“听音乐的首要原则,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在一部作品中识辨每一种单独因素的能力,也不是认识它的方法,而是体验其基本幻象,感受始终不渝的运动,同时识别出使乐曲成为一个神圣整体的指令形式。即便是年幼的孩子们,当他们愉快地听一个曲调时也应该是这样。”就接受歌曲演唱而言,欣赏者在音乐厅或音乐播放器(收音机)前听歌时,一般不会受到“非音乐”因素影响(或影响很小),可以集中听觉注意于歌曲之中,因此更容易沉浸于“听”的世界中,充分感受与体会作为音乐艺术的生命含义。而如今所见太多的那种过分讲究包装的音画并现的歌曲演唱光碟,或者是电视台制作的更注重追求舞台视觉效果的综艺类节目中的歌曲演唱,因其附加了太多的音乐以外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看”的成分大于了“听”。对此,接受者不免或者因视听同时并用而使得注意力分散,或者因画面光彩夺目(甚至有刺激性)而干脆使注意点偏向视觉感受一边。特别是这些年来时不时出现在电视中的某些演唱会,舞台设置华丽多变,灯光调度眼花缭乱,加上阵容强大、满场跑动的伴舞和歌手那种奇离古怪的服饰打扮、手舞足蹈的演唱作派,更容易将接受者的“听歌”之需挤到注意的边缘,而将中心转向刺激视觉上来——如此演唱会,真的成了所谓“音乐看在眼上”的“不伦不类”了!
审美注意中心的形成,与客观对象和审美主体两个方面有关。作为审美对象的客体,应能在特定情境之中有主辅之别,强弱之差,以使将主要部分凸现于人们的注意中心。作为审美主体的接受者,在感受对象的过程中,则要有注意的焦点,而不能左顾右盼,游移不定,或者面面俱到,平分秋色。许多美的创造、美的境界,往往都是具有形成审美注意中心的特质的,如前面讲到中国画在构图经营上格外讲究的虚实藏露、宾主分层、留有空白;中国戏曲艺术中以人带景、移步换形的舞台情境处理,都是有益于吸引审美者集中注意力把握其中心内核,且又可在空域中充分展开联想与创造的。在高雅音乐会上,那些真正懂得这种审美特性的歌唱演员,一般不穿奇装异服,不去刻意弄姿作态,而是着力以歌声动人,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电影艺术是突出视觉效果的,所以,一些优秀的导演在影片中的音乐处理上,决不喧宾夺主,一般都是在需要调动观众的听觉感受而辅助画面推进艺术情趣时,出现音乐(包括主题歌、插曲等),这时,银幕上的视觉形象的强度则要暂时减弱。
审美注意的心理特征表明,一定美感的形成,并不在于外物的繁多充盈,也不在于主体的急切匆促,而是在于择其要者,引起关注,以至从某一点滋润开来,生发出美的情趣,使人真正感受到,在这种情境之中,充满了全部艺术的生命含义,充满了人类情感的体验,是一种触动心灵的精神活动。
作者单位:内蒙古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