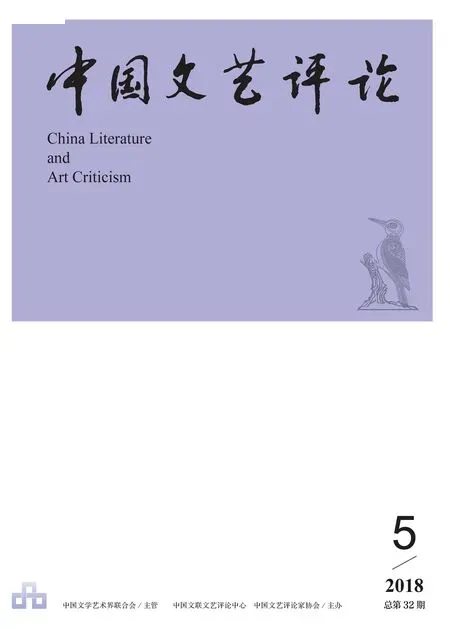文学理论亟待突破的三个问题
李春青
平心而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是越来越成熟了。何以见得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者们不再有以往那么强烈的“热点情结”了。无论面对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多么稀奇古怪的理论与提法,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差不多都已经是波澜不惊了。大家各有各的兴趣,不会像10年、20年前那样一窝蜂似的追踪时髦话题了。还有就是“学术代沟”的出现,这也是这门学问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不要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了,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与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言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有趣的是,这种“学术代沟”并不大会引起争论与交锋。大家各说各的,完全不搭界。无论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都存在着这种“学术代沟”的现象。像20年前那样某位学界前辈登高一呼,学界马上响应景从的现象是再也见不到了。所谓“前辈”“德高望重”之类的称呼,在年轻人心中,实际上就是陈旧、落伍的代名词。“晚辈”一般不和“前辈”们争论,不是不敢,也不是不能,而是不屑。如此则不同“代”的学人们在各自的“代”的共同体中交流、讨论,倒也相安无事。过去讲一代有一代的学问,那个“代”是指时代而言,一般都要几十年或上百年,现在的“代”则是指年龄,一般也就十几年。“90后”关心的事情“80后”就不大能弄明白了。因此,“学术代沟”也就成为学术多元化格局中的一道重要景观。鉴于这一状况,以下我所谈的所谓“新问题”,大约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才被认为是值得谈论的,且姑妄言之而已。
一、审美的还是文化的
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经过了来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近三十年的浸润之后,如今开始思考一个看上去简单却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文学理论与批评究竟应该以“审美”为核心还是以“文化”为核心?所谓以“审美”为核心就是以揭示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为旨归,专注于文学形式、修辞等“文学性”因素,热衷于区分文学之为文学而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在存在样式以及功能诸方面的不同之处;以“文化”为核心则是着眼于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整体关联性,致力于阐释某种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并揭示其社会文化功能。前者可以称为“审美派”,以坚持捍卫文学的纯洁性为己任,试图在人欲横流或者工具理性所统治的世界中为人类看护最后的精神家园,保存人性的种子;后者可以称为“文化派”,认为那种纯而又纯的审美性的文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文学与其他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一样,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都与人的社会身份、利益、欲望息息相关。在西方,从康德之后,“审美派”文学理论自成统序,坚持不懈地捍卫着文学的自律性,在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文化派”文学理论则与史达尔夫人、斯宾塞、泰纳、俄国民主主义者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密切关联,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又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得以蓬勃发展,只是到了90年代才渐渐停歇下来。在中国,“审美派”文学理论在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曾经一度发出声音,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等等,后来就差不多销声匿迹了。而到了80年代初期,在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这派文学理论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以至于“美”与“审美”这些概念都与“人性”“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完整的人”等一系列大词紧紧捆绑在一起,似乎只要对“审美”的神圣性略有质疑便犯了大不敬之罪一样。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当西方的“文化派”文学理论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派”文学理论却在刚刚被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促动下再度辉煌起来。只是近几年来,标榜“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研究方法与视角的论文题目在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中才比较少见了。人们开始重新呼唤久违的“审美”了。“美学回归”于是成为当下文学理论领域的一种声音。由此可见,循环往复、此消彼长似乎是“审美派”与“文化派”两种文学理论之关系模式,只不过在中西之间呈错位状态而已。
那么在经过了“审美派”与“文化派”轮番“执政”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如何自处呢?窃以为那种把“审美”纯粹化、甚至神圣化的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是以精英阶层的精神特权为前提的,是昔日的“立法者”自我确证其精神贵族地位的方式之一。对于今日已然大众化、平民化的知识阶层来说,抱住这样的“审美”象牙塔不放,只能是上演堂•吉诃德喜剧的现实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种无视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娱乐消遣功能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显然也有问题,因为文学文本及相关活动在言说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文化与意识形态形式,而且“审美”虽然并没有超现实、超历史的品性,也并不具备拯救人性的伟大功能,但它毕竟是存在于人的个体性精神活动与经验之中的。在纯粹个人性的审美经验出现的那一刹那,康德的“无利害”之说、叔本华的“自失”说、尼采的“沉醉”说、立普斯、费肖尔等人的“移情”说、布洛的“距离”说等,都是可以成立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清醒地了解各自的理论阀域限度,“审美派”文学理论与“文化派”文学理论是可以并行不悖地共存的。最要不得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不承认二者同生共存的可能性,而是要融二为一,宣称我既是“此”又是“彼”。这显然是一种大一统意识和霸权心态,是不切实际的妄自尊大,与多元化文化学术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在这种心态下建构起来的文学理论只能是一种语言游戏,看上去面面俱到,最终只能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具有任何可操作性。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比如,究竟什么是“审美”?吟诵唐诗宋词、欣赏贝多芬、巴赫与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之间真的有高下之分吗?是谁定的标准?这标准是永恒的吗?又如,把文学艺术都看作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话语表征真的是合理的吗?有什么意义?等等。
二、是理论中心还是文本中心
文学理论应该从理论出发还是从文学作品出发?张江先生的《理论中心论》一文对那种“不以文艺为对象,而是借助或利用文艺膨胀和证明自己,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张江先生的这一批评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在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用中国古今文学材料来证明某种西方理论合理性、普适性的做法由来已久,几乎成了一种文化惯习。这一文化惯习不打破,中国的文学理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学术。王元骧先生的《读张江〈理论中心论〉所想到的》一文对张江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但又认为在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演绎推理也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对文学研究与批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认为张江所批评的那种“强制阐释”或“理论中心”现象是对理论的误用而非理论本身的问题。显然王元骧先生的补充观点也言之成理。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避免“强制阐释”与“理论中心”的前提下恰当地运用已有的理论来指导文学研究呢?在这里我有几点浅见,提出来请方家批评。
其一,在运用某种理论研究具体文学现象时,要明了一个道理:世界上任何一种真正有效的理论都是在特定社会与文化语境中,面对特定现象,为着解决具体问题而提出的,所以其有效性就受到种种条件制约。理论的这一特点一方面要求我们在言说一种理论话语时一定要有具体指向,不能为谈论理论而谈论理论。这就意味着,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运用一种理论来研究具体文学现象时,必须根据这一现象的特殊性而对该理论进行调整与修正。任何对理论的照搬或移植都难免会陷入“强制阐释”的误区,正如张江先生所批评的:在展开研究之前,结论就已经包含在理论之中了。这样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看上去是对这一理论有效性、普适性的印证,实际上却是对其存在合理性的否定。
其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一种理论根本上讲就是一种视角,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切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没有问题的所谓研究只能是材料的铺排、知识的罗列,基本上是没有学术价值的。那么问题从哪里来呢?只能是在研究者已有的知识储备、理论观点和研究对象之间互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理论的价值正表现在这里。可以说,倘若没有理论的烛照,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就被各种具体材料所遮蔽,研究者不能发现问题,真正的研究也便无从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必须符合文学现象本身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理论强加给它的。否则也必然导致“强制阐释”的结果。
其三,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真正有效的理论和方法表现在对问题复杂性的揭示而不是寻求剥离了具体性的一般性或共同性。能够在看上去平淡无奇的现象中发现复杂的关联性与意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这就要求在运用一种理论方法对文学现象展开研究的过程中,要有历史化、语境化的视野,不是把这些现象看成孤立的存在物,而要看作是某种关系网络的产物。研究本身正是要对这一关系网络的形成与运作进行剖析。“理论中心”或“强制阐释”则刚好相反,总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一个结论,而这一结论又是理论本身所预设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把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对象意味着什么?文学应该是用来分析认识的还是体验玩味的?古往今来那些有价值的文学理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对文学现象的归纳概括,还是来自于另一种形式的理论话语?等等。
三、关于“标识性概念”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焦虑:大家说的都是别人的话,没有自己的声音。于是有识者就提出要创造自己的“标识性概念”的提法。这体现了一种自觉的创新意识,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所谓“标识性”也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如果把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或者学术共同体,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我们的“标识性概念”是不断涌现出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的“审美意识形态”“主体性”“向内转”到90年代的“新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化诗学”,直至近年来的“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都在一个时期里产生过较大影响,因此都是“标识性概念”。然而,如果扩大范围,把国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视为一个场域或者学术共同体,则我们在这里确实缺乏标识性概念,尽管我们对这一共同体中的主要人物及其理论观点如数家珍,但人家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彼此之间并没有构成对话态势,因此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一学术共同体之中,一直是场外的看客。我们只是看而不被看,因此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理论与观点,在这个共同体中都无法成为“标识性概念”。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看不是建立在真切具体的文学经验基础之上的,而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话语中横向移植过来的,实际上是无根的。一种文学理论,或者以无数丰富具体的文学经验为基础,或者有强大的哲学体系为依托,才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从而获得“标识性”。前者可以中国古代诗文评为代表,后者可以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来说,“体系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因此要想进入国际文学理论共同体,获得“被看”与平等对话的权利,就只能通过对自己真切具体而且独特的文学经验的理论升华来实现。在这一点上,巴赫金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楷模。在前苏联的语境中,巴赫金之所以能够提出对西方形成重大影响的文学理论见解,最主要的正是依赖于对具体文学经验的理论升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阅读都是独到的,是具有典范性的。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对话”理论是对前者作品阅读经验的理论升华;他的“狂欢化”理论则是对后者作品阅读经验的理论归纳。这些理论后来对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特别是“互文性”理论、“对话”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巴赫金当然熟知西方哲学与美学理论,但他并没有照搬和移植,而是通过对自己独特而具体的文学经验的理论概括提出了独到的概念与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标识性概念”。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经验极为丰富而且独特,文学理论如果能够对这些文学经验有足够的重视,是有可能概括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与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