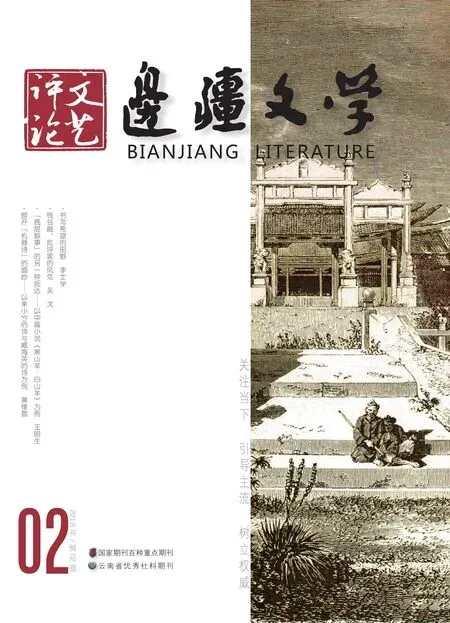重构的时间
——爱松诗歌印象记
钟 硕
(一)
满载人间烟火且又通灵澄澈,便是我眼里的好诗。爱松这本冠名“巫辞”的小集子,就是例证。不过这并非是我乐意书写它的原由。泱泱大国人才济济,有妙句出佳作者数不胜数,能打动我的,往往是诗者隐含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爱松的诗,风格和调性一目了然,它蕴含了地理和族群的母体记忆,又能穿透任何樊篱在现代性和宇宙意识下决绝前行。
打头阵的“巫辞”系列,具有鲜明的西式古典气韵,复调式,回旋、铺陈、开合明晰有序,才情匠工样样具足,意象跌宕,内蕴深厚,结构修辞都非常漂亮,有一种凝重中的挥洒自如,显露出诗人在诗学探索上的奇特意志,以及对呈表繁复的掌控能力。
相对“巫辞”,“时光令”系列显得清新可人,有的貌似闲笔,却在平实中带出一种东西方自然交融的奇特张力,“意在言外”被诗人巧妙地植入一种现代性的直落中。它分别以二十四个节气为题,暗示时空节点蕴藏的诸多不确定性,以小意象经营出大气场,给出一种宿命和企望交织的生动图景。像《惊蛰》《谷雨》《立夏》《夏至》《处暑》《冬至》《大寒》等,几乎都是神来之作,让人爱不释手。
而“人间词”和“母亲书”等系列,语言洗练而富于律动,力透纸背,表现出诗人以生命固有的孤绝和疼痛,一直于日常中爱着,不断地爱着,展示我们活着的声响——凡俗的灵魂当紧紧搂抱凡俗的肉身,怜息它的短暂。
这本小集子虽薄,质素却很繁复和丰盛。历史、个体、族群记忆,东方西方、现代与传统,探索与坚守,应有尽有,信息量十足,仿佛多声部之“混响”。而这些品格特别的诗篇,有着一个共同的关键词 :时间。我确指为“时间”,是从这样的妙句开始:“我披挂这年华/她是你的,又泽被众人//我等待你,收拾起你放出的影子/它们趴在我青幽的皮肤上/一次又一次进入,活动的时间”(《姐姐》)。“这是青铜重量敲击人间的部分/它在地底,为宫殿守灵/这是古滇太阳纹”。
生老病死,男欢女爱,诸多的万象,全在时间之中。重构时间,追索真相,自古就是诗人的本能;怎么重构和追索,则是诗人的自觉。或者说,有无重构时间的能耐,直接决定了诗者的高下——这的确是获得救赎的唯一正途。很多人都无法面对时间,难以堪受万象的搓磨。诗人之所以“神异”,在于他是在一腔赤诚中误打误撞,感天动地了,造物主便滋养了他,他终得灵光乍现。
于是诗人才可能拿出这等的勇气和才华,代表人间完成使命:“给万物下套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发响的骨节”(《冬至》)。
(二)
那只看不见的大手,送来我们,又送走我们,周而复始,给了我们最彻底的自由和平等,令我们不断领受悲喜和品尝因果,感知“天道制衡”的力量。
唯有“巫辞”,可以修复时间的真相,唤起我们灵魂深处的柔软。
我想,假如一个诗人不做营销不媚俗,且足够诚实和谦卑,他必然至少要面对三种精神困境:生命,文化和生存。同时在文本呈现上,他还要面对审美接纳的争岐,以及诗学品质上的自我诉求。“红酽酽,并非是切割时间而残留的遗产”(《父亲》)——这是爱松式的交响,故土的诗性记忆,古滇国的另一种可能,令他在时间阔大的内部打量生命,萃取真相,企盼理想家国的现前:“藉此,我得以我血肉的姓氏/我得以,我骨骼的盟誓/我得以体内,无路可逃的/蜿蜒崎岖,以及无处可安放的家族之血,来为这团/即将成形的红,做个交换”(《母亲》)。
这肉身当然是沉重的,有着诸多无奈。但也只有经由过无奈的肉身,才可能懂得诸多的悖论和荒谬,错位与抵消,全都是生命的福利——青铜已给出时间最真切的表情,以冶炼术来抵达人心,令我们走漏“原罪”后便可与天地共生。
这人间任何一种身份和角色都是诗人,任何一种文化和族群都可能领认他——诗人不接受限定却又遵从规则。在爱松笔下,先祖、亲人们的来和去,正是生命传承、重复、上升的理由,是同体大悲迷失的一种警示:“是什么颜色/在你身上,捕捉到我的欲求和颤栗……是什么颜色,一动不动/燃烧着地底古老的响动……是什么颜色改变时间的秩序……”(《哥哥》);“我趴在青铜上/承受着青幽的审判/我需要一根绳子/牢牢拴住,金属汁液下坠的重量”(《弟弟》)。
这“巫辞”悲悯,道出生命并没有什么得与失,有时重叠相拥、厮守缠缚,有时决然放手甚至远去,都是为了更好的爱。所谓重构时间,就是回到不同的现场,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心肠和渴慕,在浩瀚的大时空中,进入不同的“界”,纳受不同的图景。
这“巫辞”柔软,先祖,母亲父亲,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是恒在的,哪怕不规则的轮回有着不同的命运挤兑,所有的真相到最后却都指认了“爱”。
是的,诗人热爱这人间的烟火,热爱它天然的不完美。他明白最大的障蔽就是日常性,是现象界对六根的捆绑,只有接受这个障蔽和捆绑才可能有出路。于此,他干净地交出了自己:“也是把我们,撑开/无限平行,并与光滑世界/保持锈蚀的,一滴滴/颤栗”(《雨水》)。“几千年的王国,留给时间的阴影/并不能靠时间自行熄灭,一再被诅咒的/秘密锁孔,它的匹配之力/它的幽青齿痕,全都被你攥紧手中”(《母亲》)。
(三)
时空无尽,人心纷乱。有时,破坏和滋养并无区别。我们必须承认,正因为彼此的心千奇百怪,各自为阵,缔造出不同的生命图景,才有着不同的时间之“界”将我们阻隔。二十四节气乃秩序的钮扣,不可错乱,从上古开始,“巫辞”就是唯一穿越时空的手段,它让不同的“界” 消弭,露出本然的模样——这澄明的真相,让我们明白“代价”的存在,是为了制衡和平等。
因此诗人要用骨血与时间本体交互共存。而这些内心挣扎、游移、诘驳的句子:“用我的骨头,作为一架可以活动的骰子”(《父亲》),则引发出这样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个体的生命与“奥义”会有着怎样的关联?莫非就是这《惊蛰》里的寓言:“诚如我诸多渴念/许多年,许多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下着,黑色的棋”。
我想对于人间,奥义一定有矫正和抚慰的功能,人类只可负责享用它的功能,但奥义却没有义务和需求要向人类澄澈它的全貌。正如它对它的自身,同样没有通道,没有通道则意味它无所不在。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敬畏和随顺中关联这种功能,给出生命应有的尊严和价值。于是,诗人总是由此寄身心于语言,在“象”和“义”之间制造出“场”,完成一种救赎:“我是否在冶炼途中,迷失于青铜的呼唤/把唯一的黑,留给祈祷”(《妹妹》)。
在这么一个时代,这样的诗行,并不需要刻意去感召大众,它就在那里——安静如初,散发出文艺最本质的光辉。
基于以上,我为《巫辞》写下这样貌似遥远和晦涩的文字,仍旧是为了更彻底的爱,更确切地向那些对“巫辞”以为然甚至掉泪的人致敬。这正是“古滇国,青铜、朱比特和交响乐,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迷人的现代性,完全的异质交汇,喻体和喻旨分属于不同的经验领域,须极端隐喻,极端对“内心”之外的不顾不管,纵向通灵净化,横向同体大悲,挥毫出细节如歌,肉身即是音符里神奇消融的灵物,烟火即天国。
因此从根本上看,诗人的良知是延长时间和宇宙意识在人间的逗留。想必这就是“巫辞”的力量——以无所不在的谦卑和坚韧,接近和回归奥义的本然:“在贮贝器内,踢落那些符咒/再把影子作为你的面具/装扮成一座,发光的城”(《弟弟》)。
天使、宽厚,柔弱、邪魔、记忆与伤痛,一切的领受,都在青铜里冒出了生长原点,引领诗人在传统、古典中完成现代性的大回归。也就是说,终极的焦虑,价值的迷惘,悖论和荒诞正是原驱,诗人无须蒸发了日常去神游太极,鸡零狗碎中才有真切可行的路径:“以我的四次幻觉,最后盟誓:/我镶嵌在青铜致命的构造/我重新获得了,镜中/时间图谋的阴影和裂痕”(《孩子》)。“叶子沙沙/不舍远方……”(《盘龙寺》)。
爱松的诗作,有的抱朴泥实,有的厚重大气,有的禅妙空灵,有的清雅俊逸。而原乡,古滇国,交响乐,青铜,正是一种“去化时空”后的相遇,或者说它们本来就不曾抽离过,无需去化什么——这种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完全不可复制。这就是爱松,一个岁月的老儿子,肉身灌满了光阴和悲悯,他在邀约魂灵和它的同类一起观望,那过往岁月里的一切:“当你老了,你就会懂得/我曾经老过的所有岁月”(《当你老了——D.X》)。但最终他们会发现真正留存下来的,仍旧是地平线上无尽的葱绿和天真。
一春又一春,《谷雨》年年有:“这是谁来,替代谁的声音/这是谁能,埋藏谁的声音/这是对着死亡叫不出的声音/这是朝向我们,大风吹落的祖先”。生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可精确和限定而近乎神。轮回和重复,疆域的变更,人事的更替,情爱的无常,都是时间的小把戏。所幸生命原本没有生灭,变换的现象界中,万法唯心,唯有情怀高妙,方能催生出别样的自在与解脱,打破时间之“界”,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