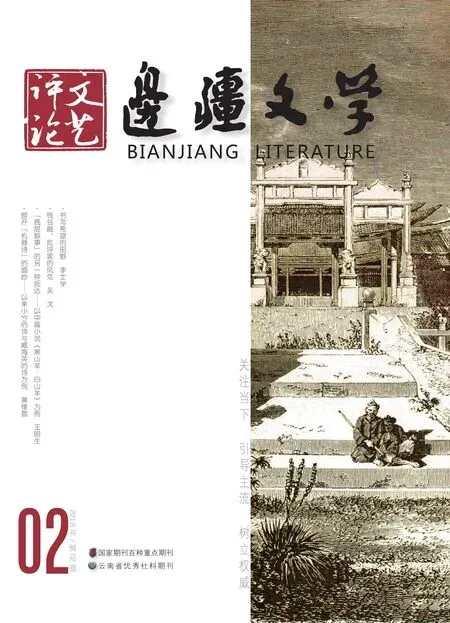异域之境下的先锋文学
——评段爱松小说
赵靖宏
昆明作家段爱松以诗歌写作步入文坛,十一岁时就开始发表诗作,现已出版诗集《巫辞》《弦上月光》《在漫长的旅途中》,其才华有目共睹。生活中的段爱松是一个多面手,除了诗歌,他还涉猎书法、音乐,擅长吉他弹唱,博客里自称 “抱着吉他唱唱诗”,虽素未谋面,但其洒脱、随性的诗人气质可见一斑。近年来段爱松“跨界”到小说领域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的小说以诗化的写作,先锋的姿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以史前古滇国为背景,建构了一个神秘、巫邪的小说世界。他的小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极具个人特色,像是一朵奇葩在秘境中开放。
一、异域之境:古滇国、晋虚城
两千多年前,段爱松的故乡昆明晋宁曾出现过盛极一时又突然消失的古滇国,它真实存在于历史中,如果不是青铜器的偶然发现,古滇国以及这段灿烂的古代文明或许还将长埋地底。无疑,青铜是开启这段尘封历史的一把钥匙。古滇国的命运与青铜及其冶炼术休戚相关,古老的冶炼术在段爱松的小说里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与巫邪之气,正如他在《青铜魇》里的叙述“铜族和林木,经过古滇冶炼术铸造融合之后,上升的部分,成为青铜器。它记载了巫术之源解析下,古滇大地的生息繁衍;下降的部分,则是毫不起眼的灰烬,它是巫术之源被省略的部分,也是古滇大地生息繁衍中,保持不变的、一种被遗弃的定势”。在段爱松小说里,除了两千多年前这个真实的古滇国,还有一个史前时期虚幻的古滇国,段爱松将其称为“梦中常常出现的更远的故乡”,他通过文字探寻古滇国的秘密,他穿梭于真实与虚幻,历史与当下,在梦境与现实中寻踪觅迹这“更远的故乡”。在命运的定势下,古滇国何等的辉煌终究在时间的齿轮下磨剩一些蛛丝马迹,那人类以及沧海一粟的个体的命运又当如何?
神秘的古滇国深埋于段爱松的故乡晋城镇的土地下,这段久远的历史遗迹给段爱松的故乡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他从小就听老人们讲述关于小城的种种神奇传说, 耳濡目染之下难免对故土心存敬畏。当段爱松开始写小说时,他便在他的一系列小说里构建了“晋虚城”。顾名思义,“晋虚城”的原型晋城镇,但又不是现实中的晋城,“虚”暗示着这个城的虚幻,是他小说里构建的另一个故乡。小说《罪赎》里穿插了晋虚城上空一直躲着古滇神兽之首“盖莽”的传说以及小男孩下睫毛变成的花妖猫屙的屎会变成青铜扣饰,小孩子的屁变成邪恶的毒物的故事;《巫奈》中叙述了巫奈奶奶的小脚和绣花鞋离地悬空,巫奈在某个风雨之夜变成一只野狗,诸如此类晦暗诡异之事在段爱松小说世界里的“巫邪之城”成为一种常态。
正如“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威廉·福克纳,“阿拉卡塔尔小镇”之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山东高密”之于莫言,段爱松的小说均发生在他虚构的“晋虚城”里,“晋虚城”是他小说创作的根脉。因为植根于具有民族和乡土特色的高密东北乡,莫言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不是拙劣的马尔克斯模仿者,莫言曾经幽默的谈到是童年的饥饿经历激发了他无限的想象力,而段爱松的想象力则是来自于云南独特的风土人文,这片相对封闭、有着多元文化又神秘的土地,孕育出他小说里那魔幻和诡异的故事,他依托于这异域之境,将远古的古滇国与巫邪的晋虚城写得魔幻无比。对云南作家而言,强行追随外界的写作趋势并非明智之举,因而大多数云南作家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愿意写自己熟悉的故乡,比如藏族作家永基卓玛,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傣族作家禾素。但段爱松又与之有不同之处,他不是单纯地写对故乡的深情,在他文字的炼金术下,故乡的每一寸土地,石寨上的地下宫殿、南玄村、上西街等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的小说明显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形成一种既本土,又现代的文学风格,这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更多的解读层次。
二、叙事和艺术的探索
段爱松说: “有自己独到的异域之境,就应该写出不一样的小说” 。只要读过他的小说,都能明显感觉到他写小说并非传统的写作方式,习惯于传统阅读思维的读者可以说是很难理解他的小说。不过,写作本就不该循规蹈矩,写作应该是顽皮的,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你让他往东,他偏往西,你让他往左,他偏往右,如此一来,才能别具一格,千篇一律的写法很难让有“野心”的作家产生写作的快感。
20世纪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问世,很多中国作家惊讶地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与此同时,中国文坛也出现了充满实验性、超现实主义、带有荒诞色彩的先锋文学,先锋作家们以语言到形式的狂欢刺激了文坛。80年代的先锋文学已经留在了文学史上,而以叙事革命为轴心,彻底颠覆既有文学传统的先锋文学及其精神却没有间断,这才是80年代先锋文学最大的贡献。先锋,是一种精神,它不是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保持作家创作的独立性和探索力,为文学创作提供多种可能性。段爱松的小说是先锋的,他不断进行着小说写作实践,他不是那种以故事情节吸引人的小说家,他热衷于叙事策略的探索,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里,你实验着尽可能多的叙事方式。
段爱松善于通过多种叙述视角来写小说,中篇小说《西门旅社》里从“店主”和“小艮”两个主人公的视角交替叙述,就像一个人在和自己的影子对话;《青铜魇》以“巫术之源”提问,“青铜器”的“巫术”回答的形式构成小说里的重要篇幅;《通灵街》更是将叙述视角的多面性发挥到淋漓尽致,通过死者的儿子、兄弟、老母亲、老父亲、奶奶、前妻、姐姐、嫂子、朋友的视角,从不同的侧面还原死者的原貌,而对于死者的死因,依然是谜一般的存在;《罪赎》也是从多个视角叙述杀人案,但却采用了非人的视角,将叙述的话语权交给被凶手残忍肢解的器官:脑、眼、耳、鼻、足、血、经、骨和影子,这实为非常大胆的写法。因而,读段爱松的小说,你会发现他的故事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他无意于编一个完整的故事给读者,他也不热衷于把故事写得高潮迭起,引人入胜,他更看重的是叙事的策略,通过形式的创新营造一个迷宫,这个迷宫充斥着各种幻觉、梦境、死亡、巫术,他以文字为通道,让读者自行解读小说文字背后的秘密,文学的秘密。
诗歌的写作经验对段爱松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我们知道诗歌的写作思维是跳跃的、抽象的,段爱松小说的叙事也是跳跃的、非线性的。此外,通过对段爱松的采访了解到,他欣赏的作家有乔伊斯、普鲁斯特、布鲁诺·舒尔茨、克劳德·西蒙、歌德等,他的阅读经验直接影响到他善于运用西方文学写作技巧。在小说《把一》里,作者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晋虚城的土基厕所、李荣家馆子等几个场景中交叉叙事,他采用意识流的写法,由医院的来苏味回忆起把一和“我”在晋虚城的土基厕所里“捻安门”,由李荣家馆子的卤鸡蛋颜色回到小学二年级的某一堂语文课,由炎热的午后联想到上西街厂房旁边的大堂里,把一和淘七、老媉的巅峰对决。2012年,一个来自晋宁县晋城镇南门村的凶徒犯下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变态连环杀人案,段爱松以此为素材写下了他的中篇小说《罪赎》。作为一个小说家,段爱松并没有以交代前因后果或以时间为序等线性方式来叙述杀人案,他不仅充分发挥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也运用他先锋的叙事、诗化的文字,将一个现实发生的新闻事件重构。他在该小说每一部分开头都引用《古兰经》《圣经》或《坛经》里的一段,并在叙述杀人案时将宗教与古滇王国的秘境融入其中,赋予这个故事新的生命。
诗意构思和诗化的语言是段爱松小说创作重要的艺术特色,他的中篇小说《青铜魇》《葬歌》《罪赎》体现得尤为鲜明。阅读这几篇小说能很直观地看到他喜欢在小说每部分的开头引入诗歌,起到某种暗示的作用,或是与下文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除此之外,他的小说语言也具有诗歌语言的美感和高度的情感化,可见长期的诗歌写作潜移默对他小说写作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诗歌写作,似乎可以说成是其他文体写作的有效语言训练,或者说成是其他文体诗性美学的某种终极指向。” 小说和诗歌同是文学的重要体裁,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能很好地将诗歌与小说融合,达到令人迷醉和惊叹的效果。段爱松小说里的很多语言,完全可以当作诗歌来欣赏,比如:
“时间世界,在时间的流动下趋于不朽。即使是死亡,也未能避免和阻止这种对不朽的孜孜追求。世间诸多秘密,就这样被置于时间不朽的流动中,尽管它们从没有被人识破过。” (《葬歌》)
“它凝视过我的眼睛,要么充盈泪水,要么射出仇恨,要么惊异万分,要么遍布追忆,要么写满贪婪,要么灌注喜悦……无数的人间表情,在我的外形与质地的引领下,暴露无遗。” (《青铜魇》)
“我是眼,无所不在的眼。我看过我,在母亲深红色的子宫中,酝酿成形;我看过我,出生之后,许多陌生的眼泪,伴随着我的哭喊;我还看过一场葬礼,在我最初的梦中,成为漫天的流星雨……”(《罪赎》)
诸如此类的语言在这几篇小说中比比皆是,这不就是没有分行的诗歌吗?虽然先锋作家如孙甘露、余华等在小说写作中对诗化语言已有尝试,但段爱松的诗人身份使他的诗化小说语言特色鲜明,而且诗歌语言的凝练、跳跃、隐晦也契合了他小说所营造出来的神秘、巫邪、幽暗的氛围,这令段爱松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韵味。但笔者认为,小说语言的诗化要有一个度,过度的诗化会大大增加小说阅读的难度,有时甚至显得晦涩,好的文学作品要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而不是曲高和寡。段爱松在小说写作上的多种尝试能看出他的勇气与先锋,但也显露出不尽成熟之处。
三、人物形象
段爱松的短篇小说以人物命名,虽是各自独立的篇目,却又相互联系,因为小说里的人物和“我”一样都来自晋虚城。无论是身在异乡,还是守在城里,他们都被一股神秘力量牵引,把一、小滴、巫奈、背果、老飞以及“我”都有一个现实生活里的自己和古滇国远古时期的影子,他们都曾在某个瞬间,因为一个声音,一个气味,或是一个场景突然被带入幻觉中,看到梦里的那个自己。作者有意制造幻境,让小说里的人物穿梭在两个世界里,就像镍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每个人物都有两个自己。这些人物在现实世界里或被时代抛弃,或重复着无意义的生活,他们的存在是虚无的,而在另一个世界,梦境当中,那个史前的古滇国里,他们驰骋战场,活得轰轰烈烈。上文提到,段爱松将虚构的古滇国称为“更远的故乡”,这才是段爱松小说里的人物魂牵梦萦的地方。现实世界里,把一凭借“捻安门”这项特殊能力获得肯定,这是他的价值所在,但他知道这项特异性来自于神秘力量,即使在重症监护室里危在旦夕,把一依然等待他背后的那个人带他回去,“他经常梦见那些奇妙的幻象,那些意象丛生的植物和动物,那些古老原始的肥沃土地,让他多么魂牵梦萦……”(《把一》);小滴赤裸狂奔追赶红色轿车里的父亲,那是他生的希望,但他终没有看到父亲的影子,唯有在幻觉当中他看到曾经的自己躺在母亲怀里吮吸乳汁才感到世界的幸福和快慰;老飞在离乡的日子里频繁地更换职业,每一份职业里他都能看到那个遥不可及的梦的碎片,透过这些碎片,他重新寻找在另一个城市迷失掉的归乡之路。相比现实世界里的自己,那个幻觉世界的自己似乎更真实。也许我们每个现代人都生活在“晋虚城”,我们自以为的现实世界才是荒诞的,而梦境里的那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
段爱松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是虚化的,他的短篇虽然看似是以人物为中心,但阅读之后读者的脑海里并没有把一、小滴、巫奈、背果、老飞这些人物的清晰轮廓。他的中篇小说,如《罪赎》《青铜魇》等,人物形象更为虚化,作者并不着力塑造人物的外貌、性格,人物在作者笔下仅仅是一个个的符号,没有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不重视人物,只不过作者看重的不是刻画某个人,也不是人的表层特征,而是人本质的、内在的东西,这也是先锋小说塑造人物常用的方式。
2016年的安徽文学年度奖对段爱松的颁奖词中这样说道:“当一个作家无法控制现实和把握人性的时候,穿越中的想象就成为了破译现实和抵达人性的另一种可能”,段爱松在他的小说里极尽想象力向读者展现神秘的异域之境,他通过史前的古滇国、巫邪的晋虚城以及发生其中的一切人和事,于现实与梦幻的切换中营造出神秘、诡异、模糊、幽暗的氛围,这是段爱松探究现实和人的另一种途径。
何平,段爱松.访谈:有自己独到的异域之境,就应该写出不一样的小说[J]. 花城,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