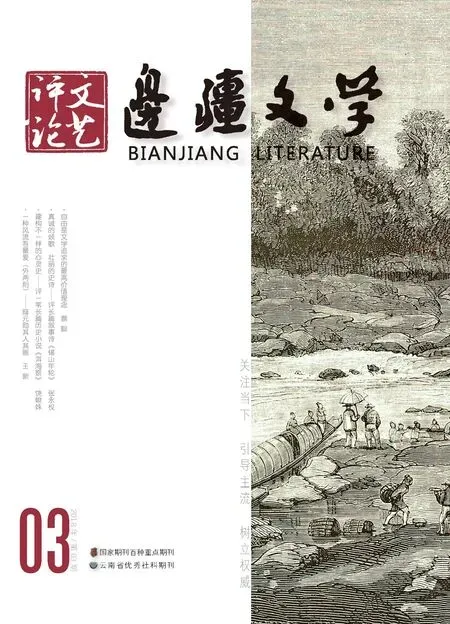浅析《洱海祭》中情节的严密性
罗茜茜
长篇小说《洱海祭》是一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截取了公元737至738这一时间段,向我们生动的描绘了发生在洱海区域的一段往事。一苇先生以他独到的笔法,化身于“我”即千夫长德隆,将自己置身于那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见证了南诏大理国大幕的徐徐拉开,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的慈善夫人形象。一苇先生曾说过:“对于我的民族而言,我和众多的民族写作者一样,是扎根苍洱大地的灌木林,或许不能撑起一方天空,却能守护云南大地的人文生态。”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民族情怀,一苇先生才能全身心的小说创作。
看完《洱海祭》,脑中一瞬间浮现的是“生命”二字。这来源于我的导师饶峻姝老师在她的美学课上所讲的一句话:“中国哲学是有生命的哲学,美学是有生命的美学。”那我能不能也说一苇先生的《洱海祭》也是一部有生命的作品?谢有顺先生讲过的这样一句话更加坚定了我这一信念:“只有看到小说和生活在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时,对小说的研究才不会变成单一的对知识、材料或者写作技巧的解析,而是会去体察作者的用心,细节的情理,灵魂的激荡,并由此认识一种生命的存在。”在我看来,无论是作者的用心,细节的情理还是灵魂的激荡,都和小说情节的严密性不可分割,小说情节的严密性是赋予《洱海祭》以生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是一篇由家园守护而展开的战争故事。小说第一节就提到了太和城、野共川、龙于图和德源城几场战役,看似不经意的描述却为整篇文章梳理了脉络,智取大和城是卷入命运纷争的导火索,野共川、龙于图和德源城之战是为了守护家园而展开的战争。长篇小说离不开故事,如果没有故事那人物的性格也许就不能够被凸显,从而主题思想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一苇先生的笔下,为守护家园而奋起反抗的战争故事成为一条主干,顺着这条主干我们看到了骄傲自大的咩逻皮,看到了美丽聪慧的慈善夫人,看到了骁勇善战的皮逻阁父子……甚至还看到了邓赕诏子民在战场上被注满了血色的眼睛。小说看似单一的主线不断分支,生动之处开出花来。咩逻皮受皮逻阁父子的蒙蔽不惜亲自率兵携儿子和儿媳妇投身于太和城之战。皮逻阁父子绝地逢生,然而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得以实践,皮逻阁在攻陷太和城后将矛头直指大厘城,小说故事也就由随之而来的一场场守护家园为旗帜的战争故事一以贯之。初读《洱海祭》时,和很多人一样对小说中的叙述者“德隆”这一角色心存疑惑,觉得一名猎户出身的千夫长在小说中却如智者一般的存在很不合情理。静下心来再读《洱海祭》,不禁为作者的良苦用心感叹不已,这也是作者在写作手法上较之于《遥远的部落》的高明之处。“内聚焦叙述的作品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通常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焦点因此而移入,成为内聚焦。”作者化身千夫长“德隆”,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文本中,他一次又一次的下跨战马手持青龙偃月刀协助邓炎诏同皮逻阁父子作战,一步步见证了皮逻阁父子的崛起以及邓赕诏部落的败落,进而让我们感受到了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我们坚信这是作者进入文本亲自投身的战斗,阅读时的心情也随着千夫长“德隆”的所见所闻起起落落。“情节要被感受所浸透,动作要和内心相联,小说才能不做情节的奴隶,而成为生命富有想象的演出。”小说中的情节描写并不只是平铺直叙的记叙,还渗透着多处人物的感受以及心理描写。开战前人物语言的相互试探,打斗时处于劣势的忐忑心理,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较量。此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将写作的边界定的范围很小,时间跨度只有一年,这反而把作者写作的才能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往下深钻的点,虽然小,却有足够的力量。作家靠有限的生活经验去写几代人是很难的,并非每个人都有曹雪芹先生一般的才华。一苇先生正是清楚地认识到了此点的,把自己的笔力集中到了某一人物、某一时间段,《洱海祭》才有如此严密的故事情节,而他笔锋所触及之处,哪怕是“林间突兀的岩石”都传递着生命的力量。
刘勰赞许风雅“吟咏性情”,鼓励用笔“为情造文”,批评汉赋某些作者“人非郁陶”,“为情造文”诗学把情感视为抒情作品的灵魂所在,那么对其他类型的作品而言,其重要性自然也被作家所重视。小说中前后四次描写了主人公吟唱自作诗词的场景。第一次是阁逻凤冒死到咩逻皮帐下求援,咩逻皮意气风发取出“浪剑”边舞边唱:“长铗蒙尘兮秋气寒,今日仗剑兮扬辉光。”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发端,我们已能看到咩逻皮出兵太和城心意已决,邓赕诏很快将卷入一场没必要的战争,第二次吟唱的主角是洱河部落首领杨农栋,在他自认为胜利在即高兴地喝过三樽“洱河春”之后踉跄着步子在船舱中吟诗起舞:“巍巍点苍……苍山洱水,尽在我心。”这一细节描写让我们隐约看到了杨农栋生命的尽头,如若他将吟诗喝酒的时间用于战斗,那皮逻阁纵使有滔天的本领也只能饮恨洱海了,可是他所谓的仁慈和大气却贻误了战机丢了身家性命。第三次吟唱的主角是皮逻阁,大厘城头,皮逻阁抚琴吟唱:“忆当年,金戈铁马越君前,江湖寥落伴君眠。想如今,浮云一别后,向人堪与言……”短短数十日,守城人一来一回调换,可叹可悲。邓赕诏在失去大厘城后为夺回家园而战,这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第四次吟唱的主角是皮逻邓,“石窦香泉”饮水工程的建成,再次让皮逻邓夫妇看到生命的希望,皮逻邓兴致勃勃地取下长剑边舞边唱“石窦香泉鸣珠玉兮……人间主乐复向求。”从这短短几句我们可以看到皮逻邓纯粹的内心,而一年前的救助蒙舍军脱险已变成了“佑我三浪拒蒙舍”。这似乎是在做最后的反抗,当“石窦香泉”被皮逻阁发现并破坏时,粮绝水涸的处境下,慈善夫人只得拱手交出德源城。小说中人物吟唱的诗词是否符合史实已无从考证,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情节处理完全是一苇先生凭自己的心意而生出。文学作品中一向主张追求真实,要求情节的真实性,即使虚构性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其呈现出来的故事情节也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加工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真实当作一种绝对化的观念。一苇先生反其道而行,不仅让人觉得其细节的合乎情理,更向世人展示了诗意化的情节处理。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命背后隐藏的灵魂。“灵魂并不是拿来嘲讽用的,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是文学最为重要的关切。”谈到“灵魂”不得不说的是小说的核心人物——慈善夫人。我丝毫不敢嘲笑慈善夫人高贵的灵魂,相反和作者一样对她始终保持着崇敬的心理。据说白族人的火把节是为了纪念慈善夫人而设立,还未读作品就已对这个神秘的女子充满敬意,从小说描述的故事情节背后更是让我记住了这个不羁的灵魂。小说的叙述者“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慈善夫人的贴身侍卫,这就为对慈善夫人的细致描写提供了可能性。这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让人怜惜的女子倾其一生扛起了整个部落的命运,夜袭太和城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光芒,“石窦香泉”的引水方案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深谋远虑,殉身弥苴河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坚贞不渝。一边是慈善夫人率领下的邓赕诏部落面对外来侵犯的不断反抗,一边是皮逻阁父子统一六诏的强大势力,两股力量不断碰撞溅出生命的火花。文学作品中善与恶的形象会不自觉地引发读者的情感,作为读者的我们在体会文本表达的忧伤、欢喜、悲愤等情感时常与作品中人物善与恶的行为或者形象联系在一起。顺着“德隆”的视角,我们希望慈善夫人功成身退,希望邓炎诏部落的子民守护住自己的家园,希望蛮横的皮逻阁父子退回蒙舍诏互不干扰,但这只是美好的期冀罢了,作者仍旧残忍地将笔尖伸到了历史的深渊处。“作家要让作品有震撼力,就要让人物的命运和读者的同情发生逆差——读者越是同情,作家越是要折磨他。人物的命运越是和读者的希望有反差,就越有吸引力。”一苇先生显然是做到了此点,他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呈现到大众眼前,再忍痛撕碎,最后回归平静,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扎实的写作功底。
倘若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都随着读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妨以慈善夫人为例这样思考:如果慈善夫人顺从了皮逻阁成了南诏王妃会如何?如果她并没有跳入弥苴河而是选择一人出逃隐居山林会如何?如果她身居室内不卷入部落战争又会如何?可能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花瓶罢了!慈善夫人的伟大正是在于她那为了部落鞠躬尽瘁,面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灵魂,这正是生命最可贵之处。
(作者系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7级在校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