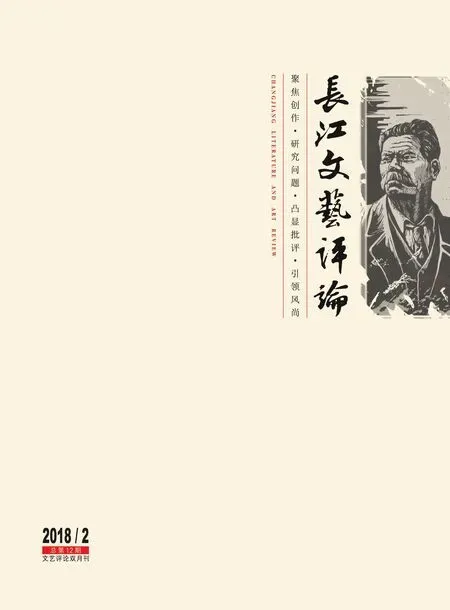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
◎刘 艳
李遇春教授在《为学理性批评辩护》一文中,这样讲道:“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刘艳一直在执着地为学理性批评作辩护,这大约是她给批评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她不仅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忠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学理性批评诺言,而且还从文学批评理论上建构着学理性批评形态。”而在会议场合,有时也会被这样介绍:刘艳一直在呼吁一种“学理性”批评……很幸运,大家能够看到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批评铺天盖地,唯独好的学理性批评较为稀缺情况之下我所作的这些努力,但我不敢冒领的是,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其实是《文学评论》已逾六十年(1957—2017)以来一直在力倡和践行的批评的标准,“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学理性”好比石韫玉,水怀珠,山晖川媚全离不开它。
学理性,差不多是《文学评论》选稿用稿标准的内核和灵魂,有了它,《文学评论》才被中国文学研究界视为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专业学术刊物;有了它,《文学评论》才能在六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赢得不同代际的读者和批评家的一致推重。
究竟什么是学理性批评?我对于学理性批评和批评的学理性的理解,直接得自于《文学评论》的熏陶。而有学者已经将“学理性”追溯到了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先生那里,自章太炎以来,继续加以梳理的话:“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同样也是学理性批评奠定的学术基业。如今依旧为人津津乐道的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朱光潜之类的民国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尽管风格各异、路数有别,但学理性却是其一致的精神标杆。”清末民初章太炎先生曾拟撰《中国通史》,他声明自己的新史将超越旧史,理由就在于要做到“熔冶哲理”,实现“学理交胜”,具体来说,“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所谓“学理交胜”,就是指在历史研究中实现史实与哲理的交融。在中国学术界,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的“六经皆史”之说广为流传,而中国学人又向来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大抵都承认史学是一切学术的根基。这意味着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必须植根于历史,如果离开了历史,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将陷入虚浮无根的非确定状态。而所谓哲理,它也不是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在具体的史实(包括文学史实、文学文本之类)分析中提炼出来的理论结晶,而这些理论晶体一旦被提炼或建构出来就会被广为接受与运用,它作为理论工具指导我们从事具体的历史批评,当然也包括文学批评在内。
这恰好可以解释《文学评论》的当代文学批评文章,为什么总是熔铸一种文学史的视野。而对于具体作家作品,哪怕是针对作家一个新长篇的“新作批评”,也总是有“小史”的梳理,将这个作品放到作家整个的创作历程里去认识和分析,发现新作所体现出的不同于作家自己此前之创作的新质、新面向和新维度,并且注意与前代和同代作家的一种联系、比对和考察。而在与前代作家的比较和考察中,有着评论者要具备“大史”视阈的内在要求——评论者要对自古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甚至包括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批评史都要有所了解。如果是能够做到深入了解,那就再好不过。因为只有具有了文学史的视阈,才能真正发现研究对象独特的价值意义之所在,你对作品的评价和指称,才是有学理性、有说服力的。而且若能具有统摄作家个人创作史和整个文学史的视阈,“在具体的史实(包括文学史实、文学文本之类)分析中提炼出来的理论结晶”,就形成了学理性批评的“理”,而这也是使评论能够真正具有问题意识,是评论实现评论责任担当乃至时代担当的前提条件。
为了形象地解释何为“学理性批评”,我曾经这样打比方,你们看《文学评论》所刊发的好的批评文章,哪怕过十年、二十年,你依然会觉得它好。如果是当初读过,它依然在你心里留有印象,仿佛一位旧人,让你念念不忘。如果是恰好翻到了,旧文新读,依然会从中有所得,你会发现这篇旧文几乎是当时对一个作家作品乃至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研究的最好水平,对于今天的评论和研究,它仍然具有一种史料和资料的价值……这样的文学批评文章,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2018年1月14日,在中国作协举行“新时代:文学批评何为”研讨会暨“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首发式上,《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曾对当下批评提出他忧虑的一面——很多批评时过境迁之后再读,问题多多,甚至是根本立不住的,他为此也郑重提出了好的评论是否应该能够经受得住时间检验的问题。
学术交谈中,陈晓明、吴俊、张清华、李遇春等师友信口就会提到,《文学评论》哪篇哪篇文章,他们印象深刻,而他们所提的这些文章,可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也可能发表于90年代,或者发表于十几年前……《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吴俊,《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距发表已时过近20年,但仍有不少学者都会提到这篇评论,李遇春曾说过:“这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到的第一篇文评论文”,“也许这不是吴最好的文章,但对于我而言是最好最难忘的”。我在准备写作拙文《童年经验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萧红、迟子建创作比照探讨》(《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时,童庆炳先生的《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在文学理论层面对我启发很大,可是距此文发表已经超过20年。而我翻到的另一篇文章《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张红萍,《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距发表也已经15年了,现在读来,仍然觉得在众多的迟子建评论里面,这篇文章差不多可以代表当时迟子建评论的最好水平。而且对于现在做迟子建研究和评论的人来说,这篇旧文仍然有参鉴价值。我曾无意当中读到了刘纳先生的《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不禁叹服作者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写实”小说的学理性阐析和既有针对性又有前瞻性的判断,现在读来都讶异于她那些高屋建瓴又别有会心的批评文字。她对于“新写实”,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在其时而失去应有的理性判断。
一直以来,学院批评和学理性批评都被混为一谈。学院文学批评文章常常被写成了“项目体”“C刊体”“学报体”,但是,“学院批评是一种依据外在的职业划分的文学批评类型,而学理性批评是一种根据内在的学术含量和质地定位的文学批评形态”。而我也曾经较为明确地指出学院批评和学理性批评的差异:“非学院中人,也可以写出富有学理性的批评,而学院中人,也很多都在做着或者说在兼做非学院、非学理性的推介式、扶植性批评甚至‘酷评’,学院中人所从事的批评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学理性批评。但由于目前文学批评从事者以及文学批评自身的现状,学理性批评更多还是学院中人所从事的学院批评所具备的特征和精神标签。起码就目前来说,学院派的学理性批评,不止不应该被否定、被远离、被贬低,反而应该被提倡、坚持并且发扬光大。”
好的学理性批评非常可贵,为何还被大而化之地扣上刻板平庸、面目可憎的“学院批评”的帽子而饱受诟病?搞评论的人,尤其学院中人,最应极为推崇,为什么反而是他们往往对学理性批评持一种疏离、不满乃至挞伐的状态呢?原因不外乎学理性批评的费时、费力和需要较为深厚的学养积累,不如即时性、推介式批评来得好写,更容易让评论者与文学现场保持高度的黏合性。这种情况已经为学者评论家深深忧虑:“许多老成的或者新锐的批评家们,虽然自己置身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但他们却无法耐住寂寞,不愿用自己沉潜往复的心力做文章,而是纷纷青睐那种能够迅速给自己带来声名、增加自己的文坛曝光率的文学时评样式,甚至对自己原本应该安身立命的学理性批评持疏离、不满乃至大加讨伐的姿态,这种反戈一击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呢?”除了这个原因,学理性批评近年受到的冲击,与媒介的变化、新媒体自媒体的产生以及相应的“媒介批评”的应运而生有关。“媒介批评”摒弃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建设性,强调批评的即时性、浅俗性。因此,“媒介批评”的出现,表面看来,似乎是在努力平衡专业批评和大众阅读之间的鸿沟,其实是在剔除批评的理性支撑和专业要求,让批评只对感受负责,不对科学性负责。媒介批评大行其道,学理性批评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作家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虽然很多作家口头上不重视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多数作家的习惯性做法是,只要有人写了我和我的作品,只要是夸了我,就是好的评论,哪怕满纸荒唐言,也没有关系,这无形中助长了关注文学现场的作家作品评论的非良性发展。好的批评生态,应该是作家不漠视文学批评,耐下心来,看看评论是否经得起推敲。而评论者也要对作品文本有着足够的重视和细读,在“理论的接地、及地、在地与批评学理性的呈现”“文本分析、文本细读与批评学理性的呈现”当中,彰显批评的学理性与建设性意义。若果能如此,或许会反作用于作家的创作、影响到时下的文学现场。
好的学理性批评,除了对学养有要求之外,往往还是费时费力之作。何平的《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也以学理性批评为显著特色,后知作者为了写这样一个新作的评论,用了很长的时间再次通读贾平凹的几乎所有作品。《极花》原发《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何平的评论发表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文学评论》反映新作的学理性批评文章,刊发可谓神速,但文章又显然不是时评、快评类文章。缘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作者提前阅读作家手稿,整个评论的阅读、思考和写作准备期,用了几个月——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积,才使学者、评论家在看似快评的时间段里,写成了一篇既有评论的新锐之气、走在新作评论前沿、又兼具学理性的评论文章。郭洪雷《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贾平凹新世纪小说话语构型的语义学分析》(《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作者用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心无旁骛,高度投入,通读了贾平凹所有作品,才得以选题和开始写作。后来听说是在学校借了一间别人不用的办公室“闭关”,三个月三条烟,除了回家睡觉,杜绝一切事务,才诞生一篇这样有分量的学理性批评文章。
对学理性评论,需要剔除的一个误解是:学理性批评一定是佶屈聱牙、不好读的。好的学理性批评,除了引人深思之外,也可以是美文,比如张学昕的《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这篇文章,既有学理性的概括和归纳,就像他在内容提要当中所言:“苏童的小说叙事,试图为我们重构一个独具个性文化精神、美学意蕴的文学‘南方’……在这些文本结构里,蕴藉着一种氛围,一种氤氲气息,一种精神和诉求,一种对人性的想象镜像。‘南方’,成为苏童书写‘中国影像’的出发地和回返地。”而整篇文章的展开,是学理性框架和逻辑整合能力统摄之下的美文般的行文:“南方生活的无限生机和活力,滞涩和酸楚,来自于他对未来的激情遐思,也来自对历史的沉淀和缅怀,但都为着撞击出现实的灵魂真相。”凡此种种,在张学昕的这篇评论中弥漫开来,不仅是对苏童小说叙事无比体贴入微的观照和阐析,而且这些句子段落里,哪里能看到那种可憎的“学报体”“C刊体”“项目体”的面目呢?
很多“学报体”“C刊体”“项目体”文学批评文章,并不是好的学理性批评文章。虽然其中不乏面目可憎、水平平庸之作,但毕竟已经盛行日久,在很多刊物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刊文范式。郜元宝《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文章投过来时,作者先是忐忑不安的,乍一看,这篇文章确实似乎不是通常的“学理性”批评的样子,但细细读来,我发现这篇文章虽然形式是散文化的,但骨子里其实是学术范儿的。文章尤胜在材料扎实,角度也较新,不是西式论文的做法,也不是现在流行的中西合璧式写法,而是更加偏重于传统治学的做派……这样的批评文章,其实依然是学理性的,与读后感式批评、印象式批评,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事情不可绝对化,很多非学理性的评论、媒介评论,也有非常好的诠释作品的评论文章。我在写作严歌苓《上海舞男》的评论时,曾读到过范迁的评论《严歌苓〈舞男〉:五度空间的上海霓裳曲》,本身即为作家的范迁,用了最作家的感觉和审美,也最作家地评论了严歌苓的《舞男》,而且他说得几乎比任何人都好,比任何人感觉都准:“昨日半夜里两点钟,看完严歌苓的新作小说《舞男》,如醍醐灌顶,恍然明白我们所谓的‘空间’,其实是道没扎紧的竹篱笆,里厢的人可以看外面,外面人也可以看里厢。庄子化身为蝴蝶,飞进飞出。故人世人眼光自由穿梭,隔墙相看两不厌。佛经上倒也讲过;此身非身,此界非界,此境非境。”可以说,他是懂严歌苓的最眼毒的作家朋友,他用最文学化的语言,说出了《上海舞男》小说叙事是有着超越四度空间、直达可以里外相看和飞进飞出的五度空间的本领的。“而严歌苓的近作《舞男》,小说的叙事结构已远非是‘歪拧’可以涵括,小说‘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绾合,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内套的故事,已经不是与外层的叙事结构构成‘歪拧’一说,而是翻转腾挪被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自始至终与张蓓蓓和杨东的故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嵌套,不止是互相牵线撮合——绾,还要水乳交融,在关节处还要盘绕成结——绾合,还要打个结儿为对方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这段我自己写的看似长篇大论的评论文字,说到底,也不过是在学理层面,表达了范迁那短短几句话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2005年我博士毕业,工作在文学所,在《文学评论》当代组工作迄今,已近一十三载。曾经不事写文、寂寂多年,也只是近三四年才开始勉力写作,实在还只是一个初习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很多师友鼓励说“厚积薄发”,其实是很惭愧的。回首看自己的过去,除了编辑工作本身就易养成人的“眼高手低”的毛病,由于工作伊始,接触的便全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最好水平的文章,当然也往往是最学理性的文章,高山仰止,自己情知一时难以写出趁手的文章供大家指正,所以便在编辑文章的过程中沉下心来,潜心学习着……《文学评论》培养了我的批评观、批评的路数,也让我形成了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的一点点心得;而在本职工作中,就可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习到所有不同选题类型的学理性批评的长处和优点,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厚待。今后,希望可以把学者和评论者的路子,走得稳当和扎实一点。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这最符合我一直以来的心理定位;作为一个评论者,我希望自己的评论能在一种文学史视阈、问题意识兼具的情况下,发现研究对象所隐含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性价值,以及它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和意义。好的文学研究者,应该能够通过自己的眼光和文学趣味,遴选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自己的评论,发现作品独具的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所欣赏的学理性批评,似乎注定就是一种较为孤独和偏冷的研究与评论范式。在当今热闹喧嚣的文学现场里,学理性批评的遭遇似乎是“冷”的,但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文学史谱系的构成与书写,学理性批评具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批评难以企及的优势。从学理性批评,我们所能获得的,似或是抵达文学经典的通道。
注释:
[1][2][3][5]李遇春:《为学理性批评辩护》,《创作与评论》2018年第1期。
[4]参见拙文:《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结合〈文学评论〉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用标准和风格来谈》,《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6]参见拙文:《与时代同行的学理性批评——以〈文学评论〉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五年来的发展》,《文学报》2017年11月16日。
[7]参见拙文:《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