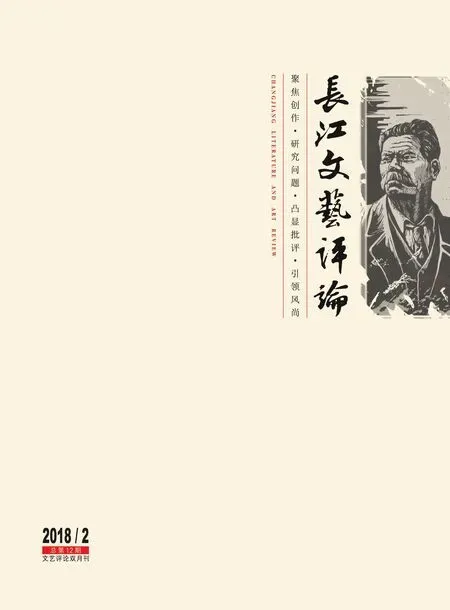文学评论何为?
——读刘艳文章有感
◎郜元宝
2008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的《王蒙自传》研讨会上遇见刘艳,她已在《文学评论》两三年,经我的老朋友、也是她的编辑前辈董之林女士介绍,算是彼此认识了。我那阵子作文勤快,但《文学评论》门槛高,规矩大,不敢轻易投稿,渐渐还是在这份崇高刊物上发了不少文章,其中就有刘艳继董之林之后认真尽职地约稿催稿的一份辛劳。
很快发现刘艳也写评论,也做文学研究,只不过做编辑太尽心了,平时绝口不提自己的文章,但刘艳评论的某些特点还是跟她的编辑工作有关。她在《文学评论》编当代文学批评的稿子,跟一般写评论的人有所不同,不是进入专题研究之后才临时抱佛脚,做起“文献综述”的案头工作,收集跟某个专题有关的先行研究;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大量审看同行文章,所以她可以超越具体的专题研究,熟悉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一般态势。《文学报》2017年11月16日那篇《与时代同行的学理性批评——从〈文学评论〉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五年来的发展》就是一个著例。在2016年中山大学“重识文学批评及作家论”研讨会上听她发言,似乎就涉及这篇文章的内容。当时觉得她“熟悉情况”,不像我们一般搞批评的人不看或很少看同行文章。这次阅读本文,上述印象又加深了一层。她的几篇论萧红、严歌苓、迟子建的文章,自始至终都是通过和学术界各种先行研究进行潜在或公开对话的形式展开,很少鲁莽地截断众流,一切从我开始——如果那样,就成为盲目的自说自话了。
文学评论的门槛确实不断增高。198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学写作评论时,老实说是比较容易“入行”的。那时写评论,没有“学院派”的洗礼,大家自行其是,固然也有其优胜的一面,就是比较自由,洒脱,将一时的印象和思考说出来就够了,文体也比较透明畅达,多少还讲究一点修辞和才气。现在光有这些不够了,一则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观念方法日益多元化,不同的声音都出来了,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要学会倾听。其次,随着“当代文学”上限和下限不断伸展,评论对象的体量和80年代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任何一个当前的文学现象,都可能牵涉到“当代文学”更深的背景,因此一味轻巧灵动的评说就显得不够,而必须借助势大力沉的开掘。如此,我更佩服刘艳这一代批评家的路数,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往往要超过从同代或上代同行那里获得的,因为他们更有建构学术共同体的自觉,更有将当下批评和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训练与学术雄心。
这几年来,研究萧红的文章乃至专著真可谓汗牛充栋了。我很赞同王彬彬教授的意见(尽管不一定完全同意他对萧红的评价),他认为有过度拔高萧红文学史地位和艺术成就的现象,应该从90年代“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热潮退回去,重温一下在此之前鲁迅、胡风、茅盾、王瑶、唐弢等评价和分析萧红时那种平实冷静的态度和方法。要在更深的历史背景与前人对话,在对话中拓展自己的思考。刘艳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萧红的文章,就是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刘禾、孟悦、戴锦华等女性主义批评模式和王彬彬教授的质疑的前提下,将切入口收得更小,亦即聚焦于萧红小说多变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姿态,实际考察萧红的小说艺术究竟给包括其导师鲁迅在内的现代小说传统提供了怎样的新因素。从叙事角度出发的考察当然也只是局部的,还不足以从总体上在王彬彬教授和上述那女性主义批评之侧自树旗纛,但叙述方式的研究毕竟弥补了以往萧红研究的某些不足之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多侧面地理解这位“宏才远志,厄于短年”的不幸的女作家。
刘艳关于五四时期小说太多作家主体的“独白叙事”,思想意识侵入客观叙事太甚,以至伤害了小说叙述的艺术,特别是导致小说叙事视角转换的稀少,缺乏虚构性和叙事的多层次多角度的丰富性——这个基本判断,又使我想起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和普实克之间围绕鲁迅小说的那场争论。夏志清也说鲁迅小说思想太外露,观念性太强,就小说艺术而言还不够理想,但普实克针锋相对,说鲁迅小说好就好在其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性。抽去思想观念,还有鲁迅小说吗?鲁迅岂是仅仅为了满足某种小说形式和技巧的理想而写小说?这场争论很难说谁对谁错,但由此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造成一种思维张力,倒是值得我们用心来对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刘艳一直是在文学史研究和当下作家作品评论两个领域同时用功,并希望将这两个领域的工作打通。这个路子很好,也是他们这代批评家一开始就自觉追求的。
说到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代际”划分,可以推荐刘艳另一篇文章《文学代际研究的尴尬处境——以“70后”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为例》。刘艳没有简单论断“代际”划分的对错,而是实际考察为何及怎样有“代际”的说法。她把这个似乎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或过于随便的问题谨慎而耐心地予以历史化,让我们触摸到这个说法得以产生的现场。她的结论——倘若我没误解的话——是认为关键在于“80后”说法的提出,是先有了“80后”,才顺推出“90后”“00后”,同时倒逼出“70后”“50后”。其中“60后”有一些特殊性,他们并有特别地强调以代际划分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中间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往往比较反感这种说法。代际,有简单的年龄意识,背后又涉及客观社会文化的变迁,既不能盲目主张,也不可盲目抹杀。
说到这里,我也感到必须意识到自己和刘艳以及比刘艳更年轻的批评界同行的代际差异实际包含的内容了。不管哪个年龄段的学者批评家和作家,除了必须对自己同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身份有一份必要的自觉,还应该把眼光和心胸更加扩大一些,像T.S.艾略特要求的那样,将整个文学史摊在自己眼前。
但是我也由此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我们可以允许他有怎样的阅读盲区?这也许不算是学术问题,却是每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个人体能、精力、兴趣、学术积累和至少体量上世界第一的文学大国之间,实在有一道谁也无法跨越的鸿沟。要求大家必须对每一个作家都能展开研究,在一个文学小国也许可以,但在我们这里,恐怕未必能够做到。
在我们这里,不知何时养成了一个习惯,形成了一种机制,造成了一种共识,比如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批评家不奔走相告,不撰文吹嘘,就是冷漠、“钝感”、失职。一部据说是突破性的大作横空出世,批评家不赶紧巴结上去,进行分析、阐释、总结、评判、预言、回顾,就是不怀好意。一个所谓的“文学热点”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批评家们如果不一拥而上,不积极参与传播、诠解、答疑、解惑,那也肯定是“批评的缺席”,是患了“失语症”,是赶不上趟儿。刘艳以逾20年的时长追踪关注和持续研究严歌苓,显然不是追逐“文学热点”之作。
批评家或许有“捧杀”的自由,有“棒杀”的威风,有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豪迈,有做小伏低围着作家打转的殷勤,有胡言乱语信口开河的爽快,但就是没有保持沉默或偶尔撂挑子、打杂、干点别的事儿的权利。这样说来,批评家们好像无形中背负了某种判决,被罚做“批评”这种苦役,否则灵魂就不得救赎,罪过就无法洗刷。但中国之大,新星、杰作、“热点”实在太多,除非风云变幻,万喙同息,否则在中国,批评家不愁没事干。与此同时,批评的回报也不可小觑。已经有不少感觉名气成就还不够大的中青年作家抱怨说,作家成名走红太难,弄批评却太容易:二三十岁年轻人发一篇文章就是“批评家”了。尤其“青年批评家”起来之后,特别是自从有关部门号召要抢夺文学批评阵地与制高点以来,确实存在着年轻的批评家被批量生产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做批评也太累。许多时候拼的可不是机灵劲儿,不是智慧、才情、学问,甚至也不是良好的职业操守,而是身体耐力。
但是,如果什么时候忽然从云端里跳下一个大神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有批评?不是已经有许多网络高手一开口就吓得专家和“砖家”直哆嗦吗?如果他们愿意花点时间过问一下文学,在网上造成一种气氛,则中国的文学阅读环境将会十分乐观,正无须乎批评家们来独担大任。再说那些出名或尚未出名的作家难道没有起码的自我批评自我提醒的能力,非要在作品研讨会上坐在批评家对面,听批评家摇唇鼓舌一番之后才茅塞顿开?不是有许多伟大的作家根本不需要批评家的“帮助”吗?既然如此,批评何为?难道仅仅是为了批评家们自己相互切磋,抱团取暖,或用“批评成果”评职称,拿项目,得奖励?
好像这样的问题并不具有普遍性,提问的人不多,愿意回答或可以就教的朋友也少。久而久之,我似乎就有了一个心结。在谈论刘艳的短文最后,我想再将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们评论别人是“奇文共欣赏”,面对自己思考“批评何为”,就算是“疑义相与析”吧。愿大家带着这些问题,在今后的批评工作中,彼此共勉。
——论代际批评的“有效”“有限”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