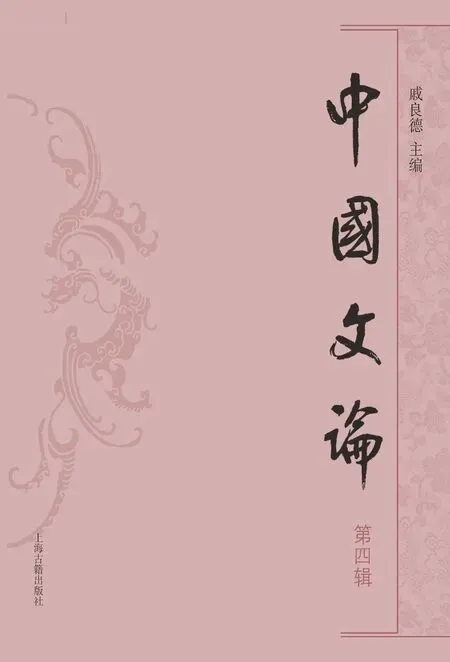刘勰在《文心雕龙》范畴创用上的卓越建树*
涂光社
《文心雕龙》是齐梁时期问世的文论经典,一千五百多年来,再也未出现能与之比肩的文论著作,在近现代更受到中外学界的广泛推崇,可谓历久弥新。
体大思精的理论,必有统合有序、思考严密精深的范畴系列。刘勰是文学领域创用范畴概念最多的理论家,他以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概念组合所作的逻辑论证覆盖文论的各个层面,并达至“思精”之境,经受住了千百年来中外文学创造和理论批评的验证,葆有逾越时空局限的理论价值。这正是《文心》被一些近现代学者称许和赞叹的缘由。
刘勰在古代文论范畴创用上的贡献无与伦比。本文就此一呈管见。
《文心雕龙》总结了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以来的理论进步,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的“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以及“下篇”的“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的《声律》《章句》《丽辞》《比兴》《练字》等篇所论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通变》《附会》《比兴》《物色》《知音》《序志》等篇在文学创作思维论、风格论、内容与形式关系论,以及继承变革、作品结构统序、鉴赏批评原则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的建构几乎达于至境。
除了那些以基础性理论名篇的专题之外,散见全书的其他范畴概念也在不同理论层面各得其所。刘勰移植和创用的范畴系列几乎覆盖了古代文论的各个层面,其中不少发挥着为后来理论批评发展导向的作用。当然,那些在未作为专题论证的范畴理论意义上一般有更大的开拓、深化的空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运用的所有范畴概念都不难在《文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或者渊源。
刘勰以后,系统的文学基础理论著述已难望《文心》之项背。自隋唐起,文学理论的拓展、更新和提升大都是在标举某一核心范畴的不同流派、不同文体和艺术主张的思想和美学追求中实现。
以“象形为先”、表意为第一属性的汉字为语言记录符号,对语词、概念的构成、运用,思维及其表达均有深刻影响。古代范畴概念文化特征鲜明,组合灵便、表述简约、义涵深厚,常两相交义,多有所通同、常指代为用,在不同语境有不同意涵,等等。刘勰的范畴创用充分显示了以汉字表述理论思考的诸多优长。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序志》对全书理论建构的概述和以范畴名篇的基础理论问题论证中,以及散见各篇范畴概念的梳理三方面,对刘勰范畴概念创用上的卓越建树略作述评。
一、 《序志》概述全书理论建构所用的范畴概念
体系缜密的理论仰赖统序严谨的范畴系列的论证支撑、建构。刘勰在《序志》篇介绍《文心雕龙》理论构成时有所显露:
其上篇“文之枢纽”的篇次安排和论说就有“经”与“纬”、“正”与“奇”的对应;《原道》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圣”“道”“文”是指代文学创作三要素——主体(著述者)、客体(抒写和表现的对象)、媒介(言辞和著述)之楷范的组合;“论文叙笔”表述的文体论原则中,“原始以表末”展示各文体的源流,“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说明称名之所然,评定各体代表作的成就;“敷理以举统”揭示其生成流变的内在依据(“理”)及其规范与统序。其中有“本”与“末”、“名”与“实”、“正”与“变”的思考,还用到“自然”“性灵”等范畴概念。
下篇“剖情析采,笼圈条贯”中运用的范畴系列更值得关注:
“剖析”常是古人思考及其论著的短板,《序志》中却被刘勰标举为自己探究文学现象的基本思路和手段,由解剖分析现象生成演化的因素、机制入手,揭示其本质和运作规律。“情采”是刘勰创用且受其青睐的组合。“情”是文学内容的核心,也是创作的动力;“采”即辞采,不仅表明文章有形式美,也凸显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之处——以言辞为媒介和载体。刘勰的《情采》篇就是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专论。此处也申明剖析“情采”为其理论探讨的切入点。
“笼圈”是指破除文体的壁垒对文学现象及其理论问题所作横向归类;“条贯”是纵向的,指发展演变的脉络。“笼圈条贯”与“经纬”的概念有某些近似处;但没有“经正纬从”那样对本末和主次的强调。
刘勰随即罗列“下篇”各个文学艺术基础理论专题:“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这些以概念命名的“剖情析采”篇章中,范畴概念组合而成的精论妙语俯拾皆是。本文后面再摘要作专门的介绍。
之后,《序志》还交代了全书立论的原则立场:
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同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遵循“势理”——事理逻辑延展的自然趋势,有不违其本然的严谨;“不屑古今”对于倡言“宗经”“征圣”的刘勰十分难得,所持的是与时俱进,唯真理是从的理念。“擘肌分理”可谓“剖析”的同义语;“唯务折衷”更是对各家学说主张、不同思想观念的包容和兼取并用;“折衷”并非无原则的调和,而是酌取各家正确、恰切的理论思考和优长以为己用。
二、 以极富创意的范畴为篇名的基础性问题专论
以范畴作为篇题,其创设依据、理论意义和应用范围,大都得到集中和充分的展示,往往最富创意,也最能显现“思精”的特点。
“剖情析采”用作篇题的范畴所论,多为文学艺术基本的理论问题。本节择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作扼要解读,一窥刘勰范畴创用的成功与基础理论上的卓越建树。
(一) 论文学思维创造的《神思》篇
“神”与“思”组合至少有这样两层意义: 其一,文学创作是精神活动、思维的创造;其二,文学活动的思维神奇微妙。
“古人云: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开篇,化用《庄子》语汇,强调神奇的文学思维能够大大超越身观局限。“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表明文学思维能够由静(“寂然”、“悄然”)而动(“思接”、“视通”)自由翱翔,“思接千载”是时间上的超越,“视通万里”则是空间上的超越。
刘勰指出“思理为妙”能实现“神与物游”的主客体交往、融合。“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为思维领域的创作三要素论。“神思”是主体的一方,“物”是描写对象,“辞令”是语言媒介,传达的“枢机”。“神思”受“志气”(精神意志等心理因素)制约,意气委顿,精神、心理状态不佳,写作兴致和灵感就会消失。“枢机”运转通达,驾驭语言得心应手,表达无障碍,对“物”的描写就能惟妙惟肖。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表明,达于“虚静”则实现创作的精神准备和心理调适,是闲静无扰、空灵自由、从容明敏的境界;“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词”是写作必需的知识积累和阅历经验理性把握、语言才能训练;“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按照对事物有深刻理解和独到见地的匠心营构的“意象”加工,遵循文学语言美的规律付诸表现。
文学是以语言为传达媒介的艺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是古代文学领域的言意之辨,刘勰对“言不尽意”之所然作出了最为切实简要的诠释:“意翻空”说的是创作思维中“意”的运作有易变幻的跳跃性,常有“言所不追”难以表达的奇特意蕴。相比之下,“言”有可验证之“实”(即有确切的语义、语音规范);“言”常常跟不上“意”的跳跃、达至同样的奇妙境域,出现如同陆机所说的“文不逮意”的现象。
言及“神思”的创造力,该篇说:“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实现拙与巧的转换,平庸中生出新意,为后世“点铁成金”、“以拙为巧”、“出奇崛于平淡”等说之先河。“杼轴”比喻“神思”之运作,如同由织工巧手驾驭的织机一样,能够把看似平常的材料组织加工成精美的织物,创造出价值大幅度跃升的精神产品。
有些篇章从不同角度对“神思”之论又进行阐发: 《养气》篇的“从容率情,优柔适会”、“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和“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等语是对“虚静”说的补充。《物色》篇有论景物描绘的三要素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和“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总术》说:“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云贵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要求作好心理精神等方面的准备,把握灵感来临的时机及其运作规律,充分发挥其非凡的审美创造功能。其中所用“数”“机”“会”的概念义分别指向思维活动的规律、灵感到来的时机、有利于思维创造的主客观因素的会合。
(二) 论风格的《体性》篇
当代学者公认《体性》是《文心雕龙》的风格专论,很有启发性。
“体性”的概念是名词性的联合结构,其“性”大抵为作家的文学个性;“体”则指作品的创作体制或一类作品的体式、规范,也有相应的文学个性(艺术特色)。《体性》篇首先强调:“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现,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点明了“性”和“体”相互间内与外、隐与显的对应关系与表里的一致性;“性”在先而“体”成于后,“性”是主导的一方等意蕴。
“性”与作家禀赋相关;“体”也非天造地设,是从审美创造的经验归纳出来的体式。刘勰指出,文学风格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才”(艺术才能)、“气”(气质个性)、“学”(学识修养)、“习”(对体式规范的接受、写作习惯的养成)。“性”包括主要受先天因素影响的“才”与“气”两方面;“体”则与后天的“学”与“习”相关联。“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几乎是西方理论家所谓“风格即人”的同义语,却更精致:“各师成心”一语出自《庄子》,原是各守成见、偏执一端自以为是的意思;在刘勰这里无贬义,“成心”指业已定型的艺术个性,遵从内在的“成心”创作,外在的“面孔”(风格)必然人各不同。
《体性》列举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类文章风格,认为作家学识和摹习对象不同,形成的文风就不同。“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可谓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艺术风格类型往往两两对应: 有典重雅正的就有奇特新异的,有深奥含蓄的就有浅显直露的,有繁博富丽的就有精省简约的,有壮丽雄劲的就有轻柔细腻的……值得注意的是,一种风格被肯定,与其相反的另一种风格未必就不好。诚然,刘勰对“新奇”“轻靡”颇有微词,针砭时弊的用意明显。
“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从后天“学”“习”辅助的必要说到天赋“才”“气”的主导作用。又举两汉魏晋作家为例,指出文章之“体”(风格)无不是作家“性”(文学个性)的彰显。
针对如何培养好的风格,刘勰说:“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斲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强调要从初学写作着手,若习染成性、风格定型(就像木器做成、丝已染色)后再求改变就困难了。于是有“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的原则。“摹体定习”指通过规范的学习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因性练才”强调须根据天赋个性去发展才能,形成独具的优势和特有的风格,“性”固然是“练才”的基础和依据,后天的“练”对“性”的发展、成就也很必要。篇末“赞”再次申言:“习亦凝真,功沿渐靡。”“真”指基本素质(“性”)而言,刘勰认为后天的“学”“习”能对“才”“气”进行陶染和改造。“功沿渐靡”表明这是个长期浸染和渐进的过程。
一般说来,有成功经验积累才有“体”的创设,才能形成可供摹习和沿袭的规范;而“性”本无常规。不过,“体”实际上也是从多样的“性”中得来:“性”的多样使“体”的划分归类成为必要也有了可能,是有规范性的“体”出现的基础;“体”是对若干“性”的归纳和总结,一“体”是一类“性”审美经验的结晶。文学发展中常因“性”的丰富变化而导致“体”的产生和分化、变更,故《神思》篇说:“情数诡杂,体变迁贸。”反过来,“体”一经确立,又对“性”发挥一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刘勰之所以强调“学”、“习”的必要,就是要求作家吸收和借助前人经验,防止任“性”而生的新变脱离正确轨范。
由此可知“体”与“性”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相互制约、相互转换又相互促进。在继承变革上它们各有侧重。
本篇的启示还在于: 风格虽可从“体”和“性”两个方面去定义,但其本质和核心都是艺术创作的个性。作为个人的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创作个性(“性”)的表现;作为流派、时代或者体裁、艺术门类……的风格,是某一集群(“体”)艺术特征的表现。如果取消了艺术家或者艺术门类、题材内容、表现方式、媒介、地域、时代、民族、流派等方面的个性,也就无所谓风格了。
《风骨》篇和《定势》篇也从不同角度对风格论有所阐发、补充。
传统理论中常常运用形象性的概念,民族文化特征鲜明。“风骨”初见于人物品鉴中,是典型的形象性概念,稍早于刘勰的谢赫曾用它评论绘画。“风骨”有一种高于凡俗的精神气质,是构成良好风格的重要因素。刘勰是以“风骨”论文的第一人,也是古代唯一剖析其范畴义,作逻辑论证的理论家。
《风骨》开篇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标举《诗》学传统,申述其对作品感化人心力量的倚重。
“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表明“风”指深挚充沛的感情内容产生的艺术感染力;“骨”指有坚实依据和严密逻辑,用洗练语言表达的“理”以及由此而来的说服力。文章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文心》所论除抒写情怀的诗文而外也包括说理的著述,有必要用“骨”强调“理”这一侧面。如《原道》篇所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之动者,乃道之文也。”“风骨”正是指诗文作用于社会人生的感染力和鼓动力。
“风骨”用于品鉴人物时,是由形貌显现的一种精神内质。风采、风姿、风韵的美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骨是体内在的架构、骨力坚挺,骨相能显示人物的精神气质;移用文论以后依然葆有这方面的意蕴。刘勰不满南朝文风的柔靡,有“风骨”是对所有文章的期盼。“风骨”虽是良好风格构成的因素,多数情况下未自成一格。篇中虽有“意气峻爽”、“骨劲气猛”、“文明以健”、“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诸多形容,也不宜把将一切有别于阳刚风格(如清新秀丽、自然冲淡、深沉静穆、轻灵温婉)排斥在拥有“风骨”者之外。
《定势》篇关于“体势”的论说,是对“体性”风格论的重要补充。开篇说:“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既称“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有普遍意义,是对文“势”形成过程所作的规律性概括。刘勰强调事物的运作有“自然之趣”,“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 自然之势也。”“自然之势”此处就是文辞合乎客观规律的展示态势。
《体性》中“性”指作家的艺术个性,“体”侧重指作家作品的体式;“才”“气”“学”“习”和“各师成心”之论说的是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而《定势》“体势”论的“体”指文章体裁,有审美经验归纳、分类方面的合规律的客观性:
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概括的是六大类二十二种文体语言风格的基本特点,以及“循体成势”的规则。
因此,王元化先生指出:“我们把‘体性’称为风格的主观因素,‘体势’就可称为风格的客观因素。”
(三) 论证继承变革原则的《通变》篇
“通变”的概念首见于《易·系辞》,要求人们了解和把握事物运动变化规律,驾驭其发展变化。如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是通晓,也是通达。通晓是透彻的把握,可对“变”进行的理性控驭。由“通”指导“变”,则有无往不利的通达,能获得发展更新上恒久的生命力。在文论中其本义依然被保有和沿袭。
《通变》首先指出文学承传变革中“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数”的辩证关系: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 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有常”指“体”之“名理”(名称、规范)在历史演进中继承、沿袭的稳定性,它们是以往审美经验的结晶,故云:“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表明,作家的通变原本“无方”,“数”(术数;即方法和原则规律。)须在斟酌“新声”中了解,通变方向途径的把握得自对时代潮流和文学未来发展趋势的探究和认识。能够处理好“有常”与“无方”的辩证关系,则“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拥有无限发展前景和旺盛生机的“文辞气力”。
刘勰追溯文学演进的历程,认为有“从质及讹”的趋势。反对汉赋“夸张声貌”的走向极端以及普遍的因循模仿。提出“参伍因革”有因有革的通变原则。并以“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大声疾呼,鼓吹作家通晓规律、适应新变的时代要求,拥有在创作中凸显一己情感和气质个性的自觉意识。
《通变》之“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表明,文学发展是回旋式上升、日新月异的。“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是谓文学的前途只属于创新和变革,通晓规律才能有层出不穷的升华。“趋时必果,乘机无怯”鼓励作家果敢地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各自的机遇进行创造。“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指参照古往今来经验教训确定文章写作的法则,了解所处时代和自己的特点写出有所突破、超越前人的作品。
《文心》重视创新求变,是其与时俱进的文学发展观的体现,但“变”须合规律,有原则,有继承,有创新。“通”中必有继承,绝非无原则的因袭,“通”是对渊源、发展脉络以及演化趋势、机制透彻的了解。
“通”诚然不等于继承,但包含继承的因素,且比继承的层次更高。“设文之体有常”的“有常”就是对成功经验、模式的承传。“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明确指出“有常”之“体”是从“故实”中得来。篇末“赞”的“参古定法”是对“通”在继承这一层面义涵的概括。
《文心》其他篇中也能见到“通变”“变通”的概念,但理论意义上皆未能对《通变》有所突破: 《议对》以为“动先拟议”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之“通变”是指政治,而非写作。《征圣》云:“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徵之周、孔,则文有师也。”《铨赋》:“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颂赞》说:“《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时序》称:“质文代变。”《神思》则曰:“情数诡杂,体变迁贸。……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面后通其数”;以及“神用象通,情变所孕”。《镕裁》亦称:“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物色》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论章法构辞处也有“变”的讲究,《章句》说:“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丽辞》云:“《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
“奇”“正”之论也往往与“通变”有关联,如《辨骚》总结的效法屈《骚》的正道:“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定势》称:“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而俱通。”“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风骨》云:“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知音》论鉴赏,其“六观”是鉴赏的六个方面,其中有“三观通变,四观奇正”。
(四) 论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情采》篇
《情采》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也是学术界的一种共识。然而,以“情”代指内容,以“采”代指形式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情”作为文学抒写的对象、内容的核心,包含着首肯自然情感、灵慧之天性的意蕴,是文学自觉时代精神的体现。“采”作为辞采有美文的意涵,既突出了文学以语言为媒介的特点,又反映了古人以美文为文学的观念。
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除了“文”与“质”、“华”与“实”以外,能够指代内容和形式的概念还有很多。内容方面有侧重主体因素的心、神、性、情、志、意等,侧重客体因素的有道、理、义、事、物等;形式方面的有文章、辞令、言、声、藻采、体势等。《情采》篇就交替使用了不少指代一致的概念: 质、情、性、理、志、心等均指文学内容;而文、采、言、辞、音、藻之类则指作品的形式。当然,既以“情采”为题,说明在构成文学内容的诸多因素中“情”处于首要和核心的地位,而“采”则表明文学形式应当是有美的。
“情采”作为一对范畴出现,是文学自觉时代理论进步的产物。魏晋时期人们对个性的价值和自然情感的合理性给予了更充分的肯定,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的看法,陆机作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论断,都是这种进步的反映。“情”比“志”的意义宽泛:“志”可谓一种特殊的与实现某种理想目标相联系的“情”。而男女相悦和师生、朋友间的情谊,父慈母爱夫妻兄弟的情都爱属于“情”,却未必与“志”相关。比起先秦两汉正统诗学只强调“言志”和文学的政教功能来,可以说是一次解放,对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创造美的功能意义也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情”一般指作家的情怀,即作家的情感及与情感相联系的思想精神、气质个性、心志意趣。“情”指代内容,突出了文学艺术以人的感情活动为核心、为动力、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特征。文章内容的构成尽管包括“情”(主体因素)和“理”(客体因素)两方面,但“情”无疑是主导和统领一切的。与自然科学理论和抽象的哲学论著不同,文学作品虽然也以理服人,但主要靠的是以情动人。
“采”即辞采,指文学语言,强调它是美的文辞;于是凸显出古人文学观念的两个基本点: 文学的媒介是语言文字;文学是艺术,有美的形式。换言之,具有美的语言形式是文学的根本特点。如《情采》开篇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比现代流行的文学定义或许更简要,合乎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
《情采》篇以生动的比况、精辟的论证准确地阐明了内容形式的关系:“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 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 质待文也。”表明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但有主有从。“文附质”、“质待文”可谓是经典性的精炼概括: 形式依从于内容,内容有待于形式表现。水的质性虚柔所以能结成层层沦漪,树木枝干质性坚实因而花冠挺拔。两个生动的譬喻不仅道明外在的形式取决和依附于本质和内容,而且告诉人们内容与形式是不容剥离的。后两个比喻说明内容有待形式去表现,但也有两层意蕴: 虎豹皮毛的文采是它们迥别于犬羊的优越资质的自然外现,而犀兕的皮革则须由人工的修饰才能充分表现其美质。前者赞赏美质外现的自然天成,后者肯定了某些时候人为美的功用及其使用的必要性。刘勰指出: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此立文之本源也。
是谓文学美有不同层次,藻采之美(外在的文辞修饰之美)是低层次的,应当从属于内质;本色的、有坚实内在依据的、生气勃勃和灵动的美是起主导作用的高层次的美。犹如铅粉黛色可以打扮女人的容貌,而那动人心魄的美来自其天生丽质。刘勰以经纬交织况喻内容形式的先后、主次之分,又表明两者相辅相成不宜有所偏废。以矫正柔靡繁缛的南朝文风为己任,倡导《诗经》“为情造文”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批判汉代辞赋家搜奇炫博繁文丽藻“为文造情”的本末倒置。
其后又在指出文章“述志为本”、“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的同时,重申“言以文远”的古训,指出言好的艺术形式对作品传播有极大帮助。
概言之,内容是形式生成和构结的依据,又仰赖形式去表现和传播。情采并茂两相副称——“文质彬彬”才合乎理想,得以传之久远。
本篇警示“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时风,有“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心术既形,英华乃赡”等语。其他篇也不乏类同议论,如《风骨》说“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章表》主张“辞为心使”反对“情为文屈”;《附会》认为“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杂文》说“情见而采蔚”,《诸子》称“气伟而采奇”;《比兴》说:“拟容取心”……都与《情采》所论相通,有兼及作家作品的内外表里、强调因内符外的共同点。
《镕裁》论内容的镕范、形式的剪裁:“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櫽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也。”声称:“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镕裁,何以行之乎?”
《附会》论作品结构统序,有内容形式内外、主从的系统整合:“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以及“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三、 散见各篇范畴概念的梳理
散见《文心》各篇的范畴概念,两相对应的如“文”与“质”,“奇”与“正”,“刚”与“柔”,“华”与“实”,“因”与“革”,“雅”与“俗”(“郑”)……独立成词的概念有“自然”、“性灵”、“虚静”(“闲”)、“滋味”、“和”(“中和”)、“意”(“意象”)、“心”、“志”、“气”、“韵”、“趣”、“悟”、“境”、“圆”(“圆通”)、“法”、“素”、“朴”、“拙”……在文论不同层面各得其所,以其应有之义介入理论表述。下面是对它们简要的梳理。
1. “自然”
《原道》说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心生而言立”合乎“自然之道”,以为一切有美质的事物皆有美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明诗》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体性》指出作家创作个性的外显就是风格,“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定势》以“机发矢直,涧曲湍回”和“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譬喻,事物的运动和展示都遵循“自然之趣”、“自然之势”;《丽辞》认为文辞对仗的依据是“自然成对”;《隐秀》称隐秀之美的出于“自然会妙”。凡此种种,都贯穿着自然论的宗旨: 高境界的美自然天成;卓越的风格、美的表现形式,出神入化的艺术创造,都合乎艺术的客观规律。标举“自然之道”是对事物客观属性和规律的尊重,以及对真美和作家天成之灵慧和原创力的推崇,显然得益于老庄美学思想的滋养。
2. “中和”“中正”
《乐府》开篇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引《尚书》语,表明“和”原是音律之美。随后感慨汉初乐府“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西汉官方乐府渐离轨范,“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说三曹乐府诗“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又强调“淫辞在曲,正响焉生?”
《声律》称美籥、瑟的器乐演奏有“宫商大和”。指出文学语言音响之“和”也非“同”,与“韵”相比,是一种更难造就的语言音响之美:“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从文学语言应该用标准音的角度,批评陆机作品仍“多楚”声,“可谓衔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
《奏启》:“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多失折衷”的“折衷”即得当,无过无不及。《章句》云:“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指出文章换韵无论快慢,都要避免过犹不及。其“折之中和”与“折衷”同义。
《封禅》称:“《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书记》说“律者,中也。……以律为名取中正也。”
“中”与“正”是经常联系的。《明诗》有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中。”《论说》说:“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其后有“言不持正,论如其已。”“中正”指不偏不倚合乎传统规范的正道。
刘勰对“和”之美的推崇深受传统乐论和重视声律的时代潮流影响,所以《乐府》引经据典,云:“律和声”,盛赞“中和之响”、“和乐精妙”;《声律》称美“宫商大和”“和体抑扬”;和非同,“异音相从谓之和”。《章句》论文章章法,以为一韵到底单调乏味、两句一换韵的急促都有偏颇,要求“折之中和”。对“和”的追求也扩大到篇章结构等方面,《附会》强调作品整体的协调性,故以“如乐之和”的境界为高。
3. “雅”与“俗”
郑玄注《周礼》“风赋比兴雅颂”时云:“雅者,正也;古今之正音,以为后世法。”“雅”有合乎传统、规范、标准的意蕴。《文心·夸饰》所谓“《诗》《书》雅言”之“雅言”指周王朝中心地区的语言,是当时有标准音的“普通话”。
刘勰在《征圣》篇说:“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明诗》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平子得其雅”。《铨赋》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章表》:“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颂赞》亦曰:“风正四方谓之雅。”又称:“《风》《雅》序人,事兼正变。”《定势》则言:“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
另外也有对“雅文”、“雅懿”、“雅章”、“温雅”、“儒雅”、“博雅”的赞赏。
“雅”与“俗”的对举中则对“俗”(与“郑”)的审美情趣多有贬抑:
《乐府》说:“迩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 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史传》称:“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通变》前有:“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实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其后称:“斟酌乎质文之间,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体性》所举“八体”中有:“一曰典雅”、“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指出:“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壮与轻乖”,“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故要求“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定势》有:“若雅郑而共篇,总一之势离”、“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
《才略》云:“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以及《知音》所谓“然而俗监(鉴)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和《时序》的“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等,对与“雅”、“正”相背离的“俗”、“奇”都是贬斥的。
“俗”也非一无是处。《谐隐》“辞之言皆也。词浅会俗,皆悦笑也”已有肯定通俗审美情趣及其效果的成分。《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俗怨”促生济世拯民的远大志向和慷慨意气。
《序志》综述“近代文论”之时,亦自称“或泛举雅俗之旨”。
4. “意”
“意”在《文心雕龙》现身八十次左右。与“心”、“志”、“情”、“思”同指心灵精神情感活动,但“意”有对某种构想和思维取向的侧重。在指内涵时“意”与“义”也或有通同、互代,言及经典内蕴、义理多用“义”,说创作内容的构思则多用“意”。
“上篇”“文之枢纽”前三篇宣示为文之楷范,故多用“义”“理”与“辞”,而少见“意”与“采”。
《原道》有“精义坚深”、“彪炳辞义”与“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征圣》有:“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而藏用”;“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与精义并用”;“赞曰: 精义成文,秀气成采”。《宗经》有:“辞亦匠于文理”;“《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诗》主言志,训诂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尚书》所记之言,特别是《诗经》的文字中多况喻和委婉的表达,故其“文意”较难理解。)“《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
《正纬》说:“原夫图箓之见……义非配经。”《辨骚》则称屈原的作品“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其所谓“经”当有(或主要指)《诗经》。
“下篇”中《神思》列首统领创作论各篇,讨论文学创作思维活动的规律,要求作家在最佳精神状态中立意、作表达的构想,即在“虚静”中匠意并作成功的文辞表达。是全书“意”论最为集中,具有理论意义的一篇。其中“意”六见,为全书最多者,还在文论中第一次使用了“意象”的概念。
倡言精神达至虚静之境“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称“神思方运……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以及“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说“神思”还会营构“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奇妙表达;最后有“神用象通”的总结。崭露出创意和匠意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的核心地位。
《风骨》有云:“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
刘勰所谓“风骨”指文章的感动力: 其“风”指充沛清峻的感情内容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其“骨”指有坚实依据和严密逻辑,由洗练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刚健气势和不容置疑的说服力。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曾有“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之说,可谓切中肯綮。
刘勰从不同角度探讨,力求在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找到立意和匠意正确途径。
《定势》有“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反正而已”;“密会者以意新而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
《镕裁》称:“立本有体,意或偏长”,“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魏晋南北朝是探究汉语声韵和章法结构美的规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声律》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章句》说:“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 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丽辞》论对偶称:“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事类》论典故运用,云:“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比兴》释“比”称:“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夸饰》批评“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并引《孟子·万章》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之语证之。《隐秀》的“隐以复意为工”以造就多重意蕴者为高手;《养气》的“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表明“意”的营构,要合乎思维规律。《物色》论主客体的兴会时称:“一叶且或迎意。”
《时序》论时代思潮、社会风尚对文学内容的影响,说战国著述:“故知炜烨之奇意,出自纵横之诡术”,“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才略》评议作家褒贬有差:“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说玄言诗赋“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说司马相如“覆取精意,理不胜辞”,而“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
《序志》综述全书理论建构,“意”的概念频出:“或撮题篇章之意”、“泛议文意”、“或有曲意密源”、“但言不尽意”,透露出“意”的探究在《文心》理论思考中的重要性。
刘勰文体论各篇中出现了“寓意”“构意”“甘意”“留意”“隐意”和“意深”“意隐”“意显”“意义”等组合。
《颂赞》:“及三闾《桔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哀吊》:“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沈膇。”《诔碑》:“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其声者也。”《杂文》:“庚敳客咨,意荣而文粹”;论七体“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谐隐》:“楚襄宴集,而宋玉《好色》,意在微讽”;“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章表》:“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无谐辞,可相表里者也。”《诸子》称:“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奏启》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书记》说:“休琏好事,留意辞翰”;“陈遵占辞,百封各意”;“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檄移》的“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更是用到了“意义”一词。
“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意少一字则义阙”中的“意”“义”只是以通同互代。“意义”成词,则还兼有两者互补的一面。“意”是作者心灵构结,每每有巧拙、显隐、审美取向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有高雅卑俗以及精切偏谬之别。“义”往往有普遍意义的道义、理路的逻辑规定,以及法则的宣示。
刘勰所用概念有的在后来的理论批评中更受重视,甚至衍生新的范畴概念系列,或者发展成为一个流派、一个时代审美追求和文学风格的中心范畴,但大多在《文心》中已见其端倪。下面介绍的“性灵”、“滋味”、“趣”、“韵”、“格”、“调”、“圆”、“境”就属于这一类。
5. “性灵”
“性灵”五见,皆于《文心》重要篇章的关键性论述中。《原道》云:“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宗经》有二:“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与“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情采》说:“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序志》称:“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以灵矣。……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都是指自然赋予人的非凡灵慧、生命活力和异彩纷呈的个性。刘勰呼唤作家洞悉性灵、陶冶性灵、抒写性灵,其中有领悟,有赞叹,也有珍惜之情。以后文学史上的性灵说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的。
6. “滋味”
从现有材料上看,刘勰是最早直言文学滋味的人,不像之前的陆机那样以“大羹之遗味”比况文学的美感体验,也有别于同时代的钟嵘只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文心》用到“味”和“滋味”的地方有十多处。食物滋味须经品尝才能生之于口,了然于心;文学艺术的“味”也得之于鉴赏。作为动词的“讽味”“可味”和“味之”的“味”是以领略“滋味”为归宿的品玩、鉴赏。如:“扬雄讽味,亦言体同风雅”(《辨骚》);“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采》);“味之则甘腴”(《总术》)。
“滋”可训多,无论指美食还是针对美文,滋味大抵是一种若干因素复合而成的美感,且以含蓄隽永为特点,故刘勰论“味”常与“隐”相联系,赞赏“余味”和“遗味”: 如云:“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而《宗经》则有“余味日新”;《史传》也说:“儒雅彬彬,信有遗味。”既由若干因素综合而成的,也就应该依循“滋味”之美生成的机制,是诸种因素有主次统序的复合体,故《附会》云:“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且以“道味相附”为上。《丽辞》的“左提右挈,精味兼载”和《声律》的“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则完全是从文学语言音响美的组合上去说的。有前后左右的副衬、映带、平衡;也有上句与下句的相互对应、补充、拓展与协调。
7. “趣”
“趣”本义是趋。艺术论中常指审美心理的取向和好尚,与“味”比较,在重浓厚隽永上“趣”或有不如,而个性化特征和新奇多变倾向明显。《明诗》批评东晋玄言诗“辞趣一揆”;《章表》赞赏曹植的表“独冠群才……应物制巧,随变生趣”;《哀吊》中称潘岳的哀辞“体旧而趣新”。《颂赞》说挚虞《文章流别论》评介“颂”的体式原很精当,但随后对傅毅《显宗颂》“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之评则流于“伪说”。
《体性》论风格,审美取向是风格的构成因素,故前面到说“才”“气”“学”“习”对风格形成的影响是有“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作“八体”之分则有“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评介作家亦有:“子政简易,趣昭而事博”。《镕裁》说,“万趣会文,不离辞情”,唯经“镕裁”,才能做到“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
还有章句构成和用字上的原则: 《章句》说:“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因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丽辞》赞赏“反对者,趣合而理殊”对意蕴的拓展,称许“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
《练字》引曹植评司马相如、扬雄之作语,说二人用字上“趣幽旨深”,非“师传”、“博学”不能理解。
8. “韵”
刘勰在《文心》三十余次用到“韵”。
“韵”原是一种为音乐和语言拥有的音响效果,有声音复合中生出的协调、和谐之美。南北朝的文人特别讲求文学语言的形式美,音响美是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术》中对文章作“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区分,以为有韵的“文”更富美感,更有文学性,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认可。《声律》概括的是那个时代探求语言声韵美规律方面的收获,其中说: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而杂句必睽。……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
随后批评陆机文“多楚”,即多影响“《诗》人综韵”标准音(“黄钟正响”)的“讹音”,指出“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丽辞》论称“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章句》则曰: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 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列举两汉魏晋赋家押韵的不同取舍,最后的“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唯“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是刘勰对章句音韵之美规律的总结。
《明诗》的“柏梁列韵”和“联句共韵”记录了汉武帝诏令群臣柏梁台联韵赋诗的雅事。评骘作家则称赞西晋潘岳“锋发而韵流”(《体性》),以为孙楚、挚虞、成公绥“流韵绮靡”(《时序》),东晋袁宏的赋作“情韵不匮”(《铨赋》),“张衡讥世,韵似俳说”(《论说》),“柳妻之诔惠子,辞哀而韵长”(《诔碑》);而《时序》则称:“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这些针对文章的“韵”,无不与作者的思想风貌和艺术个性合拍。
有“韵”在其中的一些概念现身各个门类艺术,以至用于评论人的气质格调,有“气韵”“情韵”“韵味”“神韵”的组合。
9. “调”
“调”亦源于音乐,有音调以及调节两种意义。
《原道》的“调如竽瑟”,《书记》的“黄钟调起”和《乐府》的“吹籥之调”皆指乐曲音调。《乐府》的“宰割辞调”是说“魏之三祖”对乐府诗体的改造,称其“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遗曲”;说曹植、陆机的乐府诗虽有佳篇,因未由伶人配乐而“俗称乖调”。《明诗》的“五言流调”谓五言诗体是四言的流变。《章句》的“调有缓急”、“改韵从调”、“环情草调”则针对文学语言声响。《附会》的“旨切而调缓”之“调”已逾越乐曲范围,为文辞音响节奏;《体性》的“响逸而调远”则指风格的超迈。
音、义有为调节、调和之“调”者。如《乐府》的“瞽师务调其器”、“杜夔调律”,《诔碑》的“辞靡律调”,《章表》的“体赡而辞调”,《附会》的“辞旨失调”,《声律》的“操琴不调”、“调钟唇吻”、“颇似调瑟”,《练字》的“四调单复”,《总术》的“调钟未易”,以及《养气》的“调畅其气”。
10. “格”
“格”的意义也不一。《章句》的“六字格而非缓”的“格”指句式稍长。《祝盟》的“神之来格”之“格”是来、至之意,以“正”亦可解。《征圣》的“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所谓“格言”指可以为人法则的话语。
“风格”的概念两次现身,《夸饰》的“虽诗书雅言,风格(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的“风格”侧重道德风范方面。《议对》云:“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序;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其“风格”指晋代四位文臣所作之“议”各自的特点,虽非其人文风总的概括,却已是指这种文体的写作而言。只不过刘勰和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理论家还未把“风格”的概念提升到与其所用“体性”通同的文艺基本理论范畴的高度。
11. “圆”、“境”、“悟”
刘勰佛学修养深厚,《文心》之作意虽不在弘扬佛法,其中却未尝寻觅不到佛学思维和语汇的蛛丝马迹。刘勰用了佛学中常见的“圆”“境”“悟”之类,即使不是特意如此,也会偶有流露。
《明诗》有“圆通”“圆备”,《知音》有“圆照”“圆该”;《论说》《对问》《镕裁》都有“圆合”;《比兴》有“圆览”,《隐秀》有“圆鉴”。“圆”是周延和完美无缺的,故《风骨》批评“骨采未圆”的妄为,《指瑕》发出“虑动难圆”的感慨,《杂文》以“事圆而音泽”为上,《丽辞》说“必使理圆而事密”……
刘勰所用“悟”“境”不多,也未完成向文论范畴义的转移。
“悟”就指理解,并未凸显体认、理解的豁然跃升。《明诗》有云:“子贡悟琢磨之句。”《练字》称对“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四条用字原则,“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指暇》说“匹”是两两匹配的意思,而“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
除《隐秀》存疑的补文之外,“境”在《文心》只是两次见到: 《铨赋》的“与诗画境”是说赋从《诗经》的“六义”之一发展成与风、雅、颂区界分明的独立文体。《论说》的“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是谓玄学“崇有”与“贵无”论辩的层次远不及佛学“般若”的至境。此“绝境”指至上的绝妙境界,虽非针对文学艺术,也是精神之至境。创作也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审美创造有领域的区别和层次高下之分,“境”和“境界”移用于文论也属自然,但完成移植是在佛学影响更为深广的隋唐以后。
12. “镕铸”“镕范”
《镕裁》称:“规范本体谓之镕。”《诏策》有:“垂范后代”,《风骨》有:“镕铸经典之范”,《事类》:“皆后人之范式也”。镕的本义指浇铸金属器物(如钱币)的模子(模范);“镕铸”的概念义是按楷范模式造就的意思。“范”原义也是模型、模范。
13. “法”
《通变》云:“参古定法。”《定势》的“效奇之法”,《附会》的“驭文之法”,所谓“法”皆是须遵从的法度、规则的意思。
14. “素”
《养气》有“岂圣王之素心”、“素气资养”;《程器》的“固宜蓄素以弸中”;《书记》的“或全任质素”和《议对》的“辞气质素”,其“素”都指向纯朴的素质天性。
15. “巧”与“拙”
从来就有“巧拙”的对举,《文心》同样: 《诸子》称:“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镕裁》说:“巧犹难繁,况在乎拙?”《附会》:“则知附会巧拙,相去远矣。”除《神思》的“拙辞或孕于巧义”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构思而外,其余之“拙”皆贬义: 如《事类》的“张子之文为拙”,《指瑕》的“拙词难隐”,《附会》的“拙会则同音如胡越”。
16. “闲”
《才略》:“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 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于闲畅。”
《养气》的“常弄闲于才锋”、《杂文》的“思闲可赡”、《物色》的“入兴贵闲”则皆与《神思》的“虚静”相通。
以上这些范畴概念散见全书,用于不同层面的论证。其中不少发挥着为后来的艺术追求和理论批评导向的作用。那些未成为篇题作专门讨论的范畴一般在理论上有更大拓展、深化的余地。此后,文学理论批评在以范畴概念进行系统的逻辑论证方面已难望刘勰之项背。自隋唐起,文学理论的拓展、更新和提升大都是在标举某一核心范畴的不同流派、不同文体和艺术主张的思想和美学追求中实现。所用范畴概念均不难在《文心雕龙》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或者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