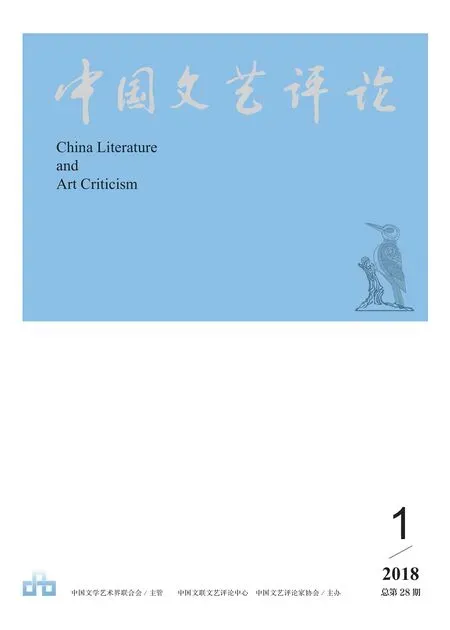互看与重构
——以《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为中心的考察
王一梅
2016年年末,《收获》杂志推出了“《收获》文学排行榜”系列评选,在各类文学排行榜“盛行”的今天,《收获》杂志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创刊60周年之际才推出文学排行榜。针对2016年度发表的小说作品,根据专家和读者的投票,《收获》杂志分别评选出了“长篇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排行榜”和“短篇小说排行榜”,又具体分为“专家榜”与“读者人气榜”两类。其中,“专家榜”的筹备、遴选、初评和复评历时四个月,其结果具有较高专业性,反映了当下文学创作的趋势。本文以2016《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为例,对此进行考察。
一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针对2016年度的小说创作,来自评论家、文学报刊、专业机构、新媒体等评选发布的小说排行榜多达二十余种。每一种排行榜都无法完全消除其特有的指向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片面性。小说排行榜的数量虽然不少,但自觉地按长篇、中篇和短篇的形式分类评选的却不多。其中,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王春林的“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和“中国作家·雨花读者俱乐部2016年小说排行榜”不仅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而且分别指向小说排行榜的专业化、个人化与大众化,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此,笔者将2016年《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与上述排行榜中的中篇小说排行榜进行比较,在“互看”中解析前者的代表性与指向性。
2016年《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由八位专家对入围的25部中篇小说进行投票,最终评选出10部上榜作品。从这些作品的首发刊物来看,有三部作品刊载于《收获》,其余的七部作品分别来自《人民文学》《花城》《当代》《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和《芒种》。这八本杂志均为传统的纯文学期刊,其中《收获》《花城》《当代》和《十月》更被称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八位评委中,既有活跃于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也有重要纯文学刊物的编审,还有高校中专事文学批评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家榜”体现了相当的专业性与严肃性。此外,上榜作品的作者中不见“50后”作家的身影也值得关注。这些作家中,“60后”作家三位(迟子建、尹学芸和陈希我);“70后”作家五位(张楚、石一枫、小白、旧海棠和肖江虹);“80后”作家两位(孙频和宋小词),仅有迟子建是已被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的作家。从评选结果来看,“60后”与“70后”作家逐渐成为当下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这也说明,“专家榜”较为及时地反映了当下中篇小说创作者年轻化的趋势,也表明《收获》杂志对文坛新生力量的关注和扶持。
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是国内最早的年度小说排行榜,截至2016年已持续进行了17届。该排行榜由23位评委对入围的51部长篇小说、52部中篇小说和54部短篇小说进行讨论和投票,最终评选出25部上榜作品,其中中篇小说10部。从评选方式和上榜作品来看,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与2016《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有一定相似性:同为多位专业评委集中评选;上榜作品集中首发于重要的纯文学杂志;两份榜单中出现了五部相同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专业性小说排行榜在思想趣味和审美判断上的趋同性。较之《收获》“专家榜”,中国小说学会的榜单中,“70后”作家的“表现”并不突出,“50后”“60后”作家则赢得了更多关注,而且上榜作家的年龄分布更加均匀:“50后”作家三位(陈河、裘山山和孙颙);“60后”作家四位(迟子建、尹学芸、陈希我和许春樵);“70后”作家两位(张楚和陈仓);“80后”作家一位(宋小词)。此外,在《收获》“专家榜”中,“80后”作家孙频的《我看过草叶葳蕤》高居排行榜的第二位,而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的前三甲中没有“80后”作家的作品。虽然相较于《收获》“专家榜”的“激进”,中国小说学会的这份榜单显得有些平稳且“保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50后”“60后”作家继续保持稳健创作势头的同时,当下“70后”和“80后”作家的中篇小说创作已经得到了文坛和学界的相当关注。
作为专事文学批评的学者,王春林的 “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榜单中的21部中篇小说全部来自纯文学期刊,其中有七部是《收获》“专家榜”的上榜作品。“中国作家·雨花读者俱乐部2016年小说排行榜”则有着较高的读者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反映出受众对于当下中篇小说的阅读接受情况。上榜的10部中篇小说中有三部为《收获》“专家榜”的上榜作品,这份有着“大众化”指向的排行榜中的作品也无一例外地都来自纯文学期刊。可见,当下传统的纯文学期刊依然是“孕育”中篇小说的重要园地,为广大中篇小说作者提供了优质的成长平台。
综上可见,一方面,“70后”作家已逐渐步入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期。另一方面,以传统的纯文学期刊作为首发“阵地”有利于中篇小说保持自我的文学性与独立性,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这似乎也成为局限中篇小说传播与推广的不利因素。即使是上文提及的“雨花读者俱乐部”,也还是在相对特定的“文学圈子”里开展活动。虽然现在传统的纯文学期刊纷纷采用新媒体开展宣传(如创建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小说、评论等),但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各类小说网站巨大的传播影响力面前,前者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的。传播与推广的受阻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篇小说的写作与生产,这其实也可视为2016年度中篇小说“缺席”大部分小说排行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新时期文学发展之初,中篇小说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1977年,它起于青苹之末时,有12部作品发表,1978年,翻一番,36部。1979年,又翻一番,84部。1980年,再翻一番,已经是172部。1981—1982年,竟猛然连翻数番,达到1150部。它冲击和席卷我们的文学生活。”探究其原因,张韧的观点可谓是一语中的:“作家对社会历史的审美思考的要求,独特的结构容量和审美属性,这是中篇小说崛起于当今文坛的内部因素。”从当代文学思潮的演绎来看,中篇小说深刻影响甚至引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小说“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中篇小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谓“合为时而著”。用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现实生活做相对及时且全面的反映,可视为中篇小说“崛起”之初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虽然在之后的“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中篇小说的这一特点逐渐弱化,但作为新时期中篇小说的一种创作传统并未完全消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创作传统不断发生新变。这其中关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中篇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应如何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是简单地将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在现有主题之下去刻意搜集素材成文,将小说写成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还是在保有文学性与陌生性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做深入具体的考察?这是当下中篇小说创作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016年年初,《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通过新媒体迅速传播,在这篇“非虚构”作品中,她以一位“返乡者”的姿态,刻画了一幅日渐凋敝的农村现实图景。“尽管从表面上看,农民的房子越盖越高、越盖越新,但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失去了完整的生活,造成了夫妻分居、留守儿童、老人孤独、环境污染等巨大代价,很多人内心彻底失去了安定感,多年延续下来的稳固的价值观轰然坍塌”。在今天的农村中,一些“坚固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了,随着它们的逝去,面对遥遥领先且日新月异的城市,落后而又日渐凋敝的农村该“何去何从”呢?类似问题在近十几年的文学书写中屡见不鲜,城乡问题也逐渐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一类经典题材。可以说,媒体只是借助这篇“非虚构”作品又一次把城乡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面对本年度这个由“非虚构”作品产生的“社会热点”,中篇小说作家们也相当默契,在2016年《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的上榜作品中,有三部作品(《营救麦克黄》《橙红银白》和《直立行走》)都涉及了这一热点。但应注意到,“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当下中国的现实城乡经验以及中国文学状况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关于城乡文学的叙事也悄然出现了某些新的特质”。也许这三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视的“窗口”,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当下中篇小说作家以何种姿态、何种方式介入现实,而且还可从中考察城乡文学叙事中“新的特质”,而“结构性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次“重构”。
《营救麦克黄》中,“70后”作家石一枫以时下热门的“狗权”问题为切入点,以一场救狗行动,牵涉出了对社会阶层矛盾和贫富悬殊问题的深刻反思。他沿用了在《地球之眼》等小说中已熟稔运用的二元对立模式,并做了更细致地推进。这一次他设置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一是身处大城市上流社会的精英,二是来自偏远小县城的打工者,三是由农村入城的贫民。其中,第一阶层与第二阶层、第三阶层明显构成对比乃至对峙的关系:一个是中心、一个是边缘;一个代表精英,一个象征草根。所以,在颜小莉和黄蔚妮所谓的“友谊”中,“主导权在谁手里是很明确的,被主导的那一方只有逢迎与配合的份儿”。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救狗行动中,这种对峙被正面呈现。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占据绝对优势的黄蔚妮们并没能轻松取胜,他们看似有理有据、底气十足,实则不过是虚张声势,正如开着保时捷的“富二代”徐耀斌——“这条一米六五的硬汉”,“挥舞着芦柴棒一般的瘦胳膊宣告”。这一次,“芦柴棒”不再是夏衍笔下受压迫受损害的包身工,而是家境优越行事张扬的“富二代”,在这样一种有意的“倒置”中,作者的反讽意图表现得十分明显。相比高度受重视的爱犬“麦克黄”,在救狗行动中无辜受伤的郁彩彩被黄蔚妮们“主动”忽视。对于这个丧父后与母亲暂住于北京郊外的农村女孩,目击者颜小莉饱受良心的折磨,为了给女孩筹集医疗费,她设计了一出“虐狗”勒索案。虽然黄蔚妮一方支付了“赎金”,但颜小莉最终失去了与她的友谊,这段友谊曾被她视为来到北京之后最大的收获,阶层的跨越与和解最终未能实现。如果说来自小县城的颜小莉尚有一丝能力去挣扎、去抗争,那么来自农村的郁彩彩和母亲则是毫无希望,只能在城市中无限“下沉”。《营救麦克黄》不仅展现了当代大都会的众生相,同时也是一部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启示录”。也许可以借用并改造雨果在《九三年》中的名言对黄蔚妮们说一句:在相对正确的狗道主义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同样是反映当下的社会阶层现状,宋小词的《直立行走》是一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小说。小说中的杨双福是当代城乡文学叙事中的一类经典形象——进城的乡下人,她在进城之初满含着对大城市的好奇与憧憬,但在寻求扎根城市的过程中屡屡受挫,饱受屈辱与苦难。杨双福的遭遇在新世纪以来的城乡文学叙事中具有普遍性,但如果仅局限于此,《直立行走》并无新意。所幸作者加入了对城市工人的历史与现状的思考,表现了社会阶层问题的复杂性。小说中,周父周母在1998年双双下岗,下岗工人是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群体。对他们来说,“从头再来”“分享艰难”并非易事。周家人也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沦落”为城市贫民,为了争得按人头补偿的拆迁款,周母选择对病故的周父秘不发丧,现实生活给了她一个两难的抉择:是选择摆脱简陋的蜗居生活,在宽敞的新居中“直立行走”?还是选择人伦亲情,重塑工人阶级的尊严“直立行走”?也许,光荣与尊严已属过去,重新拾起也并无多大的现实意义。小说中有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景,周父病亡后秘不发丧的秘密被揭开,众人集聚周家逼仄的小屋,这里有电视台女记者高高在上的鄙夷与质问,有周午马愤恨宣泄式的回应,有杨双福有条有理的陈情,也有拆迁办肖主任的虚与委蛇与警察程式性的喊话。此刻,每位说话者似乎都在“控诉”,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他们都有理由“控诉”,但是我们又能说谁掌握了真理与正义呢?多种声音的“交锋”交织成了复杂的时代变奏曲。
相较《营救麦克黄》和《直立行走》,“70后”女作家旧海棠的《橙红银白》带有明显的主观抒情气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通过“我”的主观视角,将三叔一家十几年间的故事娓娓道来。这其实是一部关于城乡文学叙事的“成长小说”:不仅回回和三叔需要时间“成长”,日渐凋敝的乡村也需要时间“成长”,相比迅速“成长”的城市,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乡村和乡村中人的成长。小说以小见大,借由个体的成长经验来探察种种时代症候。谢有顺曾借用普实克有关抒情与史诗的区分,指出:“‘70后’作家群中较少有像茅盾、莫言这种以注重表现广阔的社会画面为中心的‘史诗的’写作,而更多是一种‘抒情的’写作”。《橙红银白》虽是一部写实性的作品,但更多地带有抒情性的特质,作者并不十分在意故事情节,小说更像一首叙事诗,它不急不缓地讲述,一点一滴地蓄积情感。或许在写实小说越来越重视话题和关注度的当下,旧海棠这种内敛含蓄的写作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再写实的小说,就其内在的精神旋律而言,都必须要有诗性和抒情性,才有更为丰富的文学性”。在这个意义上,《橙红银白》为当下的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考维度。
三
“70后”作家张楚的《风中事》有关“‘85后’青年的混乱恋爱观”,作者自述自己“妄图对这些从小吃肯德基长大的一代人的恋爱观做一次乏味的图解梳理”。在他看来,“恋爱是美好而简单的事”,“它简单、实际,有点浪漫,也有些世俗”。但是在“80后”警察关鹏的世界中,恋爱既不美好也不简单:物质与欲望至上,爱情式微。小说通过“串”式结构,以关鹏的三段恋爱经历为主线,不仅对当代社会中人赤裸的欲望做了放大式的呈现,也对“80后”的婚恋观做了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考察,这个看似轻浅琐屑的风月故事折射了当代社会的驳杂性与繁复性。小说并不局限于表现个人之爱的微茫,还通过顾长风的婚变纠葛和段锦的秘密代孕反映了家庭伦理之爱的微茫。“70后”作者面对的是下一代人个人之爱与家庭伦理之爱皆已微茫的现状,时代的断裂是其切身之感。
似乎是有意回应《风中事》,“80后”女作家孙频在《我看过草叶葳蕤》中选择往前回溯,以“70后”主人公李天星的人生爱情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个体在时代中被抛弃的焦虑。于是,一种代际间的“互看”在两个独立的小说文本之间展开。如果说张楚着力展现“80后”一代的爱之微茫,那么孙频侧重呈现的是“70后”一代的生之艰难。“节日”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名词,此处的“节日”不是庆贺,也不是消解权威、打破秩序的狂欢节,它是面对时代突变的人们自我补偿与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害怕被时代抛弃的人们急于想赶上时代的步伐,在焦虑中只能采用这种喧嚣的方式来显示自我的存在。从时代的反叛者到随波逐流者,李天星最终只能在情欲和欢场中沉沦,依靠感官刺激来适度缓解焦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看过草叶葳蕤》指向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生之艰难并不简单地指向生存,也不是单纯地指向某一代人,它指向的是具体时代语境中个体生命的内在精神世界,它指向的是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博弈。小说的结尾,李天星和杨国红一同见证了县城中心百货大楼的爆破坍塌——大楼作为曾经时代的见证,现在指向了永恒的缺席。
如果说张楚和孙频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跨代际的“互看”,那么,两位“60后”作家尹学芸和陈希我则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互看”,对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人情与人性,历史创伤记忆和当下现实热点做了深刻的烛照与洞悉。陈希我的《父》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和力度的小说,小说围绕年迈父亲的赡养问题展开,在兄弟四人的犹豫、瞻前顾后与相互推诿中父亲最终客死他乡。赡养老人是现实问题也是热点话题,小说中夹杂的老年人街头暴走、公交车让座等事件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但是作者并没有对社会热点做铺陈式的列举和粗浅化的分析,而是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反思历史,对两者皆做了纵深掘进。父亲这一辈人不仅承受着历史的创伤记忆,而且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们逐渐由“中心”被抛弃到了“边缘”,当他们走向暮年时,他们已不仅仅是被抛弃,更是被遗忘。下岗后的父亲在公交车上因为让座问题而对一个小年轻动起手来,在当下的语境中,对此举的解读通常会联系到特殊的时代记忆:老人的暴力行为是对这种记忆的延续。但显然,父亲不是占有主导话语权的一方,他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别人表述。也许对父亲而言,面对一个不能与自己沟通的晚辈,“暴力”是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暴力的“基因”是可以遗传延续的,大哥和他的儿子就“遗传”了父亲的“暴力”。从这个角度上看,《父》似乎有着更大的“野心”,它真正想要呈现的或许有关整个民族的心理建构。
《李海叔叔》中,“我”作为讲述者,从个体记忆出发,以一个晚辈的视角讲述了李海叔叔的故事。在他与我们家近30年的交往中,两家人从开始的亲密无间到有选择性的遗忘再到后来的冷漠与疏远,这其中揭示出时代变迁中微妙复杂的人情与人性关系。曾经在我们一家人眼中,李海叔叔“就是高门贵客,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段亲戚关系满足并保持了我们一家人的虚荣与自尊。然而直到长大成年,“我”才发现,也就是在相同的时期,“我们”也是李海叔叔一家的“精神寄托”。两家人在相互的审视与想象中,每个人也在看他人的过程当中建构自己。“我”在多年之后回味这段人情交往时才恍然明了:我们家渐渐地将李海叔叔当成了一个“标志”,而李海叔叔“也一定从这种标志性的身份中悟到了什么,逐渐偏离了自己的航道也未可知”,于是,“一份原本淳朴、纯洁、纯粹的情感扭曲了,变异了”。相较于父辈,“我”和李海叔叔的子女之间的交往更显微妙:因为我们“骨子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结论”。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难道虚荣与虚伪是一对孪生姐妹?”这似诘问,也似慨叹,却直抵问题的核心。
早在1981年,就有学者指出,“中篇小说反映生活是否深刻,不在于把故事编造得如何曲折离奇(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而在于在有限的画面中开拓出深刻的思想来,在于创造出典型人物来。”这也是值得当下中篇小说作家们持续关注并思考的问题: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开拓出深刻的思想?以上四部中篇小说有着一定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四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指出:“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我觉得,在遭受痛苦与希望减轻痛苦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人类学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常数。文学不停寻找的正是人类学的这种常数。”在此,卡尔维诺其实对“文学何为”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一方面,文学应当是轻盈的,依靠轻盈可以重构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消解生活负担,但文学也并非逃避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被视为是文学的一种超越性。这或许为当下的中篇小说家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有限的篇幅内开拓出深刻的思想固然重要,但文学的这种超越性也不容忽视。
同样是发生在北国大地上的“洗澡”故事,相较于2001年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空色林澡屋》要“复杂”得多。迟子建在创作谈中写道:“这部中篇与我其他中篇不同之处,在于可以有两种解读法。如果读前三分之二,只是关乎洗澡的部分,也算一个完整的故事,未尝不可。但岁月风雨吹打,让我对后三分之一的内容,更加满怀期待(那里有人性寒霜的一面,有落寞和虚无),所以希望读者读到底。”《空色林澡屋》中,关长河讲述的皂娘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前三分之二”,皂娘面容丑陋,命途多舛,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她以美好、真诚与善良的心灵与命运进行着抗争。她的空色林澡屋为疲惫的旅人提供了一处荡涤灵魂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暂时放下现实的沉重,灵魂可以溢出肉身之外感知生命的轻盈。小说“后三分之一”的内容则围绕勘察小分队成员争夺空色林澡屋难得的一次“洗澡权”展开,在“比一比谁的委屈更深,磨难更大,辛酸更多”的“诉苦大会”中,每个人都竭力展示人生中最幽暗最屈辱的经历,每个人都渴望在空色林澡屋中沐浴肉身,以期通过这种“仪式”来减轻现实的沉重与痛苦。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皂娘和空色林澡屋,还是讲故事的关长河,抑或是那场 “诉苦大会”,所有的这一切到最后都似真似幻,真假难辨,这也使小说在写实之外带上了一点浪漫与轻度魔幻的色彩。这并非是作者刻意经营的结果,正如蒋子丹在评论迟子建的另一部小说时指出:“作者似乎并未在表现手法上刻意经营,精神意志的内在需求成为一种无形的手,支配着作者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不同的空间。”贯穿《空色林澡屋》始终的仍然是作者“精神意志的内在需求”,所以将小说读到底后,真假虚实都不再重要,正如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写道:“其实真名和假名,如同故事中的青龙河与银河,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它们在同一宇宙中,渡着相似的人。”
对于那篇为自己赢得较高关注度的小说《百鸟朝凤》,肖江虹表示:“这个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其实前辈们早就表达完了……所以这些年我写了一系列关于民俗的作品,就是希望能在主题的拓展和表达上有所突破。”顺着这个思路,在《傩面》中,肖江虹将目光继续对准了正在消失的民俗——傩面和傩戏,两代人、两种对立的思想在遥远封闭的山村相遇并碰撞交锋。作为走出山村的年轻一代,在颜素容的眼中,傩村早已虚化为地理学意义上的一个处所,她梦想“把钱挣足,就在那个能吹海风的城市过完一生”。传统古老的傩戏被年轻一代视为落后愚昧的产物,他们追求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傩戏中的鬼神之说不过是虚妄的存在,对经营傩面生意的梁兴富来说,物质财富远比傩面背后所谓的文化信仰来的实在。作为傩村最有名的傩师,秦安顺老人苦苦坚守着濒临失传的傩戏和傩面手艺,另一边,身患绝症返乡后的颜素容以乖张暴戾的态度对待不明真相的父母和乡亲,这种看似猖狂的举动背后掩藏着的是挥之不去的绝望与焦虑。一老一少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相遇了,一个是生命迟暮的老者,一个是命不久矣的青年,他们比常人更能感知“向死而生”的意味。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生命境遇中,颜素容渐渐被傩面与傩戏所感化,并最终在这一传统的民俗文化中找到真正的精神原乡。傩师戴上傩面的一刻便已神灵附体,他们不仅为亡灵引路超度,也为生者祈福祷告。从这个角度上看,傩师其实与皂娘有着相同之处,他们都是“渡化”他者的“圣人”。在他们那里,现实中的痛苦与沉重得以一定程度的消解,无处安放的灵魂得以皈依,受创的心灵得以疗救……所以肖江虹认为民俗代表的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种“诗意”——“诗意”本身指向的就是一种超越性。
小白的《封锁》是本次上榜作品中最为特殊的一部,说它特殊,不止因为它的题材,也不止因为它的技巧性,还因为它的想象力。小白自述在《封锁》中“讲了一个人的人生最后被虚构颠倒过来的故事”,“虚构”是这部小说最常见的要素。即使是在气氛压抑紧张的审讯室内,“虚构”也并未停止:“审讯室内,有一种诡异的合作气氛。似乎双方共同努力,正在设法完成一个联合作品。审讯规则已被悄悄替换,如今故事技巧和想象力更重要,准确性退居其次。”毋庸置疑,想象力为虚构提供了支撑,刚出场时那个“软弱、胆小、权宜、得过且过”的鲍天啸也一步步在想象的故事中完成了抗日锄奸的现实壮举。或许作为想象与虚构的产物,某些时候文学也只有在想象与虚构之上才能完成对现实的重构与超越。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学者孟繁华近些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中篇小说是“高端艺术成就”。他指出“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从突然崛起到逐渐消沉再到渐次稳定,在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中篇小说是不容被忽视的,作家毕飞宇甚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在这个意义上, 2016年《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专家榜)的十部上榜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从中我们可以考察当下中篇小说创作的某些特点,思考中篇小说未来将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