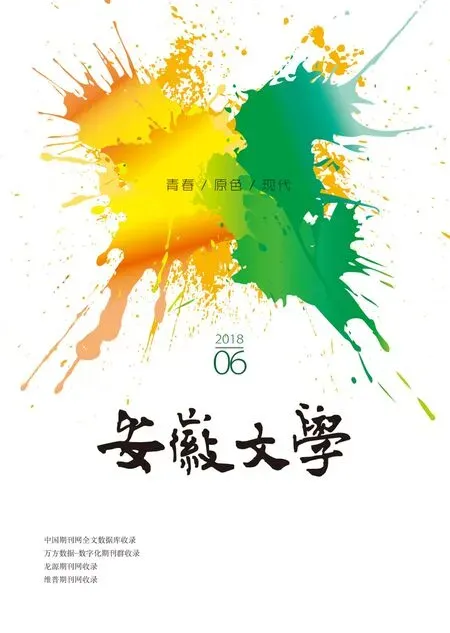试析汉乐府《芳树》
韩 梅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芳树》是《汉铙歌十八曲》之一,从一开始的产生到后来为文人所接受并加以大量拟作,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芳树”始于汉民歌,自魏晋开始被定于朝廷礼乐之一,用于典雅庄肃的场合。经过何承天“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以后,便开启了对汉铙歌模拟创作的先河,《芳树》也成了文人喜爱模拟的一个题目。从谢朓、王融等至后世的广大文人都对《芳树》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创作,突破了乐府旧题的束缚,他们没有沿袭《汉铙歌十八曲》“建武扬威德,风劝战士”(崔豹《古今注》)的写作模式,而是为其带来了新的思想内涵,这些诗作中不乏佳作,给以“芳树”为母题意象的系列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文就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辑录的历代乐府诗《芳树》,考察后代拟作《芳树》与汉乐府原辞之间的关系,探析后代拟作之间的发展及变化特征。
一、历代《芳树》拟作与汉乐府原辞之比较
《芳树》原辞如下:
芳树日月,君乱如於风。芳树不上无心温而鹄,三而为行。临兰池,心中怀我怅。心不可匡,目不可顾,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它心,乐不可禁。王将何似,如孙如鱼乎?悲矣。①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解释《芳树》曰:“古词中有云‘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若齐王融‘相思早春日’,谢朓‘早玩华池阴’,但言时暮、众芳歇绝而已。”此曲难解,众说纷纭。在陆侃如、冯沅君所著的《中国诗史》一书中认为“此曲句读难定,庄述祖《汉鼓吹歌曲句解》以己意改定,似嫌武断。篇中有‘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等句倘可懂得,知道这是篇情诗,但时代无考,各家解说均误。”②赵敏俐则把《芳树》列为“不可解的一类”③。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篇表达女子失宠而哀怨的作品,推测《芳树》与班婕妤《怨歌行》、托名为卓文君的《白头吟》相似,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封建女子“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的悲惨命运。结合以上种种论述,可以说《芳树》原辞是描写被弃佳人如芳树一样的美丽动人,但因命运坎坷不平,时时透露出哀怨凄凉之意。
在后世的拟作中,“芳树”意象成为了诗人们描摹刻画的对象以及寄托情思的载体。如陈李爽的《芳树》:
芳树千株发,摇荡三阳时。气软来风易,枝繁度鸟迟。春至花如锦,夏近叶成帷。欲寄边城客,路远谁能持。
此诗以乐景写哀情,极言春光明媚生机勃勃之景,反衬自己长年漂泊在外思归不得归的浓厚悲凉的思乡之情。以季节的变迁来抒发久居在外,无法归乡的苦闷,以客观景物与主观感受的不同来对照反衬诗人乡思之深厚,别具韵致。再如韦应物《芳树》:
迢迢芳园树,列映清池曲。对此伤人心,还如故时绿。风条洒余霭,露叶承新旭。佳人不可攀,下有往来躅。
这是一首悼亡诗。首二句起兴比喻,即是对现实芳园的描写,亦是对往日夫妻欢乐生活的再现;次二句感叹伤情,睹物思人,追念之情频频溢出。一种“空游昨日地,不见昨日人”(韦应物《有所思》)的凄凉惆怅油然而生,末句“佳人不可攀,下有往来躅”则流露对亡妻的追忆之思。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云“乐府之兴,肇于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④“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意为不顾诗歌原辞的故事,只从诗题表面着手赋作,以己之意附加之,而这也是在历代拟作发展变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见,吴兢已然察觉了这一改变,一语便道破其变化的缘由。
在李直方所著《谢宣城诗注》中曾言:“汉以后迭有新制,即芳树一曲,魏曰邕熙,吴曰承天命,晋曰天序。”⑤即便是古辞的名称也有不同,更何况是主旨的变化。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辑录的16首《芳树》中,其思想内容和古辞的原意已经有所不同,拟作的作者们借古乐府辞,按照所处时代的审美风潮,对古乐府加以改造,不再关注古辞原有的故事情节和情感心绪,他们注重的是诗歌文字的技巧和性情的感发。这种种的“改造”都在体现着对诗歌艺术性的自觉追求以及诗歌逐渐文人化的过程特征。
二、历代《芳树》拟作之比较
郭茂倩《乐府诗集》一共辑录了17首,包括汉乐府《芳树》,也包括从齐梁至晚唐文人的所模拟的《芳树》16首。在文人所拟的16首《芳树》中,时间跨度从齐梁至晚唐,在这一时期,文学自身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芳树》系列的诗歌中,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文人自身经历及生活背景的不同,也会使同题拟作有不同的主旨或思想。本节主要通过对比拟作在形式、主旨、修辞、描写等方面的差异,探究拟作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一)形式之变化
王先谦云:“芳树十七句,共二句句二字,一句句五字,一句句二字,一句句四字,一句句三字,一句句四字,一句句三字,一句句五字,二句句四字,一句句七字,三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一句句二字。”(《谢宣城诗集》)⑥汉乐府《芳树》从二言到七言不等,拟作中从第一首谢朓的《芳树》开始就是完整的五言句式。之后的梁、陈所拟皆为五言,直到唐徐彦伯的《芳树》始为五七言,再至晚唐罗隐《芳树》则为杂言,但依旧以五七言为主。
由汉乐府参差不齐的句式到齐梁时期整齐的五言句式,究其原因,与这一时期声韵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齐梁时期,沈约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在此基础上,对声韵的重视使得“永明体”得以出现。《南齐书·陆厥传》载: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⑦
永明体一大特征便是讲求声律,而“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正是其声韵格律要求之体现。永明体的出现,实现了自然声律到人为总结、规定并施之于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随着声韵的发展,汉乐府参差不齐的句式必然会被整齐的五言句式所取代。如陈顾野王的《芳树》:
上林通建章,杂树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风吹梅迳香。幽山桂叶落,驰道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
这首诗在声韵上与汉乐府五言相比较,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有一种声律之美。“平上去入”的声韵要求使其更具有诗意之美。
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不断繁荣,五言古诗已逐步脱离乐府入乐的要求,从而发展成了不入乐的徒歌,即锺嵘所说“不备管弦”(《诗品序》)的五言诗,那么对于文人五言诗来说,摆脱对于乐律的依附而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诗歌,已经成为其发展的必然之势。
从形式上看,“永明体”也属于五言体,但是与唐代的五古和五律又有区别,从概念上来看,相对于永明体,唐代的五古和五律区分得更为细致,对声律的要求也更为严格,这当然是诗歌形式自身的发展需求。在此发展的基础上,诗歌形式在唐代已趋于成熟,诗人们可以选择所需的形式,以抒发自身的思想情感,这也是为什么唐代诗人拟作的诗歌形式变化多端的原因所在。
(二)主旨之变化
《芳树》系列诗歌是由不同时代、不同诗人所拟作的作品所组成,其诗歌的主旨必然会存在差异性,而诗歌中所体现的差异性正是解读《芳树》系列诗歌主旨变化的重要因素。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对《芳树》的解题言:
“古词中有云‘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若齐王融‘相思早春日’,谢朓‘早玩华池阴’,但言时暮、众芳歇绝而已。”
由此可见,郭茂倩已经注意到后代拟作《芳树》与古辞原意已有所不同。虽然历代学者对于《芳树》古辞的原意争论不休,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篇表达女子失宠而哀怨的作品,笔者也认为此曲是一首爱情作品。
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辑录的16首《芳树》中,最早进行《芳树》拟作的文人是齐谢朓,其辞云:
早玩华池阴,复鼓沧洲枻。旖旎芳若斯,葳蕤纷可继。霜下桂枝销,怨与飞蓬逝。不厕玉盘滋,谁怜终委细。
方东树为“起四句说盛,后四句说衰,而迟暮众芳歇,言外有比兴。”(《昭昧詹言》)。这是写时光已逝,众芳已绝,蕴涵着对时光流逝的叹息。可见,从一开始文人拟作的诗歌题意便与古辞原意已然有所不同,对后来的文人而言,在承袭拟作的同时,不管是师其辞或是袭其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前代文人的影响,在拟作时便会表达不同的主旨意义。如沈约的《芳树》:
发萼九华隈,开跗寒露侧。氤氲非一香,参差多异色。宿昔寒飚举,摧残不可识。霜雪交横至,对之长叹息。
这首诗从树的姿态、外在的环境等多个角度展示了芳树的枝繁叶茂与芳香四溢,然后借助外在的环境写芳树备受摧残,“霜雪交横至,对之长叹息”则表达了诗人对其遭遇的同情。与谢朓的《芳树》相比,其所表达思想的也不尽相同,更是与古辞原意迥异。
对于《芳树》主旨的变化,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的影响。对于诗歌自身的发展而言,需要切合时代背景的审美风尚,而对于作诗者而言,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家庭背景都会对其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对汉乐府基本精神的评价,作诗者必然都是有感而发,既然是有感而发,必然感发的情思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便有了不同的诗歌主旨。
(三)语言风格之变化
《芳树》原辞云:
芳树日月,君乱如於风。芳树不上无心温而鹄,三而为行。临兰池,心中怀我怅。心不可匡,目不可顾,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它心,乐不可禁。王将何似,如孙如鱼乎?悲矣。
其语古朴真挚,就像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的:“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鄙,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的确,“质而不鄙,浅而能深”是汉乐府民歌的语言特色,虽似粗线条的勾勒,但整体呈现出的却是朴素淳厚之美。
经过文人拟作对汉乐府的修饰与改造,诗歌的形式逐渐以轻艳为主,甚至逐渐走向了藻丽柔美的文风。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其中“丽”、“绮靡”、“浏亮”都是说文章要美,而且是形式上的美。如梁武帝的《芳树》:
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一叶度春风,芳芳自相接。色杂乱参差,众花纷重叠。重叠不可思,思此谁能惬。
此诗为萧衍感物兴怀之作。绿树成荫,散发醉人的芳香,然而秋天一到,纷纷落地,黄花堆积成堆。由花及人,勾起对年华易逝的叹息。其辞文雅典丽,与《芳树》原辞相比,不再是对故事的简单勾勒,而是更加注重文字的技巧和表达,使得诗歌所表现的情韵别具一格。再如丘迟的《芳树》:
芳叶已漠漠,嘉实复离离。发景傍云屋,凝晖覆华池。轻蜂掇浮颖,弱鸟隐深枝。一朝容色茂,千春长不移。
钟嵘称“丘(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其语辞采逸丽。此诗借助正面的描写和侧面的衬托体现了芳树之美好,用词秀丽,末句“一朝容色茂,千春长不移”,以“一朝”和“千春”来形容芳树的芳香永驻。诗歌语言精致华美,与原辞直白浅显的遣词用语不同。
(四)描写技巧之变化
郭茂倩《乐府诗集》辑录的历代拟作《芳树》,时间跨度从齐梁至晚唐,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诗文追求和描写技巧,即便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发展期,诗歌的描写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以古辞《芳树》来说,描写过于简单浅显,于历代拟作来看,描写技巧以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变化着,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细腻。如王融的《芳树》:
相望早春日,烟华杂如雾。复此佳丽人,含情结芳树。绮罗已自怜,萱风多有趣。去来徘徊者,佳人不可遇。
原辞《芳树》“芳树日月,君乱如於风”中,“芳树”只是起兴,与诗歌所述故事并无较大关联。以首句起兴,这是汉乐府常用的手法。而此诗以芳树喻佳人,“佳丽人”与“芳树”的命运已然成为一体,“芳树”不单单是起兴的作用,同时还是诗人赋咏的对象以及寄托情思的载体。再如张正见《芳树》:
奇树舒春苑,流芳入绮钱。合欢分四照,同心影万年。香浮佳气里,叶映彩云前。欲识扬雄赋,金玉满甘泉。
姚思廉《陈书·文学传》称张正见“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言“张正见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张正见的五言诗,对仗工整,辞藻艳丽。此诗不仅对仗工整,声律精细,而且在末句“欲识扬雄赋,金玉满甘泉”还借用扬雄《甘泉赋》的典故,借古抒怀,以表达作者内心的想法,这与汉乐府民歌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不同。同是文人拟作赋咏,张正见的《芳树》,还增添了对色彩的描写,使得笔下的景色更加生动形象。
不仅如此,相比于南朝和唐前,至唐后期在景物描写上更为详尽,描写成分明显增加,特别是对于细节描写的刻画更为细致。如元稹《芳树》:
芳树已寥落,孤英尤可嘉。可怜团团叶,盖覆深深花。游蜂竞钻刺,斗雀亦纷拏。天生细碎物,不爱好光华。非无歼殄法,念尔有生涯。春雷一声发,惊燕亦惊蛇。清池养神蔡,已复长虾蟆。雨露贵平施,吾其春草芽。
此诗以芳树不畏寒秋和环境的恶劣来喻自己的高尚情操,从树的形态以及树所生存的周边环境等多个角度来展现芳树的坚忍不拔以及可以忍受一切恶劣环境的美好品质。从树的枝干、花叶到周围的游蜂、斗雀等,由近及远,由里而外,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其笔下描绘的景物更加具体且有强烈的画面感。
如前所述,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16首拟作《芳树》与原辞相比,在诗歌形式、主旨、修辞、描写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变化。在南朝时期,文人拟作在形式上虽已初步具有对仗、齐整之美,但篇幅较小,这就限制了描写的力度与深度,使得拟作者无法加入更多的东西。经过唐人拟作在规模和篇幅上的拓展,诗歌的体裁更加多样化,描写细致生动,诗歌形式趋于成熟、走向完善。此类乐府诗,随着朝代的更替和文学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着,在不同的时间段有着不同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在整体上与文学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
注释
① 文中所引诗作均出于:郭茂倩.乐府诗集[C].中华书局,2016.
[1]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3]赵敏俐.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研究[J].文史杂志,2004(04).
[4]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李直方,罗香林.谢宣城诗注[M].香港:龙门书店,1968.
[6]谢朓.谢宣城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