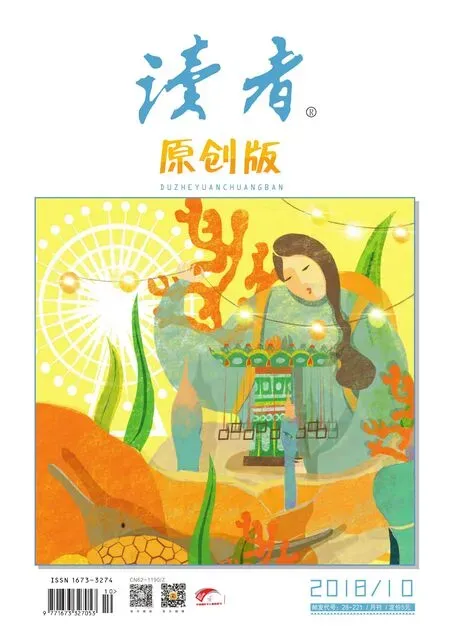写给天上老师的作文
文|格桑亚西

一
年后,回乡。
说是故乡,其实不算确切。我的家族不在这里繁衍,老祖宗不在这里埋葬,不过我在此地出生倒是确凿无疑的。
当年的教堂是在的,早已经恢复了礼拜,不再是过去那个杂乱的木工房。教堂里重新树立起慈爱的圣母玛利亚雕像,窗上悉数安装了玻璃,木门上破损的浮雕也得到修复。
记忆中两棵高大的槐树,不仅枯干,还似乎矮小了许多。
自觉胡子拉碴,相貌猥琐,不料还是被在教堂边晒太阳的大娘一眼认出。
“啊呀,这不是那谁家那谁谁吗?”
“啊呀,胡子这样长!”
画龙画虎难画骨,她们凭记忆认定的,是躲藏在虚妄的表象下面,骨子里的那个我。
寒暄。
她们得知我的父母早已过世,长兄旅居海外,皆不胜唏嘘。说起往事,恍若昨日,诸如母亲人好,父亲落魄,兄弟俩幼时贫寒,等等。如数家珍之余,也有不堪回首、难以忘怀的意思。
然后,她们说到一个名字。
是一位新亡的故人。30多年前,她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她姓彭,原籍成都,高度近视,西南师范学院毕业,传为富商独女。
她个子不高,多才多艺,精于弹唱,尤擅手风琴。她性格执拗,语言犀利,待人接物时,冷冷的目光透过厚玻璃镜片射出,让人不寒而栗。
她生下儿子未满周岁即与丈夫离异,此后一直独身,抚养独子成人。
除了有限的家务,老师的全部身心皆投入教学。这一点,在恢复高考的次年,我升入高中后,感受颇深。
边城萧索,山高水冷,冬日尤其昼短。她天不亮即守着我们早读,夜深了,才肯放众人回去。那是我生命中印象深刻的一幕:已然沉寂的校园,路灯暗淡着,拉长踽踽独行的身影。我身体疲乏,精神上却是快乐的,那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事关“穿皮鞋”抑或“穿草鞋”的激励。
“穿皮鞋”抑或“穿草鞋”,这是彭老师对考上大学与否的两种人生的描摹。
她并不用标语上“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之类的陈词滥调糊弄我们,而是斩钉截铁道:“考上,穿皮鞋!落榜,穿草鞋!而且是一辈子!”
直截了当、掷地有声的“皮草说”振聋发聩,完完全全震慑住了一众家境苦寒的平民学生。
中文系出身的她批改作文极其严苛,错用的标点符号和字词,皆逃不脱镜片后面鼓鼓的金鱼眼,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她也用红色水笔耐心列出。我小学以来常常获得高分的虚假文字,在她的火眼金睛下自是乏善可陈,从曾经高达99分的顶峰跌到70分上下,有一次竟然不及格,让我好生郁闷。
现在想来,她的执着、敬业、好强、严格,除了性格使然,其中也有独身女人的任性和意气。
二
有关她的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以下几桩。
其一,我们两家门对门同住芙蓉院将近10年。她平常不怎么让儿子出门,也不欢迎小朋友们串门。黄昏时分,常听得手风琴伴奏下引吭高歌的清脆童声,满院的人都知道,是她在家里教授独子声乐。
厚积而薄发,后来不久,她的独生子果然在校际舞台上一鸣惊人,朗诵、独唱、器乐,赢得满堂彩。最成功的一次,是母子俩合作出演话剧《园丁之歌》。她扮演循循善诱的老师俞英,儿子出演活泼调皮的学生陶利,一位青年男教师出演方觉,在剧中是个简单粗暴的角色。
母子俩的普通话相当标准,相比之下,“方觉”的“川普”就糟糕透顶,拿腔拿调不说,还怪模怪样,其逼仄促狭的乡土味,引得台下笑声不断,生生把教育战线一出严肃的伤痕剧变成半个《欢乐喜剧人》。
但演出还是大获好评,以至于很久以后,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议论。芙蓉院家长教育子女,她乖巧的儿子永远是参照系。家长恨铁不成钢的后果,自然是她的儿子招致了小伙伴们的羡慕嫉妒恨。
掐他家的红花,打他的橘猫,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有的。天地良心,我也是“黑手党”之一。
其二,她使我初尝竞选的滋味。
因为我是本校教工子弟的缘故,新生报名伊始,我得到一件光荣而辛苦的差事—接待新同学。
受此重用,喜出望外的心情是铁定的。
一连三天,在她的号令下,我鞍前马后,屁颠屁颠,忙得不亦乐乎。
指点食堂方位,协助落实住宿,帮忙搬运行李,安排打扫卫生,该做的做,没让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全做了。上上下下,皆大欢喜,我的“政绩”赢得了满堂彩,自己也因为得到肯定而飘飘然。
然后是正式开学。
接待工作很烦琐,但它的好处立竿见影。
在第一次班会上,班主任宣布无记名投票选举班委。新同学大都来自其他初中,人地生疏,接待工作让我快速混了个脸熟,给大伙儿留下了深刻印象。汗流浃背的卖力模样,拿鸡毛当令箭的工作作风,小题大做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工作热情,让我的人气一路飙升,证据就写在黑板上—我的名字后面,不断增加着一连串的“正”字。
我努力抑制住心中的狂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其实,专注于接待新同学的几天里,我真没想过要混个“一官半职”,但是当名字作为候选人被粉笔列出示众以后,荣誉感、好胜心以及一些模糊的欲望和桃红色的幻想统统就被勾引起来,大写的“正”字越多,这种渴望出人头地的潜意识和内在冲动就越强烈。
不出所料,票选结束,黑底白字,我是压倒性的第一。
大局似已尘埃落定。未曾说话、初次做同桌的红衣女生甩了我一如花笑靥。
心中激动地打着腹稿,我已准备好在就职演说时闪亮登场,同时不无遗憾地想,同桌的她,人还算白净漂亮,只可惜有点儿胖。
结果大出预料,班长位置旁落,“内阁”名单上,票数最高的我,继续当我的课代表。
班主任没有多作解释,她轻描淡写地说:“民主还得集中,选举结果仅供参考。”
肥皂泡破灭,选举就这样画上句号。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选举经历,由激动到灰心,时间很短。它的不成功刺痛了一个14岁少年敏感而脆弱的心,并留下永久的疤痕。它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后来很多年,经历过各式各样的选举,挫败感始终如影随形。
有时候不无遗憾地想,如果当年的选举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尊重选举结果,那就会在一个人、一群人,在整个高1980级2班学子心中,播下事关民主的种子,伴随青年的成长,在气候适宜的时候生根、发芽、开花,甚至结果。
璀璨的笑容不见了,同桌恢复了冷若冰霜的神情。整个高中阶段的两年间,我们之间自始至终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其三,1979年元旦,我班组织迎新年联欢晚会,糖果有限,但张灯结彩,群情振奋。班主任指派我扮演“新年老人”,戴一蓬她的巧手儿子用旧毛线做的大胡子,说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也算在众人面前出足风头,露了回脸,多少洗雪了落选的前耻。
说起来,“新年老人”貌似后来的圣诞老人。资本家小姐出身的老师貌似是懂的,只不过那个年代,乍暖还寒,没有人敢大张旗鼓地欢度西方节日。她只好洋为中用,土法上马,别出心裁地搞了场亦土亦洋的嘉年华。
其四,高二下学期,临近填写高考报名表,她看似不经意的点拨,使我剑走偏锋,最终考取北方的大学。
那天下雨。快下晚自习了,收拾书本的她忽然抬头,对我说:“你不是少数民族吗?”
还真是的。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如此这般填报,诸事果然顺遂。我在8月底打起背包,坐上北上的火车,和往事挥别。
三
大一回家,和同学相约看望彭老师,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黑衣服,厚眼镜,依旧是冷冷的样子。
一别遂成永久。
后来听说她退休回到省城,继承了落实政策的老房子,在家里办了补习班,辅导慕名而来的学生。不是为赚钱,而是教师职业的惯性使然。
若干年,她并不和独生子一家生活在一起,这也是人们叹息她死后几天才被人知晓的因由。
我于是有些伤感,讷讷的,不知道该和故人们再说些什么。
想来,老师是回天上的中学课堂了。我这篇作文,延续高中记忆—大河畔,教堂边,辛酸又快乐的往昔,压抑又意气风发的20世纪70年代末。
写好提交,指望着老师严厉地批改,想来,也还是超不过70分。
再见了,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