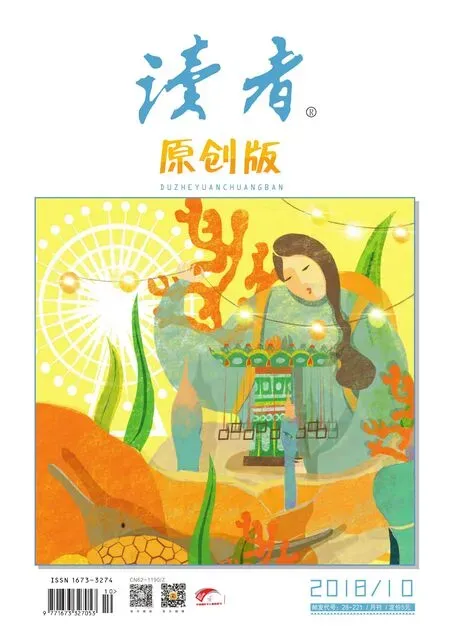我青春的故事
文|章 红

九月
火车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暮色刚刚降临,夜尚是柔和的夜。一场阵雨才过,空气湿润清新,愈发让人感受到城市初秋夜晚的明净。
在喧嚣的人流中,我迅速找到南京大学的接站牌,奋力挤了过去。
来自永宁镇的18岁女孩,穿着白色的确良长袖衬衣,领口各绣一朵小红花—那是我母亲的手艺。我母亲的一切手艺都是自学成才:刺绣、纳鞋底、裁剪衣服……我带着母亲绣的红花,雄心勃勃地来到这座大城市,寻求人生的发展和机遇。
“雄心勃勃”,这个词用在这儿再确切不过了。雄心使我无暇为自己的土气窘迫,我可能有点儿紧张,但绝不瑟缩。我走到那块牌子前,大声说:“我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个男生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让我跟他走,然后我就上了一辆大客车。
车内只有零星的几个人。车窗外是路灯、车灯照射下一掠而过的树木横斜的疏影—以后我会知道,这条宽敞的四车道叫中央路,两旁高大的行道树叫悬铃木。来自永宁镇的姑娘,表面安静,内心骚动,对车子将要开到的地方有一种急不可耐的期盼。这种期盼鼓舞着她,使得初次出远门的胆怯不再成为一个问题。道路向前延展,树木朝后退去,外面那个庞大世界的声音被车窗阻隔了,只有内心的声音放得无限大:南京,我来了!
元旦舞曲
宿舍是一幢年代久远的四层红砖楼房,在一个世纪前,这所大学尚是一所女子学院的时候就存在了,目前它叫8舍。斑驳的红漆地板被拖洗得发白,楼道宽阔阴暗,回旋着沁凉的微风。每上一层楼就有一面壁立的大镜子迎面而来,在每一个转侧之时瞥到镜中自己的身影,总有一点儿不知如何自处的感觉。
大学生活就这样不容分说地开始了。
第一天上课我就迟到了。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现在看简直是方寸之地,但其时在我眼中像迷宫一样庞大而复杂。课表上写着:新教402。“新教”是新教学楼的简称,我之前去过一次,模糊知道它的方向。我仓皇地奔跑,跑过主干道,跑过图书馆后面的小径,小径两旁有竹林与层叠的花草树木:一串红、大丽花、鸡冠花、夹竹桃、山毛榉、鸡爪槭……初秋的阳光尚带一丝威力,树叶与花朵的香味在阳光下发酵,我像一只急速扇动翅膀的眩晕的蜜蜂。
集体生活也令我恐慌。桌上摊着饭盆、书本、香脂、镜子、笔、零钱、饭票……床上永远乱成一团。我不会跳交谊舞,不会打牌,不会织手套、围巾、毛衣,不知道怎么和女生亲如姐妹,不知道怎么和男生逗趣聊天,不知道如何像个成年人一样和老师说话……18岁之前生活环境里所有的缺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没见过的世面、没关注过的知识、没掌握的技能,统统开始了它们的报复。
舞会越来越风行了,一到周末,大学生俱乐部光影流泻,乐声悠扬。那年元旦,学校在北园草坪举行盛大的露天舞会。我挤在人群中观看,就像观看一种异域风情,绝不认为和自己是有什么关系的。操场上一拨儿一拨儿的人潮,随着曼妙的乐曲舒缓起伏,青春的热烈气息与冬日枯草的芬芳味道混合在一起。冷月寒星缀在无垠的苍穹,好像只有地上热腾腾的人群是可以相互温暖的。
突然,在两首曲子的间歇,一个男生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了句什么。
最初我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对我说话(我前后左右都是人),没有反应。
他又说了一遍。这次我意识到他是在对我说话,可我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此时乐曲响起,我猜测他是不是嫌我站得靠前,影响别人跳舞了,就往后退了一步。
不料他跟进一步,继续对我说了句什么,我便又往后退了一步。
他仍然坚持着又说了一遍。我终于听清,他说的是:“我请你跳舞好吗?”
我的脸上“腾”地升起一股热气,脸红得估计不可收拾,慌乱无比地嗫嚅了一句:“可是我不会呀!”
我一边说一边迅速后退,挤出人群,逃之夭夭。
那个舞会的气息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真遗憾,我再也没有遇上过那么美好的舞会了。
转系
有一天早上起床,睡在我上铺的皓月把双腿悬在床沿上,笑嘻嘻地说:“你知道昨天睡着以后你说什么了吗?”
一颗心立刻悬了起来,跟着她的腿晃。我说什么了?
“猜猜看,很感人的。”她继续笑嘻嘻。
“是什么?”
“你说,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
一颗心放下了。然而才下眉头却又上心头,梦真是不留情面啊,让你逃不开自己。
高中三年,那是一种囚笼中的生活。做不完的题目、讲不完的试卷、上不完的自习,无穷无尽地重复,反复演练以保证熟能生巧。夜晚,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笔尖在试卷或作业本上沙沙跳跃,此外,教室里一切都是沉寂的。我想冲破这巨大的沉寂,如同一根草妄图顶开石头。
整件事情像一场被迫参加的长跑比赛,腿早就软了,肺部因为缺氧仿佛要爆炸了,终点—我考进了南京大学化学系。
然而,我发现我学不会高等数学—或许也不是真的学不会,而是丧失了学习的愿望与动力。高中三年彻底透支了学习兴趣,损伤了心性,我的内心干涸了。
我很痛苦。学不下去,又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梦中都在忏悔。18岁的我每天都在想: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去吗?永远没有机会去读想读的书,永远没有机会去尝试写作的梦想?进入大学的新鲜和喜悦未及体会,先感觉到了绝望。
有一次去别的寝室,见桌上摆了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忍不住就看起来。总觉得它是随时会被人拿走的,我的眼珠快速地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
一个女生说:“你看书的样子很贪婪。”
这种“贪婪”到底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写了一封几页纸的信,倾吐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中文系的向往。我把信递交给学校教务处,教务处转交中文系。在曾是赛珍珠别墅的中文系小楼里,老师对我进行了面试,接下来我就从化学系转到了中文系1985级—感谢那个黄金时代,那个时代以及我身处的南京大学都有一种开放宽容的风气,愿意为学生提供挖掘自我潜力的机会。
我转到中文系之后,分析化学专业的一位男生托人来询问转系过程,随即也转了过来,他就是作家李冯,曾为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与《十面埋伏》担任编剧。在南京大学中文系1985级,有天文系1983级转来的男生,后来在美国攻读了语言学博士,现在从事双语教育研究;有信息物理系转来的女生,现在是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与博导,同时也是汉语音韵学领域的专家。
中文系
到了中文系,我过上了日日可以读小说、看闲书的生活。宿舍六个女孩,根据个人看书的嗜好分为港台派、山药蛋派、先锋派……一个酷爱哲学的女生荣膺“穿裙子的尼采”称号,我呢,是名著派—我在宽仅90厘米的单人床内侧搁了一块木板,上面全是托尔斯泰、卢梭、狄更斯、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
我们还愿打愿挨地订了条室规:周末必须关在寝室写作,交出文章才许出门。我们很肉麻地把这写文章的事叫作“杜鹃啼血”,坐在宿舍里,像中学生写不出作文一样咬着笔杆,写几行字就瞥瞥别人,不时询问一下:“你‘啼’出来没有?”
文章写好后,大家共用两个笔名:一个是“贝禾”,是“稿费”两个字的偏旁;另一个是“火鸟”,是“烤鸭”两个字的偏旁—预备拿了稿费去吃烤鸭。
那是最愉悦、最轻松的一段读书生活。每过一段时间,寝室里便流传着新鲜的书单:《爱默生演讲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钱钟书的《管锥篇》、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马斯洛的《动机和人格》、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本书出来,大家就一哄而上,无论懂或不懂,在读书这件事上无人自甘人后。北园门口有家专门卖学术书籍的小书店,一到下课时分,狭长的店面便被挤得水泄不通。
黑板报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媒体。某个下晚自习的夜晚,路经黑板报,在那儿读到一首诗《想起爸爸》。“爸爸,是不是我们苦日子的船回来了”,如泣如诉,一颗心立刻被击中。我站在黑板报前,掏出纸笔,借着一丁点儿昏黄的灯光,用歪斜的笔迹一字一句抄下来。回到宿舍,我像献宝一样,朗读了这首诗。
接下来,宿舍里的每个人都把它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又抄在信纸上,附在家信中寄给父母。那是我所目睹的一次无意识的行为艺术,关于文学如何打动人心……
高云岭56号
有一天系里开大会,地点在第一食堂。辅导员宣布散会之前突然说:“我们年级有位同学以‘章郁’为笔名给杂志社投了一篇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杂志社的老师现在就在会场。请这位同学站起来一下,让我们大家为她鼓掌。”
我坐在人群中,突然觉得整个食堂大厅轰然作响,一种从天而降的声音,高亢而明亮。我的脸上也有灼烧之感,因为这难以置信的好运。
我坐着一动不动,知道命运开启了一道缝隙。
两个月前,我给《少年文艺》杂志寄去了一篇稿件。“南京高云岭56号”,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熟记这个地址,熟悉这本杂志。担心作品不能发表,没有勇气署真名,我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章郁。
一直没有消息,然后我就把它忘了。
“既然这位同学不好意思站起来,那请她散会以后留下来,杂志社的老师在会场后面等她。”人群向出口处拥去。
而我,向命运开启的那道缝隙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