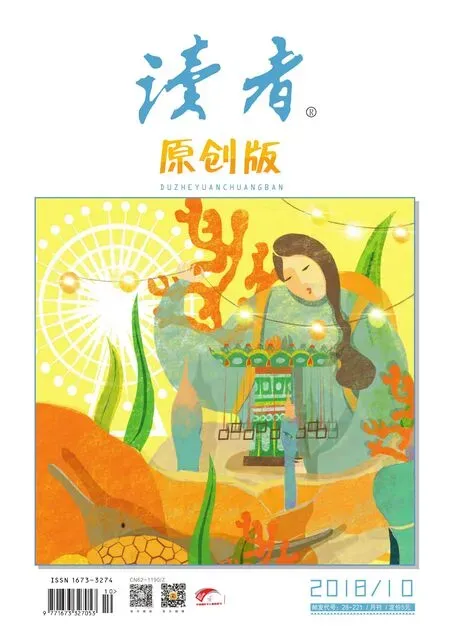黑白相片
文|南在南方

没在相片里看见过自个儿之前,我们从镜子里、水里看见过自个儿,甚至,我们还撒泡尿照过自己。“撒泡尿照照自己”,那是老师批评一个同学的话,这让我们好奇,七嘴八舌地说:“这是不可能的。”有高年级同学出主意:“在地上弄个坑,一人一泡尿就能照见了。”我们照他的话做,尿开始是浑浊的,等淀清时,我们蹲在坑边看见了自己,只是这个过程非常快,后蹲的同学眼睁睁看着自己不见了,像是让泥土给吸进去了。
可是看见相片里的自己,有点儿慌张,像是被什么抓住了,可自己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也许就像白胡子老头儿说的:“照相机捉人的魂儿呢。”
我们跟着那个挎着照相机的人,东一家西一家,听他说照相的好处:“老年人照张相放着,回头是个念想;小孩儿照张相,长大好看咧。”大多数人家会说一句:“唉,好是好,就是没钱给。”偶尔也有一家要照全家福的,大呼小叫,换衣裳,洗头发,搬小板凳……照相师傅正要按快门时,老头儿忽然站起来进屋,提着水烟袋出来,他觉着这样才有点儿意思,不然不晓得手放哪儿。
过半个月,照相师傅送相片来,又有一大群人围着看。如此这般,一来一围,来多了围多了,我们都想要照张相。
我真正照了一回相是几年后的事情,那时我叔浓丹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在此之前,在我们那个地方,他很有名。他会画画,你搬个板凳坐在他面前,他摊开速写本,拿出铅笔,不大一会儿,就把人像画出来了,鼻是鼻,眼是眼,真像!他背着相机照相,好像是件自然而然的事。
有一回,我看见他洗相片。黑洞洞的小房里亮着红灯,摆着各种瓶子,显影液、停显液、定影液,等等。胶卷里的人影出来了,朝相纸上印,看着熟悉的人浮在水中的纸上,我吓得叫出了声,这后来成了笑谈。
人像开始是棕黄色的,冲洗几遍就黑是黑、白是白了。这个印象挥之不去,后来写小说,说一个女孩儿单纯,就说她像海鸥125拍出来的。
没过多久,浓丹不照相了,他还是想画画。可乡下总会有照相的,有一年来了一个四川小伙儿,住在乡政府里,拿着名册给人照身份证相片。他穿着一件一身口袋的衣裳,看上去很特别,偶尔头发滑到额前,就那么一甩,头发就甩回去了,帅气。偶尔,他也会给年轻女子照生活照。他好像是用颜料还是胭脂,给照片上点儿色,涂上腮红,嘴巴也是红的,很好看。
三个月后他走了,我小时候的伙伴也不见了,两天之后才知道是跟他私奔了。那时我上高中,回家,她的母亲流着眼泪说她不见了。我劝她不要难过,过一时应该就有消息了。
她的消息来得有些迟。两年后,她回家了,抱了一个小娃娃。她说起四川:“格老子的,顿顿米饭,吃不完了就喂猪,龟儿子的。”我们听得有点儿发愣,觉得她掉进福窝里了。
那时,好像人们热衷于寄相片,山外的亲戚、本村参军的小伙儿,时不时会寄相片来,相片背后写几个字—“某某留念”。有一年,有人从外头带回一个相框,把家里的相片都放在相框里,挂在墙上。这事一下时兴起来,大家都找木匠做相框。
一晃,要高中毕业了,好像都有点儿半明半暗的惆怅。每个人都买了一个笔记本,请同学写赠言,还要索一张相片,差不多都是一寸的,贴在当页。
也要和要好的同学合个影。那个照相师傅耐得烦,我们要站在花前就站在花前照,要站在树下就站在树下照,这种相片一般洗两寸的。
接下来就要照合影了。老师坐在前排,校长坐中间,他们身前半蹲着一排女生。老师们身后站一排人,再往后放一排板凳,板凳上站一排人。相机架好,照相师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取景框,常常是站得太散,没框进去。“挤挤!”他喊着。
这张已经发黄的合影夹在一本书里,前些天,我翻出来看,我记得他们在教室里的座位,可有一半人的名字在我嘴边像是呼之欲出,却终是没有叫出来。这让人着急,立刻打电话问一位在老家的同学才弄明白。那时,我们清瘦,目光单纯,甚至羞怯,而这些现在都没有了。
我有一张十二三岁时照的相片,棱角分明,双肩上补着补丁。那时我能砍柴了,从山上扛着柴回家时磨破了衣服。那时衣裳的肩膀、膝盖、屁股的位置总要补补丁。
这张照片是叔叔浓丹照的,他一直留着,前几年找出来给我说:“是个纪念啊。”我最开始摆弄文字时喜欢写悲剧,浓丹先生看了说:“这么好的姑娘,你写死一个,又写死一个,总得留一个给自个儿当媳妇吧?”言犹在耳,他去年突然去世,已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