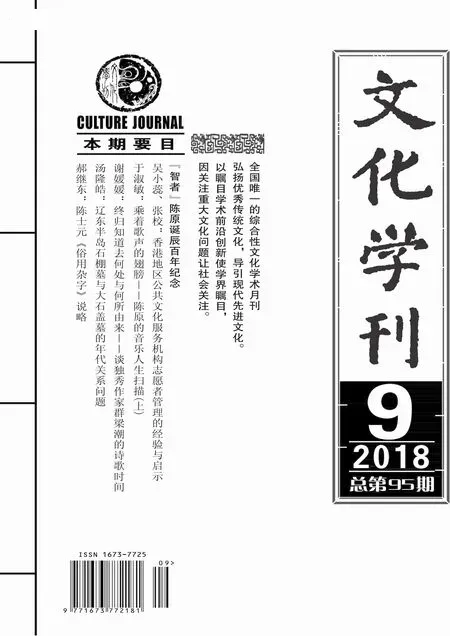渔樵寄此身:“我是识字耕田夫”
艾
今年,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也是当代史上可视为“文革”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红卫兵”运动尾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五十周年。
具有一定历史知识者,自然因“戊戌变法”而深入思索国运大事,庆贺“改革开放”之成就。同时,作为如今已年届“古稀”的当年的“知识青年”一代,进入了喜欢怀旧的迟暮之年,也会不由地感慨那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履历。相去一百二十年前不曾经历的“戊戌变法”,尽管属于国家大事,但不是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沉重,而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历史知识。但发生于当年青春岁月亲历的“知青”遭遇,却如近在眼前、历历在目,酸甜苦辣,波及几代人的社会记忆,难以从心头拂之而去——那是一代人的青春的“非常岁月”。甚至于,把知青经历同参军当兵并列,将之列进了时下坊间流行民谣“四大铁”——“一块儿吃过糠(共度60年困苦时光),一块儿同过窗(同学),一块儿扛过枪(当兵的战友),一块儿下过乡(同一个青年点的知青)”。

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我是识字耕田夫》
我曾经常自道,“本人农民出身”,说不清是自诩还是自嘲。城里长大的孩子,“文革”中学《毛选》,对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不甚了了。“插队”后,所见所闻感悟颇深。时间稍长一些,重温伟大领袖这个伟大教导,再猛然想起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来的呀,不觉懵懂:到底要谁教育谁呀?悖论也。然而却没处求解,亦不敢打问。时间再长些,则愈发茫然矣。
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
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慈姥岩前自唤渡,青衣江畔人争扶。
今年蚕市数州集,中有遗民怀裤襦。邑中之黔相指似,白髯红带老不臞。
我欲西归卜邻舍,隔墙拊掌容歌呼。不学山王乘驷马,回头空指黄公垆。
苏轼的诗句“我是识字耕田夫”,往往被解读为苏轼具有亲民爱民思想情感的体现,认为在其奏议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带有较为鲜明的平民色彩。
此外,历代还有不少关乎“识字耕田夫”的诗章。例如,“我亦本是耕田夫,仅能识字勤须臾”(宋王庭圭《次韵李教授闵雨》),“催儿挂豆更栽芋,坡老自谓我亦识字耕田夫”(宋徐照《釜下吟》),“湖外家家粳稻足,况有鱼蚬兼茭菰。长年饱饭一无事,不愧识字耕田夫”(清杭世骏《胡三应瑞爱皋亭山水有结庐之原诗以坚之》其二),“辱公期望恐难称,大愧识字耕田夫”(清揆叙《宋中丞牧仲以宋本施注苏诗见惠赋此奉谢》),等等。
世人往往习惯于用理想化、道德化乃至意识形态化的视阈绑架文学家,更要换位思考他首先更是同样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啊!还原其一生坎坷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更让人觉得是其对人生的一种自叹与感慨。苏轼自幼的理想与期待会是甘愿当个“耕田夫”么?若无特定的无奈与失望,陶渊明甘于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去吗?既如此,当初还何必逃离乡野呢?作为读者本身,这也会是君之远大理想或期待吗?原诗题为《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乐之。既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学土秦少游贤良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华》,其“且作诗为戏”似乎亦不难可悟出点儿别样味道来。
默数金陵友,在者犹四人。纠曹今别乘,法官驾朱轮。
千钟已弗暨,一念还酸辛。况我病所缠,渔樵寄此身”。
输子曳朱绂,斑衣奉慈亲。(宋刘宰《寄同年朱景渊通判八首》其二)
南宋一代名臣刘宰,因其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一度隐居乡里长达三十年。“况我病所缠,渔樵寄此身”,抒发的显为困厄失落情怀。
相对于半个世纪前的“识字耕田夫”,陶潜、苏轼、刘宰和王庭圭等,毕竟都是官场失意的士大夫呀。正该是求学读书年龄而无书可读就被整体抛进山野的“知青”们,算什么呢?所谓“知识青年”,却并非知识分子,更难以确定其社会身份。“我本耕田夫,识字略可数”(南宋方岳《上鹤山作图书所扁》),真好像是写给初中尚未毕业,尤其是那些刚上初中就赶上了“文革”随即转身为“知青”者的集体写生画像。于是乎,“知青”成了一代人的集体社会称谓。
全国形成了一个分散各地的,苦闷、压抑、茫然、彷徨的,一个大部分并不具备真正“知识分子”身份的名曰“知青”命运共同体。“知青”仅仅是其临时的政治身份。“他们更看重个人命运的不公和悲剧性,更看重历史的荒诞与不可理喻性。他们还有青年的锐气和朝气,还有燃烧的热情,将苦难揉碎,再化为想象力表现在文学之中。……他们身上由‘文革’激发出来的自我意识,在‘文革’后通过文学得到了另外一种方式的体现,这大摡是谁也未曾预料到的”(李辉《敬畏真实》)。此即以当年“手钞本”为先导的一时间喷涌而出的“知青文学”潮。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以“伤痕”文学为发端逐渐形成极具时代特点的“知青文学”潮,涌现了一批有过知青经历而创作“知青”题材小说的作家。除了所占比例不多的少数肯定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作品外,大都以揭示“文革”罪行、知青的悲惨遭遇和乡村的阴暗面为主题,以描写苦难的历程、进行血泪的控诉为特征。直至90年代,在继续出版知青题材长篇小说外,还涌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和知青回忆。
作为“知青文学”作者的一些“知青作家”的创作准备及其书写,几乎就是一个痛苦乃至惊心动魄的反思过程。此间,以《厚土》等优秀作品在文坛脱颖而出的作家李锐,被评论誉为“少见的具有思想家素质的作家”,对“知青问题”“知青文化”的反思尤显敏锐、深刻。例如,当他一口气读完一本有关“先进知青典型的《一代新人》时”,不由得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也为自己深深地震动了:“那是一个只要精神,不要无知的狂妄的时代;那真是一个把谎言奉为真理的荒谬的时代;那真是一座用无数人的无数谎言搭建起来的世界最高峰”。针对有的人把“知青”命运与世代为农的村民相比,说什么“你们受的这一点苦算的了什么”?他认为这是个不足取的类比,“是一个偷换了的命题,是谁说让农民世世代代地绑在土地上”。他多次驳斥“知青运动”成就了“知青作家”之说。“不错,‘文革’和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使一些后来成为作家的知青刻骨铭心地体验了生活,体验了永生难忘的生命过程。但那并非是特别为了未来的作家而设立的必修课,那是一场灾难一场全民族八亿人的血泪交织的浩劫”。“拿八亿人的灾难,拿上千万知青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来换几个作家不是太奢侈,太冷酷,也太可怕了吗?”“从狂热到苦难的剧烈的热胀冷缩粉碎了整整一代人的信仰,坐在精神的废墟之间,面对命运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拿出来的不是理性而是求生的欲望,每个人可以依靠的不是勇气而是刻骨铭心的悲哀”。对那些自感“青春无悔”者,“还要把沉沦当做浪漫和理想来炫耀”的沉沦者,他感到“一言难尽的悲哀”[注]引文均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锐散文》。。毫无疑问,“知青文学”是社会记忆中的集体控诉,深深的历史“伤痕”。畸形的知青文化是尚未远去的社会记忆,历史的的创伤。
想当年,紧跟伟大领袖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曾经何等“风光”。如今,竟沦落为不伦不类的群体,能不“一念还酸辛”,只是心里想到不敢出口。“况我所缠”之病,在于前途渺茫,茫然也。虽也有人高唱“扎根农村六十年”,绝非大多数的心声,哪个甘愿此生“渔樵寄此身”沦为“识字耕田夫”耶?从“红卫兵”到“知青”,违背党心、民心,不得人心,一场畸形的政治运动,塑造了影响数代人的畸形文化。要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矫正、肃清这个畸形文化的影响,仍然是个十分艰难而又痛苦的理性反省过程。
在其所经受的教育背景下,他们曾经以当年国统区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憧憬,义无反顾地充当了“以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毛主席”的“红卫兵”,随即又以跟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革命豪情 “上山下乡干革命”。不曾想,到头来竟是如此——葬送了青春不算,还需要替历史罪过忏悔、赎罪。——这个世界怎么了?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被愚弄被侵害被侮辱的群体,一个坚韧地承受了历史性政治罪过的群体。国之殇,民之殃也!
“知青问题”与“知青文化”是特定年代直接源出于罪恶的“文革”的重大社会问题。多年前,大约“知青”运动发生三十年之际,曾撰一篇短文《青春之祭:“知青岁月”诗痕》。又过了二十年,已经渐渐老去的这代人,重温半个世纪前的这个刻骨铭心的社会记忆,无啻再次为“文革”开个追悼会。“追”者,再次提醒世人要不懈地清除孳生那种罪恶的文化垃圾;“悼”者,则以历史定论缅怀那些为翻过这历史一页而献身的英烈和先贤。“俱往矣”,所幸那个可诅咒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未来不会为之提供重演的机遇。正视历史向未来,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还是刘禹锡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写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吟之,似可藉以化解、平复五十年后此际的心绪,聊以长精神。这两句诗,也曾是“文革”时期的报刊社论和“派仗”斗嘴言语的时髦名句。半个世纪之后重吟,语境和寓意回异矣。
戊戌七夕于邨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