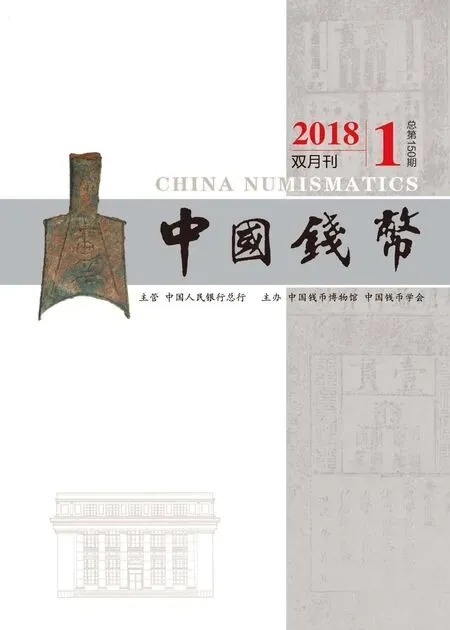从钱币资料看印塞王国与后印希王国对罽宾统治的交替
杨富学 (敦煌研究院) 袁炜 (贵州省博物馆)
一 印塞与后印希王国之存废及其年代学问题
从公元前180年开始,印度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建立了诸多希腊化国家,史称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 Kingdom,简称印希王国),有时又称希腊—印度王国。约公元前130年以降,塞种逐渐南侵诸印希王国,约公元前125年至公元前100年,塞种首领毛乌斯(Maues)以罽宾为中心建立了印度—塞种王国(Indo-Scythian,简称印塞王国)。
关于印塞王朝建立的时间,学界见仁见智,但能够确定的只有公元前130年月氏到达大夏,迫使塞种南迁,嗣后建立了印塞王朝。所以对印塞王朝建立的时间从前129年到前80年的都有。近二十年对这方面研究学者主要有余太山、R. C. Senior、Bopearachchi和Pieper诸位先生。余太山主张印塞王朝建立于公元前129年之后[1],R. C. Senior主张立国于公元前125年左右[2],而Bopearachchi和Pieper则主张于公元前90年建立[3]。今按,《汉书·西域传》言:“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4]可见在汉武帝通使罽宾时,其王即为乌头劳,而非印塞王朝的建立者毛乌斯。故毛乌斯统治罽宾的下限要早于汉武帝去世的公元前87年。此外,呾叉始罗帕提卡铜盘铭文上用佉卢文记载 20 20 20 10 4 4 mah ā rā yasa mah āṃtasa Mogasa(78 年 大王 伟大的 毛乌斯)[5],虽说此纪年之具体年份难以坐实,但虑及“78年”必须落在公元前129年之后和公元前87年之前这个时间段内。当时西北印度唯一适合的纪元就是始于公元前186/185年的希腊纪元了,依此纪元,帕提卡铜盘年代在公元前108/107年,可见,彼时毛乌斯已统治呾叉始罗,故Bopearachchi所谓印塞王朝于公元前90年建立之说明显未安。故此,笔者综合余太山和R. C. Senior之说,再考虑到汉武帝在位后期,罽宾君主已是乌头劳,进而推定毛乌斯统治罽宾的时间当在公元前125年至公元前100年左右。
公元前140年左右,希腊人以阿富汗为中心所建立的大夏国(Bactria)遭到塞种的入侵而灭亡[6]。公元前130年,月氏人又南下大夏,逼迫曾击灭大夏的塞种继续南下。虽然印度西北部和北部地区的希腊诸王国因兴都库什山之阻隔而得以幸免,但与希腊、罗马世界的联系几乎断绝,故希腊、罗马文献对印度的这些希腊王国缺乏记载,致使现代学者对印希王国及其后印度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历史的重构不得不有赖于考古发掘和钱币资料。作为印希王国、印塞王国、后印希王国的组成部分,罽宾的情况亦概莫能外。有幸的是,《汉书·西域传》对罽宾有记载,不惟记其物产民俗、钱币铸造和政权更替,而且特别关注该政权与西汉王朝之关系。这些记载尽管很简略,但为印塞王国、后印希王国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关键性的时间坐标。
19世纪以来,随着钱币学、碑铭学的开展,西方学者以之为据对公元前1世纪之印塞王国史进行了重构,多将《汉书》所记载的罽宾与印塞王国(Indo-Scythian)勘同。比较典型的为塔恩(W. W. Tarn)的说法,认为罽宾君主乌头劳乃希腊文αδελφον一词的对译,从而认定张骞所言有误,误将印塞王国君主斯巴里里斯(Spaliris)及其称号中的αδελφον(意为“国王的兄弟”)一词当作国王姓名了。此外,将罽宾君主阴末赴(即Hippostratus,赫帕斯特拉托斯,考证详后)视作希腊文Ἑρμαῖον一词的对译,将阴末赴比定为后印希王国君主赫马攸斯(Hermaeus),进而推论,在公元前49年左右,斯巴里里斯之子斯巴拉加达莫斯(Spalagadames)被赫马攸斯所杀,赫马攸斯成为罽宾君主。约在公元前30年,斯巴里里斯之弟斯巴里里西斯(Spalirises)又推翻了赫马攸斯,继任罽宾君主[7]。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后印希王国”,乃指希腊人灭印塞王国而重建的最后一个印度—希腊王国(Late Indo-Greek)。为别于印塞王国之前所存在的诸多印度—希腊国家,故称“后印希王国”。
随着印塞王国、后印希王国年代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汉书》所载罽宾与印塞王国的勘同是存在问题的[8]。嗣后,有学者对此说予以修正,认为乌头劳并非希腊文αδελφον的对译,而是印塞国主阿泽里西斯(希腊文Αζιλιεου,佉卢文Ayilishasa)的对译。这种说法认为,西汉元帝(前49年~前33年)时,赫马攸斯弑阿泽里西斯之子阿泽斯二世(Azes II)而成为罽宾君主,并于西汉成帝(前32年~前7年)时与贵霜君主丘就却结盟,联合铸币[9]。但这些说法仍然与印塞王国年代学相矛盾。
二 印塞王国统治罽宾之时代
有鉴于上述诸多争论,笔者试以钱币学为主要依据,结合汉史的记载,以及碑铭题刻、佉卢文文献等,进一步探讨印塞王国、后印希王国对罽宾的交替统治及其大致年代。
《汉书·西域传》言:“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10]其中,前二者转述自《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第一次西使见闻[11],事在公元前128年之前,而“塞王南君罽宾”之谓却不见于《史记》,仅在公元前1世纪初左右罽宾一带的钱币和出土铭文中有所反映。
据钱币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斯时罽宾一带出现了一位非希腊名字的塞种君主毛乌斯(Maues)[12]。此人称号前后有别,在早期钱币上称作“大王”(希腊文βασιλεως,佉卢文mahārā ja)。此后,又从帕提亚王国米特拉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处借用了一个更为显赫的称号—“王中之王”[13]。“王中之王”称号希腊文写作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佉卢文作rā jatirāja,系对国王的称呼,“意为一国之内王者中力量最大的一个,与疆土面积大小无关”[14]。此外,在呾叉始罗帕提卡铜盘铭文上用佉卢文记载 20 20 20 10 4 4 mahārāyasa mahāṃtasa Mogasa(78年 大王 伟大的 毛乌斯)[15],也可印证《汉书·西域传》所言“塞王南君罽宾”乃指塞种君主毛乌斯占领罽宾事。就钱币学证据言之,毛乌斯占领罽宾后,与希腊保持着密切联系,一者毛乌斯与希腊公主Machene联姻,并发行铸有两人肖像的钱币[16];二者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os)发行的钱币,其正面希腊文铭文为ΒΑΣΙΛΕΩΣ ΑΝΙΚΗΤΟY ΑΡΤΕΜΙΔΩΡΟY(王 无敌的 阿特米多鲁斯),背面佉卢文为 rā jatirā jasa Moasa putrasa ca Artemidorasa(王中之王 毛乌斯 儿子 阿特米多鲁斯)[17]。由以上两点观之,塞王毛乌斯与希腊的关系非同一般,尤有进者,其子甚至还取了希腊式的名字。
从钱币学证据看,继毛乌斯之后统治呾叉始罗和犍陀罗等地的是阿波罗多托斯二世(希腊文Απολλοδτου,佉卢文Apaladatasa)[18]。《汉书·西域传》言:“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19]罽宾国王乌头劳之名当来自音译。“乌头劳”之上古汉语拟音,依高本汉作⋆?o-d’ǝu-lâu(61a+118e+1135a)[20],依王力作[ɑ-do-lau][21],其读音与阿波罗多托斯二世(Apollodotus II)名字的前三个音节极为相近,故《汉书》罽宾王乌头劳当是阿波罗多托斯二世的缩译。值得注意的是,除《汉书》载及乌头劳外,成书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古罗马游记《红海航行记》也述及乌头劳[22]。《红海航行记》记载:
由于他的远征,有希腊铭文的古代钱币依旧在Barugaza流通,这些钱币上刻印着阿波罗多托斯和米兰德的名号,他们在亚历山大之后统治北方诸省[23]。
今按,在印希王国和印塞王国的历史中,有两位君主名为阿波罗多托斯(Apollodotus),但从印度Gogha地区出土的公元一世纪钱币窖藏来看,大量的阿波罗多托斯二世(乌头劳)、少量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银币与大量的公元一世纪西部州君主纳哈帕纳银币混杂出土,这与《红海航行记》记载公元一世纪Barugaza流通阿波罗多托斯钱币相吻合[24]。故《红海航行记》所述阿波罗多托斯当为乌头劳,与《汉书·西域传》所载罽宾国王乌头劳为同一人。乌头劳在位时代,钱币学者推断在约公元前85年至公元前65年之间[25]。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武帝始通罽宾……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乌头劳登基时间抑或在公元前87年之前不久,比钱币学者推断的时间稍早。对于乌头劳的族属,虽说其姓名是以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来命名的,但钱币学证据却显示为塞种[26]。
钱币学证据还表明,乌头劳之继任者狄俄尼索斯也曾发行钱币,正面希腊铭文ΒΑΣΙΛΕΩΣ ΣΩΤΗΡΟΣ ΔΙΟΝYΣΙΟY(王 救世主 狄俄尼索斯),背面佉卢文铭文Mahārājasa tratarasa Diuanisiyasa(大王 救世主 狄俄尼索斯)[27],足见狄俄尼索斯业已称王,只是其钱币的出土数量和种类都很稀少。推而论之,狄俄尼索斯在位时间应不长。《汉书·西域传》言:“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欲复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28]是见,乌头劳之子在成为罽宾王不久便被文忠和阴末赴所杀。
三 后印希王国对罽宾的短暂统治与印塞王国的复国
《汉书·西域传》言:“(文忠)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29]“容屈”一词已有学者考证为“希腊的”之意,如是,则“容屈王子”即“希腊王子”也[30]。“阴末赴”之上古构音,依高本汉作⋆?iǝm-muât-p’iu(651y+277a+1210i)[31],依王力作 [ǐ am-muǎt-pʻǐwōk][32],可与后印希王国君主赫帕斯特拉托斯(Hippostratus)勘同。《汉书·西域传》言:“(罽宾)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33]这一记载似乎将钱币的正背面说反了,因为,按照中亚钱币传统,人像一般在正面而非幕面(背面),而马、驼或其他动物一般在背面而非正面(文面)[34]。故书此存疑。考虑到阴末赴是西汉“授印绶”的罽宾王,故《汉书·西域传》对罽宾钱币的描述当以阴末赴发行的为准。在公元前1世纪的罽宾,仅有赫帕斯特拉托斯发行过一面为君主头像,另一面为乘马骑士图的钱币(如图)[35]。
是知,容屈王子阴末赴本为希腊王子,后为罽宾王(印希国君),亦即赫帕斯特拉托斯(以下统称阴末赴)是也。至于阴末赴在位的年代,西方学者以其所辖呾叉始罗城被塞种国王阿泽斯攻占暨阿泽斯纪元始于公元前58/57年这两个因素推断,阴末赴在位末代为公元前57年[37]。今按,《汉书·西域传》言:“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使以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38]西汉孝元帝即位于公元前49年,至迟是年阴末赴尚继续统治着以呾叉始罗为中心的罽宾地区。是故,阿泽斯于公元前58/57年即位并创立所谓的“阿泽斯纪元”之说大体上说是可以信从的。阿泽斯于公元前49年之后才攻占呾叉始罗取代阴末赴。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德国学者所言阿泽斯纪元并非始于公元前58/57年,而是公元前47/46年。阿泽斯纪元是安息纪元的延续,阿泽斯纪元元年乃安息纪元201年[39]。果如是,则阴末赴与西汉使者失和应在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46年之间。
《汉书·西域传》载:
成帝时,[罽宾]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40]
此事在《资治通鉴》中被系于汉成帝和平四年(前25年)[41]。由“前罽宾王阴末赴”一语可见,在公元前25年时,罽宾国王已非阴末赴。由钱币学提供的资料观之,继阴末赴之后统治呾叉始罗者乃塞种阿泽斯;继阿泽斯之后又由塞种Vijayamitrasa统治。阿泽斯在位年代可通过Rukhuna圣物盒上的佉卢文铭文推定。铭文云:
Apraca王Vijayamitrasa在位的第27年,阿泽斯纪元73年,希腊纪元201年,在Sravana月8日,Rukhuṇa建立了这个塔,Apraca王的妻子,Apraca王Vijayamitrasa,Iṃdravarmeṇa指挥官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儿子。[42]

印塞王国赫帕斯特拉托斯钱币[36]
若阿泽斯纪元始于公元前58/57年,那么,阿泽斯纪元73年则相当于公元15年,相应地,Vijayamitrasa接替阿泽斯之时即应在公元前12年。是知,公元前25年重新派遣使者入汉朝贡谢罪的罽宾王应为阿泽斯。
通过《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到,自武帝至成帝,西汉与罽宾使臣往来密切,可借由悬泉汉简而得到佐证,其中有两条简牍记录了汉使报送罽宾使臣:
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竝、叶贺所送莎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
以给都吏董卿所送罽宾使者。(Ⅱ90DXT0213②:37)
此二简的时代当在西汉宣帝至成帝之间[43],大体相当于印塞王国乌头劳、狄俄尼索斯和后印希王国阴末赴统治期间。
四 结论
通过以上论证,可以大致勾勒出公元前2世纪以降罽宾地区在印塞王国、后印希王国统治时期其王位的更迭及其与西汉关系的轮廓。公元前125年至公元前100年左右,塞王毛乌斯南君罽宾,建立印塞王国。大约在公元前87年之前不久,乌头劳继任罽宾王(印塞国王),与西汉通使,但经常劫杀西汉使臣。乌头劳死后,其子狄俄尼索斯继位,但不久便被西汉使臣文忠和希腊王子阴末赴合谋攻杀,印塞王朝之王位被后印希王国阴末赴取代。公元前49年之后,阴末赴与西汉恶交,其位又被塞种阿泽斯夺回,印塞王朝复国。阿泽斯在公元前25年试图恢复与西汉的外交关系,但被西汉成帝拒绝。
概而言之,公元前2世纪以降,罽宾地区的统治次第可概括为:印希王国→印塞王国(毛乌斯建)→后印希王国(阴末赴建)→印塞王国(阿泽斯复建)。
注释:
[1]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
[2]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V,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6, p xlii.
[3] O. Bopearachchi &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p. 208.
[4][19][33]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5页。
[5][15][42]S. Baums, Catalog and Revised Texts and Translations of Gandharan Reliquary Inscriptions, Gandharan Buddhist Reliquaries, Gandharan Studies, Vol. 1, Seattle, 2012, pp. 200–251.
[6] H. L. Jones,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Book 11,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8, p. 261([古 希 腊 ]斯特拉博著,李铁匠译:《地理学》第11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761页);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283-287;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 141.
[7]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339-350.
[8] 杨巨平:《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8~10页。
[9] 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30页。
[10] 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4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1、3162页。
[12] [意]朱莉阿诺:《西北印度地区希腊至前贵霜时代的钱币》,[意]卡列宁、菲利真齐、奥里威利编著,魏正中、王倩编译:《犍陀罗艺术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13] John Marshall, Taxila-An 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Vol. I: Structural Remains,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 1975, p. 46([英]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14] Kazuo Enoki, On the so-called Sino-Kharosthi Coins, East and West 15, 1965, p. 256([日]榎一雄著,杨富学、樊丽沙译:《论所谓的“汉佉二体钱”》,《丝绸之路民族货币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
[16]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I,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1, p. 2.
[17] O. Bopearachchi, Was Indo-Greek Artemidoros the son of Indo-Scythian Maues? Amluk Dara Hoard revisited,Νομισματικα Χρονικα 2, 1998, p. 28.
[18] O. Bopearachchi &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p. 208-212, 251.
[20] 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kholm, 1964, pp. 36, 50, 292([瑞典]高本汉著,潘悟云等译:《汉文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34、59、500页)。
[21]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1、176、157页。
[22] J. Cribb,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Periplus', D. W. MacDowall & S. Sharma & S. Garg (eds.),Indian Numismatics,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Essays in Honour of Dr P. L. Gupta,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1992, pp. 131-145.
[23] W. Vincent, The Voyage of Nearchus, and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09, p. 102.
[24] John S. Deyell, Indo-Greek and Ksaharata coins from the Gujarat seacoast,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144,1984, pp. 115-127.
[25][26]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Vol. IV,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6, p. xxxix.
[27] O. Bopearachchi &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 254.
[28][29]《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5、3886页。
[30]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31] 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kholm, 1964, pp. 173, 87, 311([瑞典]高本汉著,潘悟云等译:《汉文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284、124、535页)。
[32]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4、26、110页。
[34] 夏鼐:《“和田马钱”考》,《文物》1962年7~8期合刊,第61页;李铁生:《古中亚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35] 袁炜:《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所见西域金银币考》,李小萍主编:《金银货币与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店,2017年,第38页。
[36] 转引自O. Bopearachchi & W. Pieper,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repols, 1998, pl. 48, fi gs. 215-216.
[37] M. Alram, Coinage and History: Form the Greco-Bactrian Kings to the Kushan,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2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页。
[38]《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6页。
[39] H. Falk & Ch. Bennett, Macedonian Intercalary Months and the Era of Azes, Acta Orientalia 70, 2009, p. 211;[德]Harry Falk撰,刘震译:《古代印度的纪元概念》,许全胜、刘震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
[40]《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6~3887页。
[41]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30成帝和平四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978、979页。
[43]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7~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