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觀世音經》的源流和傳承
——先行研究與現存文本綜述〔1 〕
池麗梅
提起漢傳佛典中最爲短小的佛經,大多數人都會聯想到玄奘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下文簡稱《心經》)。事實上,還有另外一部更爲傳奇的佛典,其早期版本僅由249個漢字組成,較《心經》傳統版本的262字還要少13個字。這部佛典,就是誕生於中國北朝時代並且在民間生生不息延傳至今的《高王觀世音經》(該經别名衆多,下文採用其俗稱《高王經》)。雖説該經的普及程度遠遠不及《心經》或《法華經·普門品》(俗稱《觀音經》)等衆人耳熟能詳的佛經,但是作爲一部中國的草根佛經,《高王經》不但富有傳奇色彩,並且和前兩部佛教“真經”也不無關聯。
首先,《高王經》是以《觀音經》及觀音信仰在北朝的普及興盛爲時代和宗教背景應運而生的中國撰述經典,换句話説也就是一部佛教的疑僞經典。在北朝的華北地區,曾經湧現衆多的“草根經典”用於簡潔平易地闡釋《觀音經》,都自命爲“佛説觀世音經”;遺憾的是,除《高王經》以外,幾乎失傳殆盡。而《高王經》能够得以傳世,除了該經的實踐特色以外還有政治因素的影響。《高王經》中的“高王”,就是東魏時代不可一世的權臣武將高歡。《高王經》以高歡冠稱經名,顯示了高歡對於該經的弘傳和普及的助力和影響。本爲衆中之一的“佛説觀世音經”,由於高歡的政治勢力的介入,開始冠以“高王”之稱(即《高王觀世音經》,或簡稱《高王經》),並在同類經典中鶴立雞群,佔據了流通與傳承的絶對優勢。而《高王經》的流傳和普及,反之也賦予了高歡統治勢力以神聖性,有效樹立了這位權臣在民間,尤其是河北一帶的威望。當權者利用佛教來鞏固强化政治統治的現象並不少見,但是以人名來冠稱佛經實爲罕見。在這個意義上,《高王經》堪稱研究中古佛教與政治關係的另一絶佳事例。
另外,自武周時代至唐開元年間,《高王經》經歷過短暫的入藏。作爲一部“草根經典”,能够證明《高王經》來歷的,唯有一段離奇的神僧夢授的傳説。也就是説,和大部分傳世僞經不同,《高王經》從未試圖僞裝成西天佛説的“真經”。但是,就在《高王經》華麗變身成爲入藏典籍之際,還是在形式上經歷了一定程度的包裝。並且,當時用於打造《高王經》的參考模式,就是《心經》這塊極具權威的模板。可以説,無論是《高王經》的起源還是後來的歷史演變,都爲我們思考中國佛教僞經的形成與接受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關於《高王經》的研究,日本學者的起步是最早的,並且每一次都源於新資料的發現。例如,塚本善隆於1934年訪華考察房山雲居寺時,首次注意到雷音洞的石刻《大王觀世音經》(即《高王經》)。時至20世紀60年代,在整理出口常順藏吐魯番本時,其中的《折刀經》寫本(亦即《高王經》)再次引起日本學者的關注。此後至今的半個世紀左右,在日本、中國(包括臺灣地區)爲主的佛教史學、佛教文獻學、佛教美術史學學者的共同推動之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衆多的成果。在文本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先學們已經發掘了至少14種北朝隋唐五代的文本,包括5種造像經碑本、4種石刻經本、5種敦煌吐魯番出土寫本。另外,還有幾種宋代以後的寫本、刊本也開始逐步應用於相關研究。在這些堅實的文獻學基礎之上,學者們在《高王經》的經名來歷、文本的譜系、信仰源流這三個方面,都展示了全方位的拓寬和深入。
雖然《高王經》的文本發掘和研究已有長年深厚的積累,但是一直没有相關主題的專著付梓。因此,對全球範圍内散藏的各種形態的已知文本,以及各國學者先後或同步展開的學術積累,尚未有嚴密的綜合性整理和評述。爲了更好地繼承多年來先學們辛勤開創的基礎,筆者在此將以先行研究的回顧和現存文本的概觀爲敍述脈絡,大致按照著手該課題的人物及論著發表年代的先後順序,勾勒《高王經》相關研究至今以來的發展過程,最後指出當前殘留的主要課題,爲日後《高王經》等中國撰述經類的綜合性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略盡綿力。
一、 主要先行研究的回顧
(一) 草創期的《高王經》研究——三位日本學者的奠基
1. 塚本善隆與房山雷音洞刻《大王觀世音經》
1934年夏末秋初,塚本善隆一行六位日本學者訪華考察房山雲居寺,翌年三月即以《東方學報·京都第五册副刊》的形式出版了專題研究《房山雲居寺研究》(1)塚本善隆、長廣敏雄等著《房山雲居寺研究》,汪帥東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其中,由塚本善隆執筆的《石經山雲居寺與石刻大藏經》專設一章討論了雷音洞中的石經(並附有拓本圖版),其中之一就是《大王觀世音經》(《石經山雲居寺與石刻大藏經》圖版八B)。塚本先生公開了該石經的録文,確認《大王觀世音經》就是《高王經》。並且以經録所載《高王經》應驗記爲綫索,指出東魏時代的盧景裕等范陽盧氏,及其與菩提流支以及《高王經》的關聯。最後,塚本先生注意到作爲一部中國撰述的僞經,《高王經》能受到開鑿石經的靜琬的重視而被刻在雷音洞中的事實,指出了疑僞經典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價值和意義。遺憾的是,塚本先生對房山雷音洞石刻《高王經》的研究並没有引起學界的重視,後來的《高王經》研究者幾乎無人提及先生的貢獻。筆者注意到塚本先生的相關研究,乃是承蒙中國中山大學哲學系王磊博士的提醒與指教。
2. 牧田諦亮及其先驅之作《高王觀世音經的出現》
《高王經》研究的另一位先驅,是爲佛教史學以及佛教疑僞經典的研究留下了不可磨滅功績的日本學者牧田諦亮。牧田先生繼1964年發表的《中国仏教における疑經研究序説——敦煌出土疑經類をめぐって》(2)牧田諦亮《中国仏教における疑経研究序説——敦煌出土疑経類をめぐって》,《東方學報》第35號,1964年,383—384頁。,1966年又在《佛敎史學》第12卷第3號首次登載了《高王觀世音經的成立》一文;時至1970年,先生又在其專著《六朝古逸觀世音靈驗記の研究》(京都 : 平樂寺書店,1970年)當中,收録了上述期刊論文的增補修訂版《高王觀世音經の出現——北朝佛敎の一斷面》(157—178頁)。幾年之後,牧田先生關於疑僞經典的代表作《疑經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年)上梓問世,其中收録的《高王觀世音經の出現》,去除了前著中的副標題,内文維持了前著的原貌。2014年,由牧田諦亮著作集編集委員會編集的《牧田諦亮著作集》第1卷《疑經研究》(京都 : 臨川書店,2014年),其中收録的《高王觀世音經の出現》(305—325頁)也没有明顯的改訂。
牧田先生對於《高王經》的關注,一方面是他關注觀音應驗記、觀音相關疑僞經典等反映觀音信仰發展的各類文獻的結果,更爲直接的契機應該在於當時尚屬罕見的敦煌吐魯番遺書中的疑僞經文本的出現。在《高王觀世音經の出現》中,牧田先生提到了法藏敦煌遺書P.3920,但他更爲直接的研究對象是流傳到日本的出口常順藏吐魯番寫本“佛説觀世音折刀除罪經”(推定爲8世紀鈔本斷片)。牧田在論文的最後,採用與《大正藏》本第85册所收本(部分)對照的方式,首次公開了該寫本的録文。幾年後,該寫本的圖版在藤枝晃《高昌殘影 : 出口常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録》(京都 : 法藏館,1978年)中首次公開;至於這套藏品的題解,還有待於多年之後藤枝晃《高昌殘影釋録 : 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京都 : 法藏館,2005年,131—133頁,“寶車菩薩經、觀世音折刀除罪經合卷”條)的付梓。
作爲先驅之作,《高王觀世音經的出現》除了上述對當時的新出資料吐魯番本的介紹,其論述和考察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拓展和貢獻 :
(1) 《高王經》經名的起源——“高王”=高歡
《高王經》的經名最早出現在北朝正史中盧景裕傳附録的一則應驗記中,因此牧田先生在北魏末年乃至東魏時代的政治戰略等歷史背景的脈絡中,再現了盧景裕的生涯和事蹟、與佛教的關聯;同時首次點出盧景裕傳附應驗記中的“高王觀世音”中的“高王”即東魏權臣高歡。
(2) 《高王經》的信仰與流傳
列舉了14種收録《高王經》相關記載的佛教、正史、類書,推測北齊時代的魏收在《魏書》中收録高王觀世音經的應驗記,或是有意圖通過冠稱高王觀世音經來讚譽高歡之遺德。
(3) 《高王經》的日本傳來
在該論文第322頁注18中,根據《大日本古文書》第七卷的記載,回顧了該經的日本傳來。據説,天平十年(738)十一月九日本經返送狀提及該經;天平十年經卷納櫃帳記載己櫃中藏納觀世音經百三十二卷,除觀世音菩薩授記經等以外,還有“高王觀世音經一卷白紙黄表紫綺楮紫檀軸”。牧田先生提到的天平文書的記載非常重要,但是至今爲止尚未引起後代學者的關注,也無人提及《高王經》的日本傳鈔本。
3. 桐谷征一及其奠基之作《僞經高王經のテキストと信仰》
桐谷征一教授的長篇論文《僞經高王經のテキストと信仰》是《高王經》研究的奠基之作(3)桐谷征一《僞經高王經のテキストと信仰》,《法華文化研究》第16號,1990年,1—67頁。,不僅將石刻經中新資料提供於佛教經典研究,並且指出,研究中國撰述經典(僞經)的源流,須要釐清經名的起源、經本的譜系、信仰的源流這三條主要脈絡。他所提議的這三條思考脈絡和《高王經》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不但持續地影響今日的《高王經》研究,也爲佛教疑僞經典的研究樹立了重要典範。
(1) 新資料的介紹
首次介紹了當時尚不爲人知的《高王經》的石刻經本,包括房山石經雷音洞(第5洞)的隋末唐初石刻經本《高王經》、房山石經第3洞初唐石刻經本;確定了兩種刻經的鐫刻年代,登載了兩本的拓本(圖版)和録文,並與牧田介紹的吐魯番本列表比較。首次登載了法藏敦煌遺書P.3920的圖版和録文,並與《大正藏》本列表比較。
(2) 《高王經》内文的經源
在追溯《高王經》文本源流之際,桐谷先生著眼於該經内文與英藏S.4456《救苦觀世音經》開頭部分的類似性,指出《高王經》的這一部分,很可能是以《救苦觀世音經》或其初期文本爲經源而形成的。也注意到和《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的關係。雖然桐谷先生並非有意識地專門討論《高王經》的經源,但是他所拓展的這一思路對《高王經》研究的深入而言影響甚爲深遠。尤其是僞經《高王經》的内文,基本上是將來自不同佛典的經文綴接而成的,因此比定其經源對於理解《高王經》的形成至關緊要。
(3) 《高王經》文本的譜系
桐谷先生整理《高王經》文本時,指出該經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繁簡二流”的傳承譜系 : 一是所謂“繁體形”的流傳譜系,是依據早期文本和中後期文本的比較,整理而出的自房山石經雷音洞石刻經本至《大正藏》本,經文自簡而繁不斷增補的發展譜系。二是所謂“簡體形”的流傳譜系,著眼於983年成書的《太平御覽》(卷六五四)引隋代陽松玠《談藪》,以及《佛祖統紀》等宋代文獻所收王玄謨故事中的“十句觀音經”(983年成書的《太平廣記》卷一二亦引同文,但未注明出典),與S.4456《救苦觀世音經》或《高王經》的開頭部分有類似之處,認爲《高王經》的流傳過程中,有人精練簡化了《高王經》的主體部分經文的字句,最終形成了極爲簡短的“十句觀音經”。
(4) 《高王經》的信仰與流傳
桐谷先生討論了《高王經》産生和流傳的歷史環境,唐代學僧以及經録作者對待此疑僞經典的態度。指出《高王經》反映的信仰特色乃是融合了法華信仰、般若信仰、佛名信仰等的“迎合庶民情感卻缺乏主體性的雜亂信仰”,在分類上屬於“追求現世利益型的信仰”。並且,搜集整理了自南北朝乃至宋代的各種資料中的《高王經》相關靈驗記,大膽猜測《續高僧傳》等中記載的孫敬德傳説出自道宣的原創。其論證和結果不見得完全準確,但是靈驗記是理解《高王經》的流通和信仰流傳的重要途徑之一,積極地搜集整理並加以考察的思路極爲重要。
(二) 繼往開來的漢語圈《高王經》研究
1. 于君方《觀音 : 菩薩中國化的演變》
嚴格而言,于君方(Yü, Chün-fang)教授的《觀音 : 菩薩中國化的演變》(Kuan-yin:theChineseTransformationof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4)于君方教授此書,由陳懷宇、姚崇新、林佩瑩三位學者聯名翻譯,2009年7月由法鼓文化出版刊行。,原著以英語寫成,並非漢語圈的《高王經》研究。但是英語圈的相關研究太少無法單獨立項,另外考慮到于教授乃華裔學者,因此將該著作置於本節討論。于教授主要在此書的第三章《中國本土經典與觀音信仰》集中討論了《高王經》(110—118頁)的文本、經名、起源、相關的歷史人物以及幾種類似的靈驗故事之間的關係。于教授是最早注意到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藏、推定爲北齊造像經碑上所刻《高王經》的學者之一,但她關於《高王經》特點以及相關問題的論述,基本建立在牧田、桐谷的研究成果之上,並没有明顯的創新。
2. 李玉珉及其《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
中國臺灣學者李玉珉在《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2002年)(5)李玉珉《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235—331頁。一文中,介紹了幾件重要的《高王經》造像經碑刻本,包括 :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藏推定北齊時代的造像經碑(館藏號B63S5)碑陽正面刻《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碑側到碑陰的下半段,刻《佛説觀世音經一卷》、《佛説觀世音經一卷》(相當於《高王經》)、《天公經》三經,並且指出了此碑所刻《高王經》的重要性。還首次介紹了北朝造像經碑刻本,指出該本爲《高王經》現存最古的文本,但是因受國圖拓本錯裱的影響,誤認此碑爲西魏大統十三年(547)杜照賢等刻碑。該論文雖非討論佛教或《高王經》的專論,但是在討論觀音信仰和觀音造像關係的語境中,指出《高王經》以河北地區流行的觀音信仰爲背景而誕生,一旦問世後又反之助長觀音信仰的流行,爲理解《高王經》的問世提供了確實的宗教背景。
3. 《高王經》的各種新出文本
自21世紀初,中國大陸的學者也開始關注《高王經》的各類文本,並試圖通過經文的校訂來解析該經的内容變遷,或者確認該經的最古文本。例如,李小榮在《〈高王觀世音經〉考析》(2003年)(6)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104—108頁;後來收入其專著《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中率先介紹了一件俄藏敦煌遺書中的《高王經》(俄敦531號)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另外兩件(TK.117和TK.118);並且以法藏敦煌遺書P.3920所書《高王觀世音經》爲底本,以俄敦531號、TK.117、房山(第3洞)石經本、《大正藏》本對校,推測P.3920《高王經》受《神咒經》《佛名經》的影響,具有密教特色。其次,王振國《跋龍門石窟兩部觀世音内容的石刻僞經》(2006年)(7)王振國《跋龍門石窟兩部觀世音内容的石刻僞經》,收在《龍門石窟與洛陽佛教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討論了同爲龍門石窟老龍洞内壁刻《高王經》和《佛説續命經》之間的關係,並以老龍洞永徽二年(651)劉彦深刻《高王經》本爲底本,以《大正藏》本及敦煌本等對校,確認石刻經本爲古本。
同一時期,張總也開始關注《高王經》,他於2002年付梓的《説不盡的觀世音——引經、據典、圖説》(8)張總《説不盡的觀世音——引經、據典、圖説》,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就已經提及《高王經》的造像經碑本,但是與李玉珉相同,誤認此碑爲西魏大統十三年杜照賢等刻。幾年後發表的《〈高王觀世音經〉刻寫印諸本源流》(2004—2006年)(9)張總《〈高王觀世音經〉刻寫印諸本源流》,李振剛主編《2004年龍門石窟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648—652頁。,則概括性地介紹了自北朝乃至近現代的刻經、寫經、印本《高王經》。除先學已經介紹過的幾種文本以外,張總移録了李玉昆1990年(10)李玉昆主編《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所録龍門石窟第1861龕内刻《高王經》(當時所在不詳)經文,並且首次提及俄敦01592號《高王觀世音經》、俄敦01591號《佛説救苦觀世音經》,指出這兩件敦煌寫本爲兩經的古本形態,但是没有提供録文;最後還介紹了遼金西夏、明清時代乃至現代的《高王經》後期文本。在這篇論文中,張總教授提出了經本分期的重要理論,就是將中古時代的《高王經》的發展階段分爲古本形態和近本形態。其中,日藏吐魯番本、俄敦01592號等5件寫本,以及先學介紹的石刻本都屬於内容簡短的古本;法藏P.3920增加了偈語部分的文本則代表近本形態。
4. 《高王經》研究的新階段——文本譜系和經源來歷的精密考證
將《高王經》研究推入新階段的是劉淑芬教授的《中國撰述經典與北朝佛教的傳佈——從北朝刻經造像碑談起》(2006—2008年)(11)劉淑芬《中國撰述經典與北朝佛教的傳佈——從北朝刻經造像碑談起》,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45—167頁。和張總教授的《書評 : 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2009年)(12)張總《書評 : 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唐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639—645頁。。
劉教授的論文,是在討論北朝造像經碑與中國撰述經典弘傳之間關係的框架之下,將《高王經》作爲個案之一。該論文的重要性,首先體現在文本的介紹和比對。(1) 首次詳細介紹了河南禹州市出土的東魏武定八年(550)由杜文雅(雍)、杜英俊等十四人所建造像經碑的碑陰下方所刻《高王經》,是迄今所見最古老的《高王觀世音經》版本,並提供了全本録文。(2) 提到了另外幾種據説是《高王經》的石刻經本,比較重要的包括 : (A) 據謝振發未刊稿《刻經碑像之研究》介紹的“隋代造像刻經碑”。此碑其實就是李玉珉介紹過的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藏品(館藏號B63S5),無紀年,推定年代暫有北齊或隋代的分歧。(B) 另據謝振發的同上未刊稿,首次提及“唐高宗永淳元年(682)阿彌陀佛造像”碑陰中段所刻“佛説高王經”,此即後來2016年倉本尚德書中所介紹的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的一件藏品(13)倉本尚德《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第五章“《高王觀世音經》の成立と觀音像”,法藏館,2016年,416—456頁。。(3) 通過諸本的内文比對,指出東魏到唐初的《高王經》文本(武定八年本、亞洲藝術館藏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本、房山雷音洞本)的内容基本上相同,此階段最普遍的經名爲《高王經》。劉教授總結的這個階段的文本,就相當於張總2006年文章中的古本階段。最後,劉淑芬的另一重要貢獻在於揭示了《高王經》中的六方六佛號與大正藏本《觀虚空藏菩薩經》後所附《寶網童子經》引文之間的關聯。
劉淑芬2008年的文章出版以後,張總在《唐研究》第十五卷中發表了書評(2009年),不僅訂正了前書中的一些誤解,也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新見解。(1) 首先,指出了因受國圖拓本錯裱拓本的影響,誤導學者將《高王經》碑刻視爲西魏大統十三年杜照賢等所刻造像經碑。肯定了劉淑芬的説法,該《高王經》碑刻實乃東魏武定八年(550)杜文雅(雍)等十四人所刻造像經碑,乃迄今所見該經最古老版本。(2) 糾正了劉淑芬的幾點失誤。例如 : 劉淑芬認爲(A)山西平定僧志朗等刻碑記“觀音經”(14)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6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49頁。和(B)山東東平郡須昌縣北齊皇建元年(560)海壇寺碑(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編號797號)記“觀音經”中的觀音經即《高王經》。但是,張總據實地踏查確認(B)碑陽所刻“觀音經”實爲《法華經·普門品》,並指出劉淑芬提示的證據不足,(A)“亦恐難推爲《高王經》碑”(641頁)。(3) 明確指出“這部很短的中土撰述,其實幾乎全從印度原典中輯出編成。其‘淨光悲媚(秘密)佛’至‘法護佛’五佛出自《大方等無想經》卷四(《大正藏》第12册,1098頁),‘普光功德山王佛’出《觀世音授記經》,而六方六佛出自《寶網童子經》,最後一段則出自聖堅譯《除恐災患經》(《大正藏》第17册,555頁),末句實出《請觀音經》中句”(642頁)。因爲是篇幅有限的書評,張總雖有以上敍述,没有展開。但這是《高王經》研究史上,首次從經源的角度,系統地思考該經經本成立的重要論述。尤其作爲《高王經》的經源,《大方等無想經》《觀世音授記經》《除恐災患經》還是首次被提及。具體的經文比定,尚有待張總2016年文章的公開。
2010年,張總又發表了《觀世音〈高王經〉並應化像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沙可樂捐觀音經碑像》(15)張總《觀世音〈高王經〉並應化像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沙可樂捐觀音經碑像》,《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24—31頁。一文,首次介紹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沙可樂捐觀音經碑像的碑陰所刻《高王經》及刻經題記,附有圖版及録文。指出在《高王經》古本和近本的分期中,俄敦01592號《高王觀世音經》(摘抄了部分録文)、吐魯番本的兩件寫經和東魏武定八年本、房山石經的兩本、龍門石窟的兩本、哥倫比亞大學藏本屬於樸拙的早期古本。又通過具體討論幾種《高王經》古本的字句與其經源《除恐災患經》之間的異同,指出古本階段的本文演變特色之一,就是鐫刻或書寫的時代越晚,其中的個别字詞反而越接近經源《除恐災患經》的原貌。最後,該論文詳細介紹了河南省鶴壁市五巖山石窟中,東魏興和元年(539)十月十日題記的觀音像窟,提供了該窟造像題記的圖版並録文,特别强調了題記中助建者之一的“高王寺主”。以觀音爲主窟像、配以罕見的日天子和月天子像的特殊設計,以及“高王寺主”的助建,讓張總確信該造像窟與《高王經》之間必有某種關聯。
此後,敦煌研究院的王惠民先生發表了《高王觀世音經早期版本敍録》(16)王惠民《高王觀世音經早期版本敍録》没有登載於期刊等紙本形態,而是傳播於網絡空間,現在已經很難追溯最初發表的年代和最初的形態以及内文的變遷。筆者於2017年8月1日查閲的是登載於敦煌研究院網站上的注明爲2009年12月3日的文章(http ://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737215779923&Page=5&types=1),但是文中引用了張總2010《觀世音〈高王經〉並應化像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沙可樂捐觀音經碑像》,因此該文章的改版應該還在2010年以後。,全面綜述了至2010年爲止已知的《高王經》的各類文本,包括 : 東魏武定八年本、亞洲美術館藏碑刻本、房山雷音洞石刻本、房山第3洞石刻本、哥倫比亞大學藏碑刻本、傳龍門石窟1861龕内石刻本、龍門石窟老龍洞内石刻本、日藏吐魯番本、俄藏俄敦0531號敦煌寫本、法藏P.3920號敦煌寫本、俄藏黑水城TK117號刊本、俄藏黑水城TK118號刊本、《大正藏》所收日本藏本及用於對校的韓國光武二年(1898)刊本(17)除上述文本以外,王惠民還誤録了西魏大統十三年(547)杜照賢造像碑本,視此本爲《高王經》現存最早版本。但是早有學者指出,西魏大統十三年(547)杜照賢造像碑上並没有鐫刻《高王經》,不存在所謂西魏刻本的《高王經》。另外一件是收藏於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的附1095年題記的宋刻石板(F1914.56),上刻觀世音聖咒,此件也和《高王經》無關。。
在該文中,王惠民根據《高王經》經本的演變進程,提出了三段分期的看法 : 將東魏本、亞洲藝術館本、哥倫比亞大學藏本、房山石經2本、俄敦531號本、吐魯番本歸類爲維持了該經原貌的早期版本;法藏P.3920敦煌本附加了咒語等增補,屬於第二階段;俄藏黑水城本等以後的韓、日刊本增補了序文、咒語等文本,劃分爲第三階段。這種分期法,其實就是在張總2006年文章中提出的《高王經》古本(各種石刻本、日藏吐魯番本、俄敦01592號等五件寫本)和近本(法藏P.3920)的兩段分期法的基礎上,再將張總歸納的遼金西夏明清以來的各本一併歸類在了第三階段而已。
經過長年的資料收集和各種設想的醖釀,在2014年國際研討會論文的基礎之上,張總2016年刊登了《疑僞經中的摘抄與編撰例説》(18)張總《疑僞經中的摘抄與編撰例説》,載方廣錩主編《佛教文獻研究》第1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275—315頁。,其中凝聚了張教授十多年來的《高王經》相關研究的總體成果。其主要貢獻有二 :
第一,明確提出了《高王經》自中古至近現代以來的文本演變的分期法。他根據經文增補的發展,將《高王經》經本分爲古、近、今三個階段 : (一) 北朝隋唐時代的古本,内文多爲佛名;(二) 宋遼金和西夏的近本,内文增加了四種明觀音句和真言咒語等;(三) 明清至今日流傳的今本,擴增了誦經功德與八大菩薩名等。並擇取三種代表性文本,録文並列表比較。其統計結果顯示了古、近、今本的字數分量情況 : 古本(9件)僅250字左右;近本(約10件)增出一倍餘達580字;今本(約40餘件)進一步增至775字。
第二,完整全面地追溯比定了《高王經》古本的經文來源。雖然張總在2009—2010年中,已經陸續點明了《高王經》的各類經源,但是在此他具體比較和論證了《高王經》中的字句與其經源 : (A) 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無想經》(亦稱《大雲經》或《大涅槃經》),(B) 般若咒頌,(C) 聖堅譯《除恐災患經》,(D) 《觀世音授記經》,(E) 《寶網童子經》,(F)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之間的對應關係。
張總此文在結論中揭示了《高王經》這部中國撰述經典的特色在於“這個非常短小的經,其中出自自撰的成分極少,卻是從各種譯出的‘真經’佛典中,‘精心’選擇,編在一處而成”(292頁)。“《高王經》的特點是其經本來源。其古本最爲重要,可以説幾乎全是取自翻譯的佛典;以後的近今本也大量汲取成經中的成分。形成了疑僞經中一種特殊情況。探明《高王經》中的‘底細’以後,可知疑僞經也可以由編者之意圖與民衆之需求,從翻譯的‘真經’之中摘編採取而成”(315頁)。
(三) 新一代的日本學者及其《高王經》研究的最新進展
《高王經》的研究是由日本學者草創和奠基的課題之一,遺憾的是,自桐谷征一1990年的文章刊登後很多年來,日本學界對於相關課題一直没有進一步的深入。這種沉寂,直到2011年,青年學者田村俊郎《中國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高王觀世音經〉とその展開——サンフランシスコ·アジア美術館所蔵經碑を手がかりに》一文發表後纔被打破(19)田村俊郎論文發表於日本道教學會《東方宗教》第118號,2011年,1—31頁。。新一代的日本學者,很多精通漢語,並且關注漢語圈研究的新舊成果,注重田野考察和新資料的發現及應用。此論文是繼李玉珉、劉淑芬以來,首次深度專注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藏北齊造像經碑(館藏號B63S5)的研究。
(1) 田村俊郎根據在亞洲藝術館展開的實地考察結果,首先詳細介紹了碑上鐫刻的四種刻經的具體佈局,並全部録文 : 碑陰全面鐫刻《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卷廿四》(刻經A);碑左側下半部到碑陽的下半段,刻《佛説觀世音經一卷》(刻經B);碑陽的下半段續接《佛説觀世音經一卷》(相當於古本《高王經》)(刻經C);續刻《佛説天公經一卷》(即古本《天公經》)(刻經D)。
(2) 在實地考察和録文確認的基礎之上,展開了文本比對 : (A)將刻經C《佛説觀世音經一卷》内文,與東魏本、房山雷音洞本、房山第三洞本、吐魯番本、大正藏等本的《高王經》列表比較,確認刻經C本也是《高王經》古本之一。(B)將刻經B《佛説觀世音經一卷》與英藏敦煌本S.4456《救苦觀世音經》比較,確認刻經B爲《救苦觀世音經》之古本,S.4456乃擴增本。但是,田村2011没有注意和使用到張總2006提及的俄敦01591號《佛説救苦觀世音經》古本。
(3) 以新出資料的刻經B、刻經C爲依據,重新討論了桐谷有關《高王經》《救苦觀世音經》《十句觀音經》三者之間關係以及《高王經》“繁簡二流”的傳承譜系的問題。修正了桐谷關於《高王經》的主體部分經文的字句,簡約後形成十句觀音經的所謂“簡體形”流變的説法,認爲先有刻經B即《救苦觀世音經》古本,後衍生出S.4456《救苦觀世音經》的擴增本,從此再簡化形成後世的十句觀音經,也就是説十句觀音經並非《高王經》本身的“簡體形”流變結果。同時,田村認同刻經B=《救苦觀世音經》古本和刻經C=《高王經》古本之間或存在影響關係,或兩者有共同的源流。
(4) 以“讀誦千遍”爲著眼點整理討論了各種觀音靈驗記,推測《高王經》的起源“觀世音經”在5世紀中葉即已存在,當時存在兩種“觀世音經” : 一是《法華經·普門品》的傳承;二是後來被稱爲《高王經》的源流。但是,田村俊郎認爲以“高王”冠稱該經的做法,無法追溯到唐代以前。
經過以上幾個重要問題的討論,田村俊郎在結論中指出 : 亞洲藝術館藏經碑的碑陰整面刻寫的四種觀音相關經典,除《普門品》以外就是三部短小的觀音系統僞經,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在於强調讀誦經典千遍而脱離諸難、獲得救贖,與《普門品》相比,體裁極爲簡潔,且具有實踐性特色。揭示出亞洲藝術館藏經碑的刻經選題的内在邏輯,是以刻經A普門品爲經典依據,以C—D的三種刻經來開示具體的修持方法、督促信仰的實踐,四經相輔相成地共同提示了整套的教化體系。
幾年之後,另一位青年學者山﨑順平發表了《〈高王観世音經〉の原初テキストについて——南北朝から隋唐の諸本の比較検討から》(20)《集刊東洋學》111號,2014年,41—60頁。,又補充了兩件宋代以後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漢文《高王經》(包括折本寫本TK70、折本刊本TK183)。該文在繼承先學研究的基礎上,收集和整理了10種唐代以前的《高王經》諸本(其中包括首次確認爲《高王經》文本的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寫本016G),全部提供録文。不但詳細討論了各本之間的字句差别,並且通過漢字字體的特徵推測各本的鐫刻或書寫年代,試圖判定《高王經》的原初形態。其所採用的11種文本依次爲 : 東魏武定八年碑刻本、亞洲藝術館藏碑刻本、房山雷音洞石刻本、龍門老龍洞石刻本、房山第3洞石刻本、哥倫比亞大學藏碑刻本、日藏吐魯番本、俄藏俄敦00531號寫本、俄敦01592號寫本、甘肅省博物館藏016G號敦煌寫本。
該文著眼於古本《高王經》的内容、字體,得出結論 : 東魏本的題記雖説最爲古老,但文本内容特殊、校勘不精,不足以代表《高王經》的原本形態;而亞洲藝術館藏經碑的碑陽刻本雖無紀年,但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後期以降的南北朝時代,文本内容也最能反映該經成立當初的原形;吐魯番本與其爲同一系統,成立年代或可回溯到隋代。
最後,就是在東洋史、佛教史方面已有傑出成就的日本學者倉本尚德的《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第五章“《高王観世音經》の成立と觀音像”(21)倉本尚德《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第五章“《高王観世音經》の成立と觀音像”,法藏館,2016年,416—456頁。。該文可以説繼桐谷征一以來唯一的一篇《高王經》的綜合性研究,不但有新出文本的補充,同時對《高王經》出現的歷史背景、宗教信仰背景,以及與北朝觀音造像之間的關聯等重要主題都展開了具體論述,最後還對北朝至唐初的古本《高王經》進行對校,並進一步總結了古本内容的經典來源。該論文的具體論點和貢獻如下 :
(1) 繼牧田1970年的研究之後,再次著眼於《高王經》中的“高王”與北魏末年乃至東魏時代的一代權臣高歡之間的關係。通過史書、佛經尤其是造像銘題記等史料,考證高歡生前即被尊稱爲“高王”,還多次出現在與佛教相關的文脈當中。例如 : 高王浮圖、高王寺、《一切法高王經》。提出了高歡身邊或有御用僧人將“高歡=高王”視爲菩薩化身的大膽設想。
(2) 從東魏時代的觀音造像的情況以及高歡與《高王經》成立和流傳的關係,挑戰了桐谷關於《續高僧傳》等中記載的孫敬德《高王經》靈驗記乃是道宣編造的猜想,考證出道宣用於史源的《齊書》《齊志》乃是隋代王劭的著作。
(3) 著眼於河南省鶴壁市五巖山石窟中東魏興和元年十月十日題記的觀音像窟,以及造像題記中提到的助建者“高王寺主”。又從文獻和石刻史料中鉤沉而出“齊獻武王寺”“神武皇帝寺”等以高歡謚號冠稱的寺名,推測其前身或爲“高王寺”。並且著眼於五巖山以觀音座像爲主尊的特殊造像樣式,猜測助建者“高王寺主”或有意將高王與觀音建立關聯。懷疑是高歡身邊的御用僧人建議借助觀音造像和《高王經》應驗記,達到利用河北地區流行的觀音信仰來樹立和提高“高歡=高王”聲譽和威望的目的。
(4) 以東魏碑刻本《高王經》爲底本,以先行研究已經介紹的唐前文本以及新增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永淳元年造像刻本和山東省兗州市金口壩附近出土殘石本兩本爲校本進行校勘。結果顯示,亞洲藝術館藏經碑的碑陽刻本前半部分或保留了該經的較古形態,但是後半部分含有的唯有此本具備的語句或爲後世增補。反而是東魏本,雖含衆多異體字和同音假借字,更爲真實地反映了《高王經》作爲讀誦經典的特性和北朝時代石刻的特徵。這一部分,可以説反駁了前述山﨑順平的部分結論。
(5) 倉本的最終結論認爲 :“高王經是由一群圍繞高歡的御用僧人,利用當時河北地區尤其盛行的觀音信仰,爲了强化讀誦即可獲得很大功德的讀誦經典的特色,於是以《救苦觀世音經》爲基礎,加入了般若經的咒語,佛名,再附加偈語,在極爲短期間内製作而成的。應該是這群高歡的御用僧人們向高歡獻策,通過《高王經》的製作,配合孫敬德的應驗記,高王寺的創建,以及特殊形態觀音像的製作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將高王=高歡設定爲觀音的化身,以達到弘揚高王威名的目的,最終獲得了高歡的首肯。”(450頁)
二、 《高王經》現存文本的概觀——以北朝至唐五代文本爲主
在前一節中,筆者主要是以《高王經》先行研究的回顧爲敍述脈絡,概括了相關研究自20世紀30年代至2016年爲止的80年間的學術進程。其實,《高王經》的“草根”特性已經了注定了方法的難度和特殊性,因爲傳統的佛教經典研究方法幾乎無能爲力。若要理解《高王經》的研究意義,通過這一個案爲推動中古佛教史提供新問題和新視角,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新資料的發現和掌握與定位。因此,在這一節中,筆者將以現存文本的發現和應用爲敍述脈絡,簡述《高王經》的14種已知文本的所在、内容等概況,意在爲今後的研究掃清道路。
關於6世紀中葉左右問世的《高王經》,雖然正史、志怪以及佛教史傳中多處記載該經的誕生傳説(即孫敬德故事),但是没有任何現存的中古文獻曾經引用過該經的經文。直到武則天天册萬歲元年(695),由佛授記寺沙門明佺等七十名高僧奉敕撰集而成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録》,《高王經》方纔獲准入藏。該録的卷七中,將《高王經》視爲“無譯主經”之一,並記載其緣起 :“高王觀世音經一卷。右北齊代有囚,罪當極法,夢見聖僧口授其經。至心誦念,數盈千遍,臨刑刀折,因遂免死。今《高王經》也。見《齊書》及《高僧傳》、琳法師《辯正論》。然其經體,即《法華經》中稱念觀音,皆蒙願遂,隨類化誦,救苦衆生。”(22)CBETA, T55, no.2153, p.416, a1-7.另外,在《大周刊定衆經目録》卷一四的入藏録中,《高王觀世音經》被歸類爲“小乘修多羅藏”的單譯經之一(23)CBETA, T55, no.2153, p.468, a7.。這是《高王經》問世以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被編入中國的佛教大藏經。
好景不長,開元十八年(730)左右成書的智昇《開元釋教録》的入藏録中,將《高王經》與《淨度三昧經》《最妙勝定經》《觀世音三昧經》等合計十部所謂“古舊録中僞疑之經”正式排除於藏外(24)《開元釋教録》卷二 :“《淨度三昧經》三卷、《法社經》二卷、《毘羅三昧經》二卷、《決定罪福經》一卷、《益意經》二卷、《救護身命濟人病苦厄經》一卷、《最妙勝定經》一卷、《觀世音三昧經》一卷、《清淨法行經》一卷、高《王觀世音經》一卷(或云《折刀經》),《淨度經》下十部一十五卷,並是古舊録中僞疑之經。《周録》雖編入正文,理並涉人謀,故此録中除之不載。” (CBETA, T55, no.2154, p.699, b27-c10)。另外該録卷一八的“别録中疑惑再詳録”中,有一段關於《高王經》的考證 :
《高王觀世音經》一卷(亦云《小觀世音經》,半紙餘)
右一經,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在防造觀世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不堪考楚,遂妄承罪,明日將刑。其夜禮懺流淚,忽如夢睡見一沙門教誦救生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驚覺如夢所緣,了無參錯,遂誦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下斫之,折爲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换,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承相高歡,乃爲表請免死。因此廣行于世,所謂《高王觀世音經》也。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及《辯正論》《内典録》等。(撰録者曰 : 此經《周録》之内編之入藏,今則不然。此雖冥授,不因傳譯,與前僧法所誦何殊?何得彼入僞中,此編正録?例既如此,故附此中。)(25)CBETA, T55, no.2154, p.674, c30-p.675, a14.
顯然,智昇在決定《高王經》的入藏問題上,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不但依據“《齊書》及《辯正論》《内典録》”等抄録了《高王經》問世的相關傳説,指出此類經典的問世可謂“冥授,不因傳譯”,但從編録體例而言,須與同類經典一視同仁排除藏外。《開元釋教録》中關於《高王經》的記載,反映了開元年間經本的特徵,有幾點很重要的提示 : 當時的正式經名爲《高王觀世音經》,爲一卷本,文字分量約“半紙餘”,並有《小觀世音經》或《折刀經》等别名。
《高王經》經歷了武周時代的短期入藏,到開元年間即被判定爲僞經而被排除藏外,直至20世紀初日人刊刻《大正藏》等藏經之際,纔得以復歸佛藏當中。與其入藏的多舛命運和備受各代學僧冷落的現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高王經》在民間流傳中呈顯的長久而蓬勃的生命力。或許因爲《高王經》的内容短小精練、信仰實踐的特色濃厚,即使不仰賴高僧大德的認同或借助佛教大藏經有組織的系統性傳承和流通,該經文本的現存狀況,無論從數量上看,還是從流傳的多元媒介而言,可以説是超乎尋常地得天獨厚。
由於《高王經》現存文本的種類和數量繁多,先學們根據經文内容增補的遞進,提出了各自的文本分期理論。由於筆者主要關注《高王經》在北朝的起源及其在中古時代的傳承,因此文本的擇選也限定於先學所言之“古本”階段。具體而言,將以東魏武定八年的碑刻本爲上限,以法藏P.3920敦煌本爲下限,回顧先學談過的14件文本。在概述這14件《高王經》文本的過程中,將大致按照文本的成文年代依次介紹,儘可能提供録文、概括文本内容、特色或問題,同時簡略回顧該文本的研究現狀。
1. 東魏武定八年(550)二月八日,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經碑本
現在河南省禹州市博物館,收藏著東魏武定八年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經碑,高175釐米、寬39釐米、厚23釐米,碑陰刻有《高王經一卷》。倉本尚德依據《(民國)禹縣志》卷一四《金石志》、《河南文物》等記載,指出此碑和另外一塊西魏大統十三年(547)杜照賢等十三人的造像碑,都來自於梁北鎮杜岡(康)寺村(436頁)。此地爲北朝東魏和西魏反復爭奪之要地,兩方石碑的題記年代前後僅隔3年,助建者同爲杜氏一族,但是其前後所奉正朔有變。據此,北村一仁指出,杜文雍等人樹碑刻寫《高王經》,不僅顯示杜氏一族的觀音信仰,或者也是他們歸順東魏高氏的一種表態。
因爲原碑的風化磨損情況嚴重,研究時更多還需仰賴早年的拓本及其圖版。該碑拓本的主要收藏單位包括 : 中國國家圖書館金石組(26)《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6卷,15—17頁。誤將碑陽題記曰“大魏武定八年歲次庚午二月辛巳朔八日造訖”的“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經碑”碑陰所刻的“高王經一卷”,與碑陰題記曰“大魏大統十三年歲在丁卯十一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造訖”的“杜照賢十三人等造像記”誤置一處,誤導學者將此“高王經一卷”視爲“大魏大統十三年”的經刻。張總2009查實,這一失誤“應是國圖拓本將此與西魏碑裱在一處所致”(641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7)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資料收在(http ://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近年又有日本京都大學藏中國歷代碑刻文字拓本編委會(編)《日本京都大學藏中國歷代碑刻文字拓本》(全10册,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15年)出版,該叢書的“南北朝碑刻(下)卷”的第393頁中,收録了“高王經一卷”拓本(圖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在整理拓本時,犯了與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相同的失誤,將大魏(東魏)武定八年造迄“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碑”碑陰所刻的“高王經一卷”(同書,第393頁,編號NAN0464B),與大魏(西魏)大統十三年造訖的“杜照賢十三人等造像碑”的拓本(同書,第394—397頁,編號NAN0464A,NAN0464C-H)錯誤拼置一處。並且,没有登載武定八年造迄的“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碑”的碑陽造像碑記。因此,進一步誤導學者將“高王經一卷”視爲“大魏大統十三年”的碑刻,誤也!、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28)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佛教石刻造像拓本(圖片)收録在“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http ://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當中。在該系統中,“高王經一卷”的拓本分兩處收藏。第一,是傅圖登録號11000-1,題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記”。此拓本有兩片同組件,一是傅圖登録號11000-2,也題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記”,内容是同碑碑陽所刻造像記;二是傅圖登録號11000-3,題名同前,内容是同碑兩側所刻造像記。第二是傅圖登録號11026,題名“高王佛説觀世音經殘石”,原刻年代定爲“隋代無紀年”,兩者似爲同一碑面的拓本,不知爲何年代判定不同。至於西魏大統十三年造訖的“杜照賢十三人等造像碑”的拓本也收在該系統中,傅圖登録號10898-1,10898-5-6,10898-7,其中確實没有“高王經一卷”的拓本。等。已經出版的該碑拓本圖版有 : 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279頁)(29)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1917年初版),圖書刊行會復刻,1980年。、顔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30)顔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年。該圖録的文字版後爲CBETA電子佛典集成所收。(No.53,135頁)、倉本2016(437頁)等。登載了該碑上刻《高王經》録文的論著包括 : 《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第二函第二册(第478—479頁)、劉淑芬2008(166—167頁)、顔娟英2008(No.53碑陰,138頁)、田村2011(12頁)、山崎2014(43頁)、倉本2016(438頁)。
由於國圖整理該碑拓本時的失誤,誤導學者認爲碑陰刻的《高王經一卷》是前述西魏大統十三年杜照賢等十三人所造像碑,或誤認東魏武定八年造像經碑和西魏大統十三年造像碑各自刻有《高王經一卷》。雖然北村2008、張總2009、山崎2014、倉本2016都曾經言及這一誤解,爲了引起重視,筆者仍要舊話重提。當年,《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6卷出版時,誤將碑陽題記曰“大魏武定八年歲次庚午二月辛巳朔八日造訖”的“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經碑”碑陰所刻的“高王經一卷”,與碑陰題記曰“大魏大統十三年歲在丁卯十一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造訖”的“杜照賢十三人等造像記”誤置一處(15—17頁)。這一錯置現象,讓學者誤以爲“高王經一卷”刻寫在西魏大統十三年的石碑上。據張總2009查實,這一失誤“應是國圖拓本將此與西魏碑裱在一處所致”(第641頁)。
事實上,不僅是國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整理收藏的拓本資料(http ://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時,也犯了與國圖金石組同樣的失誤,將東魏武定八年造迄“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碑”碑陰所刻的“高王經一卷”(編號NAN0464B),與西魏大統十三年造訖的“杜照賢十三人等造像碑”的拓本(編號NAN0464A,NAN0464C-H)誤拼在一起。並且没有登載武定八年造迄的“杜文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碑”的碑陽造像碑記,進一步誤導學者將“高王經一卷”視爲“大魏大統十三年”的碑刻。最早指出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拓本誤置的是北村2008(第78頁,注63)。
唯一没有發生碑陰和碑陽拓本誤置的收藏單位,是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該單位所藏佛教石刻造像拓本(圖版)收録在“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http ://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當中。在該系統中,“高王經一卷”的拓本分兩處收藏。第一,是傅圖登録號11000-1,題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記”。此拓本有兩片同組件 : 一是傅圖登録號11000-2,也題名“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記”,内容是同碑碑陽所刻造像記;二是傅圖登録號11000-3,題名同前,内容是同碑兩側所刻造像記。第二是傅圖登録號11026,題名“高王佛説觀世音經殘石”,原刻年代定爲“隋代無紀年”,兩者似爲同一碑面的拓本,不知爲何年代判定不同。至於西魏大統十三年造訖的“杜照賢十三人等造像碑”的拓本也收在該系統中,傅圖登録號10898-1、10898-5-6、10898-7,其中確實没有“高王經一卷”的拓本。據此可知,大統十三年造像碑上没有鐫刻《高王經》,唯有東魏武定八年造像經碑上刻寫了《高王經一卷》。
武定八年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經碑的碑陽分上、下兩段,下半段鐫刻了以下的造像題記(31)該題記的圖版,見顔娟英2008(No.53碑陽,135頁),録文見同書137頁。此處引文基本依據該書録文,有個别字的修正,例如 : 摧疆-摧强、英裂-英桀。:
大魏武定八年歲次庚午二月辛巳朔八日造訖。
夫大覺秉不惻之智,非感莫應其形。真如藴無窮
之説,非聖孰宣其旨。故投藥隨機,崎嶇濟物,哀彼
沈淪繫珠之言。是以都邑主杜文雍、都維那杜英
儁、都忠正杜容徽十四人等,上爲 皇帝陛下、諸
邑七世父母、一切有形,敬造石像一區,堪室華離,
靈容澄湛,表彰往聖,合生等福。 乃頌曰 :
真仙捨逝,譬彼虚空。蒼生靡托,雕鐫遺容。捐金弗
愛,致敬顒顒。 躬懷曠濟,解喻金剛。中孝仁厚,攝
弱摧强。示人寶□,万代留嚮。 邕々此邑,濟々仁
林。英桀比肩,禮讓爲心。逢兹善政,競抽家金。懃亲
建立,悀躍難任。論其罕返,類芥投針。
最後,該碑碑陰也分上下兩段,《高王經》就刻在碑陰的下半部分,現録文如下(32)對照拓本圖版的結果顯示,倉本2016的録文最爲準確,也是本文的依據。:
高王經一卷
佛説觀世音經一卷,讀訟千遍,濟渡苦難,拔除生死罪。觀世
音菩薩,南无佛,佛□□緣,佛法相因,萇樂我緣。佛説男无摩


六佛名号。東方寶光□殿妙尊音王□、□方樹根花王佛、西

勝佛、下方善治月音王佛。釋迦牟尼佛、弥勒佛中央。一切衆
生俱在法戒中者,行動於地上,及以虚空里。慈憂於一切,寧
2. 北齊造像經碑本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現藏有一塊無紀年題記的造像經碑(33)金申2007認爲“佛像造型欠缺力度,綫條柔弱,獅子龕置於碑首,真僞可疑。”金申編著《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鑒》,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石碑高148釐米、寬71釐米、厚8釐米。碑陰全面鐫刻《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卷廿四》;碑左側下半部到碑陽的下半段,刻《佛説觀世音經一卷》(相當於古本《救苦觀世音經》);碑陽的下半段續接《佛説觀世音經一卷》(相當於古本《高王經》);續刻《佛説天公經一卷》(即古本《天公經》)。
該碑出土地點不明,造碑年代也有爭議,主要有以下三種年代判定。(1) 北齊刻碑説 : 考察和討論過此碑的學者,包括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34)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篇2,吉川弘文館,1995年,b445頁。,另李玉珉、田村俊郎從圖像和刻字的特徵,判斷爲北齊所刻。(2) 隋代刻碑説 : 張總2006、劉淑芬2006(引謝振發的録文及觀點)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藏繆筌孫藝風堂拓本(“藝19688號”)題解云“碑後具有隋開皇八年題記”,而暫將其視爲隋代刻碑。但是親自前往藏碑單位查閲過該碑的田村俊郎並未在原碑上發現紀年題記,並且張總2006也贊同圖像和刻字具備北齊風格,隋代刻碑的説法或不可取。(3) 北魏以降刻碑説 : 山崎順平2014根據刻字中的南北朝時代字體以及同碑所刻《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卷廿四》,認爲該碑的鐫刻年代可以追溯到包括北魏後期的南北朝時代。其年代判定的主要依據爲普門品位列第二十四品,認爲此爲提婆達多品增入《法華經》(557年以後)以前的古本形態。針對這條論據,倉本2016(第452頁,注14)中指出,已知的北齊時代的石刻《普門品》全部都是第二十四品;至少在北方,《普門品》開始作爲第二十五品流通,尚有待隋仁壽元年(601)闍那崛多漢譯《普門品》偈以後。據此而言,《普門品》位列第二十四品的事實,可佐證刻碑年代追溯至包括北齊在内的北朝時代,但是繼續上溯乃至北魏後期則言過其實。在此,筆者暫且認同有實地考察經驗並且以圖像和刻字的風格爲論據的上述第(1)種,即北齊時代刻碑的説法。
除拓本收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藝19688號”)以外,已出版的圖版收入於d’Argencé1974(35)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Diana Turner, et al.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Sculpture :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Tokyo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4. Print.(146—147頁,第65圖)、松原三郎1995(第b445頁)、Yü2001(112頁)、金申2007。田村2011(7—10頁)對《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卷廿四》等四種刻經全部録文。山崎2014(45頁)移録了其中的《佛説觀世音經一卷》(經文相當於《高王經》),倉本2016(439—446頁)將相當於《高王經》的經文用於與東魏本的對校。現依據田村2011(9—10頁),引用該碑所刻相當於《高王經》的《佛説觀世音經一卷》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佛説觀世音經一卷
佛説觀世音經,讀誦千遍,得度苦難,拔除生死罪。觀世音菩薩,南無
佛,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緣。佛説摩訶般若是大神咒,南無摩
訶般若是大神咒,南無摩訶般若是大明咒,南無摩訶般若是大無
等等咒。淨光秘密佛、法藏佛、師子吼神足遊王佛、告須彌登王佛、法
護佛、金剛師子遊戲佛、藥師琉璃光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
寶王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
佛、西方皂王神通艷花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佛、
下方善寂月音王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東方快樂佛、月明照住王
佛、過去堅持佛、分别七淨佛、妙法蓮華花上王佛。令一切衆生類,在
土界中者,住於地上者,及以虚空中。慈愛於一切,令各安休息。晝夜
修慈心,常念誦此偈,消伏於毒害。常夜半起,三稱六方六佛名字,永
拔三途八難之處,上衆法堂快□□□□。
3. 北朝山東兗州石刻經本
徐可然2012(36)徐可然《兗州金口壩佛教碑刻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25—27頁)介紹了一塊在山東省兗州市金口壩附近出土的殘石,上刻《罪福報應經》和《高王經》。該石的拓本圖版見於倉本2016(437頁),據其考證,從殘存文字判斷,此碑字體具有北朝期刻字特徵,經文内容具備古本形態,也有可能比東魏本更爲古老。倉本2016没有提供録文,而是直接將其用於與東魏本的對校,現據圖版録文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中闕)訶般若是大无等等咒。淨光秘密佛、
(中闕)佛。六方六佛名号。東方寶光月殿
(中闕)王佛、釋迦牟尼佛、弥勒佛。中央一切(下闕)
4. 房山石經雷音洞(第5洞)隋末唐初石刻經本

該石經的録文,先後登載於塚本1935(94—95頁)、桐谷1990(10—11頁)、田村2011(12頁)、山崎2014(49頁);倉本2016(437—445頁)以該本與東魏本對校。現根據《房山雲居寺石經》的圖版,移録此石經本的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已下大王觀世音經一卷
□説觀世音經一卷,□誦千遍,得度苦難,拔除生死罪。觀世音菩薩,南无佛,佛國有緣,佛法相國,
□樂我緣。佛□□□□訶波若是大神□,南无摩訶波若是大明咒,南无摩訶波若是大
□等等咒。□光秘密佛、法□佛、師子吼神足遊王佛、告須弥登王佛、法護佛、金剛
師子遊戲佛、藥師琉璃□佛、普光功□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六方六佛名号。東
方寶光月殿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華王佛、西方皂王神通艷華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
上方无□精進寶首佛、下□□寂月音王佛、釋迦牟尼佛、弥勒佛中央。一切衆生,在此
□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於一切,令□安休息。晝夜修治心,常應誦此經,消伏
於□□。(下闕)
5. 日本出口常順藏吐魯番本(推定隋唐代)
日本的出口常順藏品中包含一件無紀年、闕尾題,首題曰“佛説觀世音折刀除罪經”的吐魯番寫本斷片。觀其經文,起自“佛説觀世音經讀誦千遍”,迄至“善寂月音”(下文闕失),可知内容相當於《高王經》。藤枝晃1978(圖版232)載有此本的圖版(38)藤枝晃《高昌殘影 : 出口常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録》,法藏館,1978年。,藤枝晃2005(131—132頁,“寶車菩薩經、觀世音折刀除罪經合卷”條)附有寫本的題解(39)藤枝晃《高昌殘影釋録 : 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法藏館,2005年。。最早介紹該寫本的牧田1970(283頁)推測此爲8世紀寫本,没有注明依據。此後,藤枝晃2005也只是將其歸置於唐代寫本,並未特别提及書寫年代;山崎2014(53頁)認爲内容和字體呈顯隋代的特徵。
牧田1970(317—318頁)、桐谷1990(10—11頁)、藤枝晃2005(131—132頁,“寶車菩薩經、觀世音折刀除罪經合卷”條)、田村2011(13頁)、山崎2014(52頁)、倉本2016(437—445頁)以該本與東魏本對校。現根據藤枝晃1978的圖版,移録此寫本的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佛説觀世音經折刀除罪經
佛説觀世音經讀誦千遍,得度苦難,拔除生死
罪。觀世音菩薩,南无佛,佛法有緣,佛□□□,
常樂我緣。佛説南无摩訶般若是大神□,□□□
訶般若是大神咒,南无摩訶般若是大明咒,
南无摩訶般若是大无等等咒。淨光□□□、
法藏佛、師子吼神足遊王佛、高須□□□□、
法護佛、金剛師子吼遊戲佛、藥師流離光佛、
自在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
六方□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妙尊□□□、□
方樹根華王佛、西方造王神通炎華王佛、北方
月殿清□□□、上方无數精進寶首□、□
□善寂月音(下闕)
6. 龍門石窟老龍洞永徽二年(651)本
河南省洛陽市龍門石窟的老龍洞的内壁上,鐫刻著附有“永徽二年五月十五日”題記的“觀世音經一卷”。龍門石窟研究院内收藏著該經的拓本(40)在整理該石刻的相關研究之際,筆者有幸結識龍門石窟研究院的李瀾助理研究員。雖然未曾謀面,李老師慷慨代爲查找和惠贈相關資料,並給予筆者衆多指教。在李老師等人的無私協助下,筆者獲得了龍門石窟研究院提供的老龍洞壁刻《觀世音經一卷》的拓本圖版。在此謹表謝意。,該拓本圖版見於王振國2001(111頁)。觀此圖版,可知此石經現狀不甚良好,尤其前兩行幾乎磨滅殆盡,首題無從辨識,不見尾題。其經文前云“佛國有緣,佛法相因,長□□緣”,迄至“常□□此偈,消伏於□□”(下闕),可知此石經内容相當於《高王經》。該石經的録文,先後登載於王振國2001(111—112頁)、張總2006(650頁)、山崎2014(50頁),倉本2016(437—445頁)以該本與東魏本對校。現根據張總2006,移録此石經及其題記的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南无□□□若是□□□□。淨□□□佛、法藏佛、師□
吼神足遊王佛、告須弥燈王佛、法護佛、金剛藏師子
遊戲佛、藥師琉璃光佛、普光功得山王佛、善住功
得寶王佛。六方六佛名号。東方□光月殿妙尊音
王佛、南□□根花王佛、西方造王神通艷光佛、北
方月□清□佛、上方□數精進寶勝佛、下方善寂月□
王佛、□□□尼佛、弥勒佛。一切衆□類,在於土界
□□,□□□□,□以虚空裏,慈憂於一切,令各安
□□息。晝□□治心,常□□此偈,消伏於□□。
□□□□□□□□
永徽二年五月十五日,佛弟子劉□□敬造釋迦
像一軀,又鑿石造觀世音經一卷。讀誦千遍,願佛
□□流,法輪常轉,四□寧淨,兵駕永息,□□□□,
□□□□。又願弟子共法界衆生□波若雨□□
□□□□□□□弟子劉彦深□□。
7. 哥倫比亞大學初唐造像碑本(唐代刻本)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藏有沙可樂(Arthur M.Sackler)捐贈的一塊觀音經像碑(館藏號S.4426)。據該館圖録(41)Leopold Swergold, Eileen H. Hsu, Stanley K. Abe, Wendi L. Adamek, Dorothy C. Wong, and Qing Chang. Treasures Rediscovered : Chinese Stone Sculpture from the Sackler Collection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Miriam & Ira D. Wallach Art Gallery, 2009. Print.記載,該石碑高103.1釐米、寬55.8釐米、厚15.5釐米。碑陰分爲上、下兩段,下半段刻有涅槃像等三龕造像、《高王經》以及刻經題記。該碑出土地點不明,鐫刻年代也有三種説法 : (1) 圖録所收Eileen H. Hsu執筆的題解(51—53頁)認爲該碑的造像風格呈顯7世紀的特徵,但是《高王經》的刻字較古,因此推測《高王經》或爲6世紀北朝所刻,其他部分爲唐初的補刻。(2) 張總2010(24頁)認爲此爲唐代造像經碑,理由不詳。(3) 山崎順平2014根據刻字中的“觀”字的字體變化,推測此碑爲初唐以後的刻字。該碑的圖版收録在Leopold 2009(50頁,第5號展品),拓本圖版收在第52頁,録文見附録Ⅱ(113頁)。另外,張總2010(27—28頁)、山崎2014(52頁)也各有録文,倉本2016(439—446頁)將其用於與東魏本的對校。現依據Leopold 2009拓本圖版、録文,移録該碑所刻《高王經》及刻經題記的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佛説觀世音經一卷,讀誦千遍,得度□□,□□□□□。
觀世音菩薩,南无佛,佛國有緣,佛法相□,□□□□。□
説南无摩訶般若是大神咒,南无摩□□□□□□
咒,南无摩訶般若是无等等咒。淨光□□□、□□□、
師子吼神足幽王佛、高須弥登王佛、法□□、□□□
師子遊戲佛、藥師流璃光佛、普光□□□□□、□□
功德寶王佛。六方六佛名号。東方寶□□□□□□
王佛、西方造王神通焰華王佛、北方月□□□□、□□
无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音□□、□□□
尼佛、弥勒佛。一切衆生,在於土界中者,□□□□□,□□
虚空裏,慈憂於一切,令各安隱休息。□□□□□,□
應誦此偈,消伏於毒害。高王觀□□□□□
淨妙寺比丘尼靜意,爲亡闍黎及亡父□□□□□□
經一卷,願托生西方極樂國土,童子出家,
生同登此福。
8. 房山石經第3洞石刻本(總章二年〔669〕以降刻本)
北京市房山石經第3洞内,分三段鐫刻了三部經 : 上段爲有麟德二年(665)題記的《四分戒本》,中段爲總章二題記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下段爲無紀年但有供養題記的《高王經》。此下另外刻有供養的沙彌僧、童子的名字。中段刻寫的《高王經》起始即曰“佛説觀世音經一卷”,下空一格,繼續寫到“讀誦千遍,得度苦難,拔除生死罪”(下闕);經文迄至“常應誦此偈,消伏於毒害”,下空一格,然後鐫刻尾題“佛説高王觀世音經”;最後另起一行刻寫“易州淶水縣令潘彦真合家供養”題記。可知此石經内容相當於《高王經》。該石經的圖版最早收在桐谷1990(7頁),後又收在《房山雲居寺石經》(隋唐刻經第2册,373頁,“三洞二三八”)。雖然不見紀年題記,但是桐谷1990指出,同石所刻的三經中,第一段有麟德二年銘,第二段有總章二年銘,推測第三段《高王經》的鐫刻年代應該在總章二年(669)以後不久。
該石經的録文,先後登載於桐谷1990(10—11頁)、田村2011(12頁)、山崎2014(49頁),倉本2016(437—445頁)以該本與東魏本對校。現根據《房山雲居寺石經》的圖版,移録此石經本的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佛説觀世音經一卷讀誦千遍,得度

觀世音菩薩,南无佛,佛國有緣,佛法相
師子遊戲佛、藥師琉璃光佛、普光功德
山王佛、善住功德寶王佛。六方六佛名
号。東方寶光月殿妙尊音王佛、南方樹

安隱休息。晝夜修治心,常應誦念此偈,
消伏於毒害。佛説高王觀世音經
易州淶水縣令潘彦真合家供養
9.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阿彌陀造像碑陰刻經本(永淳元年〔682〕刻本)

學界最早提到此碑的是劉淑芬所引謝振發未刊稿,後來倉本2016(437—445頁)採用此碑刻本與東魏本對校。現根據筆者的實物考察,録此碑所刻經文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畫有下綫的文字爲修復接縫處的補刻) :

佛説觀世音菩,讀誦千遍,済渡苦難,拔
除生死罪。觀世音菩薩,南无佛,佛国有

般若是大神咒,南无摩訶般若是大明


弥山登王佛、法藏(護)佛、金剛蔵師子遊戲
佛、藥師琉瑀光佛、普光功徳山王佛、善
住功徳寶王佛。六方六佛名号。東方寶
光月殿妙等音王佛、南方樹根華王佛、
西方造王神通艷十(花?)佛、北方月殿清浄
佛、上方无數精進寶首佛、下方善寂月
音王佛。釋迦牟尼佛、弥勒佛中央。一切
衆生,在佛土界中若(者),行住於地上,及以
虚空中,慈優於一□,令各安隱休息。晝
夜修持心,常應誦往(此)偈,消除於毒害。

10. 俄藏敦ДХ01592號敦煌寫本


薩,南无佛,佛□□□,□法有緣,常樂我緣。佛


□佛、師子吼神足遊王佛、高須弥燈王佛、□
□佛、金剛藏師子遊戲佛、藥師琉璃光佛、普
□□。東方寶光月殿妙尊音□佛、南方樹□
華王佛、西方造王神通焰華王佛、北方月殿
清淨佛、上方无量精進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
釋迦牟尼佛、弥勒佛。中央一切衆□,在於土
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以虚空裏,慈憂於一
切,令各安隱休息。晝夜修持心,常應誦念
此偈,消伏於毒害。
(中空一行)
高王觀世音經
11. 龍門石窟第1861號龕刻經本
據李玉昆編《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録》(1990)(45)李玉昆主編《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的記載,龍門石窟第1861龕中曾經鐫刻著首題“□□觀世音經一卷”、尾題“高王觀世音經”的經本。張總2006(649頁)指出,後來幾經核對,一直都無法確定第1861龕以及李玉昆製石刻佛經表所録路洞的“觀音經一部”的所在。現根據張總2006(649頁)轉録的《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録》所載龍門石窟第1861龕原刻《高王經》的内容如下 :


……觀世音菩薩,南無佛,佛國有緣……

南無摩訶般若是無等咒。淨光……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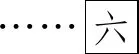
釋迦摩尼……衆生
……有……
晝夜……
艷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精進寶勝



……消伏於毒害。……
高王觀世音經
12. 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本016G號本(803年以後書寫)
中國甘肅省博物館收藏有一件15葉折本寫經(甘博016G),内文連續書寫了《勸善經》《佛説地藏菩薩經》《佛説摩利支天經》《佛説如來成道經》《佛説延壽命經》《佛説續命經》《佛説觀世音經》《佛説智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八部佛經。據《甘肅藏敦煌文獻》(第4卷,373頁)的題解所言 :“本件爲厚白麻紙,繩裝册葉,闕封面。册高14.8釐米,册寬10.3釐米。天頭2.1釐米,地腳1.2釐米,無界欄。單頁書10行至14行不等,行10至16字。共15頁,總173行。”另外,山崎2014(54頁)根據《勸善經》末尾題記“貞元拾玖年廿三日下”判斷,此後收録的《佛説觀世音經》(内文相當於《高王經》)應爲貞元十九年(803)以降的書寫。甘博016G“佛説觀世音經”的圖版,收録在《甘肅藏敦煌文獻》(46)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段文傑主編《甘肅藏敦煌文獻》(全6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卷,141頁)當中。山崎2014(54頁)收録了該經的録文,倉本2016(437—445頁)則採用此本與東魏本對校。現根據《甘肅藏敦煌文獻》公開的圖版,移録此寫本中的《佛説觀世音經》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佛説觀世音經
受持讀誦千遍,得度苦難,拔除生死
罪。觀世音菩薩,南无佛,佛國有
緣,佛法相因,常樂我緣。佛説
南无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
等等咒。淨光秘蜜佛、法藏佛、
師子咒神足幽王佛、告須弥登
王佛、法護佛、金剛護師子遊
戲佛、寶勝佛、藥師琉璃光佛、
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寶
王佛。六方六佛名号。東方寶光
朋殿清淨佛妙尊音王佛、南
无樹根花王佛、西方造王神通艷
華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无
數精進寶手佛、下方善寂月
音王佛、釋迦牟尼佛、弥勒佛。
中央一切衆生,在土界中者,於
地上,及以虚空裏,慈憂於一切,令
各安隱休息。晝夜修治心,常
求誦念此偈,消伏於毒害。
佛説觀世音經一卷
13. 俄敦ДХ.531號本(唐代寫本)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敦煌遺書中,包括一件無紀年的寫本斷片。現存部分不含首題,經文起自“佛説觀世音經一卷受持讀誦千遍”,迄至“神通艷華王佛北方月”,相當於《高王經》的經文。因此,《俄藏敦煌文獻》第6册(47)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第6册(Дх.00001-Дх.00600),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1996年。(346頁)首次公開此本的圖版時,將其定名爲“佛説高王觀世音經”。《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敍録》(上册,496頁)的題解云 :“殘卷,20.5*25。部分手卷,首尾闕。11行,每行16字。紙色白,略發黄,紙質薄。畫行細。楷書。無題字。(8—10世紀)”山崎2014(第53頁)收録了録文,倉本2016(437—445頁)以該本與東魏本對校。現根據《俄藏敦煌文獻》公開的圖版,移録此寫本的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常樂我緣。佛説南无摩訶波若波羅蜜
是大神咒,南无摩訶波若波羅蜜是大明咒,
南无摩訶波若波羅蜜是无等咒。靜光秘
蜜佛、法藏佛、師子咒神足幽王佛、告須弥
登王佛、法護佛、金剛藏師子遊戲佛、寶勝
佛、藥師琉璃光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
德寶王佛。六方六佛名号。東方寶光月
王神通艷華王佛、北方月□□□□、□

14. 法藏敦煌寫本P.3920(推定10世紀寫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中,包括一件無紀年的漢文寫本,編號P.3920。2003年出版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0册(4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0册(P.3917—40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60—161頁。(51—161頁)公開了P.3920的黑白圖版,“高王觀世音經”收録在第160—161頁。另外,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網站上(http ://gallica.bnf.fr/ark : /12148/btv1b8300237j.r=Pelliot%20chinois%203920?rk=21459;2)公開了該本的彩色圖版,並附有詳細題解。據其所言,該寫本的第1—3葉散失,現存第4—221葉(兩面書寫),每葉用紙大約高28.8釐米,寬8.4釐米,推測書寫年代爲“901—1000年”即10世紀。上書十三部密教經典(49)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音經並序》,4—39葉;智通譯《千手千眼觀音經》,40—73葉;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74—86葉;寶思惟譯《隨求即得陀羅尼經》,87—117葉;菩提流支譯《如意輪陀羅尼經》,118—157葉;《陀羅尼集經》卷2《大輪金剛咒》,2行,158葉;不空譯《佛説大輪金剛總持陀羅尼經》,158葉背面—161葉;不空譯《金剛頂經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修習瑜伽迎請儀》,162—176葉;不空譯《金剛頂經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敎王經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修習瑜伽儀》,177—210葉;不空譯《佛説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211—216葉;不空譯《佛説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217—219葉正面;《大威儀經請問》,219葉背面;《高王觀世音經》,220—221葉。,最後一部爲《高王觀世音經》(第220正面—第221葉背面)(50)上述書志信息,引自法國國家圖書館網上公開的題解(2009年9月10日)(http ://gallica.bnf.fr/services/engine/search/sru?operation=searchRetrieve&version=1.2&startRecord=0&maximumRecords=15&page=1&query=%28gallica%20all%20%22Pelliot%20chinois%203920%22%29&filter=provenance%20all%20%22bnf.fr%22)。。以下,略稱P.3920上書《高王經》爲“P.3920G”。繼《中国仏教における疑經研究序説——敦煌出土疑經類をめぐって》以後,牧田諦亮1970再次提及P.3920G。桐谷征一1990則首次登載了該經的圖片和録文,並與《大正藏》本列表比較。李小榮在《〈高王觀世音經〉考析》(2003年)中介紹了一件俄藏敦煌遺書中的《高王經》(俄敦531號)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另外兩件(TK.117和TK.118);並且以法藏敦煌遺書P.3920所書《高王觀世音經》爲底本,以俄敦531號、TK.117、房山(第3洞)石經本、大正藏本對校,推測P.3920G受《神咒經》《佛名經》的影響,具有密教特色(51)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104—108頁;後來收入其專著《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現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網站上公開的彩色圖版,移録P.3920G的内容如下(句讀爲筆者所標) :
高王觀世音經
觀世音菩薩,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淨,有
緣佛法。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
大明咒,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咒,南無摩訶波羅蜜是無等
等咒。南無淨光秘蜜佛、法藏佛、師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須彌登王佛、法
(以上第220葉正)
護佛、金剛藏師子遊戲佛、寶勝佛、藥師琉璃光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
寶王佛、過去七佛、未來賢劫千佛、千五百佛、萬五千佛、五百花勝佛、百億金剛
藏佛。六方六佛名號,東方寶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樹根花王佛、
西方皂王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淨佛、上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下方
善寂月音王佛、無量諸佛、多寶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中央一切衆生在
(以上第220葉背)
佛土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在虚空中,慈憂於一切衆生。各令安隱休息,
晝夜修持,心常求誦此經,能滅生死苦,消伏於毒害。那摩大明觀世音、
觀明觀世音、高明觀世音、開明觀世音、普王如來化勝菩薩。念念誦此
偈,七佛世尊即説咒曰離波離波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羅
帝毗離尼帝莎婆訶
(以上第221葉正)
十方觀世音一切諸菩薩誓願救衆生稱名悉解脱恐有薄福者
殷重爲解脱但是有因緣讀誦口不輟誦經滿千遍念念心不絶
火焰不能傷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莫言此是虚
諸佛不妄説
高王觀世音經一卷
(以上第221葉背)
結語
在本文中,筆者主要以《高王經》先行研究的回顧和現存文本的綜述爲敍述脈絡,大致概括了相關研究的起步和發展。自從20世紀30年代房山石經本《高王經》引起學者的關注以來迄今80年之間,在日本、中國、美國的佛教史學、佛教文獻學、佛教美術史學學者的共同推動之下,該研究課題已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文本的蒐集和整理方面,先學們已經發掘了至少14種北朝隋唐五代前後的文本,包括5種造像經碑本、4種石刻經本、5種敦煌吐魯番出土寫本等。爲了縱觀《高王經》文本的歷史演變和傳承譜系,中日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經本分期理論,對於《高王經》出現的歷史背景、經名的起源、經文的典據等也有深入的討論。
通過前文的綜述,可以看出《高王經》的研究雖然歷經多年和幾個階段的發展,主要的討論依然是圍繞經文和經本的來源和演變而展開。雖有少數幾位學者曾經以《高王經》爲個案或事例來討論中古時代的觀音信仰、疑僞經典、佛教造像、政教關係等主題,但是《高王經》本身的學術意義似乎尚未得以全面地闡發和突顯,也没有引起佛教學界的充分關注。當然,這種現象的癥結所在並不難以解釋。如同筆者在前文中指出的,《高王經》自身的“草根”特性注定了相關研究的難度和特殊性,因爲傳統的佛典研究方法不易見效,現代佛教研究的價值判斷體系也很難評估或突顯《高王經》的學術價值。
畢竟,這部極爲短小的佛經早期版本甚至不足兩百字,主體部分是一系列佛名,内容的絶大部分又都摘抄自其他的漢譯佛典。由於缺乏内容和思想的原創性,在清代以前從未有人做過注釋;現存的中古文獻反復記載著《高王經》的靈驗故事,但是從未提及或在意其經文内容。同時,它又因爲不具備直接的印度淵源而在8世紀時被逐出漢文大藏經系統,喪失了賴以傳承和傳播的正統途徑和官方保障。以上種種不利因素,不但阻礙了《高王經》及其同類“草根經典”在歷史上的傳承,同時也模糊了它們作爲學術課題的當代意義。在至今仍以學派、宗派爲主要框架和脈絡來闡述的中古佛教學研究體系當中,要爲“草根經典”在佛教思想史上找到一席之地確實勉爲其難。反之,處理此類文獻時的尷尬,也顯示出當前中古佛教學研究主流描述的局限性。從這個角度而言,《高王經》等“草根經典”的學術價值和研究意義,可以説恰恰在於“草根”的非主流特性,及其對於佛教學研究方法的主流描述所提出的課題和挑戰。
首先,《高王經》幾乎無處不在的“草根”特性,體現在文本種類的豐富和流傳地域的廣泛。面對《高王經》傳世文本的多元媒介和多姿形態,即使神通廣大的CBETA藏經檢索系統都無能爲力。儘管前輩學者苦心孤詣蒐集了國内外散藏的各種文本,但其絶大多數還僅限於“國産”文本,没有將視野放寬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域外傳本或思考《高王經》在東亞佛教圈的輻射範圍。關注西陲東鄰的出土文物或藏書,對於研究藏外疑僞經典是極爲關鍵的環節和必要條件。《高王經》以其多姿多彩的傳播和存在形態,再次提示了今後的中古佛教研究當中,不能單一或過分偏重刊本系統的文本,石刻、造像、圖像,國内域外的傳本都應該常規性地納入我們的視野。
其次,《高王經》生生不息的“草根”生命力,讓我們確切地感受到所謂佛教“小傳統”的底藴和潛力。稱《高王經》爲“草根經典”,絶不僅僅因爲它是一部中國撰述經典,更因爲支撐它的起源和傳承的最主要的原動力來自社會底層的民間和庶民的信仰。《高王經》作爲《高王經》廣泛流通,當然起源於東魏權臣高歡政治勢力的介入;但是早在此前,它作爲“佛説觀世音經”的一種已經在華北地區有所流傳方纔引起高歡及其幕僚的關注。换句話説,高歡的政治勢力借助了《高王經》在民間的影響力,但他們並非《高王經》的原創或唯一動力來源。現存文本的時代分佈顯示,《高王經》不但没有因爲高齊的亡國而失傳,反而綿延至隋唐時代並迎來自身的鼎盛時期,在武周時代甚至一度華麗升格爲入藏典籍。但是,《高王經》並没有因爲入藏而被束之高閣或開始一脈單傳,有材料顯示,於此同時,《高王經》在民間沉潛著另外一條流傳的趨勢。在《高王經》被逐出藏外以後,兩種本來並行於不同空間的文本開始出現融合的趨勢,並且在擺脱了入藏典籍的禁錮和制約的情況下,經文的内容開始迅速地擴張膨脹以迎合弘法的需要,到明代前後已經徹底轉型爲日課誦本,並向日韓等周邊國家輸出。《高王經》的傳承與傳播軌跡是發人深省的,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政治力量的助力不可否認,但它未被歷史塵埃埋没而流傳至今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其“草根”本質和扎根民間的信仰基礎。作爲中古佛教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的“佛教的經典與詮釋”,有必要安裝更爲廣角的鏡頭,對《高王經》一類的“草根經典”在詮釋、推動和普及佛教方面的貢獻給予公正的評價。
最後,《高王經》的“草根性”還體現在它樹立權威的方式,既不是刻意的印度淵源或思想高度,也不是對於當權者的曲意逢迎,而是通過一則靈驗故事明確表達的針對特定磨難的救贖承諾。這則故事直接關係到《高王經》(“佛説觀世音經”)的來歷,不但在中古時代的正史、僧史資料中多有引用,一些經録也以其爲依據討論該經的真僞,時至宋代甚至有人將這段傳説改編爲序文置於經首,作爲《高王經》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步流通。這種通過靈驗故事確立“經典”權威性的案例在中古佛教中並不常見,也提示我們思考包括靈驗故事在内的志怪、傳奇、民間傳説等“小故事”在鉤沉佛教“小傳統”方面的巨大潛力。
參考文獻 :
北京魯迅圖書館、上海魯迅紀念館
1987年,《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第二函第二册),上海書畫出版社。
陳平
2000年,《河南中小型石窟調查的主要收穫》,巫鴻編《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文物出版社。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俄藏敦煌文獻》第6册(Дх.00001-Дх.00600),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
1997年,《俄藏敦煌文獻》第8册(Дх.01185-Дх.0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
馮賀軍
2005年,《曲陽白石造像研究》,紫禁城出版社。
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段文傑(主編)
1999年,《甘肅藏敦煌文獻》(全6卷),甘肅人民出版社。
金申
2007年,《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 : 珍品紀年圖鑒》,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玉昆(主編)
1990年,《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
李玉珉
2007年,《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35—331頁。
劉連香
2016年,《東魏齊獻武高王閭夫人茹茹公主墓誌考釋》,《華夏考古》2016年第2期,67—73頁。
劉淑芬
2008年,《中國撰述經典與北朝佛教的傳佈——從北朝刻經造像碑談起》,原刊《勞貞一先生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簡牘學報》第十九期,2006年),後收入《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145—167頁。
顔娟英
2008年,《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小榮
2003年,《〈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104—108頁。後收入《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王振國
2006年,《跋龍門石窟兩部觀世音内容的石刻僞經》,《龍門石窟與洛陽佛教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
徐可然
2012年,《兗州金口壩佛教碑刻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張總
2006年,《〈高王觀世音經〉刻寫印諸本源流》,李振剛主編《2004年龍門石窟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648—652頁。
2009年《書評 : 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唐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639—645頁。
2010年,《觀世音〈高王經〉並應化像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沙可樂捐觀音經碑像》,《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24—31頁。
2016年,《疑僞經中的摘抄與編撰例説》,方廣錩主編《佛教文獻研究》(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第1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75—315頁。
中國佛敎協會、中國佛敎圖書文物館
2000年,《房山雲居寺石經》(全30册),華夏出版社。
外文參考文獻 :
泉芳璟
1932年,《仏説諸法勇王經解題》,《国訳一切經》經集部·第十五卷,大東出版社。
大阪市立美術館
1995年,《中國の石佛——莊嚴なる祈り》,大阪 : 大阪市立美術館。
大村西崖
1917年,《中國美術史雕塑篇》,圖書刊行會,1980年復刻。
北村一仁
2008年,《南北朝後期潁川地區の人々と社會——石刻史料手掛かりとして》,《龍谷史壇》第129號。
桐谷征一
1990年,《僞經高王經のテキストと信仰》,《法華文化研究》16號,1—67頁。
倉本尚德
2016年,《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京都 : 法藏館。
齋藤隆一(編)
2013年,《大阪市立美術館山口コレクション中國彫刻》,大阪 : 大阪市立美術館。
田村俊郎
2011年,《中國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高王觀世音經〉とその展開-サンフランシスコアジア美術館所蔵經碑を手がかりに》,日本道教學會《東方宗教》第118號,1—31頁。
藤枝晃
1978年,《高昌殘影 : 出口常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録》,京都 : 法藏館。
2005年,《高昌殘影釋録 : 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京都 : 法藏館。
牧田諦亮
1970年,《六朝古逸觀世音靈驗記の研究》,京都 : 平樂寺書店。
1976年,《疑經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入《牧田諦亮著作集》編集委員會編《牧田諦亮著作集》第1卷,京都 : 臨川書店,2014年。
山﨑順平
2014年,《〈高王観世音經〉の原初テキストについて——南北朝から隋唐の諸本の比較検討から―》,《集刊東洋學》第111號,41—60頁。
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Diana Turner, et al.
1974,Chinese,Korean,andJapaneseSculpture:TheAveryBrundageCollection,AsianArtMuseumofSanFrancisco. Tokyo : Kodansha International, Print.
Leopold Swergold, Eileen H. Hsu, Stanley K. Abe, Wendi L. Adamek, Dorothy C. Wong, and Qing Chang.
2009,TreasuresRediscovered:ChineseStoneSculpturefromtheSacklerCollectionsatColumbiaUniversity. New York : Miriam & Ira D. Wallach Art Gallery.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