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符号物种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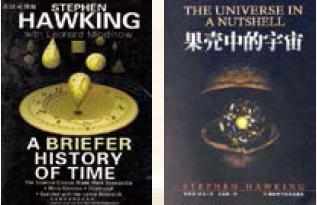


语言和我们的思维认知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有许多非常优秀的科幻作品,都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而在语言学界和认知科学界,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有趣问题。
慕明,曾经的人工智能学生,当下的互联网从业者,尚在入门的科幻作者,利用动态规划写作。相信自己在作品中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过于宏大的愿望,希望用科幻作品连接分离已久的两个世界。
2017年初,电影《降临》甫一上映,就引发了科幻爱好者的热烈讨论。与以物理学、信息科学或者生命科学为切入点的大多数科幻作品不同,这部电影的最大亮点,在于以语言学——这个科幻小说中较为少见的领域——作为构建整个故事的基石。尽管在原著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中,作者也提供了一个物理学上的解释,但无疑,语言决定思维能力这个新颖的设定,使得整个故事散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让许多人惊叹,原来科幻还可以这样写。
那么,这个设定到底仅仅是作者的想象,还是有确凿的证据呢?更概括地讲,语言和我们的思维认知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其实,除了《你一生的故事》,还有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都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而在语言学界和认知科学界,这也是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一个有趣问题。
特殊的礼物
要理解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我们需要先退一步,了解人类的语言从何而来。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技能吗?那些能识别人类口令的类人猿,甚至像在刘慈欣的《鲸歌》中,以音乐进行交流的古老鲸类,它们拥有语言的能力吗?
科幻小说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往往是乐观的,譬如在阿西莫夫的《丑孩子》中,与我们不属于一个物种的尼安德特人小孩也可以在人类保姆的教育下,顺利地学习人类语言。但是,这个问题远比看上去复杂。
首先,是生理学上的特殊性。在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长尾黑颚猴至少有10种叫声,包括对见到的不同物种做出警告,以及从叫声中可以分辨4种不同的社会脉络等等,并且,与人类类似,这些叫声是在年幼时逐渐学会的。有些科学团队训练类人猿学英语,他们都学会了上百个符号的意义。
不过,人类的语言拥有5层结构(语音、音节、字、短语、句子),而类人猿无法将简单的叫声分解为更小的结构单位。尽管它们拥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但是这无法与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相提并论。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已经发现类人猿有与人类惊人类似的布洛卡区,以及左半球优势,但是只有人类进化出了复杂语言。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直立行走解放双手使用工具,双手的使用令大脑的内部结构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人类的声带变化,使得复杂的发音成为可能。镜像神经元(看到他人动作时,在大脑中模仿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感觉)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因素。在進化过程中,这些生理因素相互作用,使语言成了我们人类独有的天赋。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份礼物也同样特殊。语言学界的泰斗乔姆斯基通过对各种语言本身的分析,提出了20世纪语言学界最为影响深远的成果,即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类能够学习到各种文法的普遍能力,是在漫长的进化后,被内建在大脑中的。它被用来解释语言习得的一般过程,说明儿童在发展语言时,使用同一个法则,来学习不同的语言。2002 年,乔姆斯基在一篇与人合著的论文中进一步提出,递归性是人类语言唯一至关重要的特性 。
这一理论刚一问世,就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核心的争论点,就在于语言到底是人类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许多语言学家表达反对,更有些人试图找出一种特殊的人类语言作为反例,推翻乔姆斯基的观点。丹尼尔·埃弗雷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深入亚马孙部族研究当地部落土语毗拉哈,发现这种土著语言不具备递归性,而具有递归性可谓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原理之一。2005 年,埃弗雷特发表论文,向普遍语法论发起挑战。他以自己研究了 30 年的亚马孙部落作为佐证,坚信语言结构并非从头脑中凭空产生,而绝大部分是文化熏陶的产物。埃弗雷特认为,仅仅依据我们具备习得语言的能力,并不能得出 “语言是先天产物” 的结论。 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发现人类盖房子盖得比海豚好,这并不能说明人类与生俱来就懂得建筑学。”
这场论战堪称是语言学界的“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而在科幻小说中,作家们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语言和认知的关系究竟为何。
语言决定论的迷思
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和刘宇昆的《思维的形状》都是基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进行的发散,即语言的决定论下的发散。这个20世纪初期的假说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受到了自己母语的限制和影响。
拥有一种特殊语言,就获得一种特殊的思维能力,这无疑是科幻小说作家喜爱的推论。于是有了《你一生的故事》中使用非线性语言,就可以预知未来的七肢桶;也有了《思维的形状》中,使用连续性语言,就融于集体意识的卡拉桑尼人。
而这个问题的反面——失去一些语言就失去一些思维能力,其实也是小说家早已思考过的问题,尤其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如果一个概念是无法想象的,那么它就必然无以名之;如果一个概念是无以名之的,那么它就无法想象。”这种语言决定论成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预设前提,书中的“老大哥”用消灭词汇的办法来缩小思想的范围。奥威尔预言,如果新话仍保留“free”(自由)一词,但消灭了“自由”的词义,只将它用在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狗身上无虱)这样的句子中,不能用在“pol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 free”(学术自由)的原来意义上,那么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不再存在。在马伯庸的《寂静之城》中也有类似的设定。
但是,当代的研究者并不这么认为。著名的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中说,奥威尔错了。“即便取消了‘自由‘平等等名词,这些概念依然会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之中……由于头脑中的概念远远多于语言中的词语,而且听者总是会主动地填补说话者未说出的信息,因此,现有的词语将很快获得新的意思,甚至会很快恢复它们的原始含义。”
在科幻小说中,张冉的《以太》正是这个理论的一个体现。失去了大部分词汇的人们,通过在手指间画出符号的方式交流,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些早已被禁止的爱和信仰。
平克指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语言决定思想”,因为“认识决定感知、理论决定观察、文化决定价值、阶级决定科学、语言决定思想”这类相对主义理论已经成了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习惯了“文化决定行为”的固定思维,容易忽视天性在人身上的作用。
而他认为,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属性,而并非文化的产物。就像大象能用鼻子来移动物体,蝙蝠可以用声呐判断方位一样,语言能力是人类大脑中与生俱来的精密构件,无须刻意学习。这种通过推测得来的进化语言观,是乔姆斯基思想的一个有力延伸,虽在学界依然饱受争论,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许多实证研究从根本上推翻了萨丕尔-沃尔夫的强假设——“语言结构决定人类思维”的理论。通过对大量人类群体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语言里缺失“左”和“右”的词汇并不代表着母语者就无法区分左右、进行旋转;语言里不区分“蓝”“绿”的土著居民也并不是蓝绿色盲,他们同样具有将蓝色毛线和绿色毛线分别归类的能力。
但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弱假设,也就是“语言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类行为”这一点,却依然在学界里有着强烈的争议,因为一系列意图验证这一假设的实验都有了支持它的结果。最经典的实验当属相对位置的表述,母语中强调“东西南北”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绝对方向描述,而母语里经常使用相对方向的人则会以“前后左右”作为描述的基准。这么看来,母语在词汇上、结构上出现的区别,的确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人类的行为。
一些語言学家据此给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修正版,即Boas-Jakobson 原则(Boas-Jakobson principle)。这个原则认为,语言的不同导致它们所必须传递的信息的不同,而不是它们能够传递的信息的不同。举例来说,母语中不强调“东西南北”的人,可能对绝对方位的敏感程度不如母语中强调“东西南北”的人,在回忆某地点的方位时,往往不会以绝对方位作为记忆的坐标,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理解“东西南北”的概念。
作为符号物种的我们
现在,让我们暂且放下争论,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既然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如此复杂,那么,假如我们将这种关系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语言与认知演化的关系,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究竟是新语言会造就新物种,还是新物种会发明新语言?
从第一部分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本身生理结构的特殊性,是语言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但是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难道六万年前的一次突变,使我们的祖先具有了发出复杂声音的能力,然后,精妙瑰丽的人类语言结构就“砰”的一声出现在古老智人的大脑中了吗?
在对人类神经和认知系统的基础研究中,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人类的大脑具有极其强大的可塑性和适应性。这意味着,环境的影响是任何认知功能研究中都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对人类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尤其重要。
许多科幻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描摹了环境影响导致的语言变化。擅长以人类学家视角描写幻想世界的厄休拉·勒古恩在《恩纳·穆穆伊的语言》中描述了一种非常复杂奇异、难以理解的语言,但是这种复杂性的由来令人惊叹。恩纳·穆穆伊人的祖先认为,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太复杂、太难以生存了,于是就消灭了所有没有用处的生物。
“他们将一个极其复杂的样本简化为一个完美的样本。整个世界成了一个绝对安全的看护室——在这里人们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做。
“但是,恩纳·穆穆伊人比他们的祖先更聪明,至少是在某些方面更聪明。他们用某种无限复杂、无限丰富而又没有任何逻辑用处的东西,将这个世界又变得复杂了,他们用的就是语言……他们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的繁茂而又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他们仅有的丛林和荒野都在他们的诗歌当中。”
这样的独特想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其中蕴含的思考是深刻的:厄休拉意识到了环境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一定是正反馈。并不是环境越简单,语言也越简单,一种环境越简单,语言越复杂的负反馈,可以使得这个世界呈现出非常迷人的特质。相比之下,雷·布拉德伯里在《黑皮肤,黄眼睛》中提到的火星移民代际间的语言演变就显得较为常规了。
科学家的想象更加动人。行为神经科学家Terrance W. Deacon提出,人类大脑和语言是协同演化的。他认为,原始语言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在一代代演化的过程中,具有较强语言能力的人类群体占据了竞争的优势。早期人类可能通过一些简单的符号化声音进行沟通,这样能提高沟通的效率和准确性,于是这些种族容易在群猎中获得更多的猎物,减少族人损失,对比那些不进行符号化声音沟通的种族,生存下去的可能就要大得多。于是经过万年的淘汰,生存下来的种族都是进行符号化语言沟通的种族。这是“鲍德温效应”的直接体现。“鲍德温效应”是指,没有任何基因信息基础的人类行为方式和习惯,经过许多代人的传播,最终进化为具有基因信息基础的行为习惯的现象。由于“鲍德温效应”,一部分基本的语言能力被写入基因,即乔姆斯基和平克认为的普遍语法,促使大脑发展区域化和结构化;而更多具体的语言要素,则以学习的方式代代延续,演化。在语言和大脑的演化上,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拉马克观念的体现,即“用进废退”。只不过,这并不是大自然的选择,而是人类社群内部的自我选择。
大自然母亲为我们铺开了一张白纸,是我们自己在上面画出了无限的图案。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人类的身体也许会与机器完美结合,人类的语言也会像《艾比斯之梦》里描写的那样,与机器语言融为一体。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这个已知世界中唯一拥有语言的物种,将仍然与它相依相伴,直到永远。
主要参考资料
《话/镜》, 盖伊·多伊彻
The Symbolic Species: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Terrence W. Deacon
《语言本能:探索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史迪芬·平克
Fisher, S. E., & Marcus, G. F. (2006). The eloquent ape: Genes, brains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7, 9-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rg1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