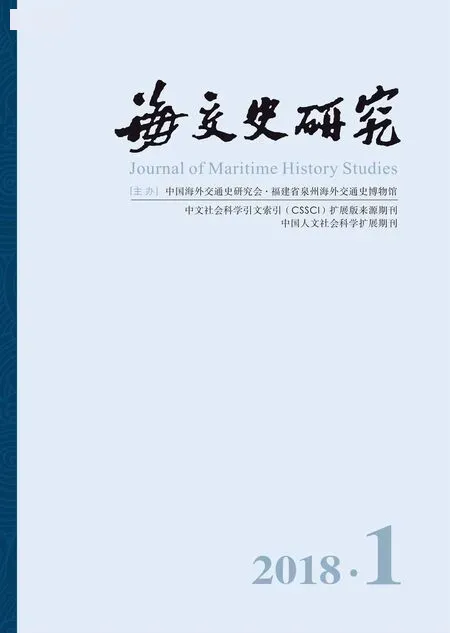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译注》中对“ÇAITON”的考释*
[法]保罗·伯希和 著 叶妮雅 译
在《马可·波罗游记》不同语言的译本中,“Zaiton”有不同的写法,如:F版,即佛朗哥-意大利语版本(Franco-Italian Version):airon、çaitem、 çaiton;LT版,即拉丁语版本:cacar、çarcairon、çarton、 çayton、zayton;VB版,即威尼斯语版:caiton;P版,即弗朗西斯科·皮皮诺(Francesco Pipino da Bologna)拉丁文译本:caycan、zaytem; TA版:即托斯卡纳语版(Tuscan Version):charia、zanto、zaton、chatan、zartom、zaito、zaiton、zarton;V版,即存于柏林国家图书馆的威尼斯语版本:marchon、zaitore、zandon、ziargati;Z版,即存于西班牙托莱多(Toledo)的拉丁文版本:caytum、çaintum、çaitum、çaytum、çaytun、zaytun,等等。*译者注:这段文字为译者根据原文中“ÇAITON”的不同写法进行重新整理而成。

早在1655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他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AtlasSinensis)》关于 “Civencheu”一节中提出将“Zaiton”认定为位于福建沿海的泉州。德金(De Guignes)也同意他的观点。*Hist. gén. des Huns, III, 169.后来,克拉普罗特(Klaproth)于1824年7月发表在《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的文章中*Journal Asiatique, V [July 1824], 41-44;又见XI [1833], 342.,注释说“Zaiton”是刺桐Tz’ǔ-t’ung的音译写法,《大清一统志》中记载“刺桐”为泉州的旧称。这一认定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为学者们所接受,直到菲利普斯(G.Phillips)和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以及后来的沙海昂(Charignon)才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克拉普罗特可能是对的,尽管他的论证中还有一些薄弱之处。
首先,克拉普罗特犯了个错误,他引用一份近代土耳其地理资料作为“Zaiton”的独立资料来源,事实上,这份资料中相关讨论的章节几乎是对马可·波罗所记录文字进行逐字逐句的重译*在Pauthier (G.),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Paris, 1865, 2 vol., 528, 及菲利普斯在T’oung Pao(1895, 455)中都还沿用克拉普罗特的观点;参阅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ed. Cordier), London, 1921, 2 vol., II, 230。。此外,克拉普罗特将“刺桐”误解为两种不同的植物,即“荆棘和毛泡桐”。遗憾的是,鲍狄埃(Pauthier)*Pauthier (G.),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Paris, 1865, 2 vol., 528.、考狄埃(Cordier)*L’Extrême-Orient dans l’Atlas Catalan, 32.和布罗切特(Blochet)*Blochet (E.), Djami el-Tévarikh,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onde par Fadl Allah Rashid ed-Din, tome II, Leiden-Londen, 1911, II, 490.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但刺桐是一种带刺树种的名字,在这里或许叫Acanthopanax ricinifolium*但这种植物还称为Erythrina Indica,桑原(Kuwabara)在Mem.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bunko, II[1928],30中就是采用这个名称。更合适。克拉普罗特认为,刺桐是泉州的旧称,因该市环城墙种植刺桐树而得名。
玉尔(Yule)一直以来也支持“Zaiton”就是泉州的说法,他认为,根据克拉普罗特的观点,刺桐曾经是泉州真正的官方用名;而泉州一名早在“7世纪或者8世纪”就已经存在,刺桐这一名称的采用及其作为“Zăītūn”过渡到外语中必定要追溯到很早的时期*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ed. Cordier), London, 1921, 2 vol., II, 237.。当然,克拉普罗特在阐释时,并没有把刺桐用作城市名的本质和缘由讲清楚。杜嘉德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Zaiton”并不是刺桐,而是“刺桐城”,并且它只是一个别称而不是真实的名字*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ed. Cordier), London, 1921, 2 vol., II, 236.。沙海昂甚至说从来没有刺桐城一说,只有“桐城”,而“桐城”一词却无法确定为“Zăītūn”的词源。沙海昂认为该名字真正的词源是“瑞桐”,夏德(Hirth)在一本1274年的文献中发现用“瑞桐”称泉州,而沙海昂则在一部现代中文文献中也看到了相同的用法。但是沙海昂犯了个错误。在1274年的文献中并没有提到“瑞桐”就是泉州;夏德在他自己的一条注释*T’oung Pao, 1894, 388;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6, 73.中用括号标出泉州又名瑞桐,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参考文献。两年后*T’oung Pao, 1896, 224.,菲利普斯回应夏德的这条注释,他说他通读关于福建的各种主要文献,但从未看到有瑞桐一说。我想这首先是夏德的误解,之后是沙海昂。在克拉普罗特发现“刺桐”一说的《大清一统志》中,关于“刺桐”的引文中紧接着讲到如果刺桐先长叶而后开花,则五谷丰登,“因此刺桐又称为‘瑞桐’(意为‘吉祥桐’)”。这里似乎没有谈到城市名,大概沙海昂引用的现代著作也是同样的情况。甚至阿奈兹(Arnaiz)在《通报(T’oungPao)》(1911, 679)中引用了近代地方史专著《晋江志》中一段类似说法的文字,但我认为“瑞桐”仅仅是“刺桐”的别名,而不是阿奈兹在译文中所说的城市名。
至于沙海昂提出的“刺桐城”不存在,而只是“桐城”一说,《大清一统志》中抄录的引文的确只写了“桐城”,明代《泉南杂志》也只提到“桐城”,在现代词典《词源》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的“桐城”这一词条也引用了该出处。但是杜嘉德已经讲到“刺桐城”,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第431页和713页也将“刺桐城”作为“桐城”的另一种说法。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刺桐城”一词可追溯至宋代。在1221年编撰完成的《舆地纪胜》中,在索引“刺桐城”条目下,有一首赞美刺桐的诗;而另一首写于12世纪中期的诗中,写到了作者偶尔在刺桐城与朋友会面。此外,在其它地方也有相似的地名。翻阅地理辞典,不难发现就有云南的刺桐关、安徽的桐城县和山东的桐城镇。
然而即使那样,也还存在着两个问题:(1)刺桐(城)这个名字是不是有可能是外国人用来称呼一座城市的?(2) “Zăītūn”是不是“刺桐”的正规译法?
第一点不太好确定。泉州作为一个官方用名,最早出现于大约585至606年间,从623年起成为正式的名称。但是到711年之前,都是作为现在福州的名字,711年才转而指代现在的泉州。在唐代的文献中似乎没有出现任何与“刺桐”有关的城镇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这一说法是宋代形成的。《大清一统志》卷328中的引文,克拉普罗特作了部分翻译,原文引自1239年完成的70卷地理专著《方舆胜览》。书中记载,“州之城墙,留从效重加版筑,傍植刺桐环绕,得名桐城。(其木高大而枝叶蔚茂,初夏开花极鲜红)如叶先萌芽而其花后,则五谷丰熟; 反之则不然,因称瑞桐。”留从效卒于962年,其城墙筑于943至958年间。泉州的刺桐一定是很有名,完成于1270年的辞书《尔雅翼》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刺桐出泉州,花先叶后,则五谷熟。” [该说法一定有误;与上文中引用《方舆胜览》的记载恰好相反,而《舆地纪胜》卷130中引用的一首写于大约公元900年的诗也和《方舆胜览》的说法一致;参阅《通报(T’oungPao)》,1911,679]。《舆地纪胜》卷130中提到“刺桐”环绕和桐城的名字,但是没有谈到留从效发挥的作用和“瑞桐”的别称。再者,这些也不是泉州城仅有的名称。《大清一统志》引用《古地名词典》中的记载,五代时,该城又称为葫芦城,因为城墙并不是方形的;后来城墙部分重建后,又称为鲤鱼城。我还要补充的是,10世纪时,该城筑有三道同心城墙,976年城墙已完全崩塌损毁。1221年的《舆地纪胜》索引词目“刺桐城”下所引用的诗就是有关城墙损毁的挽歌。至于现代的城墙,即“鲤鱼状”城墙*Ecke and Demiéville, 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 24.,是1352年由偰氏家族的一位高官“回纥人”扩建的。调查后可以得知,泉州城曾有过好几个不同的名称。在中文里,“城”这个词指城墙和城墙所包围的城市。当然这些名字与行政中心的官方名称无关,但它们可能都曾广泛使用。也许有人看到宋代文献中提到更多的是“桐城”而不是“刺桐城”时,会感觉有点不安。此外,令人有些惊奇的是,即使是说“刺桐城”, “城”字也往往被外国人忽略;如果我们猜想中国人更普遍的是单独使用“刺桐”一词,也许会更安心些。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足以让我们反驳克拉普罗特提出的“Zăītūn”等同于“刺桐”的说法,即使是在发音方面(菲利普斯试图解释说Zăīitūn是漳州话“月港”的写法*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 42; T’oung Pao, 1890, 229-231.,这点不需要讨论;再者,参阅《通报(T’oungPao)》, 1911, 690-691 中阿奈兹的文章)。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Zăīitūn”是不是“刺桐”的正规音译法?我暂且不考虑考狄埃的观点*Odoric de Pordenone, 271.,考狄埃认为阿拉伯人把泉州称为“刺桐”,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橄榄”和“橄榄树”,因为他们认为泉州的刺桐树是橄榄树的一种。然而刺桐树与任何一种橄榄树完全没有共同点,“Zăītūn”要么是“刺桐”的音译法,要么和它没有任何语义或者其它方面的联系。但是这是一个好的译法吗?如果是,如何考证它的时间?
费琅(Ferrand)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从“刺桐”入手,他认为“Zăītūn”是“Zitūn”的误写,他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Relationsdevoyages)》一书中采用了“Zītūn”的写法,他认为从比较语音学上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不能肯定地说这是令人满意的改写。如果关于留从效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么泉州作为“桐城”或者“刺桐城”的记载不会早于10世纪;而且在13世纪之前没有关于“Zăītūn”的记载。但是所有的资料,包括穆斯林和欧洲的资料,都只有“Zăītūn”“Zaiton”,从来没有写到“Zītūn”。克拉普罗特*Journal Asiatique, v [July 1824], 43.和鲍狄埃*Pauthier (G.),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Paris, 1865, 2 vol., 528.引用阿布·菲达的一篇文章,讲到旅行家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念起来就像阿拉伯语的“橄榄”一词“zaītūn”[这不是引自兰纳德(Reinaud)和古亚德(Guyard)翻译的地理书]。安德烈·佩鲁贾说这个地方波斯语里称为“Zaiton”*Wyngaert (A. van den), Sinica-Franciscana, Itinera et relatiene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III et XIV, t. I, Quaratchi, 1929, 374.。该名称的发音有可能受到阿拉伯语中“橄榄”一词的影响,但事实是在当时,该名称就读为“Zăītūn”或者“Zaiton”,因此我们应该保留这一写法。
但是,即使不考虑“-a-”,该音译法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从克拉普罗特开始,到后来的鲍狄埃、布罗切特*Blochet (E.), Djami el-Tévarikh,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onde par Fadl Allah Rashid ed-Din, tome II, Leiden-Londen, 1911, II, App. 48.和费琅,“刺桐”一词的音译写法,读起来都像是tzǔ-t’ung。现在tzǔ-t’ung应读为ts’ie-d’ung;如果是10世纪前的读音转译,我们大概会写作sidun。由于这一形式可能是10世纪后传播到国外的,正常应写为situn,而不是zītūn或者zăītūn[正如ts’an ( 刺桐即泉州,这一观点的两位主要反对者是杜嘉德和菲利普斯,他们都支持“刺桐”是位于厦门西南方的漳州的说法。他们的主要论据有: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对漳州港的高度赞赏更胜于泉州港;漳州曾在元代多次与泉州交替作为省会;后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经常谈到的大港“Chincheo”,玉尔起先认为是泉州,但事实上是指漳州;“Zaiton”在元代曾是重要的基督教中心,在漳州曾发现中世纪的基督教遗迹,而泉州则没有;最后伊本·白图泰讲到Zăītūn的纺织品,这只能是指漳州的纺织品。尽管玉尔一直坚持泉州一说,但在晚年他也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至于考狄埃,1891年他在译注《鄂多立克东游录(OdoricdePordenone)》时毫不犹豫地支持泉州一说;1895年,他又宣称支持漳州说法*L’Extrême-Orient dans l’Atlas Catalan,33.;1903年修订玉尔的著作*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ed. Cordier), London, 1921, 2 vol., II, 241.时,又表现出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阿奈兹在《通报(T’oungPao)》(1911,678-704)的文章部分反驳了菲利普斯的观点。但是那篇文章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连考狄埃在修订玉尔的《马可·波罗之书(TheBookofSerMarcoPolo)》时都没有提到它。因此,我将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时会引用一些新的资料,会比1928年桑原在《东洋文库欧文纪要(Mem.oftheResearchDepartmentoftheToyoBunko)》中的探讨更加详尽(II,30-33)。 漳州入海口,连同发达的厦门湾,组成了一个宏伟壮丽的大港区,其规模是泉州无法媲美的,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情况去推断几世纪前的情况,当时泉州港的泥沙淤积并不像今天发展得这么快。实际上,在中国中世纪的文献中,泉州的重要性远高于漳州。市舶司设立于外国船只到访的主要港口。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但很快就撤销;1103年,又重新设立,之后迁往北部的福州港;1132年,迁回泉州,继续保留其官方用名“福建路市舶司”。1225年,赵汝适从来泉州贸易的外商中收集资料,并编纂成《诸蕃志》时用的就是这一名称。蒙古人征服华南后,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1277年设立四个市舶司,其中就有一个在泉州。到1293年,市舶司发展到七个,但是并没有在漳州设立市舶司。此外,直至1293年,泉州市舶司一直享有特权:其它六个口岸对进口粗货征收的关税是总价值的十五分之一,而在泉州口岸只要征收三十分之一。这看起来确实像是南宋朝廷的政策,试图尽可能地将对外贸易集中在泉州。例如,1178年,三佛齐(巨港-占碑,Palembang-ambi)的使团来朝,皇帝不想让使团进宫,下令在泉州招待来访使节。1278年9月8日,忽必烈在泉州赐予航海女神崇高的封号,1288年、1299年、1329年和1354年朝廷又多次给予加封。 在我看来,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中世纪对外贸易的主要中心不是在漳州,而是在泉州,因此泉州就是Zăītūn。但是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菲利普斯的其它论据。 拉希德·丁*Blochet (E.), Djami el-Tévarikh,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onde par Fadl Allah Rashid ed-Din, tome II, Leiden-Londen, 1911, II, 490.在介绍中国的省份时有关于福州和Zăītūn的一段文字*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ed. Cordier), London, 1921, 2 vol., II, 239; Yule(Henry),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ed. Cordier), London, 1913-1916, 4 vol., III, 126. 玉尔在以上两本书中关于Zăītūn的译文,是在克拉普罗特的译文基础上进行的翻译,是不准确的;D’Ohsson (Baron C.), Histoire des Mongols, Amsterdam, 1852, 4 vol., II, 638,这译文也不太令人满意。:“第七个省是福州市所在的省,福州是蛮子的一个城市。以前的省会设在那里,后来迁到Zăītūn;但是现在又迁回福州。”即使是从这么一段不全面的译文中,玉尔推断出,拉希德关于福州和Zăītūn的描述,与鲍狄埃从有关中文史料翻译的福州和泉州的记载,有着惊人的相似。菲利普斯*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XXIII[1889], 24-27; T’oung Pao, 1890, 234.提出反对的依据是,在元代,漳州也曾几次成为福建的省会,因此它很有可能就是拉希德所指的Zăītūn。阿奈兹*T’oung Pao, 1911, 686.回应菲利普斯,认为他引用的资料,很可能混淆了地名,这一反驳并不恰当。当然,阿奈兹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菲利普斯认为他的资料来源于1328年的文献,但该文献中引用了1369年修撰的《元史》内容,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菲利普斯所指的这份文献的真正来源是明代编修的。但是这部明代修撰的文献所提及的资料已经修订过了。这就是《元史》卷12中写的:“三月……壬午(至元二十年,1283年4月26日),罢福建道宣慰司,复立行中书省于漳州。”不要忘了元朝的行中书省,或者简称行省,后来改名为“省”,几乎可以等同于“省”。《元史》中的记载也许让人感到意外,初看起来似乎让人很难想到这是一处误读。相同的文字不仅出现在《元史类编》中,也许它仅仅是照搬《元史》,菲利普斯还引用了另外一段文字,遗憾的是这段文字的真实出处我已无法考证。根据这段文字的记载,“漳州行省”应该是1280年就已经存在;这段文字还解释说,“漳州行省”经过暂时的废止之后,是如何在1283年又复立的。在这一点上,我仍然持有一定的怀疑,在下文中我将进一步说明。无论如何,1283年以后该“行省”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因为在《元史》卷62中,此后的行政地理资料里没有任何该“行省”的记载。如果漳州行省存在,也许只不过是个“分行省”,因为元朝似乎再次经历了叛乱,而这次叛乱最终导致了朝代的灭亡。*Phillip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XXIII[1889], 26 但是只有泉州,在蒙古人占领华南后的头几年中与福州交替作为福建真正的“行中书省”,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一直很密切。正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泉州这个名字起先是福州的官方命名,到711年,这个名字才转给现在的泉州。当蒙古人来到长江以南,为了管理最新占领的省份,采取了许多临时措施,我们可以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一些线索,尽管这些线索并不充足。《元史》中的地理部分只是详尽地记载蒙古统治半个世纪后的行政区划设置,以下是关于一些行省不断变化的记载(虽然并不全是正确的)(均见《元史》卷62):“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相当于杭州行中书省,忽必烈后,福建是该行中书省的一部分)……福州路……宋为福建路。元至元十五年(1278)为福州路;十八年(1281),迁泉州行省于本州(即福州);十九年(1282),复还泉州;二十年(1283),仍迁本州;二十二年(1285),并入杭州”“泉州路……元至元十四年(1277),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1278),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1281),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1282),复还泉州;二十年(1283),仍迁福州路”。 毫无疑问,这与玉尔的结论相一致,《元史》中地理部分记载的泉州与福州交替成为行省,正好与拉希德·丁所指的Zăītūn与福州交替成为行省相呼应,而这再一次确定了Zăītūn就是泉州的说法。但是正如《元史》地理部分总结的那样,“行省”的历史只是一种粗略的近似;真正的事实是更加错综复杂的,我们无法总是能追溯全部的细节,在《本纪》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如下: 1.《元史》卷10,第198页:“三月乙酉(至元十五年,1278年3月26日),诏蒙古带、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1278年9月18日,唆都和蒲寿庚升任行中书省,但是文中并没有提到具体地点。 3.《元史》卷10,第203页:“七月……丙申(至元十五年,1278年8月4日),以右丞塔出、[左丞]吕师夔、参知政事贾居贞行中书省事于赣州(江西赣州府),福建、江西、广东皆隶焉。” 4.《元史》卷10,第209页:“二月……甲申(至元十六年,1279年3月20日),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行]省造战船六百艘。”汪辉祖在《辽金元三史同名录》评论说,此处“赣州”有误,应为隆兴,因为行中书省所在地已于1279年2月18日下令由赣州迁回隆兴。 5.《元史》卷11,第221页:“正月……甲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2月23日),敕泉州行省,所辖州郡山寨未即归附者率兵拔之,已拔复叛者屠之。” 6.《元史》卷11,第222页:“正月……戊辰(至元十七年,1280年2月27日)……置行中书省于福州。” 7.《元史》卷11,第223页:“四月……丙申(至元十七年,1280年5月25日),以隆兴、泉州、福建置三省不便,命廷臣集议以闻。” 8.《元史》卷11,第224页:“五月……癸丑(至元十七年,1280年6月11日),福建行省移泉州。” 9.《元史》卷11,第225页:“七月……己酉(至元十七年,1280年8月6日),徙泉州行省于隆兴。” 10.《元史》卷11,第230页:提到“福建[行]省左丞蒲寿庚”上奏朝廷。 11.《元史》卷12,第246页:“九月……壬申(至元十九年,1282年10月18日),敕平滦(在河北)、髙丽(韩国)、耽罗(济州岛)及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最后三个地名显然是行省名。 12.《元史》卷12,第251页:“三月丁巳(至元二十年,1283年4月1日)……罢福建市舶总管府,存提举司,并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这说明,与地理部分的说明相反,泉州“行省”与福建“行省”曾并存。 13.《元史》卷12,第252页:“三月……壬午(至元二十年,1283年4月26日),罢福建道宣慰司,复立行中书省于漳州。”菲利普斯间接引用了该文。 14.《元史》卷13,第264页:“二月辛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2月19日),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徳为泉州行省参知政事。” 15.《元史》卷13,第269页:“九月甲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10月19日)……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行省左丞忽剌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徳分省泉州。”江淮是行省名,设治扬州,1284年迁至杭州,改名江浙行省。1286年迁回扬州,1287再次改称江淮行省。1289年第二次迁往杭州,1291年又改名江浙行省,该名一直保留到元末。 16.《元史》卷13,第272页:“正月……乙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2月27日)……卢世荣请罢福建行中书省,立宣慰司,隶江西行中书省。”根据以上相关的资料,1285年撤福州行省,并入杭州。汪辉祖在《元史本证》卷26中认为杭州是错的,应该是江西。 17.《元史》卷15:两次提到福建行省,时间分别是1289年2月11日和3月6日。因此,福建行省一定是1285至1289年间复立的;但是《元史》的各章节中都没有讲到这点,根据《八闽通志》第一章中,1328年《三山续志》的引述,福建行中书省复立于1286年。 18.《元史》卷16,第344页:“二月……癸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3月6日)……改福建行省为宣慰司,隶江西行省。”这一点已在《三山续志》中证实。 19.《元史》卷17,第359页:“二月……乙亥(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3月2日)……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邓州旧军万户史弼、福建行省右丞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爪哇……”高兴的传记中证实福建“行中书省”复立于1292年。这可以解释为中国舰队从福建出发前去征讨爪哇的一项应急措施。 20.《元史》卷19,第409页:“二月……己未(大德元年,1297年3月20日)……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兴言泉州与瑠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21.《元史》卷20,第426页:“二月……丁巳(大德三年,1299年3月8日)……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从《元史》卷134中阔里吉思的传记看来,当时福建从属江浙行省即杭州。大约1330年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元史》地理部分后来采用的资料就是在那时编纂的。 22.《元史》卷44,第929页:“春,正月,壬午(至正十六年,1356年2月2日),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为福建行中书省。”有可能1356年复立的福建行中书省设置于泉州,正如1297-1299年间那样。这样的话,菲利普斯提到的1358年的分行省将是指同一个福建“行中书省”,但是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我也无从证明这点。 菲利普斯提到的1363年(笔者认为应该是“1362年”)分行省曾设于漳州,对此我也无法找到任何的线索。在《本纪》卷46中,1362年日期不详,我只找到1362年5月24日,“泉州赛甫丁据福州路,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之。(赛甫丁)余众航海还据泉州,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陈友定复福州路。”*译者注:这与1976年中华书局的记载有出入,伯希和引用时是“复福州路”,中华书局《元史》卷46,第959页则是“复汀州路”。1357年赛甫丁叛乱并占据泉州,也许正是考虑到赛甫丁的叛乱,“福建行中书省”从泉州撤出,在漳州设立“分行中书省”。 尽管还缺乏一些小细节的论证,但我认为我们的信息已经很全面,足以确定主要的事实真相。上述20余处文字提到“行中书省”在福州和泉州的更迭,但整部《元史》中仅有一处提到“行中书省”在漳州。第13条说1283年4月26日“行省”复立于漳州,而《本纪》中却没有更早记载,说明其存在或者撤销。另一方面,第12条说1283年4月1日泉州“行省”废止,我们又看到1284年2月相同的泉州“行省”又复存在(第14条),但是没有提起这之前的复立。如果我们仅有《元史》,很有可能会轻易认为1283年4月26日的文字记载有误,以为当时复立的是泉州“行省”而不是漳州。此外,还有一段出处不明的记载,指出漳州“行省”1280年应该已经存在了;而菲利普斯提到的漳州设立“分行中书省”是在1362年。汪辉祖在《元史本证》卷26中,接受了1283年4月26日在漳州复立行省的说法,但是没有其他资料来佐证。我也接受这一说法,尽管有一些顾虑。我们还遇到许多其他情况,《本纪》中的记载并不完整。再说,尽管“行中书省”在那时几乎等同于省,但它们起先是作为应急机构,在特定情况下设立,在没有必要时撤销。在征讨华南时期,可能在漳州曾设有一个“行中书省”,但存在的时间很短。更令人费解的是1362年的漳州“分行中书省”;然而,元末的叛乱四起,类似于扩张征服时期的应急措施很有可能也会被采用。无论如何,这个漳州“行中书省”只可能是临时特别设立的机构,并不同于那个时而设在福州时而设在泉州的机构,后者一定就是拉希德·丁提到的福州和Zăītūn省。 菲利普斯支持漳州的下一个论据是在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资料中频繁提到“Chincheo”;起先玉尔认为“Chincheo”是泉州,而后又认为是指漳州。但是这与Zăītūn的问题并没有很大关系,因为16、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家看到的情况可能与13、14世纪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此外,玉尔自己也承认,他对这两个地方到底哪个是“Chincheo”感到困惑。对此,我也有同样的困惑。我无法肯定所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作者所说的“Chincheo”指的是同一个地方。至少有些提到“Chincheo”的实际上指的是泉州*Yule (H.) et Burnell (A. C.),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Terms, London, 1903, 200.,但是这些文章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其中并没有任何有助于Zăītūn的解读。 大量支持泉州反对漳州的论据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即使是马可·波罗提到的关于瓷器产于与“Zaiton”同省的城市“Tingiu”一说,或者是伊本·白图泰关于Zăītūn纺织品的记载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结论。“Tingiu”的问题我将在另一词条中加以讨论*见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中词条“Tingiu”。。我需稍加说明,这里谈论纺织品,并不是要以此来论证对“Zăītūn”的认定,只是因为该话题本身有些意思。 菲利普斯试图证明漳州丝绸生产业的发展程度远高于泉州。*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XXIII[1889], 28-30; T’oung Pao, 1895, 451-452.19世纪末,漳州的丝绸织造业很发达,这看来是事实,但这也许要归因于一位地方官的一时兴起。*Arnaiz, in T’oung Pao, 1911, 689.事实上,这两个地方的桑树都生长得很好,尽管都不及其在更北一点地区的生长情况。8世纪上半叶,福州和建州将塔夫绸作为贡品上供朝廷,而不是泉州或者漳州。此外,外国人不太可能给同样的物品取过多的名称而使自己陷入混乱。泉州、漳州以及福建其他地方生产的绸缎可能都统称为“Zaitunese”,因为它们是从“Zăītūn”运往海外的。事实上,我估计,称为“Zaitunese”的丝织品中有许多是建宁生产的织锦。*见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中词条“Camut”和“Quenlinfu”。 Zăītūn这个名字在近代初就不再使用了。但是,就像玉尔在《马可·波罗之书》*Yule(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ed. Cordier), London, 1921, 2 vol., II,239.中所写的,它是如何于16世纪末出现在波特罗(Botero)的著作《环球行纪(Relazioneuniversale)》中,被定位于广东和宁波之间的,至今仍然是个谜。在1595年的《阿克巴宪法(īn-iAkbarī)》中,书中关于Zăītūn的描述也仅仅是文学性的,并不真实。但是在16世纪流行的这样一个词可以让人记起Zăītūn曾经的辉煌:第一时期的西南季风当时称为mavsin-iZăītūnī,即“刺桐季风”*Ferrand (G.), 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du VIIIe au XVIIIe sièle, Paris, 1913-1914, 2 vol., 486.。 伊本·白图泰*transl. Defrémery and Sanguinetti, 269.说,在泉州穆斯林有他们自己的城。无论这个摩洛哥人*译者注: Moor在英语文献中指摩洛哥人,也曾用来指在11-17世纪创造了阿拉伯安达卢西亚文化、随后在北非作为难民定居下来的西班牙穆斯林居民或阿拉伯人,是西班牙人及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the Moor,这里指的是伊本·白图泰本人。对中国的“Pintoan”描述是否属实,他在这点上讲的差不多是实话,因为大部分外国人,包括穆斯林,都居住在泉州的南郊,一个叫做泉南的地方*参阅Hirth,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6, 75; Ecke and Demiéville, The Twin Pagodas, 4.。在1225年的《诸蕃志》中,赵汝适谈到一个阿拉伯人在城外东南角建了一个外国人公墓;这个阿拉伯人自己就住在泉南*Hirth (F.) and Rockhill (W. W.), Chau Ju-kua, St.-Petersburg, 1911, 119.。在该书的另一个章节中,赵汝适又提到两个南毗人(Namburi,马拉巴尔海岸的婆罗门),父子俩,在“泉之城南”安家,这个名称显然是指泉南*Hirth (F.) and Rockhill (W. W.), Chau Ju-kua, St.-Petersburg, 1911, 88.。泉南这个名字后来还一直沿用。上文中,我间接引用了明代文献《泉南杂志》中的一句话。 说到非汉族部落如云南西南部的金齿(“Çardandan”)和上东京(“Caugigu”,Upper Tonking)族群时,马可·波罗描述了纹身的做法,但是只有在“Çaiton”这一章节中,他提到纹身在中国本土使用;来自上印度(“Upper India”)的人让本地艺术家给他们的身体纹身上色!我没有其他关于在泉州纹身的资料。但在《元典章》卷41中,讲到这么一件古怪的事,1309年杭州有个人强行在他的妻子背部和大腿上纹上蓝色的龙和魔鬼图案,让她裸露游街;更有甚者,他还打他的岳母,最后他被处刑87大板,他的妻子被送回娘家。 马可·波罗谈到“Çaiton的五座非常壮观的大桥”,最大的“长达三英里”。由于这段文字仅出现在Z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拉丁文版,现存于西班牙托莱多。中,因此玉尔自然没有对此作出评论;但是里奇(Ricci)和罗斯(Ross)、彭泽(Penzer)或贝内代托(Benedetto)都没有任何阐述。我并不是要辨别出所有的桥。但其中有一座一定是顺济桥,它建于1211年,横跨泉州城南的晋江,位于通往漳州的公路上*参阅《大清一统志》,328,6 a;Phillips在T’oung Pao(1894,7)中写的Shun-chih-chi’ao[顺治桥]是错误的,尽管Ecke在Sinica(VI,296)中引用了该写法;正确的写法见Ecke and Demiéville, The Twin Pagodas, 4 and Pl. 6 a。。至于那座“长达三英里”的大桥,当然是著名的洛阳桥或称万安桥,它建于泉州湾北端的洛阳江上,位于通往福州的公路上,是早期中国工程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桥建造历时六年,始于1053年,1069年竣工,是在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蔡襄*Giles,Biogr. Dict. No.1974.的倡导下修建的,蔡襄是仙游(位于泉州边界东北面)人。我们很难估算马可·波罗所谓的“三英里”的真实长度,但是中国的文献中记载该桥长达3 600英尺,一英尺约长七分之五英里。菲利普斯*T’oung Pao,1894,7.称1575年(不是“1577”)到访福州的奥古斯丁神父(the Augustine Fathers)曾描述过该桥。但是这需要我们默认假设门多萨(Mendoça)书中提到的“Megoa”是指泉州,而“Megoa”看起来更像是兴化,哈克路特学会(Hakluyt Society)的编辑在出版门多萨著作时就说明了这点。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肯定是泉州的描述,同时也是一个极富兴趣的描述,出自卫匡国1655年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AtlasSinensis)》。卫匡国曾两度过桥。他还记录说逆流和顺流处,桥墩呈斜角,他的描述与马可·波罗当时的一段未被人熟知的文字几乎相同。艾克(Ecke)*Ecke,Sinica, VI, 271-272, 296, and Pl. 22, 4; 23, 9 and 11;Ecke and Demiéville, The Twin Pagodas, p. 4 and Pl. 71 a.进一步提供了洛阳桥的详细情况和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