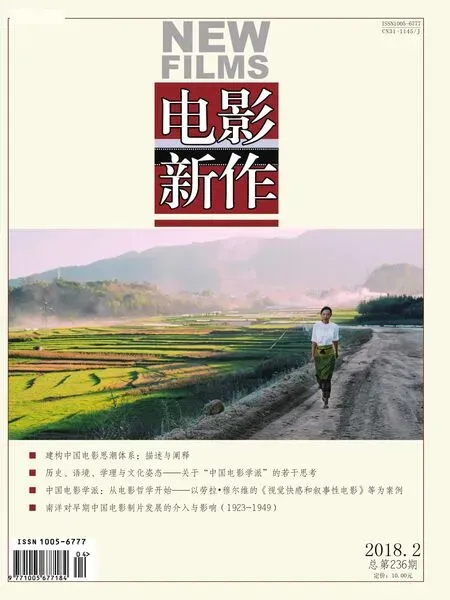《暴裂无声》:悬念、叙事与视觉图式
李啸洋
《暴裂无声》的上映,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一方面,忻钰坤的《暴裂无声》继续用《心迷宫》里的悬念叙事,悬念叙事的偏移、分叙与相斥,引发观影的别样体验;另一方面,影片直接指涉现实,暴力和人性的暗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般的情节,以及电影呈现和底层社会的道义焦虑,成为电影表现的另一重维度。《暴裂无声》不同于《心迷宫》,它不再是环形的、纯悬念的,它超越了悬念叙事层面,试图意指更深刻的社会存在。本文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电影叙事和叙事表征的意义。
一、悬念分述与叙事偏移
法国叙事理论家热奈特认为,叙事包含了三重话语。热奈特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能指”,指出事件本身和本意叙事构成了第一重话语;第二重话语是“所指”,指人物和关联性事件,包括事件之间的连贯、反衬、重复等不同的关系。叙事的第三层话语,是热奈特所言的“叙述”,即“生产性叙述行为”和“行为所处的或真或假的总情境”。
《暴裂无声》的因果叙事链如下所示:矿业老板昌万年爱射箭,但因箭数不准,本来目标是一只羊,却误射中张保民的儿子;律师徐文杰看到昌万年射死人的这一幕;昌万年为了脱罪要挟律师,抓走了律师的女儿;律师害怕自己的女儿会有同样的下场,而张保民阴差阳错救了律师女儿;陈述真相时,律师选择了沉默,张保民虽然知晓真相,但他无能为力,只能痛哭无声。在这个序列里,热奈特所言的“生产性叙述行为”,始终萦绕着悬念“麦格芬”。《暴裂无声》中的生产性叙述行为,使用了一系列的场景、动作、台词来维持。
查·德理(Charles Derry)在考察美国悬念和惊险电影之后,给出了他对悬念的定义:“悬念是我们在两种不同的、都会造成紧张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时持续的犹豫。从某种意义上讲,悬念是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恐惧所造成的持续冲突的复杂消长过程。”《心迷宫》里,围绕着情欲、死亡、罪恶,“麦格芬”的环绕与游弋,激发了观众的“猜谜”,从而引发出好奇、担忧、恐惧与同情等诸多情绪体验。
悬念的生产问题上,《暴裂无声》采取了与《心迷宫》同样的策略:嫁接。嫁接重赋了悬念的危险系数,也重构了电影的时间序列。《暴裂无声》的意义生产,借助于符号、姿势、图像以及嫁接性的道具编织。电影中,符号和戏剧性动作的嫁接共出现了四次:一次是张磊失踪之后留下的奥特曼面具,这个面具日后反复出现在另一个小孩的手中,成为叙事编码的一条线索;另一重嫁接,是杀人者昌万年射箭的动作,“开弓”动作不断被小孩模拟;第三重嫁接,是对两个小孩失踪的嫁接;第四重嫁接,是“证据”的嫁接,昌万年所说的“我要的东西在你那儿”,电影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证据”到底是指他射杀了张保民儿子的证据,还是弘昌矿业吞并金泉矿业的证据?这个概念“麦格芬”,是虚指的,它保持了悬念的暧昧,引发观众的焦虑体验。
布朗克的隐喻理论中,理据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基本主词引发次要主次的部分特征;第二,建立一套平行或者与基本主词相符合的隐含结合体;第三,同时诱发次要主词中的相似性变化。理据是修辞学的概念。它是引发本体和喻体之间的重要纽带。何为理据?理据即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构成了修辞格。《暴裂无声》围绕“昌万年弓箭射杀小孩”的戏剧性动作,不断使用各种情境来模拟、回溯、再现这一场景。小孩拉弓和昌万年的拉弓,共同构成悬念的情节性要素:发现、重复、模拟。电影里,戴奥特曼面具的小孩拉一张空弓,做出射箭的动作,电影结尾时,小孩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死亡拼图,还原了整个凶杀现场。昌万年的弓箭和设计动作,在各种场景中循环、变化,并以此推进电影叙事。“拉弓”动作的相似与变化,不仅牵引电影悬念、维持紧张感,也在生成悬念的同时来暗示真相。不过,忻钰坤对这个“麦格芬”的使用较为飘散,它去掉了戏剧动作的核心要素,更多时候,维系断断续续的戏剧性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场景,它提示、暗示观众“这里有戏”,让观众下意识地将小孩拉空弓和昌万年是实体弓箭联系起来。这是叙述边界地带的暧昧设置。小孩拉空弓的整个戏剧性动作,成为整个叙事驱动链条里一个独立的齿轮。因为自始至终,整个独立的场景都是以旁观、提示者的身份出现,它散漫地镶嵌在电影不同的视点中,必要的时候成为解谜电影悬念的序列信息。更多时候,小孩拉弓是顺应了悬念表演。电影的结尾,昌万年并没有交代他杀死张磊的事实,真相被掩盖了。小孩在黑板上画出真相,“空弓”姿势与昌万年的“实弓”构成了一对平行的戏剧动作,观众唯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才能鉴照真相。
刘子曦探讨了“社会叙事”的四个特征:普遍重要性、具体时间性、内在因果性与潜在反抗性。《暴裂无声》的悬念分述,无法在情绪体验上产生《心迷宫》一般令人惊讶的效果。《心迷宫》悬念产生的好奇,使观众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卷入好奇的漩涡。好奇的漩涡指向了情绪的惊险体验。《心迷宫》里的真相,是罗生门式的,怀疑式的,游戏式的,在不同的见证者那里真相有着不同的面目。《暴裂无声》则以解释和揭示真相为最终目的。忻钰坤预先用三个人物预设了三种身份:张保民是底层人,话语权缺失;徐文杰是律师,代表了法律和正义;昌万年是矿业集团董事长,用利益操纵社会。电影中张保民在路上举着照片拦截大卡车,企图寻找儿子的下落,但寻子未果。电影接入了另一条线索“你在村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导演用这个悬念分述出张保民和村长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条线索也交代出村长和弘昌矿业是利益共同体。这是一条辅助线索,它看起来更像导演特意设定的一个意义参数。这个悬念是偶发性的事件,它要和下一条真正的线索组合起来,拼凑成故事的全貌:张保民的好友栓子来他家送药,他指着日历上一辆白色的轿车说:“看见一辆银灰色轿车,不是本村的。”有了这一条线索,电影才开始走出悬念哑谜,进入真正的追逐,遂有了摩托追逐轿车、山洞藏人的情节。可以说,前一条线索是事先安插的、偏移在故事线以外的悬念假设,第二条线索才是“实证”的,它扭转了故事的依赖路径,从而完成故事的形塑。《暴裂无声》关注的真相不像《心迷宫》一样,会让观众长舒一口气,而是背负了沉重的社会悲剧。《心迷宫》是一部典型的希区柯克式的悬念电影,《暴裂无声》则像是社会新闻和日常经验构型的故事:寻人启事,矿山吞并,法律隐恶。悬念暗箱与偏移,为故事引入社会层面的思考:矿山黑吃黑、底层失声、贫富差距以及正义丧失。
二、符号、暴力与动作隐喻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划定出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在索绪尔的基础上,罗兰·巴尔特将符号视为系统,他将符号系统分为语言和言语。巴尔特的语言系统是一种“社会性的制度系统”,也是一种值项系统。言语是一种个体行为和个体选择,言语因组合而成。
《暴裂无声》中,羊肉和三角形构成了电影意义的符号系统。电影开始时,导演用大篇幅影像营造羊肉这种意象,不论是羊肉馆里钩子钩挂的整排羊肉,还是案板上被切分的羊肉,抑或是肉卷机里被削片的羊肉,羊都是一项重要的隐喻。“羊”代表弱者,象征着被宰割、欺辱。电影里,昌万年逼迫金泉矿业的老板就范,逼迫其吃肉,金泉矿业的老板说:“我信佛,吃素。”昌万年把羊肉卷塞到他嘴里,说:“这个习惯可不好,羊,也吃素。”血红的羊肉营造出一种不祥的氛围,伴随电影声音的渲染,羊暗示了血腥和死亡。电影中段,磊子失踪,他给小羊在家里搭了一个小窝。电影结束时,他的母亲抱着羊羔哭泣。羊羔就是失踪的磊子的象征,羊羔代表了希望,也代表了希望的破灭。
电影符号学家麦茨认为,电影符号学的最大障碍便是研究“符号的动机”和“意义的延续问题”。《暴裂无声》里,围绕羊的符号群都是描述的语义群,三角形符号则构成了麦茨所言的“叙述的语意群”,“叙述的语意群”下辖了“轮替(叙述)语意群”和“直线叙述语意群”。除却羊,三角形也是一个重要的符号。三角形符号和三角形人物关系,延续了电影的意义生成。三角形象征着稳定,也象征着暴力。电影开始,磊子摆出的石头图就是一个三角形,他的背景则是三角形铁塔。此外,昌万年的办公桌上摆设的也是一个三角形的金字塔。
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结合了结构主义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所创造的结构主义模式,发展出符号分析的格雷马斯矩阵图。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中,叙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即结构叙事的主要矛盾。“非x”是指与“x”有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的矛盾。“非反x”与“反x”构成了叙事结构的次要性矛盾。正是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双重推动下,叙事才得以曲折展开。三角形是一个稳固的象征,电影中底层人张保民、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律师徐文杰三者构成了重要的三角矩阵,三角建立起一种时而聚合、时而离散的关系。三角关系的轮值、转换、比照,使得电影的戏剧性张力大幅度增加。围绕“孩子失踪”这一情节,电影编织了张保民、徐律师和昌万年三个人的复杂关系。三角关系的对峙与矛盾,在森林射杀一场戏里显得尤为突出。这场戏中,悬念的“麦格芬”集中爆发。故事的真相是“x”张保民和杀死张保民之子的“反x”昌万年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三人对垒的戏剧性高潮里,电影又嫁接了“非x”律师徐文杰和“x”张保民之间的次要矛盾。真相的显与隐、模糊的证据、作证与否、知与不知都囊括在这场戏里。麦茨所言的“意义的延续问题”,在这场戏里得到了最深刻的探究。这场戏将电影关于真相和意义的追问,推至了最高潮,并通过电影语言、符号和动作姿态等混合使用,使得这一场戏集体爆发,开掘出电影叙事的深层内涵。
除了两个符号,电影中的“哑”和“吃”也构成了动作隐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到:“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电影中,张保民的“哑”,本身就象征了底层社会的失语状态。寻找真相未果,正义受阻,这些都在张保民的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除了“哑”,《暴裂无声》中的另一个重要的隐喻动作是“吃”。昌万年出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嘴巴的特写:他在大口吞噬一个鲜红的西红柿。他给学校捐款,因为将西红柿的汁水滴在了衣服上,照相的时候把王校长的衣服穿在了自己身上。这个“遮”的动作,揭露了他的性格——好面子、霸道。电影里,最契合昌万年动作的,就是吃羊肉,饕餮般地吃。“吃”构成了一种隐喻。贪吃、暴力、吞并矿业公司、隐匿杀人案件共同构成了罪恶图景。不论是吃西红柿、吃羊肉,还是吞并小矿业公司,电影展现给观众的是一种“食物链”的连环效应。
暴力问题也是《暴裂无声》探讨的一个重命题。电影中的暴力短、平、快,风格类似于韩国电影。德国哲学家康德将“超验”(Transzendent)和“先验”(Transzendental)区别开来,认为“先验”虽不一定来自经验,但也不与经验违背,而且是在经验发生之时感性同时起作用的东西。先验是在经验界限内知识之先天可能和先天使用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形式的规律,它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和普遍有效的。《暴裂无声》中的戏份是现实经验的,也是先验的。宋洋饰演的张保民,形象和动作风格上很容易让人想起韩国电影《老男孩》《卑劣的街头》《坏小子》等。电影中的暴力是感性的、经验的,没有太多形式化的套路渲染,而暴力动作更多的是信手拈来。电影后半段的砸办公室、烟灰缸砸脑袋,暴力的日常性和突发性显得尤为明显。《暴裂无声》中的暴力,用“暴力美学”来称呼似乎并不恰当,因为它既无法像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那般触发观众的复仇快感,也不能像吴宇森的《英雄本色》那样凸显男性气质。
三、声音、空间与社会记忆
听是寻找发音声音的聆听;语义聆听用来解释解码信息,简化聆听则将声音(口语、声响等)作为被关注对象本身。《暴裂无声》的配乐统摄在悲剧性的主题之下,电影里没有设置固定的听点,而是与使用一种弥散的、环境的声音。声音内聚于视觉和感知的整体之中,合成器的声音架构出戏剧性空间,也拓展了电影的情绪氛围。声音扩展了叙述环境,变成一种持续的状态。电影中,环境声音是诡异的、潜伏的、危险的,如果去掉影像,电影中的配乐颇具恐怖片的特征。但是,配乐加入了苍凉底色,为影片着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德勒兹将电影定义为“用运动与任意瞬间对接来复制运动的系统”。《暴裂无声》的配乐充满流动感,也颇具实验性。该片的配乐师王宇波说:“我会着迷于声音的结构,用极简的方式构建多元的空间和潜藏于人内心深处,深层的情感波动与平静。我渴望真实,而真实本身就是刺痛的。”电影中类似于机器的轰鸣声和开矿声都较为压抑,却成了银幕叙事的扩展。在电影叙事中,时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概念。同样作为环境声,《暴裂无声》与好莱坞电影的音响效果并不尽不同。时频表示频率和频度,《暴裂无声》用简单、重复的声音频度和回环声,制造出声音的回响效果,声音起到了渲染效果。
《暴裂无声》的情节设置,可以找到许多“事件原型”。这些事件原型构成了记忆原型,将电影指向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暴裂无声》里,使用了诸多的社会日常事件,包括逼迫钉子户签约、煤矿事故、打猎误射、寻子未果、开矿污染、律师被捕,这些情节均能在社会新闻中找到原型。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瓦布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讨论了家庭集体记忆和社会集体记忆。他认为,人的记忆都是经过一定的文化构型进行“重建”的。这种重建,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比如习俗、礼仪、仪式等。个人记忆通过这些组织性和仪式性进行记忆规划,从而达到强化集体记忆的目的。电影重构了社会性记忆,并使之重新成为影像记忆的一部分。社会记忆在一种互动的框架之下,完成了认知、强化与重构现实的认知。电影当中,底层张保民、中层律师徐文杰、上层富人昌万年,分别构成了电影的象征部,凝聚成电影想要探讨的正义、金钱等关系之力。沿着这些时间原型,电影形构出了这样一则故事:张保民是底层平民,因为不服从矿业集团利益分配,拒绝签订契约。矿业老板昌万年非法采矿,为了矿难和杀人消除罪证,他要挟律师徐文杰合作。矿业老板昌万年爱射箭,但箭法不准,其目标本意是一只羊,但是却误射中人。昌万年要徐文杰处理和掩盖的,到底是矿难,还是杀人案件?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影在这些事件中投射的社会记忆,也形成共同的记忆肌理。
忻钰坤的电影构型,在剧作上以社会为参照体系。电影以叙事的连贯性与社会互蕴为因果,电影中悬念的出发点,都围绕现实社会的具体事件而展开。电影中饶有意味地加入了一个动画片的形象:奥特曼。奥特曼在电影中生成了形而上的意蕴。奥特曼是卡通形象,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张保民背的书包、屠夫儿子的面具、电视动画片,奥特曼都成为一种真相存在的象征。忻钰坤在映后会上,回答设置奥特曼形象的问题:“为什么是奥特曼呢?它在动画片里其实是一个超人的形象,它是简单的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但是影片里面我们是在描写成人世界的复杂。而这样一个真相其实对人有特别大的杀伤力。孩子戴着一个超人的面具游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无能为力,到最后他也只能袖手旁观。这其实会让观众觉得很揪心。”
电影里奥特曼出现场景颇多,而奥特曼也只是一张面具。面具象征了一种面对真相的无力感。奥特曼的面具,既是一个表征被遮蔽的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再现凶杀现场的过程。电影是个逐层逼近真相、用符号拼图的过程,山川崩塌使得张磊死亡的真相成了迷局,但导演还是给观众留下一丝希望:虽然张磊失踪了,但是律师徐文杰找回了他的女儿。电影结尾,一直戴着奥特曼面具的小孩终于卸下了面具,真相也终于天下大白了。“象征不是任意的,某些象征总是具有物质对象,或者具有一个感觉形象,而这个感觉形象是一个‘观—念’,尤其对于某个语言共同体来说,象征图式是人们能够共同看得见的信念。”象征呈现的是观念部分和精神的部分,担当着精神层面的秩序建构。“奥特曼”形象是正义的象征,它以正义者的身份,充当见证者。
《暴裂无声》使用了回忆、追溯、超现实等多重电影手法。在电影正式进入叙事之前,即张保民正式寻找儿子张磊之前,电影的剪辑有很大的跳脱感。这种跳脱感,源于导演对多元故事空间的容纳与吸收。所以,观众才会看到张保民一会在矿坑里和人打架,一会在餐馆里和别人打架。“重新衔接才有无穷的方式。这是一个潜在的关联空间,一个纯可能发生的地点,事实上,不稳定性、异质性、某一空间的关联缺失所表现的,往往是一笔潜在的财富”。在电影中,任意的空间也创造出了意义的关联。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小孩的空间交汇上。张磊和爰爰共同出现在山洞里,导演将现实与超现实两个空间并置在一起,令电影充满了迷幻色彩。张磊和爰爰共同上山的那一段影像,很像亚历山大·罗戈日金的电影《春天的杜鹃》。《春天的杜鹃》里,女主人公用鼓声召魂;《暴裂无声》里磊子的魂魄也将爰爰带到了高地上。不过,这段很快复归于现实。电影用山洞的崩塌和爰爰的苏醒,暗示张磊已经去世。两种空间使用超现实的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叠合手法,创造出惊人的艺术效果。空间表征意义,就是一种精神状态。空间的创设,将电影的戏剧性焦点放在情感的感知上,空间的规划与安排,让电影主题和精神得以延续。空间创造出独特的图谱,也创造出忻钰坤区别于其他导演的视觉图式。
【注释】
①[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
②[美]查.德理.论悬念惊险电影[J].世界电影,1992(6).
③Black.M.Models and Metapho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
④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J].社会学研究,2018(2).
⑤[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5.
⑥[法]克里斯蒂安·梅茨.电影的意义[M].刘森尧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5.
⑦[法]克里斯蒂安·梅茨.电影的意义[M].刘森尧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27.
⑧[法]格雷马斯.论意义[M].泓缈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45-14.
⑨[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3.
⑩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