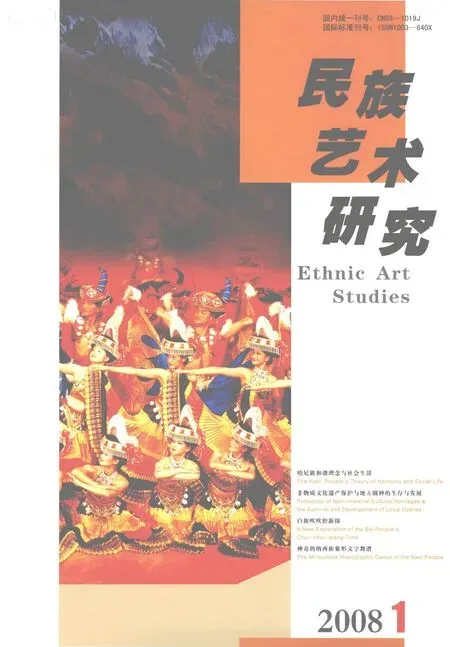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民族舞蹈学”学科建构的若干思考
——从“非遗名录”舞蹈“进校园”谈起
于 平
一、“非遗法”与“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传统舞蹈”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即“非遗法”。该法在第一章《总则》中指出:“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还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在定义“非遗”后,这里的“三性”指的是保护“非遗”的原则,而“三个有利于”则是强调“非遗”保护的功效。
在“非遗法”的第三章,阐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务院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作为“非遗名录”的最高层级,这个名录的产生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从本级“非遗名录”中择优、择重推荐而成。也就是说“国家级非遗名录”是自下而上、逐层推荐的结果。这项“推荐”工作,一要介绍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二要介绍项目的传承范围、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三要提出保护应达到的目标和应采取的措施。
其实,“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推荐与核准,早在“非遗法”通过之前的2006年就公布了首批“非遗名录”。这一批“非遗名录”于该年5月20日公布,共518项;此后第二批510项于2008年6月14日公布,第三批191项于2011年6月10日公布,第四批153项于2014年7月16日公布。按照第二批之后三年一核准的规律,今年早些时候就应该公布第五批了;但现在第五批“非遗名录”正在公示之中,这次是将“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结合在一起公示的。这说明公布“非遗名录”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而且在于“传承”,“传承”才是最有效的“保护”。其中“非遗名录”项目“进校园”就是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
上述四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舞蹈类共有131项,约占10%左右;在四个批次里分别是41项、55项、15项和20项。如果按地区分布来统计,排前三位的分别是云南省(24项)、西藏自治区(18项)和四川省(12项);接下来是广东省(9项),然后是并列的湖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均为7项);均为6项的还有河北省、浙江省和甘肃省,另有山西省、陕西省和河南省均为5项。如果按民族属性来统计,最多的是藏族——除西藏地区本身的18项外,云南迪庆、青海玉树也共有“锅庄舞”;四川芒康则共有“弦子舞”,另有“跳曹盖”;青海省还有“藏族螭鼓舞”。云南省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传统舞蹈”项目最多,且占这一类别的六分之一,这其中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舞蹈——其中彝族有9项(铜鼓舞、葫芦笙舞、烟盒舞、打歌、跳菜、老虎笙、左脚舞、乐作舞、三弦舞)之多,其余有傣族2项(孔雀舞、象脚鼓舞),哈尼族2项(棕扇舞、铓鼓舞)以及佤族木鼓舞、傈僳族阿尺木刮、基诺族大鼓舞、纳西族热美蹉、布朗族蜂桶鼓舞、普米族搓蹉、拉祜族芦笙舞、怒族达比亚舞等。这其实意味着,“传统舞蹈”作为“非遗名录”的丰富性与多民族文化共存的丰富性是密切相关的。顺便说一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示的舞蹈方面的“代表性传承人”共有124人。其中各种“龙舞”有14人,各种“狮舞”有7人,各种“灯舞”有6人,各种“鼓舞”有5人;另有“花鼓灯”5人,“秧歌”4人,“高跷”4人,“竹马”3人,傩舞“3”人;少数民族舞蹈的传承人以藏族为最多,有18人;其余土家族有6人,维吾尔族有5人,蒙古族有5人,彝族有5人,瑶族有5人……
二、“原生态舞蹈”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正是由于“非遗法”的立法和“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公布,通过课堂传授、校园传承成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乃至一条重要路径。“非遗名录”中的“传统舞蹈”,在相关院校的专业教学中被称为“原生态舞蹈”;而所谓“原生态”,指的是由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自发参与、自主传承、自然变迁。既往的专业舞蹈工作者也深入民间直面“原生态”,直面这样一种稚拙而朴素、率性而真诚、鲜活而生动的文化资源——或稍加整理呈现于舞台,或借用“图式”风化于创作,或提取“舞动”适用于教学……在我们既往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也把进入课堂的教材称为“代表性”舞蹈——这既是从众多“原生态舞蹈素材”中选择出来的“代表性”舞蹈,也是未来用于“舞台化创作”典型呈现的“代表性”舞蹈素材。
然而,对于当下的“非遗名录”舞蹈“进校园”,由于强调“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实质上在于强调用“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知道,人类把自身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来加以审视,迄今不过500年历史。威廉·A·哈维兰写道:“1534年,雅克·卡蒂埃为法国实地考察圣劳伦斯河,使得他接触了一些原住民群体成员。这种接触引发了他对其他民族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导致了人类学的发展。”后来得到充分发展并得以不断完善的“人类学”,使命在于“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试图形成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可靠知识——既涉及使他们相区别的东西,也涉及他们共享的东西。”*[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我们知道,“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上位学科。但一般认为:“人类学被划分为四个领域:体质人类学和三个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主要研究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研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类。”*[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事实上,“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种族中心主义”挑战,因而大可不必过于将其与“研究生物有机体的人”的“体质人类学”并置一处,尽管也有学者认为人的“生物特性”与其“文化”会交互影响。“文化人类学”范畴中的“文化”,被设想为“通常无意识的准则”,是作为初级社会形态的“族群”运行的“准则”。所谓“挑战种族中心主义”,是指“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之间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却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文化’。”*[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就“文化人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而言,“考古学”主要通过物质遗存研究过去的文化;“民族学”则专门研究现在的文化,因而又被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我看来,这个“现在的文化”是指“历史传承到现在的文化”,是至今仍存的活态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就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时期以来,不少舞蹈学者积极参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高扬起“舞蹈人类学”的旗帜;准确地说,这个“舞蹈人类学”就其关注的对象而言,其实指的是舞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舞蹈的“民族学”。舞蹈的“民族学”作为学科建设可借鉴“音乐”相关学科建设的办法,仿效“民族音乐学”而建构“民族舞蹈学”。这其中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是“民族音乐学”还是“民族舞蹈学”的学者,都是相关学科的民族志学者,都是以“田野工作”作为最基本的工作。
三、萨克斯《世界舞蹈史》开“民族舞蹈学”之先河
“民族舞蹈学”的学科建构可以参照“民族音乐学”。伍国栋指出:“‘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一学科名称是一个复合词语,它由‘民族学’(ethnology)和‘音乐学’(musicology)两个词汇复合而成。虽然这一复合词汇在中国音乐学界已通常被译作‘民族音乐学’,但亦有部分学者认为将它译为‘音乐民族学’更为妥当……但无论如何,这种从‘民族音乐学’到‘音乐民族学’的词序组合变化选择,其主旨都是想要突出本学科‘民族学’与‘音乐学’相结合关系中的‘民族学’内容,同时从字面上又可与当今已普遍采用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形态学’等音乐学分支学科称谓相并列、相对等而处于同一学科层次……由于‘民族音乐学’突出了‘民族学’内容,而‘民族学’在社会科学中又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子学科或本身也可被视为是‘人类学’,因而与近亲的文化学、民俗学等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某些国外的音乐学著述中,此学科和与此学科研究领域相同的课题,同时还有‘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音乐民俗学’等称呼不同而学科性质基本相同的表述。”*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通过研究,《民族音乐学概论》对学科做出了以下定义:“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族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的理论学科,田野考察是其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将所考察和研究的音乐对象,视为是一种音乐事象,倡导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个体或群体)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建构、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类型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类型的基本形态特征、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可以看到,这个定义基本上是用“民族学”(也即“文化人类学”下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音乐学”的考察和研究。作为“艺术学”学科门类下同一级学科的“音乐与舞蹈”,如果将上述定义中的“音乐”换成“舞蹈”,基本上可定义“民族舞蹈学”。
伍国栋在回顾“民族音乐学”的简史之时,指出其前身的学科被称为“比较音乐学”。这个萌芽于18世纪中叶的“比较音乐学”,主要是“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并以某种音乐传统的音乐作为参照系去看待和观察另一种音乐传统的音乐的。”*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的、后来被称为“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家,有一位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 1881—1959)其实也可视为我们“民族舞蹈学”的先驱者。由他所著《世界舞蹈史》在《序言》中所说:“‘艺术’一词不能阐明舞蹈的全部概念……舞蹈打破了肉体和精神的界限,打破了耽溺于情欲和约束举止的界限,打破了社会生活和发泄个人特性的界限,打破了游戏、宗教、战争和戏剧的区别,打破了一切由更为高级文化形成的各种界限……人类需要舞蹈,因为对生活的热爱也迫使四肢不再懒散;人们渴望跳舞,因为跳舞的人能获得魔力,为自己带来胜利、健康和生活乐趣;当同一部落的人搀着手一起跳舞时,便有一条神秘的系带把整个部落与个人联结起来,使之尽情欢跳——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德]库尔特·萨克斯:《世界舞蹈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很显然,这种不能被“艺术”一词阐明的“舞蹈”,只能用“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来阐明。
库尔特·萨克斯继续指明:“从我们未开化的祖先传下来的舞蹈,是一种有层次表现精神极为兴奋时的活动情况,后来扩展到祈求神明,扩展到自觉地力求成为控制人类命运的超人力量的一部分。舞蹈变成了供奉牺牲品的祭仪,变成了表现念符咒、做祈祷以及先知预言的活动;舞蹈成为能召唤和驱散自然界的力量,医治疾病,能使死者和他们的子孙取得联系;能保证提供营养物,在追逐中交好运,在战斗中获胜利;可以赐福于田地和部落,是创造者、保管者、侍者和保护人……在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与古代文明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比舞蹈更具重要性的事物……舞蹈不是一种仅为人们所能容忍的消遣,而是全部落的一种很严肃的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生活里,没有任何场合离得开舞蹈:生育、割包皮、少女献身祭神、婚丧、播种、收割、庆祝酋长就职、狩猎、战争、宴会、月亮盈与蚀、病患——在所有这些场合,都需要舞蹈……舞蹈是拔高了的简朴生活——这种说法道出了舞蹈固有的全部特征和最完整的含义。但是它还可扩大到从科学这个领域来思考,只是不能根据这种思考给它‘下定义’罢了。这种定义是不容易确定的;事实上分析到最后,也许会得到‘下定义’是不可能的结论。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应该抛开刻板的仓促的分类法——工作和娱乐、法律和自由可融为一体,而这种觉察不到的融合可能就是舞蹈的主要特点。因此从确定的意义来讲,给舞蹈下的定义不可能比‘有节奏的活动’更严谨……”*[德]库尔特·萨克斯:《世界舞蹈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很显然,库尔特·萨克斯从“‘艺术’一词不能阐明舞蹈的全部概念”出发,最后得出“给舞蹈下的定义不可能比‘有节奏的活动’更严谨”的认识,其实也就是今日“民族舞蹈学”对其更为广袤的视野而形成的更为深邃的认知。
四、民间舞蹈的“动态切入法”与“文化类型划分”
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以“民族舞蹈学”目光从事研究工作的专著应该是罗雄岩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该书前言中写道:“半个世纪以来,在民间文化与各民族淳朴民风的陶冶下,笔者由一个民间舞蹈的学习者,转变为民间文化的研究者;同时深深感到,我们这代人既然有幸学习了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就该系统地研究它们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民族审美情趣,建立与之相应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新学科……1986年,笔者在北京舞蹈学院开始讲授《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课程;此后,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学科的理论结构与研究方法……以舞蹈文化的特殊性、民间舞蹈文化特征、中国原始舞蹈遗存、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类型、‘动态切入法’为基础理论;以可操作的‘动态切入法’作为核心理论,研究中国民间舞蹈的形式特征与文化传承规律……”*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第三章便是《“动态切入法”的理论与操作》。如罗雄岩所说:“动态形象是舞蹈文化理论研究的根本,是‘动态切入法’的核心理论……动态形象是‘音’‘象’‘动态’互动的文化符号。舞者是在一定时间与空间通过动态形象展示文化信息的;舞者的动态形象中,对于民族的原始文化符号与今日的文化信息都会有所体现,它们是有待研究者辨析的充满生命力的形象。因此,‘动态切入法’的核心理论,是诠释动态符号所展示的深邃的文化内涵,辨析原始舞蹈文化遗存、时代文化信息,运用新的艺术实践与理论的升华……”*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为便于操作,罗雄岩提出了“动态切入法”的32字口诀,即“特定层次、多种因素、纵横探索、深入研究、贵在升华”和“动态切入、意境描绘、个性升华”。在他看来:“前20字是从五个方面探索舞蹈文化的步骤;后12字是操作的核心,又是完成研究目的三个递升的层次。”*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从该书所列“操作示意图”来看,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民族学“田野调查”(或实地调查)方法的平移和改造,也可以说罗雄岩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就学科而言就是中国的“民族舞蹈学”。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第六章为《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类型》,其中有“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类型划分方法比较”一节,分别介绍了李雪梅的“地域生态划分法”和笔者的“语言族系属划分法”。其中李雪梅的观点首见于其论文《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新文化区》,她将中国民间舞蹈分为“六大文化区”:一、秧歌舞蹈文化区——北方汉族,以北方旱作文化为代表,属于黄河流域文化中心的农耕文化;二、花鼓舞蹈文化区——南方汉族,以南方稻作文化为代表,属于长江流域文化中心的农耕文化;三、藏族舞蹈文化区——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体,典型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以农牧文化为代表,属于游牧和农耕混合型文化;四、蒙古族舞蹈文化区——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温带草原游牧文化为代表,属游牧和定居轮牧型文化;五、西域乐舞舞蹈文化区——西北地域以维吾尔族为主体,以典型的绿洲文化和游牧文化为代表,属于灌溉农业和游牧混合型文化;六、铜鼓舞蹈文化区——西南地区多民族,以农耕文化为代表,并根据具体情况可划出亚文化区或文化圈,如朝鲜族舞蹈文化圈。在上述“文化类型划分”的基点上,李雪梅撰写了《地域民间舞蹈文化的演变》的专著,其中特别强调“环境与舞蹈文化的关系”——不仅阐明了环境的自然要素对民间舞蹈形成的影响,也阐明了环境制约的劳作方式对民间舞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李雪梅详细论述了《舞蹈文化区中的舞蹈类型》(第四章)、《民族民间舞蹈的区域变化与发展》(第五章)、《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空间传播》(第六章)和《民间舞蹈文化现象的环境反映》(第八章)。可以说,这是一部十分有水准的“民族舞蹈学”的专著。
罗雄岩在书中所提及的“语言族系属划分法”,所列材料来源是笔者的《风姿流韵:舞蹈文化与审美》。其实,这一观点首先发表于《四夷乐与边疆民族舞蹈的生态格局》一文。后来在与彭松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古代舞蹈史纲》中,列入第十一章《四夷乐与边疆民族舞蹈》。边疆民族乐舞,在古时称“四夷乐”(周代也称“四裔乐”)。这是古人从以“中原”为“中”的空间方位上来区分边疆民族乐舞,今天对其加以讨论与“种族中心主义”无涉。该文认为,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始终在进行的,尽管方位的侧重会有变化,交流的主客也会易位。对边疆民族舞蹈生态格局的考察,是该文最早提出以语言格局为参照,并以历史文献作为数据进行了描述。除汉民族舞蹈外,该文认为中国民俗舞蹈可以分为三大生态格局:这就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生态格局、汉藏语系·苗瑶和壮侗语族生态格局、阿尔泰语系生态格局。在后来出版的《风姿流韵:舞蹈文化与审美》一书中,修订为“中国民俗舞蹈‘四大色块’的人文格局”,增加了“汉族色块”,并将“汉藏语系·苗瑶和壮侗语族生态格局”调整为“澳泰色块”(因为有学者认为这两个“语族”可能应属于“澳泰语系”而非“藏缅语系”)。这种“舞蹈文化类型划分”的理念也是“民族舞蹈学”的重要学科构成,只不过那时还缺乏学科建构的自觉。
五、逐步建立起对民族舞蹈文化特异性的体系化分析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民族舞蹈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与“民族民间舞蹈”关系最为紧密;换言之,本源意义上的“民族民间舞蹈研究”就是“民族舞蹈学”的研究,就要采用遵循“田野工作”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巫允明所著《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和在此基础上撰就的《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教程》,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民族舞蹈学”研究成果。在后一部著作中,作者附录了一篇《论“原生态舞蹈文化”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其中写道:“对于‘原生态舞蹈文化’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我在1994年曾提出和发表过:借助于语言学所使用的‘民族语言系属’理论,对同语言系统民族的族源、民族习俗与原生态舞蹈间的关系进行舞蹈文化研究的可行性论述。以后的十余年中,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吸纳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将二者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引入对‘原生态舞蹈文化’的研究。经前后近2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研究方法是可行的……”*巫允明:《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具体而言,巫允明强调“‘研究’必须立足于‘考察’。”*巫允明:《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她说:“考察,即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强调的‘田野考察’……希望通过‘田野考察’获取对既定研究目标所需的翔实材料,首先需要进行全面、细致和大量的案头工作……考察过程中,除将调查事实与案头材料进行核实、比对外,要对不同年龄层的长者进行有准备的访谈,从他们的回顾中取得对过往历史的见证资料……一个调查者的记忆再好,到后期整理调查资料时的回忆难以毫无遗漏,因此考察者每日书写工作日志就显得尤为重要……舞蹈属于一瞬即逝的动态艺术,对于原生态舞蹈文化的考察,以录音、录像和摄影进行记录,缺一不可……”*巫允明:《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以上所谓“吸纳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以“民族学方法”所进行的“民族舞蹈学”研究。
如果说,“民族舞蹈学”主要是用“民族学”方法来研究“舞蹈”,特别是如库尔特·萨克斯所言“‘艺术’一词不能阐明舞蹈的全部概念”的“舞蹈”;那么在舞蹈学科中最接近“民族舞蹈学”的当属“舞蹈生态学”。资华筠、王宁著《舞蹈生态学》“前言”中写道:“‘舞蹈生态学’1988年由中国艺术研究所立项,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了《舞蹈生态学导论》,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理论体系……20多年来,这门学科所建立的基础理论,全面应用于舞蹈研究、教学、评论、实地考察等,经受了实践的验证,也在实践中有所丰富、提高。2000年联合国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民间舞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门类,这些舞蹈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舞蹈生态学’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自然舞蹈的评价、择定、保护方法科学化诸多问题,更加显示了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资华筠:《舞蹈生态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
在《舞蹈生态学》的“总论”中,资华筠、王宁讨论了该学科的学科定位、研究目标与特点以及研究方法。其中指出:“舞蹈生态学是对舞蹈艺术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宏观与系统考察的科学。它以舞蹈为核心,以舞蹈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探索不同舞蹈的产生、存在、发展的规律,研究其特点的形成,讨论它如何受到环境的影响,又如何反转过来影响了环境。”*资华筠:《舞蹈生态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这个关于“学科定位”的表述与“民族舞蹈学”的学科内涵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如其所言:“舞蹈生态学……突破有些舞蹈研究仅就舞蹈现象的局部分析就事论事的局限性,从‘舞蹈与人类’这个大主题中,用多元综合的方法分析舞蹈的自然形态,揭示舞蹈的内在本质。从‘艺术与人类’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探讨艺术的本质与规律,是近年来各门艺术研究的共同路线,也是艺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因为舞蹈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有着如前所述以‘人’为媒质的特性,研究‘舞蹈与人类’的关系更为直接,有更特殊的意义,也更为迫切。无论是生物人、社会人——个体或群体,均离不开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获取到宏观地研究舞蹈本质的一把钥匙,以舞蹈与环境关系为出发点,开启舞蹈生态学的原理。”*资华筠:《舞蹈生态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在论及该学科的研究目标与特点时,作者在提出“舞蹈生态学以舞蹈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目标”后,指出“舞蹈生态学的研究目标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舞蹈(Natual Dance)。因为只有这种舞蹈是原始舞蹈的延续,是始终与民族、社会、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的。它是民族文化的要素,也是表演舞蹈(Performance Dance)依据的素材。研究自然舞蹈,才能抓住作为文化事象和人类创造的舞蹈艺术的根本……舞蹈生态学提出的对自然舞蹈形态分析(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nce)的可操作性概念,对民族舞蹈风格特色的观察、分析将更加清晰有据。继而结合其表意审美内涵,提炼各舞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语汇系统’,归纳‘同形舞目类群’,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层次分明、脉络清晰,涵盖了舞蹈形态、功能、源流谱系和播布区等的多维舞种(Multidimensional Choreospecies)概念,这无疑对探寻由于各民族的环境差异以及在不同步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人文因素制约着舞蹈发展的表征性现象与深层次缘由的认识,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遵循这一路径层层深入——由表及里、由局部向全面拓展,必然对其民族文化特异性的社会人文缘由及生成发展规律有更加科学的认知。此外,借助考古、文献等来追溯舞种传衍、播布路线和在此过程中的功能演变,并分析这种变化反转过来对舞蹈的外部形态又产生何种影响……将有助于梳理舞种进化源流谱系,丰富并深化对其历时性的研究。正是在‘形、功、源、域’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对民族舞蹈文化特异性的体系化分析,并有望实现舞蹈科学研究‘质’的飞跃。需要说明的是,‘民族文化特异性’研究,不只是为了‘别异’,更期望在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中相互汲取、促进,探究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性。”*资华筠:《舞蹈生态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9-11页。细读“舞蹈生态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目标与特点,我倒倾向于视其为较多借鉴了“生态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民族舞蹈学”。
六、“民族舞蹈学”研究的中国先贤及其主张
实际上,中国自现代以来,就不乏以“文化人类学”目光来审视“舞蹈”者,闻一多《说舞》就是其中最为重要者。在《说舞》一文中,闻一多指出:“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便是节奏的动;或更准确点,是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动。所以它只是生命机能的表演。但只有在原始舞里才看得出舞的真面目,因为它是真正全体生命机能的总动员,它是一切艺术中最具综合性的艺术……现在我们更可以明白,所谓表演与非表演,期间也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生命情绪的过度紧张、过度兴奋,以至成为一种压迫,也是一种愉快;所以我们也需要在更强烈、更集中的动中来享受它……一方面在高度的律动中,舞者自身得到一种生命的真实感(一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感觉),那是一种满足;另一方面,观者从感染作用也得到同样的生命的真实感,那也是一种满足。舞的实用意义便在这里。或由本身的直接经验(舞者),或由感染式的间接经验(观者),因而得到一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感觉,这虽是一种满足,但还不算满足的极致、最高的满足;是感到自己和大家一同活着,各人以彼此的‘活’互相印证、互相支持,使各人自己的‘活’更加真实、更加稳固,这样满足才是完整的、绝对的。这群体生活大和谐的意义,便是舞的社会功能的最高意义;由和谐的意识而发生一种团结和秩序的作用,便是舞的社会功能的次一等的意义……”*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2页。在闻一多所处的时代,“表演舞蹈”并不发达,且矫揉造作;而“文化人类学”所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使他通过《说舞》来申说一种主张,申说“群体生活大和谐”的意义,申说“团结和秩序”的作用,从而唤醒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舞蹈界有一场关于“舞蹈美学”的大讨论,起因一是整个社会兴起的“美学热”,一是针对王元麟《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反映关系》的批判。因为王元麟认为:“要把舞蹈本身的美学特点弄清,就要先抛开其他的特别是文学的审美作用因素,从舞蹈的纯然形式作用来进行分析和认识……它的纯然形式常常就是我们舞蹈界称为‘风格素材’的舞蹈动作本身的舞蹈表现……我们对舞蹈审美的自身认识,不能不首先从舞蹈动作开始。通常有一种看法,以为舞蹈动作只是舞蹈的形式,其实动作本身正是它美学的内容之所在。”*王元麟:《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反映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美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正是这句“动作本身正是它美学的内容之所在”挑战了舞蹈界的“常识”,因而遭到“群起而攻之”。实际上,批判者在用“表演舞蹈”美学观照来批判王元麟“非表演舞蹈”(也即资华筠所谓“自然舞蹈”)的美学特质。因为在王元麟看来:“我们讲舞蹈的美学内容,就是指某一特定社会生活内容在某一舞蹈动作上的特定风格的反映……事实上,任何民族的任何具有风格特点的舞蹈动作,当初都和该民族地区特定生活动作相关联,只不过今天不一定能找到其生活动作的蓝本。作为特定概念的‘舞蹈动作’,无论今天有无现实蓝本,它总是要以一定社会群众的审美传统和习惯为存在基础,它本身就是个特定的美学概念。”*王元麟:《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反映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美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王元麟所说的“舞蹈的美学内容”,本质上就是“民族舞蹈学”的“美学”。
王元麟认为:“事实上,我们所有舞蹈的风格及其美都是它特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们所表现的风格和美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它们这些表现为人体律动和造型的特定风格与美开始都是联系于一定社会生活现实的具有功用意义的人体动作姿态的……舞蹈动作作为一种特定的风格和美的形成,是由该特定民族的社会实践决定的。这里有各种历史的、地域的因素交错作用,但基本生产劳动方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但是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劳动方式对舞蹈美的作用大都是在劳动方式具有该社会普遍性意义的时候才能发生。因为最初舞蹈者进行舞蹈活动时,并不是如我们的‘生活动作典型化’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反映劳动动作;而是因为这种普遍的劳动动作已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肌肉活动习惯。当他们需要把自己的过剩精力以舞蹈的集体形式表现出来时,这力量就必然沿着他们的肌肉活动习惯的通路发挥出来。事实上,他们正是在这种自己习惯的肌肉活动中才更体验到一种生命的自我欢愉……但这种不自觉或下意识发生的动作却必然是他们生活和劳动习惯动作的再现。作为这种感情的外部形式,各民族地区千差万别,但又都是由该民族长期的社会实践所形成的体态运动习惯决定的;而作为长期形成的体态运动习惯,在个体的肌肉活动组合定性可以交付给下意识的时候才具有意义。”*王元麟:《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反映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美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页。这段表述其实已暗示了我们“民族舞蹈学”学科建构的聚焦点与方法论。
其实,就我国当代“民族舞蹈学”的学科建构而言,值得特别关注具有世界视野的于海燕。她的《世界舞蹈文化圈纵横谈》在划分并概述“世界八大舞蹈文化圈”(中国、印度、印度—马来、波利尼西亚、阿拉伯、拉丁美洲混合、黑非洲、欧洲)后,对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异同加以了比较,论及了八个方面:“一、东方舞上身、上肢动作多于下身、下肢动作;东方舞面部表情丰富多样,西方芭蕾身体及四肢表情多些……二、东方舞的戏剧性语言多于技术性语言……三、东方传统舞蹈中程式化语言多于示意性语言,西方舞蹈则反之……四、东方舞蹈多以收势为主,或称‘主静’;西方芭蕾多以放势为主,或曰‘主动’……五、东方舞蹈‘亲近大地’,或曰‘立地’;西方芭蕾喜欢趋向天空,或曰‘向天’……六、东方舞蹈讲究曲线美、对称美,西方舞蹈讲究直线美和不对称美……七、宗教信仰的力量使东方传统舞蹈得以滋生绵延千百年,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使西方芭蕾在400年历史长河中得以长足进步。就是说,东方舞蹈的发展生息借助了宗教力量,西方芭蕾的发展传播借助了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八、傀儡戏的发展,曾经为东方传统舞蹈输送了有益的养料,进而使传统舞蹈不断进步完善;西方生产力的进步,劳动、生活节奏的加快,促成了一系列社会新舞种的诞生,如迪斯科、霹雳舞、灵魂舞等等。”*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3页。这正是“民族舞蹈学”之前验明正身的“比较舞蹈学”的研究。
结 语
关于“民族舞蹈学”学科建构的若干思考,是由“非遗名录”舞蹈“进校园”所引发的。这个“进校园”不同于我们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进课堂”,也不同于“高雅艺术进校园”的展演活动。那时“进校园”主要是作为“表演舞蹈”素材的教材建设,作为与之相关的职业舞者的能力培养。因此,深入民间的采风或多或少会带有教材建设的代表性、训练性、系统性的考虑;与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建设最具关联性、也最具提升性的是“教学法”的课程建设。现在我们关注的是“进校园”的“非遗名录”舞蹈的本真性、原生态和综合化,这一工作将需要“民族舞蹈学”的指导,也必然促进这一学科的积极建构。归纳以上思考,我们想说的意思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民族舞蹈学”是一门以“文化人类学”,特别是以这一学科下位学科“民族学”(也即“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理来观照研究舞蹈的学科。虽然以“民族学”的学理为主,其实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文化人类学”的另两个下位学科——“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二、“民族舞蹈学”的学科建构无须“重打锣鼓另开张”,可以积极借鉴“民族音乐学”学科建构的已然成果。事实上,“民族学”视野中的舞蹈研究,几乎就难以脱离音乐来进行。库尔特·萨克斯认为“‘艺术’一词不能阐明舞蹈的全部内涵”,他其实还有一段更精彩的表述:“在原始社会里,一般的舞蹈经常用歌声伴奏,一切歌曲都是为舞蹈编造的;事实上,除了舞蹈歌曲之外就没有别的歌曲了……”三、“民族音乐学”在学科定形的建构中,梳理了从早期“比较音乐学”发展而来的进程,也梳理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音乐民俗学”乃至“音乐民族学”等称谓的整合。这也给我们当下“民族舞蹈学”学科建构过程中的积极整合提供了镜鉴。四、在“民族舞蹈学”的相关学科建构中,舞蹈学界与音乐学界有较大差异。舞蹈学界似乎尚未见成熟的“舞蹈人类学”“舞蹈文化学”“舞蹈民俗学”等等,但有相对完备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舞蹈生态学”,是在音乐学界未曾谋面(未见“音乐生态学”)、但却深度关联于“民族舞蹈学”的学科建构。五、“舞蹈生态学”的成功建构,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是必须用“生态学”的学理来弥补“民族学”乃至“人类学”的欠缺与不足;同时,也使这一方法相近、对象同一的学科建设在认识上具有更大“公约数”,在实践中具有更大“普适性”。六、比较正式地提出“民族舞蹈学”的学科建构并非说我们既往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而是指我们既往缺乏这方面研究的自觉——特别是指缺乏学科建构“科学性”的自觉。我们希望“民族舞蹈学”学科建构有个“名正言顺”的开端,以便今后能以“民族舞蹈学”的名义开展学科研讨、丰富学科内涵、充实学科肌理、完善学科构成。让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