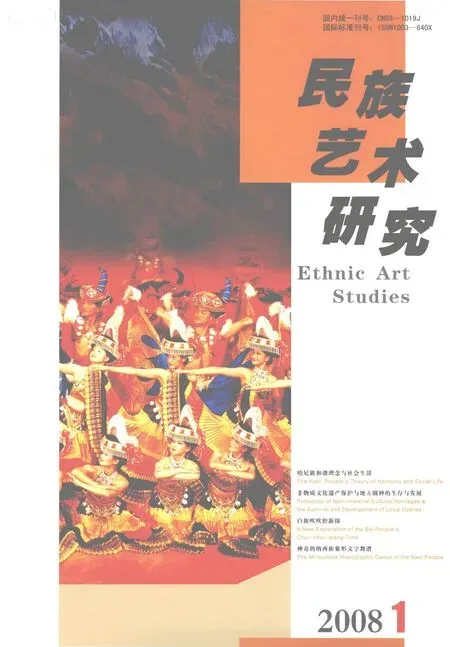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圈舞”:圆形与舞蹈的交互作用
江 东
前些年,中国舞坛出现过一个十分精彩的女子群舞,舞名直接就叫《圈舞》,那是一个由四川舞蹈学校表演、李楠创作的傈僳族舞蹈作品。由于之前没怎么看过傈僳族的舞蹈,对于傈僳族人民的舞蹈形态不是很熟悉,因而这个作品不但给我带来了认知傈僳族舞蹈的契机,而且尚不止于此,这个作品在带给观众相当饱满的舞蹈艺术意象的同时,也用超强的舞蹈表现力传达出了一种精神的含义,那是一种十分强悍的力量,一种坚韧不摧的巨大民族向心力。通过这个作品,我不仅获得了对于傈僳族舞蹈的感知,更获得了十分尽兴的审美意趣。一个作品能产生如此好的艺术效果,除了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作品的舞蹈编导在建构舞蹈作品上的艺术功力和品味外,更让人想到了本文所涉探讨对象所具有的能量:“圈舞”形式,的确具备着巨大的艺术能动性。
实际上,采用“圈舞”的方法来进行舞蹈创作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这种呈圆形的场面调度或叫队形变化,原本就是群舞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图案,似乎并不足为奇,我们可以在国内外大量的优秀舞作中看到成功运用“圈舞”的形式而最终获得成功的例子。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从民间到舞台——“圈舞”现象可谓是不绝于目。
一、“圈舞”的文化功能
“圈舞”,英文称为Circle Dance或Chain Dance,是一种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原发性舞蹈形式。所谓“原发性”也即,它不但在我国各民族舞蹈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的现象,同时也是世界各地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舞蹈形态。从世界范围内的“圈舞”现象来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不论其动作如何变换、其曲调如何不同、其服饰如何迥异,而围圈齐舞的这种方式却是高度一致的。不同国度的人们,都会聚在一起,在空地上、在篝火旁、在大树下、在水塘边,以及各式各样的不同场景中,拉手搭肩联袂而舞。这种现象是很耐人寻味的,君不见,为何处在不同地域条件下的人们,却都会形成相同的舞动轨迹呢?如若对其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自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不论各种研究结果的结论呈现出怎样的不同,也不管其结果会怎样地千变万化,我们都不难获得这样一个基本认知:“圈舞”,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舞蹈形态。
维基百科认为:“圈舞”或许是人类已知最为古老的舞蹈形态,是人类开始懂得舞蹈之后的最初形式。这样一个论定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世界各地大量的舞蹈例子都可以为其佐证。翻开我国老一辈舞蹈理论家郭明达先生翻译的《世界舞蹈史》这本著作,能够证明上述论定的“圈舞”例证实在是不少;而在我们熟知的中国各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舞蹈中,这类“圈舞”现象亦不鲜见。
各种原发性的圈舞种类,是民间或者社群在举行各种祭礼、仪式、庆典、民俗等活动中的主角儿。它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这样的围圈齐舞的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参与其中的人们随着共同的舞动会在各自的心理层面生成一种“聚在一起”的感受,这种感受非常质朴,完全是踏实可感的。想想人类的确是喜欢这种“聚在一起”的社会性感受的。纵观人类的习性,不管是从那一门学问的研究角度出发,都不会忽略人是倾向于社会性生存的一个生物种群,人是害怕独处的,孤独感是大部分人在努力回避的一种状态和情绪,因此,人类是需要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和场合的,这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存需求,特别是在劳动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就曾对“群体心理”进行过十分精到的分析。因此,“聚在一起”的感受会让人类产生彼此在情感沟通上的极大满足感,从而获得对于人类心灵的抚慰具有积极意义的心理上的安全感。正是对这样一种安全感的天然期待和追求,人们围圈齐舞的行为及热情是其自然的本能所致。也正因如此,“圈舞”为这样一种人类的身心需求提供了最直接、最简便、最易完成的根本条件。于是,人们在联袂踏歌振舞中,时时刻刻体味着“群体”的力量和意义,感受着“聚在一起”的踏实感,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着彼此的情感,分享着彼此的快乐,进而让个体的灵性获得了极利于身心健康的疏导通道。如此看来,“圈舞”的最初形成与实际上与它所具有的功能直接相关。
说到“圈舞”所具备的特有功能,我们亦可以在比较其与其他舞蹈形态之间的差异而获得,比如同样古老的“排舞”和“对舞”等形态,这些舞蹈形态同样是传统舞蹈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但与它们相比,“圈舞”所具有的“聚在一起”的特质更为明显而集中。特别是其极大的随意性,可以让参与者随时加入其中,这种自由而自如的组织方式,也显露出“圈舞”所具有的更为便利的操作性。
二、“圈舞”的原发性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圈舞”的分布是极其广泛的,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可以见到这种舞蹈,并且在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佛教等文化圈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而在我国的各族舞蹈中,圈舞同样十分流行。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在许多现有的研究文献中,中国民族舞学研究者在这个领域的开掘和呈现,都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竭的丰富养料,也由此可见我们在圈舞形式上的丰富储存。那些既有的成果固然很能说明问题,但一些活生生的现象更是让我难以忘怀。
几年前,笔者曾去过西藏林芝,在一个大广场上,每天傍晚都会聚集着大量的群众“聚在一起”共同舞动。当地的文化馆在照明和音乐等方面提供了方便,男女老幼们自发地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自娱自乐地不停欢舞。这种圈舞是大家围圈而舞,相互间各不接触彼此的身体,只是沿着一个圆形的大方向做共同的动作。动作都是有编排的,多以藏族舞蹈为基础。人们踏着统一的步伐,十分投入地跟随领头人完成一段一段的舞动组合,沿着圆圈的方向循环不已。应该说,林芝的群众性广场舞在风格、场面以及自娱性等方面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放眼全国,类似的情况是极为普遍的,大江南北、戈壁边陲,群众性的圈舞迄今依然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醒目的作用。
而从美国迈阿密驶往加勒比海的一艘艘豪华邮轮上,每当客满出海时,都会在夜晚安排一个热带庆典晚会,每逢此时,身穿各种沙滩装的各国游客们便会随着现场音乐集体而舞,舞到兴高采烈时,往往会组成一个大圈,后者双手搭在前者的腰上或者肩上,共同完成着统一的舞步。历经岁月的磨砺,在今天,可以说,古老的圈舞形式仍在继续为世界人民带来快乐。
就在2017年7月于新疆艺术学院举行的“维藏朝蒙”民族舞蹈展示的活动中,主办方安排了这样一个环节:邀请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在学校的操场上席地而坐,现场演奏出欢快的维吾尔族乐曲,而来自各个民族的参与本次展演活动的青年舞者们在广场中央围圈而舞。一时间,不同的民族踏着相同的节拍、围圈齐舞的方式再次成为大家共同欢乐的统一方式。
因此,从这些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延续着的圈舞现象中不难看出,作为承载了人类最基本情感、沟通与交流的圈舞,至今都在继续为我们服务。
三、圈舞的精神实质
凝聚力显然是圈舞所具有的一大社会功能。通过上述“聚在一起”的心理诉求,在参与圈舞活动的同时,人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凝聚力被增强。圈舞是一种群体参与的活动,其鲜明的群体参与性是十分显而易见的。由于有了一群人的参与,才让这种舞蹈形式得以成立,因此“群体”的整体性原则及其道德会产生对于“个体”行为的规范。这也是勒庞所谓群体“湮没”个体的一种具体表现方式。在这种“湮没”中,群体作用于个体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情绪的传导和规训,而非言语式的说教,舞蹈时大家相互情绪的感染成就了成为彼此传导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通过这种情绪上的感染,个体是很容易“从众”的,很容易把自我的情绪投射在集体的情绪之中,因此,这个过程是伴随着舞者相互作用、相互促发、彼此共进的情绪递进而完成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也就这样形成,从而完成了个体在精神层面上的自我价值实现,乃至完善。
正是这样一种凝聚力让圈舞获得了自古延续至今的精神价值,为个体生命的体验带来积极的意义。也正因此,圈舞这种以圈形舞动为本体的舞蹈方式彰显了圆形的力量,从而成为舞台作品大量应用的基本图形。
四、圈舞的圆形指代
在专业舞蹈圈,“一○八”是业界为群舞作品常见的队形归纳出的三种基本形态,意指:一排,圆形和八字形。这种对于“一○八”舞蹈队形的总结归纳,起初是很有些调侃意味的,批评者借此诟病如今的群舞作品大都很难避免使用这些队形,在舞台的呈现上总是绕不开它们。实际上,队形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物理图案,其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之所以编导们不能绕开它们,是因为它们各自有着其无法替代的功效。
从图案构形的角度来认识,圈舞所象征的圆形图案本身就具有独特的美学气场,其带给观者视觉特有的感受,显然会形成其特殊的含义乃至深意。这也正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前辈编导,都会不约而同地从对于舞台调度的科学主义认知角度出发,对舞蹈图形的调度做过形式分析研究,并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不少成果的因由。
早在20世纪上半叶,正当美国现代舞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当时的现代舞大家韩芙莉就曾撰写过一本《舞蹈创作艺术》的专著,书中对于包括圆形在内的各种舞台调度图案形式都有一些探索和解释,特定的图案产生特定的审美感知,同样也具有特定的艺术感染力。我们从韩芙莉非常知名的舞蹈作品《震教徒》的剧照中,便可看到她在实践中运用圆形图案的情况。
无独有偶,中国舞蹈家进行类似探索的也大有人在,于2014年出版的《舞台调度的王玫研究》一书 ,就是北京舞蹈学院王玫教授常年琢磨和研究的心血结晶。在书中,王玫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剖析了各种图形所具有的特定含义。而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她在处理圆形时的一些精彩之笔。还记得她根据曹禺话剧《雷雨》创编的现代舞《雷和雨》,就十分成功而精彩地使用过一个圆形调度,让人久久无法忘怀——她让话剧原作中那些有名有姓的角色们围成一个圆圈鱼贯前行,其中一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脱离圆圈进入中央开始了一个双人舞段,舞毕回归圆圈,然后又是另一对角色开始他们的舞段。在一段又一段的双人舞段行进的过程中,所有其他演员一直在沿着圆圈行走。这种处理非常有效地对原作的人物和关系进行了重新地组接,构成了在舞剧环境下的新的表现,很贴切,也更加符合“舞蹈”的艺术表达。
同样,在俄罗斯芭蕾大师艾夫曼创作的《奥涅金》中,有一个场景的处理也非常有意味:天幕上是一个圆形的图窗,里面播放着视频内容,而相映成趣的是舞台上也出现了两个由男舞者群舞联臂组成的圆圈,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圈舞效果,与天幕上的圆圈相呼应,从而产生了相当有视觉震撼力的艺术效果。在艾夫曼创作的另一部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中,当安娜在情感与欲望的漩涡中挣扎时,创作者运用了两个圆形,让安娜交互在两个漩涡的边缘线上被惯来甩去,极好地呼应了她的内心独白,把她的命运和内心独白通过两个圆形的舞动外化了出来。
圆形舞动给视觉带来极强震撼的还有法国现代舞大师贝雅的《包来罗》,相信所有看过这个作品的观众都会印象深刻。这个作品利用了两个圆形,一个是巨大的圆形红色桌子,另一个是围绕着这个红桌为中央核心的男子群舞。舞蹈是一层一层推进的,先有红桌上的独舞者伴着《包来罗》的乐曲做着具有“微量元素主义”式的舞动。当呈圆形的男舞者不断加入其中,圆形舞动的力量逐渐显现,周边的圆形群舞与红桌上的独舞形成了颇有视觉意味的对比与呼应,奇妙的审美形态也就此产生。最终,在独舞的一声召唤下,所有舞者跃上红桌,沿红桌边沿形成了一个圆形的调度,让舞蹈达到了最高潮。这个作品充分利用了圆形所具有的视觉效果,让舞蹈自始至终产生着巨大的艺术张力,显现出编导所具有的超强艺术功力。
当然,最令我难忘的圆形处理,莫过于台湾舞蹈家林怀民所创造的极致效果,他在《流浪者之歌》的结尾部分,安排了一位舞者将堆积在舞台上的成堆谷粒用一支犁耙一圈圈地耙成一个巨大的类似树干年轮一样的圆环图案,演员的缓慢倒行让这个过程消耗了不断成长的时间,而这么漫长的动作过程,竟然没有引起观众的不耐烦,反而让观众伴着这种大胆而富有禅意的艺术处理,修行一般地去感受编演者们的宁谧心迹,同时也让观者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去体味,去冥思,去参悟,去修整,那个在地面上像涟漪一样一圈圈放大的巨大圆环,成为人们进入禅境的通道,从而给人的心灵带来抚慰,同时也让《流浪者之歌》这部作品的主旨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在2017年被评为国家艺术精品扶持工程的舞蹈诗作品《黎族家园》(海口市艺术团出品)的尾声中,一群黎族群众跟随着男主人公的脚步围着一个大圆奔跑,那种向着光明、向着未来、向着美好生活不断进发的群体性民族情感,被这种沿着圆形的跑动给充分地激活了,进而给观众带来颇为积极的艺术想象及其生活态度呈现。
脱胎于圈舞而成形的圆形,为我们的舞台带来了饱满而不尽的意象,为艺术家的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只要我们的艺术家能够更加智慧地对其加以利用,这个圆形的图案一定会为我们的艺术舞台带来无限的艺术想象力。
结 语
对“圈舞”赋予的圆形舞动的解读是咀嚼不尽的,从圆形舞动之中生发出的艺术意象也是无法穷尽的,所有这些从民间到舞台的鲜活例子,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圆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圈舞”的意义也于此奠定,它被百姓自然地纳入自己的舞动表达之中,也被艺术家们提取到艺术的高度予以表现,其本身是一种取之不竭的意义与形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