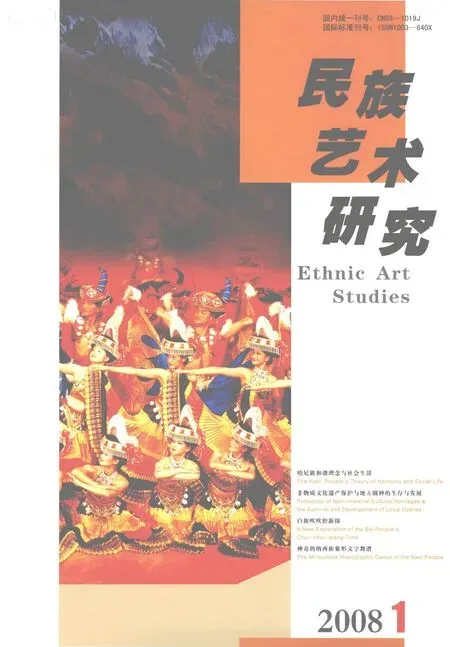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发展的得失之于艺术学理论建设的借鉴意义
贾 涛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的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西学东渐文化大潮,中西方美术交流开始活跃,促使一部分人眼光向外,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绘画;同时也促使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守护者们竭诚呵护之,与否定思想针锋相对。由此便掀起了一场有关中国画学术研究的狂澜,许多人喜欢用“中国画学”作为它的关键词。当时的中国画学发展态势可以用“迅猛”一词来形容,一如当今的艺术学理论,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学科相比,中国画学的确立于不败之地。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队伍庞大,社团众多。在20世纪上半叶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不断涌现,且名家巨擎皆参与其中,如黄宾虹、邓实、余韶宋、金城、俞剑华、于安澜等,甚至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其中的主导力量。一些美术史家深涉画学领域,学术成就卓著,著名的如傅抱石、滕固、郑午昌、潘天寿等等。这些著名画家或理论家并非各自为战,他们加入各种学术研究社团,总体推动。比如,1909年在上海最早成立了由钱慧安任会长的“豫园书画善会”;1915年由余绍宋主持在北京成立了“宣南画社”;同年在上海成立了以乌始光为会长的“东方画会”;蔡元培于1918年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由陈师曾任会长;1920年以金城为主导的“北京画学研究会”在北京产生;1927年金城去世后,一部分成员脱离北京画学研究会,成立“湖社”,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画学研究团体。在广州也有类似组织,叫“广州国画研究会”,并将黄宾虹吸收在内。在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相关研究会,上海地区不少于十个,而地处中原的河南大学于1931年成立了“河南大学中国画学研究会”,由著名美术教育家陶冷月任会长,《画论丛刊》一书的作者于安澜为其中重要组织者。据统计,20世纪上半叶全国范围内共成立美术社团有300个,与中国画学研究相关的100多个。*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画学研究组织如春雷催雨,蓬勃兴旺。
其次,研究成果丰硕。中国画学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一片生机,不仅参与人员众多,名家荟萃,相应的学术活动十分频繁,且成果丰硕,巨著名篇时现。如家喻户晓的《美术丛书》(1911年,黄宾虹、邓实主编),《书画书录解题》(1932年,余绍宋编),《画论丛刊》(1937年,于安澜编纂)等,这些编纂类画学著作大放异彩。同时画史研究空前活跃,主要著作有: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22年),滕固《中国美术小史》(1925年),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年),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1929年),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年),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年),秦仲文、胡蛮等亦有此类著作出版。*参见马鸿增:《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画著述评要》,《美术》1993年第6期。
再次,国内国外画学研究交相辉映。在国内画学热潮推动下,对国外画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与译介同样引人注目。尤其对日本学者画学著作的译介出版兴盛一时,其中包括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陈师曾译,1921年),梅泽和轩的《六朝美术》(1923年,东京出版;傅抱石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中国绘画史》(1937年),金原省吾的《唐宋之绘画》(1935年,傅抱石译,商务印书馆)。这一时期中国画学著作类出版数十部,译介出版国外画学著作十余部。
其四,相关学术期刊众多,学术论文丰硕,从中足见中国画学学术研究之活跃。据统计,从1911年至1949年,国内出版发行的中文美术期刊(包括特刊、增刊、附刊等)近400种。*许志浩:《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比较有影响的有:《真相画报》(1912年创刊)、《艺术丛编》(1916年创刊)、《湖社月刊》(1927年)、《艺林旬刊》(1928年创刊,为中国画学研究会会刊)、《亚波罗》(1928年创刊)、《美术丛刊》(1929年)、《艺术之路》(1929年)、《国画月刊》(1934年)等。有了这些学术阵地,相关的画学论文发表更为可观,比较有影响的包括:陈师曾《文人当之价值》、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等。可以认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或是学术影响上,这一时期的画学类期刊、文章都堪称上乘。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学研究可谓灿烂辉煌、登峰造极,其影响日隆,其研究成果累累,其研究队伍层出不穷,大有压倒其他一切艺术学科之势,就连它的母学科——中国美术史研究也相形见绌。这种态势理应如人所愿,趁势建构起中国画学学科——它确实已然具备了学科建设的各种学术条件:如中国画学史、中国画学文献及其整理,中国画学知识体系等;同时又拥有一支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以及成就斐然的学术成果。然而,这一学术潮流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互代,很快便沉寂下去,甚至销声匿迹,形成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之局面。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即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画学研究在学术界基本变成个人兴趣,只有一些个别学者还在坚持,如俞剑华、伍蠡甫、钱钟书、于安澜、王世襄、周积寅、陈传席等,而画学研究的风势、规模与成果都一落千丈。在高校,不仅没有以往如北京大学、上海美专、国立杭州美院等高校那种骄人的画学研究社团,甚至连中国画学(论)课程都不见踪影。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画学(或中国画论)课在高校还十分罕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2000年之前只偶尔邀请一些学者做过中国画学的专题讲座。*笔者所在河南大学美术系于1999年开设中国画论课,任主讲教师,在当时国内已属罕见。进入21世纪,即轰轰烈烈的中国画学学术研究沉寂半个世纪之后,才有一些高校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开始招收中国画学(或中国画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最近又有重拾昔日风头之势。而作为一个学科,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才重新认识到这一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于是开始撰文发声,强调要重视中国画学学科建设,著名学者陈绶祥、陈振镰、郎绍君、刘曦林等皆有相关文章与言论,笔者也曾撰文呼吁。*参见:陈绶祥《中国画学是中国美术学建设的一把钥匙》;陈振镰《“中国画学”学科建设诸问题》;郎绍君《“中国画学”的范畴》;刘曦林《20世纪中国画学之理论建构与价值取向》;樊维艳《中国哲学视野下的中国画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等。同时笔者也曾撰文谈及,见拙文:《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学学科建设》,《美术观察》2011年第2期。这些本该在20世纪上半叶一气呵成的学科建设问题,直到今天还悬而未决。
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发展的局限
中国画学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的火热到下半叶的冷落,说明了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哪些?当然,它离不开时代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但是最根本的,恐怕还要从学术与学科发展自身去找原因。因为同样的时代气候变换,却造就了其他学科发展的良好态势,如文学、美术学、戏剧学、影视学等,而中国画学显然后劲不足。说到底,不能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与维度去解决其学理性问题,才是其发展阻滞的关键因素。通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学研究,它发展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著作出版到文章发表,从社团活动到国际交流,虽然丰富多彩,却几乎没有涉及画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中国画学”的名称叫得很响亮,中国画学的具体问题研究亦很丰富,可就是缺少学科自觉,缺少整体性学术把握。轰轰烈烈的学术运动背后,没有谁去关心、研究中国画学学科的体系问题、系统问题、学理问题,只在文人画、中西艺术关系、传统技法锤炼等方面一味纠缠,结果,随着这些问题的沉潜与消失,中国画学学科也随之销声匿迹了。这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学科建设的最大痛点。
第二,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学学术展开过程中,目标没有明确设置,学科没有精准定位,效果没有智慧预见,纷繁而无统领,丰富而无头绪,致使由画学走向何处的学理认识根本性不足。尤其是学理研究的缺失,极易造成学科高度不够,学科功能不明,学科基础不牢。即是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画学学术研究,缺乏最基本的学科学理认知,即如中国画学的学科定义、性质、范畴、类别、系统、内涵、目标、任务;中国画学的文化基础、学术发展前瞻等等,很少有文章涉及,更没有专门著作自觉而深入地研讨。必要的学科定位的缺失,使得这一学科始盛终败、有花无果。
第三,学术研究多停留于认识层面,没有与绘画实践活动密切关联,没有阐明画学学科的界线与范畴。尽管中国画学的研究者中不少是绘画大师,但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研究上尚有明显不足,大家似乎不太在意它们之间的派生关系,而过多地关注个别问题研讨。同时,一个学科的建立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范畴与学术边界,要弄清自身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以便为学科准确定位打基础。20世纪中国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一如中国画学学科与绘画创作的关联性研究,中国画学在美术大学科中的定位与地位,中国画学与其他艺术学科如文学、社会学等的区别与联系,中国画学与西方画论之沟通等问题,皆不甚明了。
第四,基本的学科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只能拘泥于一些具体层面的推进,而难以系统提升。正如一个建筑,选址不当,位置不确,地基不牢,框架不明,其他都是枉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研究根本上就存在主次不分、重复无绪的问题。如在研究对象上,大家齐抓共上,瞄准传统中国画论诸多著名篇章反复编纂,虽有提高、提升之必要,而又陷入了过滥过繁之弊端。这一时期的画学研究,要么就事论事,要么针对热点持续发力,却对学科学理问题视若无睹。
同时,也许是时代的局限,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学研究囿于学科自身,不能融通其他艺术理论,未能打通学科关节要害,无法整合为统一的学理认识。其散兵游勇式的学术攻坚,会产生一些经典,而最终也会在个性化资源消耗殆尽之后,沉寂下来。不能正确认识画学学科的艺术属性而囿于成规,不能有效提升学科认知而就事论事,不能超越学科自身局限而走向更广阔的理论视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学研究无异于划地为牢,只能在一个庞大的笼子里打转转,最后困在这个小圈子里自生自灭。
重温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学术研究的“悲壮”一幕,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一个关键疑问:它能否在学理认知清醒的条件下获得突破?能否冲开中国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死穴,让这一学科真正建立起来?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画学尽管属于美术理论的一科,但它实际上就是整体美术学科理论的缩影与突出代表,一切美术创造,包括传统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等,都有一个画理在里边,一通百通,触类旁通,更何况中国画学在美术学科中本来就具有核心作用、基础作用!因此,丰富而浩瀚的中国画学,完全可以上升为美术学科的全科理论。事实上,中国古代画学的史、论、品、技,本身就是美术众多分支学科的交叉平台,画家与雕塑家、书法家、鉴藏家、工艺大师之密切关系,让人几乎忘记了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
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如火如荼的中国画学研究由于其学理认识不足,而成为一个孤独的艺术斗士,最终寂灭在它的前进道路上,半途而废。反观如今的艺术门类,我们何尝不是面临着相同的、相似的局面?如果没有艺术学理认知的统领与提升,如果仍然囿于各个门类艺术的单一认识,如果认为各门类艺术理论可以取代总体学科认知,如果在学位点建设中与其他门类学科里纠缠不清,那么我们很可能重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发展的覆辙,各艺术学科会各自为阵、互不相通,甚至出现散乱无绪的学术乱象。喧阗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危机。
三、得失之于艺术学理论建设的借鉴
历史是一面镜子,学术史也是一样。联想到当前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建设,我们在回顾、感喟中国画学这一学科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的同时,不能不有所触动。能不能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用于当今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与研究,切实地在学理认知清醒的条件下获得突破,从而避免走它的老路?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而且是可行的。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理论起步不久,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学研究相比,它的研究队伍并不庞大,它的研究团体亦不繁多,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却惊人地相似。
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门类的一个一级学科,自诞生之日至今不过数年时间,这一学科的设立,像一个标志,标志着艺术学必然要走学科化道路,必然有建筑在具体艺术类型之上的学理性认知与研究,从而有别于以往历史上任何艺术学科。
正是由于此,艺术学理论的设立才不被一些人理解,才有因它而带来诸多争议。包括一些著名的专家在内,并不清楚设立这一学科的真正意图,在很多场合出现了各种质疑声,甚至批评、反对声。他们认为,这一理论学科没有必要建立,既不能直接用于艺术创造,又建立在空洞的理论之上,与艺术各门类及其实践相脱节。艺术的发展主要居于艺术实践的突破,重在艺术生产、艺术创造,艺术必然要以艺术作品作为核心标准来衡量其价值。既然有了艺术的各个门类及门类艺术理论,再来一个总体的艺术学理论实属多此一举。甚至认为,纵使艺术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引领,那也是各学科各艺术类型的理论最为直接,一种悬空了的艺术理论要运用时无疑是在纸上谈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似乎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真的多余、无用。这样一来,学科存在的认识基础就不牢固,它的发展肯定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
更多的专业学者当然不能苟同这些观点,包括笔者在内。在许多重要场合我们不仅赞同设置艺术学理论这一一级学科,而且提出了设置这个一级学科的理由,即将原来附着在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艺术学”中的第一个二级学科“艺术学”保留不变,并相应调整为一级学科,只是当时的称谓仍然叫“艺术学”。*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办举办的艺术学门类升级专题论证会上,笔者就这一问题做相关发言。可参见《艺术教育》杂志2011年相关报道。“艺术学”这一称谓学科性质比较明显,至于应当叫“艺术学”还是“艺术学理论”,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当另文讨论。总之,艺术学成为门类之后,原来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调整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而且置于其他四个一级学科之前。也许是因为一些专家担心“艺术学”这一称谓与艺术门类相同,有混淆之虞,故而定名为“艺术学理论”。无论如何,它的一级学科性质却就此固定下来了。
简单地说,这个一级学科设置的初衷,从学科沿革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它只是原来艺术学二级学科的升级版。*在2011年门类调整升级之前,艺术学作为一级学科归属在文学门类之下,是文学门类中的第三个一级学科。此一级学科艺术学又下设八个二级学科,包括艺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美术学、设计学、影视学等。原二级学科的艺术学肩负着学科理论整合及学理研究的任务,毕竟在它之后还有七个平行的、以门类为主的二级学科,这与门类升级后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性质与任务是一致的。然而,由于艺术门类的设立,二级学科的艺术学相应调整为一级学科之后,这一学科的设置反而不能被一些人理解接受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它存在的价值置疑,二是对它“扩容”后的职责范畴担心,担心它是否会与其他一级学科交叉重叠,担心它的培养与发展方向。
价值问题下文还要讨论;而重叠、重复乃至交叉问题确实令人疑惑。仅在实践操作的层面上,近几年来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它与学科设置无关,只能是转型过程中的认识问题、方法问题。比如,作为一级学科,它自然要设置博士学位点,原来在文学门类下具有艺术学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经过申报审批调整,基本调整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博士授权点,这确实等于“扩容”了。原来的二级艺术学学科多与具体艺术门类的二级学科相照应,即是说它们存在着学科艺术理论与门类艺术理论的密切关联,而不仅仅是交叉;一旦同时调整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具体艺术门类学科的关联性就被分割开来了,二者都需要独立运行、自成体系;原来相互包含的这些学科变得不能再简单包含、直接互代。因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具有无比的独立性,它必然与其他艺术门类学科拉开距离、明确目标,才能自证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以往二级学科的艺术学有明显不同。这样一来在研究生培养问题上就产生了一种实际问题:即,原来一些具有二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的高校、研究院所,并没有实际培养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经验、基础与师资。尤其是师资,其大多从事本科门类艺术研究,或者说多数是门类艺术理论的导师、学者,现在让他们直接指导艺术学理论的博士,只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按照学科性质分开研究指导,走学科专业化之路;二是仍然以门类艺术理论为主,使之兼具艺术学理论学科性质。前一种情况恰恰符合当前艺术学理论的学术要求,而后一种状况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要求相左,可在一些学科点确实存在。因此,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设立若干年后,不少艺术学理论专业博士点的学术指导,仍然按照门类艺术理论进行。这种“取便、就近、顺路”式的学科转型,不仅是一种惰性,也实在是一种错误;不仅是一种误读,还是对学科认识的曲解。这样培养的结果,肯定不符合这一学科的基本要求,从课程设置到日常教学到论文选题、写作,都会相去甚远。事实上,国内一些一级博士、硕士学科点,不是将之收归于美术学、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等学科之下,就是将其挂靠在文学、历史学等门类之下,将艺术学理论变相改造成为这些门类或学科的“扩展版”,真正让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成了可有可无、悬而且空的空架子。这当然是一种重复、重叠和无谓交叉。
对此,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多次反复撰文指谬,在一些公开场合、学术研讨上也有过激烈争辩。尽管目前在一些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问题上(诸如选题、论文撰写等环节)基本形成共识,但在博士研究生培养、部分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问题上,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学术实践,在一些地区、地方或领域,比如正在筹备中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及其成员单位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认识相对清醒;而在另外一些单位,仍然存在认识模糊(甚至故作模糊)、操作随意、师资配置不合要求等问题。尽管当前艺术学理论学术研究相对红火,比如研究队伍逐步扩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术影响日渐显现,但是,如果学科意识不强,不能抓住学科根本,不能在学科认识上达成共识,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无疑是有害无益的。
如前所述,目前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过多地关注艺术学理论的二级乃至三级学科,有意将艺术学理论划分于各种不同的领域中,分解出众多的枝杈。这样研究起来具体、实在、简便、易于把握,但是,它于总体学科学理建设有何裨益?艺术学科的基础性研究交于何处?长此以往,会不会出现前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研究过程中的问题与结果?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研究,要么挂一漏万,要么以一当十,从而陷入逻辑的乃至认知性陷阱。具体包括如下问题:一两门、两三门的门类艺术史能否代表着全部艺术史?个别的或几个门类的艺术理论能否映照出全部的艺术学理论?艺术学理论的真正学科基础是什么?它与其他门类艺术正确的关系是什么?它超越于其他门类艺术的原则与标志是什么?艺术学理论的学理根本在哪里?我们都清楚元艺术学是它的学科基础,而元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理论如何兼容?有学者提出“审艺学”“艺理学”研究问题,能否将它作为突破学科局限的一把钥匙?*参见梁玖:《审艺学及其价值》,《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以跨学科研究视点认知艺理学的内在研究诉求和特性主题》,《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6期。等等。这些问题不理清、不解决,学科发展就难以落在实处。
这不是危言耸听。看一看当前的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各种会议即可见一斑。这些名为艺术学理论的学术研讨,其议题虽然符合学科学理要求,但提交以至入选的文章则往往张冠李戴,十之七八游离于学科本身。那些从门类艺术到门类艺术研究的自不必说;只看与艺术学理论相关的选题,要么从一两门学科理论出发,或者由一两种艺术现象、个别艺术史生拉硬扯到艺术学理论的层面;要么将门类艺术的个别,硬生生地提升到一般,意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参见第十三届中国艺术学理论年会(南京,2013年)会议论文集。此类研究,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牵强附会的感觉,艺术的门类理论没有深入,而艺术学理论仍然浮于表层。当然,对门类艺术理论的借鉴是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如何借鉴?如何升华?如何摆脱习惯认识而升华到学科学理层面?如何将门类艺术理论有效地充实于总体学科理论中?学术研究不能想当然,更不能一厢情愿。其中,摆脱个别门类艺术理论习惯性认知,在总体艺术学理论视野中考察、关注、研究、探讨相关问题,至关重要。即是说,艺术学理论是各门类艺术认识、实践的基础理论,它既有自身理论建设的任务,也有指导、引导、启发艺术实践的价值,它的学科价值与理论立足点,是自上而下的总体把控,而非具体、个别的一般应用。它并不是空洞无益的理论卖弄,更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基于各门类艺术而提炼出的共性与真知灼见,是带有规律性、基础性的学科理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熟,会是一种标志,将成为各门类艺术创作、认知的牢固基础。
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还有待转型,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已经认识到并在竭力扭转这一局面。艺术学理论应当名副其实,据此,普及它的学科基本理论显得更为迫切而必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一哄而起、一拥而上、有始无终的尴尬。
目前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使人联想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的发展历程,其中的得失,尤其是所失部分,对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或许有直接的警示意义。
结 语
概而言之,艺术学理论及其学理研究,恰恰是一种超越,一种融合,一种升华,它会将艺术各门类、各学科的共性放大,加以归纳提升,使之上升到学理的高度,然后又回归到各个门类,用以指导艺术实践,甚至拓宽单一艺术门类的局限,让艺术的创造发展无穷化。同时作为综合艺术理论,它的学术系统越成熟、越完备,那种超越的境界会越高,单一艺术门类的发展空间就会拓展得越来越宽阔。当代艺术发展与古代相关的一点,即其综合性、丰富性,任何基于一技一专一能的发展,都会遇到无法解脱的盲点与局限。复合型、综合性艺术创作的发展空间会更为广阔,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学科发展的半途而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以此为视角的艺术学理论及其学理研究,其学术价值才会突显出来,并被广泛认可。任何忽视这一学理研究的做法,任何视艺术学理论空洞无益的认知,任何以偏概全的相关学术研究,只会重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学科发展的老路,只会使之在盲目繁荣、一时喧闹中无所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