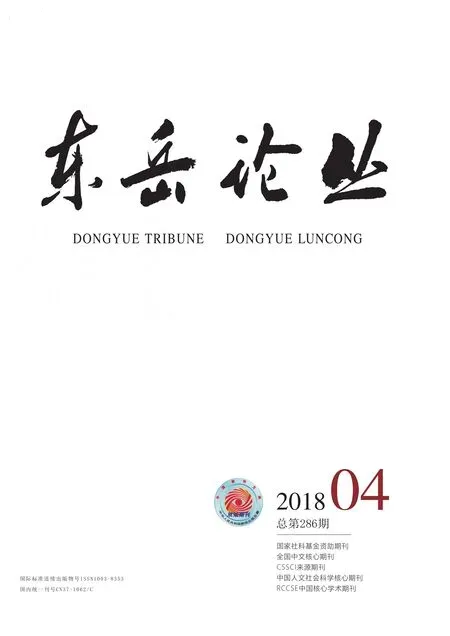《小说月报》语境中的《怀旧》
——兼论《怀旧》阐释史上的几个问题
鲍国华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387)
1921年1月,商务印书馆的名刊《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起由沈雁冰接任主编,成为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在后世的诸多新文学史著中,第十二卷第一期似乎成为该刊进入历史新纪元的标志。而在此前的十年间,由王蕴章、恽铁樵交替担任主编*《小说月报》创刊后的第一、二年和第三年一至四期,以及第九、十、十一卷由王蕴章主编;第三年(卷)五至十二期(号),第四、五、六、七、八卷则由恽铁樵主编。自1910年创刊到1913年第三年第七期,称某年某期,此后则称某卷某号。的《小说月报》尽管努力经营,成绩不菲,但其地位与价值不免被改版后的盛名所掩盖,长期未获关注,甚至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遭遇否定*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有关《小说月报》的条目代表着一定时期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创刊于191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原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主要刊登旧诗词、文言文和改良新戏等。自1921年1月第十二卷起由沈雁冰主编,大力革新内容,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行机关刊物。”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1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1921年以前的《小说月报》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除综论清末民初小说和报刊的论著外,就笔者目力所及,至少出现了两部专论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著作*分别为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和谢晓霞《〈小说月报〉192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二书都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增补修订而成。,在史料和论断上均有所收获,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然而,尽管以上成果在肯定改版前的《小说月报》的地位与价值,特别是剥离其与“鸳鸯蝴蝶派”之关系上颇为用力,但仍不能避免以日后大行其道的新文学为基本参照,对《小说月报》前十年的肯定和否定,也大体上基于该刊对于所谓“新”“旧”趋向的不同取舍。因此,研究者关注并强调改版前的《小说月报》在新旧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无意中使该刊一直笼罩在新文学的巨大“阴影”之中。且不论其中“新”与“旧”的相对性和研究者的不同立场,即使在新文学由蓄势到萌芽再到兴盛的20世纪20年代,以《小说月报》同人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文人是否时时感受到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及其市场)的巨大压力,在山雨欲来中饱尝风雨飘零之感,努力通过避“旧”趋“新”来维持生存,尚存疑问。同时,将《小说月报》由创刊到改版十年间的文坛走向,定位为新文学的初生到确立,也略显单一。事实上,新文学与所谓旧文学各有其路径,虽彼此间存在交集,甚或冲突,但绝非你死我活,或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关系。以新文学的趣味、立场和趋势阐释改版前的《小说月报》,未必能对后者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不过,无论是以“新旧转型”还是“在历史缝隙间挣扎”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研究者对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的考察,无一例外地给予一篇小说以格外的关注,这就是发表于该刊1913年4月25日第四卷第一号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作者署名“周逴”。23年后的1936年,随着一代文豪鲁迅的逝世,其二弟周作人发表《关于鲁迅》一文,率先披露《怀旧》的作者即为鲁迅。这篇小说日后备受关注,收入1938—2005年间的各版《鲁迅全集》,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与周作人的文章不无关系。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学人的《怀旧》研究,产生影响最早也最大的当属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论文《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该文作于1967年,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个汉译本,此后又多次重译,启发并规约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大陆学人对于《怀旧》研究的思路和想象力*普实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一文,最初的汉译本由沈于翻译,发表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署名“雅罗斯拉夫·普鲁塞克”,并收入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5-471页,署名“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后又有邓卓译本,收入《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9页。近年来又有郭建玲译本,收入李欧梵编:《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01-108页。。在普实克的论文之后,关于《怀旧》主题与艺术的阐释不断深入。如王瑶《鲁迅〈怀旧〉略说》一文指出:“(《怀旧》)除过它是用文言写的以外,在精神上或风格上它都是‘现代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作品的发轫。”*王瑶:《鲁迅〈怀旧〉略说》,载《名作欣赏》1984年第1期。这一观点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学人对于《怀旧》的基本判断。此后出现的研究成果,在细节上各有所见,但对于小说“先声”价值的肯定则相近。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学人开始尝试与普实克对话,或努力超越其论断。张丽华的论文《从故事到小说——作为文类寓言的〈怀旧〉》*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收入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70页。,试图在清末以来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的视野中,将《怀旧》视为一部在形式上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来重新阐释其主题意蕴以及这一主题所可能蕴含的自反性的文类指涉意义,对普实克的研究视角有所拓展。费冬梅《〈怀旧〉的主题与形式——对普实克论文的再讨论》一文*载《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2期。则提出《怀旧》作为一篇旧体文言小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散文及诗词的影响,尚不能担当“现代文学的先声”之重任,体现出突破前人的勇气。然而,以上成果在引用和分析《怀旧》的文本时,绝大多数出自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即使兼及恽铁樵的评点,也是小说文本引自《鲁迅全集》,恽铁樵的评点引自《小说月报》,从《小说月报》引用《怀旧》文本的,只有张丽华。当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鲁迅全集》的编校质量日臻完善,文本的可靠性自不待言。但考察《怀旧》的文学史价值,从小说最初发表的刊物出发,顾及具体的历史语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小说月报》上的《怀旧》初刊本,除小说本文外,还包括主编恽铁樵的随文评点和篇末附志,以及一帧插图,均为《鲁迅全集》本所无*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和2005年版均在第7卷图片页刊载了《怀旧》初刊本的两页书影,其中一页包含插图。。可见,《怀旧》的初刊本和《鲁迅全集》本在文本的信息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试图从《小说月报》出发,考察《怀旧》发表的历史语境,借此重新估价学术界对于《怀旧》主题与形式阐释的深度与限度。
一、重读几则常见史料
鲁迅本人对《怀旧》的记述,出现在与杨霁云的通信中。在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回忆早年的文艺创作,特别指出:
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鲁迅:《340506 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鲁迅不仅忘记了小说发表时的题目和笔名,连刊物也误记为《小说林》(尚存疑),因此,《怀旧》未能像该信中提到的其他几篇作品,如《斯巴达之魂》《说鈤》等一同编入1935年5月出版的《集外集》。鲁迅提供的信息不全面,加之私人通信在当时尚未公诸于世,对于《怀旧》的重新发现,推延至鲁迅逝世以后。不过,鲁迅的记述中也有准确之处,就是得到几本小说(当为刊物)作为奖品。查《小说月报》征文通告,确有“一经登载,当酬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载《小说月报》第一年第一期,1910年7月25日。标点为引者所加。此后各卷各期均有类似表述。之语,可证鲁迅对于这一细节的回忆无误。
1934年5月22日,鲁迅再次复信杨霁云,修正了对于《怀旧》发表的记忆:

杨霁云来信今已不存,难以确知其内容。根据复信,大约杨氏对于前一封信中鲁迅提供的刊名存疑,在来信中提出发表小说的刊物为恽铁樵主编之《小说月报》。鲁迅则否定了这一判断,坚持认为是《小说林》,而且把“批评的老师”这一头衔转赠包天笑。事实上,《小说林》的主编是黄摩西,包天笑只是主要撰稿人。看来鲁迅确实忘记了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情况,以致张冠李戴,使杨霁云未能找到这篇小说,编入《集外集》。
如前文所述,将《怀旧》的著作权授予鲁迅,始于1936年周作人《关于鲁迅》一文中的相关记载:
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覆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知堂:《关于鲁迅》,载《宇宙风》第29期,1936年11月16日。
周作人的这段回忆非常详尽,包括小说的创作时间、主要情节、发表刊物,还特别指出题目和署名都由周作人所加,投稿者亦非鲁迅本人。但在细节上也存在一点失误:《怀旧》发表于《小说月报》时,并非“卷首”,之前还有署名“铁樵”的短篇小说《烹鹰》和署名“公短”的科学小说《再生术》,《怀旧》位居第三。虽然周作人忘记了小说发表的具体年月和题名,但指出辛亥冬天创作,过了两三年寄出,编辑是恽铁樵,无疑为寻找这篇小说提供了线索,缩小了范围。
《关于鲁迅》发表后,引起时人的关注。一位被称为“葛乔先生”的人,根据上述线索在上海徐家汇的一家私人图书馆查阅《小说月报》,找到了这篇被周作人忘记发表年月和题名的小说。于是,《怀旧》被重新刊载于1937年3月出版的《希望》第一卷第一期,编辑还特地在小说前加上“编者记”,说明这一经过*《怀旧》载《希望》“特别文献”专栏,其“编者记”云:“友人葛乔先生读了这一节文字(引者按:指周作人《关于鲁迅》一文中涉及《怀旧》的文字),就想尽种种方法去调查,终于在徐家汇一家私人图书馆里被他查着,原来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怀旧》,署名是‘周逴’。葛先生并费了许多工夫,将全文抄出,交给本刊发表,这是很可感谢的。文中批语,当系编者所加,现并不删去,以见当时杂志的编例,标点和旁点也仍旧。”载《希望》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3月10日。。接着,复旦大学文摘社于同年4月出版的《文摘》第一卷第四期又根据《希望》的刊本予以转载*载复旦大学文摘社编:《文摘》第四卷第一期,1937年4月1日。。周作人似乎对此也意犹未尽,若干年后又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回忆: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民国元年用文言所写的,登在《小说月报》上面,经发见出来,在杂志上转载过,虽然错字甚多,但总之已有人注意了。*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一○秃先生是谁》,《鲁迅的故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所谓“在杂志上转载过”,应即前文所述之《希望》及《文摘》,而且周氏只记述事实,却未归功于自家,态度颇为诚恳。《怀旧》经两次转载后,终于以“鲁迅小说”的身份重新走进读者视野。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于1938年出版,《怀旧》收入第7卷《集外集拾遗》中,从而第一次进入鲁迅的作品合集。此后各版本的《鲁迅全集》均收入《怀旧》,唯文本和注释有不同程度的修订。归还鲁迅之于《怀旧》的著作权,并使小说重见天日,周作人和那位“葛乔先生”功不可没。
此外,周作人论述《怀旧》的文章,尚有多篇,如《鲁迅的故家》之《九两种书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之《八八金耀宗》《八九秃先生的书房》《九○太平天国故事》诸篇,以及《知堂回想录》之《九二辛亥革命一——王金发》等等,或挖掘人物之原型,或探究情节之本事,内容各有侧重,亦屡见重复。其中《知堂回想录》之《九八自己的工作一》一篇,论述最详,而且偿还了1936年所作《关于鲁迅》一文中“查旧日记”之夙愿:
这回查看日记,居然在壬子十二月里找到这几项纪事:
“六日,寄上海函,附稿。”
“十二日,得上海小说月报社函,稿收,当复之。下午寄答。”
“廿八日,由信局得上海小说月报社洋五元。”
此后遂渺无消息,直至次年癸丑七月这才出版了,大概误期已很久,而且寄到绍兴,所以这才买到:
“五日,《怀旧》一篇,已载《小说月报》中,因购一册。”廿一日又往大街,记着“又购《小说月报》第二期一册”,可知上面所说的一册乃是本年的第一期,卷头第一篇便是《怀旧》,文末注云:
“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本文中又随处批注,共有十处,虽多是讲章法及用笔,有些话却也讲的很是中肯的,可见他对于文字不是不知甘苦的人。但是批语虽然下得这样好,而实际的报酬却只给五块大洋,这可以考见在民国初年好文章在市场上的价格,……至于那篇《怀旧》,由我给取了名字,并冒名顶替了多少年,结果于鲁迅去世的那时声明,和《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并退还了原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317页。
查1912—1913年《周作人日记》原文,与《知堂回想录》中的引文略有分别: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寄北京函,又上海函。
十二日,……上午得小泽二日函,又《白桦》一册,又上海小说社函,稿收,当复之。下午寄答。
廿八日,由信局得上海小说月报社洋五元。
(一九一三年七月)五日,……《怀旧》一篇,已载《小说月报》中,因购一册。*《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427、456页。标点为引者所加。
可见,《知堂回想录》中的引用,后两则与日记原文相同,前两则有明显增饰。由于日记往往过于简略,非如此无法记述《怀旧》由投稿到获得用稿通知的过程。而周作人强调刊载《怀旧》的《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拖延至1913年7月才出版,也可能出于误记。这一期版权页上标注的出版时间为1913年4月25日。《怀旧》投稿、收到用稿通知及稿费并刊出时,周作人均在绍兴。刊物延迟数月才进入绍兴图书市场,使他无法在第一时间见到,也属正常。当然,也不排除这一期的实际发行时间就是当年7月。而1913年6、7月间,鲁迅回绍兴省亲。在7月5日的日记中,有“午后同二弟、三弟往大街明达书庄买会稽章氏刻本《绝妙好词笺》一部四册,五角六分。又在墨润堂买仿古《西厢十则》一部十本,四元八角”*鲁迅:《癸丑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71-72页。的记载,当与周作人购买《小说月报》于同时同地,却没有关于《怀旧》和《小说月报》的只言片语。
以上借助若干史料,还原了《怀旧》由投稿、发表、重刊到引起反响的过程,可知《怀旧》并未引起鲁迅的重视,对题目、署名和发表刊物记忆皆含混不清。鲁迅的态度,未必如研究者所论,体现出“悔其少作”的深刻用心,或对于清末民初的文坛深致不满,事实上就是因为年代久远而遗忘。何况,《怀旧》的题目和署名,均由周作人拟定,鲁迅既未参与其中,亦非投稿人,印象不深也属情理之中*周作人为《怀旧》拟定题目和署名并向《小说月报》投稿,时在1912年末。鲁迅彼时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兄弟二人虽书信往还不断,但相关通信均已不存,是否讨论过小说的题目、署名及投稿情况,不得而知。二人的日记中亦无相关记载。因此,在没有出现新史料的情况下,可以推定《怀旧》的发表与鲁迅并无关联。。倒是周作人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代为拟定题目和署名并投稿,还在鲁迅逝世后多次撰文,既恢复了鲁迅的著作权,又对小说的主题和艺术加以阐释。周作人对于《怀旧》阐释的深度与限度,不断引发后世学人的认同、发挥、质疑与反驳,这似乎预示着此后的数十年间《怀旧》阐释史的复杂样貌。而初刊《怀旧》的《小说月报》则常常作为载体和背景,遭遇悬置。得到关注与肯定的,是由鲁迅创作的《怀旧》本文。
二、阐释的深度与限度
周作人涉及《怀旧》的文章,其价值不限于提供与小说相关的若干史料,对于《怀旧》主题和艺术的阐释,也有所创见,影响及于后世。
对于小说的主题,周作人强调“《怀旧》里影射辛亥革命时事”*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九两种书房》,《鲁迅的故家》,第214页。。这一论断为后世研究者接受,并有所发挥。查周氏原意,系指小说中的村人误将过境难民视为长毛或革命党、皆欲逃难的情节,是以辛亥革命期间绍兴发生的真实事件为本事,其中并不包含对于辛亥革命的价值判断。而在后世研究者的阐释中,《怀旧》的主题则成为对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反思与批判。周作人是“影射辛亥说”的始作俑者,此后的阐释则渐行渐远。对于这一研究思路的质疑,始于王富仁《论〈怀旧〉》一文*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90页。。该文指出这篇小说的主题不在于反省某一具体事件,而在于从文化层面对中国社会展开批判。伍斌和史承钧的论文*伍斌:《〈怀旧〉——探索“国民的灵魂”的最初尝试》,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2期;史承钧:《〈怀旧〉的时代与主题——兼评历来对它的一种误解》,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9期。则将小说主题总结为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此后,多数研究者不再将《怀旧》的主题与辛亥革命相关联,周作人对于小说主题的阐释,影响渐歇。
周作人对于《怀旧》的艺术也有所阐释:
这《怀旧》的题目定得很有点暧昧,实在也是故意的,本文说的是眼前的事,可是表面上又是读《论语》对两字课的时候,假装着怀旧,一面追述太平天国,乃是真正的旧事了,但因此使得本文的意思不免隐晦,也是一个缺点。……至于别的言动,自然不是写实的,因为是讽刺,所以更不免涉于夸张了。*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八八金耀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0页。
周作人对“怀旧”与小说叙事之独特关联的阐释,眼光独到,指出了《怀旧》文本中时空的复杂性:眼前的现实时空与追述中的过往时空相互交错与叠加,使本文结构及其内涵均体现出一定的复调性。这在周作人看来是不免隐晦的缺点,但在后世研究者眼中却成为《怀旧》文本的“现代性”之所在,是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的重要标志之一*普实克将《怀旧》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主要着眼于小说淡化情节的抒情性特质。而后世研究者对于小说之“先声”意义的开掘则是全方位的,除情节因素外,还涉及结构、叙事及文体,从而使《怀旧》的价值得到了更全面也更充分的阐释。其中,普实克的学生、捷克汉学家米列娜的研究颇见深度,在《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中国短篇小说1906—1916》一文中,米列娜指出《怀旧》文本中蕴含着“可见”和“不可见”的两个世界,并解析文本中传统符号系统和私人符号系统的二元对立关系,令人耳目一新。不过,米列娜富于创造性的阐释建立在对于小说重新断句的基础上,而《怀旧》发表于《小说月报》时已有圈点,米列娜的重新断句略显主观,似乎有过渡阐释之嫌,作为一种“创造性误读”,可聊备一说。见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499页。亦可参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一书中的相关辨析,第152页。。两相对照,周作人阐释《怀旧》的深度与限度,均格外明显。
总之,周作人对于《怀旧》的关注,无论是提供史料还是加以阐释,均着眼于小说的文本本身,刊登《怀旧》的《小说月报》仅仅作为载体和背景,并不在论述的范围。主编恽铁樵的评点与附志也被视为小说文本以外的因素,单独予以置评。而且,周作人对于《小说月报》和恽铁樵似乎还颇有微词。
在前引《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感叹《怀旧》虽获佳评,稿费却只有五元,对于这篇小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颇为遗憾。事实上,《小说月报》自1910年创刊起,即注重征集短篇小说,不仅开设“短篇小说”专栏,在第一年第一期的《征文通告》中即明确提出:“本报各门皆可投稿,短篇小说尤所欢迎。”对于稿酬则规定:“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载《小说月报》第一年第一期,1910年7月25日。标点为引者所加。这一征文通告在此后的各卷各期、包括恽铁樵主编时期均得以延续,只是鉴于清末和民初货币及其购买力的不同,稿酬等级和金额有所调整。在《怀旧》投稿并发表的1912—1913年间,标准为:“中选者,分三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三元;乙等,每千字二元五角;丙等,每千字一元。”*载《小说月报》第三年第一至六期均刊载这一通告。标点为引者所加。而刊载《怀旧》的前一期,即第三卷第十二号,特地刊发《征求短篇小说》的启事:
本社现在需用短篇,倘蒙海内文坛惠教,曷胜欣幸。谨拟章程如下:(一)每篇字数一千至八千为率;(二)誊写稿纸,每半页十六行,每行四十二字;(三)稿尾请注明姓名住址;(四)酬赠照普通投稿章程格外从优;(五)投稿如不合用,即行寄还;合用之稿,由本社酌定酬赠,通告投稿人;如不见允,原稿奉璧。*载《小说月报》第三卷第十二号。原文有断句,新式标点为引者所加。
《怀旧》全文(不含恽铁樵的评点和附志)4000余字,得稿费五元,依《小说月报》的稿酬标准,当属丙等。而且是否“照普通投稿章程格外从优”,因而在四元的基础上增加一元,不得而知。可见,在编者眼中,这篇小说的价值并不像评点和附志中所显示出的那样值得赞赏和推崇。主编恽铁樵在当时已是民初文坛享有盛名的前辈,“署名周逴”的作者鲁迅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小说月报》发表《怀旧》并借助评点和附志予以好评,出于前辈对于新人的奖掖提携,同时将评点植入小说本文之中,意在为后辈树立文章之轨范。因此,恽铁樵未必是以平等的姿态看待《怀旧》,表面上的热情赞扬也未必能够代表编者对于这篇小说的综合判断,以“丙等”标准支付稿酬,从中可见一斑。纵观恽铁樵主编的各卷各期,这类评点并不十分常见。其中或考虑到作者身份,如林纾、许指严、徐卓呆、包天笑等名家,不便采取“批评的老师”之姿态;或限于文体,如翻译小说、诗词、杂剧等,不宜从章法及用笔处立论。综上可知,恽铁樵对《怀旧》是欣赏的,不仅通过评点和附志予以大力推介,而且几乎是一经投稿,即立刻允诺刊出,并寄赠稿酬,效率之高,态度之热忱,对于初登文坛的后辈而言无疑是一份难得的鼓励。然而,对于恽铁樵而言,自家撰写的评点和附志似乎与《怀旧》的文本不可分割,读者只有将小说与评点及附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阅读,才能感受到《小说月报》的编者借助新人新作,示青年以辞章之轨范的良苦用心。后世研究者常常质疑恽铁樵的评点和附志只涉及作文的章法及用笔,忽视了小说的主题及其他艺术因素。事实上,恽铁樵恰恰是在文章学层面立论,关注的未必是《怀旧》作为短篇小说的价值。
恽铁樵于1935年去世,未能看到周作人一年后发表的《关于鲁迅》。《怀旧》作者的真实身份,于他而言永远是个谜。倘若恽铁樵生前能够知道“周逴”即后来如日中天的鲁迅,会作何感想?后人也无从知晓。新文学兴起后,恽铁樵逐渐淡出文坛,后从事中医行业,曾经辉煌的文学事业,渐成明日黄花。《怀旧》的作者是鲁迅也好,是无名后辈也罢,于他而言已无关紧要。不过,恽铁樵对于《怀旧》的评点,在鲁迅研究之外尚有其独特价值,就是提供了清末民初报载小说的独特文本形态。报刊的出现无疑改变了读者、包括作为高级读者的编辑和批评家对于小说的阅读方式。通过单行本或报刊本会产生不同的小说阅读体验。尤为突出的现象是,清末民初的报刊编辑往往兼具小说家和批评家身份,这使其在看待小说时往往独具只眼或者别有慧心,作为行家里手,眼界甚高,在编辑报载小说的过程中,也就不局限于编者立场,不但可以力推佳作、奖掖后进,还可以借助批注和按语,表达自家的小说观念和审美趣味。恽铁樵采用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方式,对于《怀旧》随文批注,同时借助名为“焦木附志”的编者按加以总结,此举延续了小说评点这一批评模式,而又有所拓展。以金圣叹、毛宗岗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往往对于已经为读者所熟知的小说文本加以评点,“原文+评点”(包括评点家对于原文的改写)并非小说面世的最初文本,原文与评点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关系。评点家的意义,在于使熟悉的小说文本重新陌生化。而恽铁樵在《怀旧》的字里行间植入评点,使“原文+评点”成为这篇小说进入传播领域最初的文本形态。这样,创作在先的原文和书写在后的评点及附志得以共识性地呈现,作为一个整体为读者接受。于是,原文和评点一并成为报载小说《怀旧》文本的组成部分。这一文本构成的方式为报载小说所独有,体现出清末民初小说作者、编辑(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独特的互动关系。
此外,借助《小说月报》提供的语境和文本形态考察《怀旧》,还可能产生以下疑问:首先,作为报刊编辑和文坛前辈的恽铁樵,对于“周逴”这类新人的投稿,在刊发之前是否会做出删改,难以确知。如果确有删改,《怀旧》的著作权还能否归鲁迅一人所有,尚存疑问。与此相应,如果恽铁樵和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家一样,为呈现个人眼光而径改小说原文,后世研究者借助不含评点与附志的文本阐释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及文学史地位,是否会造成个别误断?同时,《怀旧》的题目为周作人所加,并非出自鲁迅之手,如果以《怀旧》为视角阐释鲁迅的小说观和文体意识,是否存在区隔?《怀旧》是在鲁迅逝世后被重新发现,从而引起广泛关注的,如果小说作者的身份一直得不到确认,《怀旧》是否还会得到海内外学人的深入阐释与一致好评,产生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当然,上述疑问均属于推测,很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于鲁迅研究而言,也许会有特殊的意义。至少,借助《小说月报》提供的语境和文本形态考察《怀旧》,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也是报刊之于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
普实克在他卓有见地的论文中,将《怀旧》视为一个“孤立现象”,意在强调小说创作于“文学革命”发生之前,不能用新文学的一般趋势来加以阐释,但《怀旧》与同时代的文学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完全是一部新的现代文学的作品,而绝不属于旧时代的文学”*[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作:《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沈于译,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466页。。普实克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的视角出发,敏锐地发现了《怀旧》在小说形式上的独特性,其思路和眼光均极具启发性。借助普实克的思路并予以适当修正,避免以“新旧交替”和“现代转型”为清末民初文学唯一的剧情主线,而将《怀旧》置于改版前的《小说月报》的历史语境之中,将鲁迅创作的小说文本与恽铁樵撰写的评点及附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和阐释,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