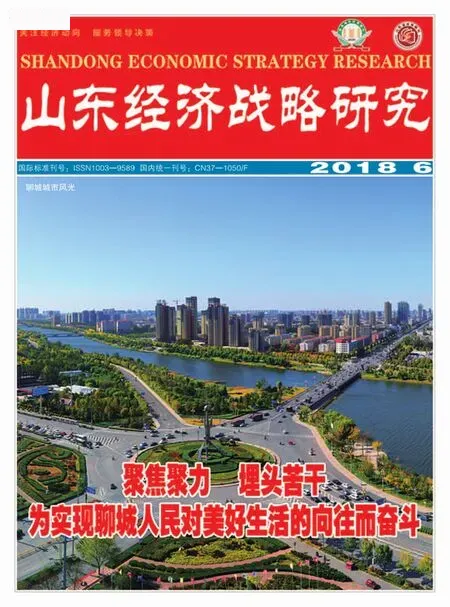李培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近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发表文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一、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李培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一)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6900多万人,占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占12.2%。到2016年,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2亿人,占28.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近3.3亿人,占43.5%。
随着工人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60%。
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工人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务业工人的人数不仅超过了工业工人,也超过了农民。
三是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减少。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到2015年,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达到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1亿多人。
(二)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9.6亿人口中,有7.9亿农民(农村居民),占82%,在4亿多从业人员中,有农民(农业从业人员)2.8亿人,占70%。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变迁,到2016年,在全国13.7亿多人口中,有6亿多农民(农村居民),占42.6%,而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有2.2亿多农民(农业从业人员),占27.7%。
农民阶级发生了几个大的变化:一是相当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劳动力,都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二是在务农的农民中,出现了一些从事种植、养殖、渔业、牧业、林业等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以及数量众多的兼业户,纯粹务农的小耕农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幅度减少;三是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农民,呈现高度高龄化,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
(三)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1978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约1500万人,约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4%;到2015年,这个群体达到5000多万人,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2.5%。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不再是“被改造”对象,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主体。二是经济地位也显著提高,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收入“脑体倒挂”的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平均收入水平已高于公务员的平均水平。
(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908万户,私营企业主(投资人)3560万人,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为87.3%;注册资本(金)90.55万亿元,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金)的53.8%;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64亿人,雇工人数1.28亿人。
私营企业主目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绝大多数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74%。二是近60%的私营企业主集中在东部地区。三是受教育程度并不高,约40%只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受过大专教育的占31.8%,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占28.7%。四是收入呈现高度分化,2015年年收入的中位数是12万元。但与此同时,根据福布斯的研究报告,2016年全球共有1810位富豪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其中,中国有300多位,富豪总数居世界第二,251位来自中国大陆。
(五)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新社会阶层”做了概括,归纳出三种人:一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二是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三是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2016年,全国新社会阶层约有5000多万人,他们在社会上影响不断增强。
二、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产生的新特征新挑战
李培林认为,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具有以下新特征、新挑战:
(一)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社会依然充满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造成我国利益格局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仍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仍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社会流动较快,具有很多发展机会和较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产生一些两难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用几十年走完很多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历程。所以,往往一个阶段还没有结束,另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存,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同在,从而使我们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处于首尾难顾、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
(三)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工人阶级的两个最大变化,一个是有2亿多农民工加入到工人阶级,另一个是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白领”职工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蓝领”职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农民阶级也发生深刻变化,不仅人数大大减少,高龄农民可能会成为我国最后一代“小农”,未来的新型“农业经营者”,将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农基础阶级的利益,特别是防止他们当中的那些弱势群体被现代化的列车抛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必经过一个漫长过程,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耐心。

(四)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防止社会分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脱离大众群体,从而造成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我国在近40年的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中,随着利益格局的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精英群体脱离群众的倾向,这是需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的。
(五)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将会长期存在。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群众因利益受损产生强烈不满,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堵塞交通、焚烧汽车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等对抗方式使人民内部矛盾走向激化,都是可能发生的。在这些事件中,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的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置稍有不当,局部问题就有可能扩散到全局,从而把非对抗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必须充分认识到此类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依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