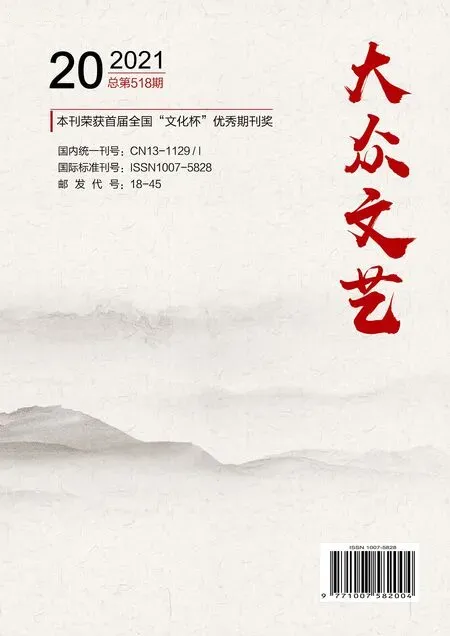张爱玲《老人与海》译作中女性主义的东方色彩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315212)
一、引言
海明威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出版于1952年,语言简洁干净,明快有力。它在文坛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欧洲,被认为是20世纪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促进欧洲文学的发展。这本小说风靡全球,在中国,其译本就超过20个。根据学者陈子善《范思平,还是张爱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新探》(陈子善,2011)中的研究,张爱玲1952年12月发表于香港中一出版社的《老人与海》译本,署名范思平,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译本。
二、文献综述
张爱玲译本具有特色,她在翻译时并没有十分忠实原文,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塑造的与大自然搏斗的硬汉形象,在张爱玲的译笔下,悄无声息地变成象征两性平等的、代表全人类的温柔的渔夫形象。很多学者认为张爱玲在《老人与海》中用到了带有女性主义的翻译手法。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主要有三种:“增补、加写前言与注脚和解释”(Luise,1991)。张爱玲在《老人与海》中,也用到了这三种手法。
一是加写前言。《老人与海》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充满男性的力量,是男性的世界,张爱玲却想表达两性平等的观念,她在其译序中谈到: “老渔人在他和海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 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和气概。” 在张爱玲眼里,“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金宏达、于青,1992)。张爱玲笔下,老人的形象和精神不再是男性特有的,而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包括女性。通过加写前言,张爱玲表达了自己两性平等的观念,“希望当时的女性能够意识到并学习渔夫身上这种坚忍不拔的品质,为自己的处境和当时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光明”(周雯思,2010)。二是增补。张爱玲将原文中“man”一词直接间接地译成“人类”这一概念,而吴劳、海观和黄源深翻译成“男性”的概念,“张爱玲翻译却通过增补的方法将女性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提高,补充了翻译文中对女性的缺失”(李俊彦,2015)。三是劫持。张爱玲将“he”译成“它”,而“she”译成“她”,“老渔人身上表现的可惊的毅力不只是属于男性的,而是整个作为社会人的男人和女人所共同拥有的风度和气概”(王惠珍,2010)。
但是,张爱玲不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译者,她自己没有指出她是女性主义,也没有明确提出女性主义观点。西方女性主义在翻译中,是张扬地,明显地,“大声地”为女性发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西方的女性主义是较激进的,她们在翻译上“颠覆男性父权制话语”(陈吉荣、张小鹏,2007),“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Simon,1996)”,来“粗暴地妇占所译的语篇(Godard,1990)”。“她们始终以颠覆原有的性别秩序为目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Luise,1991)。
张爱玲《老人与海》译作中的女性主义与典型的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张爱玲《老人与海》译作中女性主义具有东方色彩。她在译作中用叠词、颜色词和拟声词,这些具有女性特色的词汇暗示了其女性主义思想,潜移默化悄无声息地展示了女性译者身份,以柔克刚,但同时,又尊重了男性作者,体现了“和”的思想,所以张爱玲在《老人与海》译文中体现的女性主义具有东方色彩。
三、张爱玲成长中形成的女性主义
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将会产生最长久的影响(罗小年、王高华,1993)。从张爱玲的成长环境中,可以看出张爱玲不喜欢她的父亲,甚至有点恨他。张爱玲自己也曾在《对照记》中坦承“这些记忆都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张爱玲,1994) 张爱玲的父亲是个旧派绅士,与她的父亲不同,其母亲却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由于两人的种种观念都不合拍,所以经常吵架,最后以离婚收场。所以张爱玲童年极度缺乏母爱。离异后,她的父亲又娶了个女人。有一次,张爱玲因为留学的事情与父亲起了争执,在父亲与继母的毒打后,得了重病,而他的父亲并没有请医生,反而把她囚禁在家。张爱玲随后表达,“我也知道父亲绝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出来的时候己经不是我了。”(张爱玲,2003)
而对于母亲,张爱玲是又喜爱又崇拜。张爱玲把她当成榜样、可以说话交流的挚友。在其母亲去世后,都将她当成唯一想说话的人。张爱玲的母亲,因深受西方现代文化教育的陶冶,具有现代意识。四岁留学法国,而法国当时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张爱玲的母亲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熏陶。而张爱玲的姑姑先在英国的商场做会计,后又跳槽到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戏院做翻译,戏院总经理见她才华过人,礼聘她为机要秘书。独立又能力过人的母亲与姑姑是张爱玲的偶像。身边的男性都碌碌无为,而身边的女性又那么强大,这些经历造就了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孟悦和戴锦华曾评论说: “张爱玲的世界毕竟是一个女人的、关于女人的世界”(孟悦、戴锦华,1989)。
四、张爱玲《老人与海》译作中女性主义的东方色彩
张爱玲在翻译时,并没有像西方女性主义译者那样强势、张扬,而是用了更加柔和、含蓄的方式——她没有刻意模仿海明威的硬汉语气,抑制译者主体性,用叠词、颜色词、拟声词,这些女性爱用的词汇,悄无声息地植入女性主义思想,柔和了《老人与海》原文的阳刚之气,将自己“造作”的写作风格充分融入到译作中,几乎改变了译作的风格.这种方式就像太极拳,以柔克刚,充满了东方主义色彩。
1.叠词
研究表明,父母“在对女儿输入语言时,父母的语气会比较温和,而且不厌其烦,因此叠词的输入频率相对来说就高;在对儿子输入语言时,父母的语气就比较干脆利落,叠词的输入频率相对较低”(彭小红、白小芳,2014)。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声声慢》中用了七组叠词来营造了凄惨的气氛。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的语言风格是简明的。但是张爱玲高频率地使用叠词,据统计,“张爱玲译本中运用叠词约 250 余次,其形式涵盖了汉语中几乎所有常见的叠词形式,且这些叠词中所含语言成分的词性范围也较广用词也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而相比之下,余光中译本中的叠词运用仅有 170 余次,且其中‘慢慢、缓缓、轻轻、渐渐’这一类常见的叠词就占去了近 1 /4 的比重”(宋颖,2012)。
例1:His mind was on horses as well as baseball.(他心心念念除了棒球还有赛马。)
例2:“Make another turn. Just smell them. Aren’t they lovely? Eat them good now and then there is the tuna. Hard and cold and lovely.”(“再兜一个圈子。你闻闻看。这沙丁鱼可爱不可爱?好好地吃它们吧,不时还可以吃吃那鲔鱼。硬硬的,冷的,可爱的。”)
《老人与海》原文中的老人是个硬汉形象,而张爱玲用“心心念念”形容老人的喜好,似乎与海明威简明的语言风格不符。翻译老人的话语时,用了“可爱不可爱”,“硬硬的”这些充满童趣的叠词, 老人在与小男孩说话时变得温柔,很难想象一个这样坚毅的英雄会用这种语气。在张爱玲笔下,老人俨然变成外表刚强,内心柔软的形象,其柔软温柔的内在,影射了女性的形象,使主人公渔夫不仅是代表了男性,而是代表了全人类,包括女性。张爱玲翻译时不经意间展露了其女性译者的身影,将自己的语言风格放入译文中,含蓄地运用了女性主义翻译手法。
2.颜色词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Lakoff(1973)认为“女性比男性对颜色的辨别更精确,掌握的词汇更丰富”(刘莹,2009)。虽然男性和女性同时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中,他们有着不同的接受机制。张爱玲对《老人与海》原文中出现的颜色,相对敏锐,有更精确的掌控,翻译得更加栩栩如生。
例3:He broke the surface of the blue water…(它冲破蓝色的水面)
例4:He could see the blue back of the fish in the water(他可以在水里看见那条鱼的青色背脊)
两个例句都用了“blue”这个颜色词,但是通过常识,水面的蓝色和鱼脊背的蓝色是不一样的。中文中有句谚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是从蓝中提取出来的,但青比蓝颜色更深,青和蓝很难辨别,没有标准。张爱玲用女性对颜色的敏锐直觉,将鱼脊背的蓝色译成“青色”,区分了海水的蓝。
例5:…the stripes showed the same pale violet color as his tail(那条纹和它的尾巴一样出现雪青色)
这句话上,余光中译成“那些条纹也显出尾巴一样淡紫的颜色”(余光中,2010),将“pale violet ”译成淡紫色。对于颜色深浅的划分是相对的,用“淡紫色”描述鱼纹过于模棱两可,不够恰当,有些诡异。张爱玲则译成“雪青色”,区别了鱼不同部位的颜色,但是又与例4中鱼脊背的“青色”呼应,“雪”字描写出了颜色的深浅,实现了颜色的过渡。“雪青色”描述活鱼,合乎常理。
相对男性译者来说,张爱玲对颜色词的翻译更为恰当。张爱玲在翻译颜色词时,运用了她的经验及想象力,使译文“五颜六色”充满女性语言特征,展示了她女性译者的身份。
3.拟声词
女性的情感丰富,感官体验深刻,不仅在视觉上,还表现在听觉上。研究表明“女性通常情感丰富,感官体验深刻,她们在语言中喜爱使用情感色彩强烈夸张的字眼,有时又优柔寡断、用词含蓄”(宋颖,2012)。因为女性天生情感丰富,而拟声词用起来形象生动,丰富了情感,所以女性无意识地用拟声词渲染气氛,加强感染力。张爱玲在《老人与海》译本中,多处用了拟声词。
例6:…the clicking chop of the teeth as he drove forward in the meat just above the tail.(它在尾巴上面点的地方咬住一块肉,牙齿锥进去的时候噶嗒一响。)
原文并没有出现拟声词,但张爱玲却将“clicking”翻译成“噶嗒”。“噶嗒”虽口语化,但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咬的狠劲与力度之大,鲨鱼的强大与老人的弱小形成鲜明比。在这句话的处理上,余光中的版本是“它的利齿咬鱼尾前面的厚肉时清脆的声响”(余光中,2010),没有用到拟声词,理性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可以看出,这句话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张爱玲偏向于生活化的表达,使用拟声词使她的译文更令人身临其境。余光中的译文则相对客观理性,译者主体性的活动较少,使读者的想象空间较少。张爱玲将自己的语言风格用到译文中,没有抑制译者主体性,潜移默化地将女性译者身份展露无遗。
4.对男性作者的尊重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是男人的世界,都是一些捕鲸、猎狮,各种危险性的运动,张爱玲在前言中写道“捕鲸、猎狮,各种危险性的运动,我对于这一切也完全不感兴趣。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诧异,我会这样喜欢《老人与海》。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张爱玲翻译《老人与海》是出于自己的喜欢,“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是因为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1992),《老人与海》所描写的苍凉使张爱玲有了共鸣。张爱玲在翻译时,没有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激进,贬低男性,甚至使用“妇占”,而是尊重男性作者。
例7: “Don’t sit up,” the boy said. “Drink this.” He poured some of the coffee in a glass.The old man took it and drank it. “They beat me,Manolin,” he said. “They truly beat me.” “H e didn’t beat you. Not the fish.” “No. Truly. It was afterwards.”(“不要坐起来,”孩子说。“喝掉这个。”他把咖啡倒些在一只玻璃杯里。老人拿着,喝了它。“他们打败了我,玛诺林,”他说。“他们确实打败了我。”“它并没有打败你。那鱼没有打败你。”“没有。真的。是后来。”)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语言是简洁的。相反,张爱玲的译文,语言却用了她一贯的“做作”风格。虽然张爱玲在前言中提及《老人与海》应体现两性平等的观念,但她并没有在翻译时极大幅度地改动原文来达到此目的,而是含蓄地用女性语言,发挥译者主体性来实现。所以在语句结构上没有太大改动,在语言内容上也保留了原来的意思,符合海明威的“冰山风格”,尊重了原作者。
这段对话翻译,张爱玲用非口语的文字翻译了老人与孩子之间的对话,这不符合当地的质朴民风,不像一个硬朗的男性形象。这是典型的张氏女性语言,就像张爱玲在她的《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句子“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张爱玲,2002),读起来有点做作,蕴含着女性的“多愁善感”。
张爱玲在体现女性主义的同时,尊重了男性作者,体现了儒家“和”的思想,充满东方色彩。
五、结语
因为张爱玲在《老人与海》译文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却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那样张扬地为女性发声,甚至出现“妇占”现象。所以本文试从张爱玲成长环境分析,张爱玲因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身边的男性软弱无为,女性却强大独立,极大可能形成了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思想。她在《老人与海》译本中,而是运用叠词、颜色词、拟声词,这些充满女性特征的词汇,含蓄内敛低调地展现其女性译者地身份。虽然她在前言中,展示出两性平等的观点,但她并没有及大幅度地改动原文,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尊重男性作者。她也没有因此抑制译者主体性,而是将自己地语言风格不知不觉中放入译文中。张爱玲在《老人与海》译文中所展现的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原因是其具有东方色彩。
——积累AABB式拟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