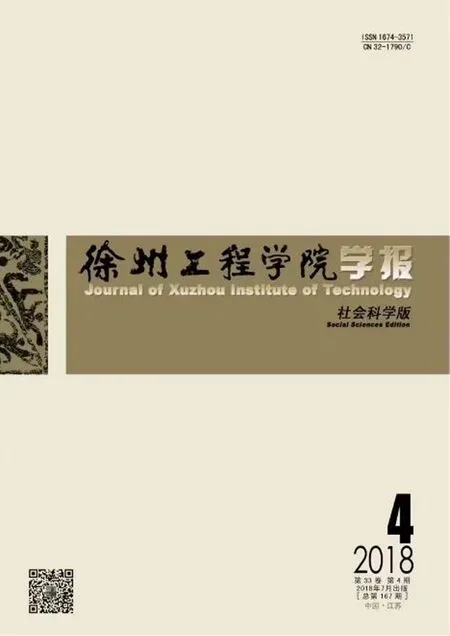山地研究的话语遗产①
徐新建
(1.电子科技大学 数字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1731;2.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一、为什么要关注山地表述的纵横演变
学术研究古今相连,形成特定的话语连续体。从时间、空间和类型维度看,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有继承性的。以“山地”为例,这一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很悠久的学术史了。在汉语文献的表述进程中,从最早的《禹贡》《山海经》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对山川地貌加以描绘、阐释的传统,并由此区分“天下”“王土”的不同分布与景观。近代之后,受西学东渐影响,又出现了持续至今的人类学转向。2015年在云南举行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就是“人类学的山地文明研究”[1]。论坛云集了海内外许多学者,从人类学视角讨论了山地文明。人类学高级论坛每次聚焦一个关键概念,如海洋文明、山地文明、游牧文明、村落文明等,2015年这届转向“山地文明”,说明了对山地研究的进一步关注。
依照学术界的一种划定,“山地”的含义大致指海拔在500~2 500米之间,相对高度大于100米或坡度大于25°的区域。按照此标准,当代中国版图内的山地区域占了国土总面积的68%以上[2]。参见图1。在这意义上,中国堪称一个山地之国,关注山地是理所应当的事。如今,随着对人类与生物圈密切联系的重视,山地研究更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话题。20世纪70年代之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BA)便把 “人类活动对山地生态系统影响研究” 列入进去,从而将世界性的山地研究推向新的时代[3]。
笔者长期在西南工作学习,对山地有种天然的认同感,比如对贵州,过去最为熟悉的地域概括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和“全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两句俗话,十分形象地表述了黔省的山地特征。所以在贵州生活工作的同事,大多对山地有天然敏感,在贵州做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与“山地研究”相关。面对这样的背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知识再生产该如何推进?有无必要对积累至今的山地研究加以梳理总结,把它视为学术史上特定的表述遗产,从中概括出值得发扬或改进的话语体系?

图1 占国土面积68%的中国山地,其中西南占了重要部分 左图引自张伟《基于DEM的中国山地空间范围定量界定》,《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年第5期,61页 右图引自http://image.dljs.net/uploads/allimg/map/china/2134152148-0.jpg
二、山地表述的古代话语
山地是人类世代栖居的一种类型。由于处境与认知的不同,对于山地的表述多种多样,形成了交错对应的多元话语。从语词本源看,“山地”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自然的概念,并不包含人;但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看,“山地”也涉及作为人类居所的山区,于是就涵盖了山民和山寨。在古往今来的传承中,“山地”已经沿用了很久,已演变为借助自然地理的概念来展开的文化表述,也就是以“山地”指代特定类型的区域文化。
但如果只使用“山地学”这样的范畴则还需严谨,因为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可以指“无人”的区域或不涉及人,可以讨论该地的植被、鸟类、矿物产等等。所以人类学语境中的“山地学”概念与文化相关,是作为与人类栖居相关的一种类型。之所以强调“一种”,是要指出不能以为身在山区就把山区无限夸大。恰恰相反,在以往的传统认知中,“山地”其实是个边缘概念,意味着贫瘠、落后乃至蛮荒,在众多人类栖居的类型中是不重要的。相比之下,平原、坝子、河谷、草场直至集镇、都市等才是世人心目中的人类宜居地和文化核心区。
此外,在山地中伴生的文明,也就是如今被称为“山地文明”的类型,显然已包含在“山地”这一特定概念之中,并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与研究。这便是进行山地表述之话语梳理的自然、文化与学术史基础。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汉语文献的山地表述沿革。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强调“汉语文献”是因为在多民族中国的表述整体中,还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山地表述需要参照对比,仅以西南为例,就需要了解藏缅、苗瑶、壮侗等不同语族人群对山地的看法。站在这些族群的主位立场去认知、理解和阐释山地的特征、意义和价值。
在汉语世界,记载山地的文献众多,流传较广。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山海经》,最具影响的莫过司马迁《史记》里的《西南夷列传》。《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组成,通过东西南北方位的顺序排列,对众多山川、河流的地貌和物产分布作了神话式描绘。其开篇之首《山经·南山经》写道:
南山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4]1
在这段描绘里,如果说对“鹊山”、“招摇山”位置及物产的介绍算得上自然地理的话语表述的话,其所涉及的山名称谓和植物食效等则已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认知。在接下来的《西山经》则出现了超出常识的奇异刻画:
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4]22
或许由于呈现出这种虚实兼顾的特点,《山海经》被后世学者视为既是史地文类之发端,亦是神话叙事的宝库[4]36,2。而也因如此,这种神怪结合的手法,开启了汉语文献对于包括西南山地在内众多蛮荒区域夸张想象的先河。参见图2。

图2 《南山经》和《海内南经》牛头蛇尾的“鯥鱼”与反足披发的“枭阳国人”[5]
与《山海经》同样重要的还有《周礼》和《礼记》等。《周礼·夏官》对现实与想象中的“天下”疆域作了方位、类型及等级式区分,描绘说: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其利害,乃辩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
《逸周书·职方》制定出由近及远的“九服”格局,称:“乃辩九服之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甸服……”
《礼记·王制》对王权治理的版图作了世俗与体制化的表述和规定,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强调“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以此为基础,再以王朝远近、轻重为标准,划定逐层递减的区位等级,形成我称之为“一点四方”的夷夏结构[6]。参见图3

图3 《周礼·职方》及《礼记·王制》呈现的“畿服图”与“一点四方”结构[9]
到了司马迁的《史记》时期,通过列传式的“西南夷”描写,再度奠定了汉语文献对于地域表述的文本范例,导致往下的韩钰典籍接续追随,重复模仿司马迁的话语样式,以中央王朝为中心、按东南西北、夷狄蛮戎的划分进行边地叙事,从而形成古汉语表述西南山地的经典传承。司马迁是如何表述西南山地的呢?首先,他从称谓上加以划分,称西南为“夷”,中原为“帝”“王”“皇”。在文字与词源学意义上,“帝”“王”“皇”均代表至高无上的圣明君主,而“夷”不过是还停留在狩猎阶段的“持弓人”而已。接下来,在表述样式上,司马迁进一步用文类进行区别,用次一等的《列传》记载西南之“夷”,而把视为最尊贵的《本纪》奉献给了中原“帝”。《本纪》以黄帝为首,用恭敬夸张的口吻作了赞颂式描绘: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7]1
称帝之后,情形大变;耀武扬威,四方归一,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7]6
与此对照,对西南夷又是如何表述的呢?作者改了笔法,写道: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7]2991
对中原王土,司马迁采用帝王叙事,竭力渲染君主个人的神奇禀赋与丰功伟绩,已呈现出后世史学的正统文风;对西南山地则只作群体勾勒,凸显“魋结”“编发”的怪异形貌以及如牲口般居无定所的落后处境,表述上更接近《山海经》的荒蛮离奇。因此,与其说作者对“西南夷”的表述是在为中原之外的他者列传,不如说是为了体现帝王正统威权而在寻找异端陪衬。
直到明代徐霞客以后,司马迁式的山地表述才逐渐改变。徐霞客通过身体力行的实地考察,对滇黔桂山区进行详细描绘,开创了山地表述的新话语。经由《徐霞客游记》流传的不少新概念和新用语,至今仍被后世学者沿用,例如“聚落”“山寨”以及“干栏”等。其中有关散居、聚居、村寨、高山、半山、水边等叙述,都超越了以往司马迁式的山地叙事,成汉语世界中关于山地研究的转型式模本。因此徐霞客的转型亦可视为对自先秦以来如《山海经》《水经》等相对独立的地理写作复兴。相比之下,由《礼记·王制》及《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开创的地方叙事,则通过把区域表述隶属在王权治理之下,变成了主流正史的话语附庸。
在汉语文献的山地表述史上,徐霞客是很奇特的现象,由他转型的地域独立写作值得关注。
到了近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进来之后,形成了一个中外古今渗透、对话的新格局。这个格局是现在我们所要面对的。从上述展现的时空和学术脉络中,不妨做一些比较,可以抓住对同一区域中不同表达的脉络,去看它缘何产生,特点何在,开启了什么,同时又有何遮蔽。
三、从“西南夷”到“熟苗地”
如果在世代流传的汉语表述体系中,司马迁撰写的《西南夷列传》堪称“山地”表述话语起点,则其中的“夷”字还可深入讨论。它蕴含很多值得发掘之处,有许多我们以为都已了解但其实不然的东西。比如说它为了区分地域等级的需要,讲“边塞”、贬“夜郎”,暗示了这些区域与中原的差异,其中还凸显了该地区的土著或迁徙,强调这个地方的人不断流动——游耕式的居住,即便定居也跟迁徙连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无君长”,即没有稳固的政治组织和领袖。这种无政治领袖的村落自治单位,与司马迁自己隶属的汉帝国相比显得格外另类。不过也正由于这样的对比性描叙,为后世存留了西南山地特有的边缘政治类型,值得在如今的山地研究中倍加关注。换句话说,今天的山地研究,若以西南聚焦的话,需要从西南之“夷”出发,分析在这地区是如何“夷”起来的。“夷”的含义本是平地,后演变为持弓的人。由于“他”的方式跟中原华夏的农耕定居的人们不太一样,又居在山地,故而被描绘为“夷”。可见,此处的夷,已被指代有别于平原华夏人的“他者”,属于教化之外的另外一群人。
有意思的是,到了徐霞客的描写中,通过把西南山地视为边缘与城镇之间的差异表述,作者进一步区分了“生苗”“熟苗”的演化。生与熟的区别不在别处,仅在于与中原的距离及接受汉化之程度。对此,徐霞客做了比较,比如有一段,他去当地仔细查看,他说,这个地方的人的居住环境十分糟糕,糟糕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就是糟糕到了比那些生苗的居住环境还要差。徐霞客写道:
……又西得一堡,强入其中,茅茨陋甚,而卧处与猪畜同秽。盖此地皆苗熟者,虽为佃丁,而习甚鄙,令人反忆土蛮竹栏为上乘耳。[8]
此处“苗熟”即“熟苗”类型,通常指的是汉化更成熟,生活水准更高的苗民。但在贵州此地见到的既然已属“熟苗”,为何居住地还会如此不堪,比“土蛮”都不如呢?此种反差值得辨析。按照学界的一般假定,某一文化被汉化(或涵化)后,会变得进步和富裕起来。其实不一定。参照如今的情景来看,那些被认为是“生苗”的人群居住地,为何更为优美自然?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保留了自生产的能力。相反,那些接近汉地被过早汉化的人群反倒丧失了这样的自生产能力了,以至于不但未能模仿汉人的居住样式,往往连原本传承的吊脚楼都已失传,落到居无蔽所的地步。所以这种所谓的“熟苗”才是最为可怜的。
在有关西南山地的日记里,徐霞客还留下许多不同类型的描述,材料丰富,生动具体,为后人留下了山地表述的宝贵遗产。
四、从“西南观”到“西南学”
为了凸显当代出现的话语转型,可暂且跳过晚清、民国,直达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期出现了汉语文献中山地表述的又一次崛起,在思想解放及西部开发浪潮下,有关西南的区域研究再度变成主流和热门话题。
在此着重说一下我参与其中的“西南研究丛书”团队。该丛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酝酿启动,云贵川三省编委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打破行省畛域,将西南视为内在联系的区域整体。于是,尽管概念仍突出“山地”,但其中的内涵和边界却不再仅仅以省为界看待或言说四川、云南或贵州的山、地、人,而是从空间上把它们当做整体,视为完整关联的地理单位和文化区,由此再度与以往沿用的“云贵高原”“岷江流域”等贯通、连接。在这种不以行政省为界的表述中,许多具有相互关联的生态与文化事象得以凸显,并通过相应的语词、术语被呈现,如“卡斯特地区”“干栏式建筑带”“铜鼓文化圈”等。这些表述与实际情况吻合,都是超越行政省域限制的。但建国以后,由于受到行省观念的制约,以上现象不仅在隶属及管理上被分割,在理论表述上也受到肢解,西南山地所内含的多种事物便受到极大扭曲,失去了彼此关联的整体特征。
此外,丛书成员还从地名源起的知识学角度对“西南”概念进行反思,提出内外对照的双向观点。比如以西南为中心看周边,而不是以中原为中心看西南。因为“西南”这一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被命名,“西南”不是自己的名称,是西南之外的他者所赋予之名,代表着别处某地人们的西和南。然而事实上,西南原本就是区域性的自我存在,是自己的中心,以西南为中心延伸出去,同样有东南西北四方,也有相应的四方边地。
在“西南研究丛书”总论的《西南研究论》里,我曾用“三角地”图式阐述过以西南为中心的空间关系,强调三大文化交汇地的区域关联[6]。参见图4。

图4 “西南三角地”图示
图4所示,三角地的东北面是黄河上游,东南面是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关键是它的西南面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所以西南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极具深厚文化的凝聚地,众多的宗教类型都能在这里见到,而且佛教的几大分支都在这里汇集,包括汉传、藏传、南传佛教。这样的西南山地就不仅只是中原的西南方和华夏的他者。“西南”是自己的家乡,拥有自己的中心。如今又有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表述能否延续?这样的话语要不要继承?如果像眼下许多论述呈现的那样,又回复到仅以某省、某县为界,用分割的眼光看待山地,我们的地域和空间研究很可能再度失去活力。由此我想强调的是,实践中的行政区划无疑具有治理之用,但学术研究及文化视野则应该是超越行政和区划的。
关于西南山地的表述话语,还可注意国外学者的相关发挥论述。他们也从不同角度关注过我们强调的“西南观”与“西南学”。例如,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的樋泉克夫便在笔者勾画的“西南三角地”基础上补充细化,对该区域的内外关联作了进一步的空间概括[9]。参见图5。

图5 樋泉克夫对“西南三角地”图示的细化
以这样的空间认知为前提,作者强调不应把西南视为中国的边境地区,或者是位于东南亚大陆北部的周边地带来处理,而应视为“从其作为中华世界面向西部和南部的窗口,以及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路上回廊的地政学、战略性的角度对西南问题展开研究”[9]。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有一批与西南山地相关的日本学界观点被陆续引进中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照叶林带”“稻作文化带”等[10]。日本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重返中国西南,深入贵州、云南做了大量的调查。他们的研究特点之一是将中国西南山地延伸到东南亚半岛,一直推及日本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那样的整体区域。由此,他们看到了水稻关联、看到了龙舟传播以及铜鼓、面具、纹身等一系列跨时空的山地文明,从而试图在理论上构建新的认知整体及与之应对的话语体系。所谓“照叶业林带”,原本是从植被意义上来表征的,是生物学、植物学的概念。由此强调的是特定地域与特定植被的关联。再往上走,在维度更高的地区是“针叶林带”,那就进入另一种景观和文化地带了。可见他们是用植物学、生态学的概念来看待这一区域的山地文化的。这样的认知很有道理,因为这一地区的植物生长与文化类型的彼此关联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说不同的植物被用作为建筑材料,从而影响到当地人的建筑方式与文化栖居。
此外也有人以区域传播为视角研究铜鼓,从中国西南延伸至东南亚诸国,将铜鼓文化看作一个分布广泛、传播久远的现象,并由此关注逐渐形成的多个类型中心及其彼此间的联系和异同。20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考古学家童恩正还做过更大的空间阐释,不仅提出中国版图内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假说,而且呼吁关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诸国的跨境联系,把该区域视为具有多重关联的文化整体[11][12]。
改革开放新时期,聚焦西南的山地研究涌现出不少值得回顾的新表述和新话语。除了“西南研究丛书”体现的跨行省关联外,值得强调的还有“民族走廊”说。在20世纪80年代“走廊”观念的提出跟人类学家费孝通对民族识别的总结反思有关。他认为要解开民族识别遗留的诸多难题,必须以重新认识“藏彝走廊”的关联作用为突破口。从后来的一系列成果来看,“民族走廊”的提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过突出“藏彝”族称的命名方式容易引起误解,该地区其他没有被提到的族群会有意见,例如羌、回、纳西等。因此后来我建议改用“横断走廊”,一方面凸显该区域的地理特征,另一方面可与另外两个传统的名称相呼应,即“河西走廊”和“岭南走廊”[13]。
“走廊”式的表述体现出山地研究的新推进。表面看,走廊与山地表面吻合,而实际上却不完全一样。“走廊”更强调一个狭窄地带、一条通道和其中的流动与交往,容易忽略其中存在看似孤立的山和村寨。
总体而论,随着在新时期的再度崛起,山地表述为更大范围的区域及空间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对中原固有的文化记忆和知识生产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中原人士每每只以我为美,尽管在诗文中也展现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那样的境界,但由于受到地理处境限制,描绘出来的山水仍以中原为参照,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他们身处的区域东高西低,认知与记忆里的河水都向东流,故而难以想象横断山区的水流会与之不同:由北及南,其中许多不但不汇入黄河长江,还流至境外,绵延到东南半岛的域外之地。
可见,山地的自然特征不但与文化类型密切联系,而且会影响该区域人们的文化记忆及审美取向,也就是从真到善再到美的一整套地方性知识。
五、“佐米亚”引出的新话题
最后还可讨论一下“佐米亚”话题。“佐米亚”由英语的(Zomia)译入,其最早源自东南亚山地民族的一种母语。引起世人关注的由头是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2009年出版的专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14]。
这里我打算先回应一下纳日碧力戈提出的术语问题。纳日教授强调,应当关注“本地、本民族的词汇贡献”。对此我十分赞同。近代以来,在外来话语的一次次冲击下,大量本地、本民族的固有词汇被排斥、遮蔽,逐渐被诸如“图腾”“萨满”等另外的地方性话语取代。“萨满”这个词原本只是北方草原地带通古斯语系中一个范围有限的用语,可是由于掌控话语权的学界精英强势推广,致使“萨满”一词逐渐变成用以指代人类所有巫术信仰及仪式的全球通用语。对此我是不赞同的,凭什么要以一种文化的方言取代其他一切表述类型?依据何在?为什们不用汉族“巫师”、彝族“毕摩”或羌族“释比”与纳西族“东巴”、苗族“东朗”……来做通称呢?由此我提出了全球表述的去“萨满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看重学者斯科特以地方母语“佐米亚”表征区域文化的做法。开始时你或许不知所云,但探求下去之后你才会懂得其中隐藏的哲理深意。
如今,随着全球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接受,“佐米亚”成为了山地文化的新标志。
在区域研究意义上,“佐米亚”的核心在于从空间上将中国的西南与亚洲的东南连为整体,使之被视为范围广大的山地文化圈,其中主要是山地民族,区域面积约为250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以上,包含了中国境内的云、贵、川、广西以及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等。该区域的传统特征是文化自治,具有持久的再生产能力,自给自足,独立性极强。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属于有文化再造能力的类型。其中人群主要以村寨为单位,表面是分散的,没有以国家的名义联系在一起,但是每一个村寨有每一个村寨的风貌、风格,有建筑、植物、穿衣、织布等所有人类所必需的生活资源,他们全部都可以再生产,可以不依赖外援来保存自己的文化,像一个小孩子根本不需要去读书上学,即可以安全、稳定地活在这个共同体中。近代以后,这些地区的共同体遭受冲击破坏,但它所具有的文化类型价值日益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和珍惜。若放眼全球版图,可与之相对照的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文化,如其中突出的“欧亚草原带”。在这一同样依托于特定地理生态的区域中,形成了范围浩大的游牧民族共同体,他们有彼此相同的生活方式、信仰、习俗和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能聚集起来,组成强大的游牧帝国。在我看来,以山地与草原等不同的区域为对照作跨区域比较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在更大时空里反思和总结人们对区域与空间不同的表述话语。
接下来可从“佐米亚”理论倒推,再度评价迄今形成的各种山地话语,包括横断走廊、西南研究,直到“西南夷”,看看在本土的汉语知识生产中,我们缺少了什么。在我看来,缺失的是理论性提升,也就是缺少了反思性的话语提炼。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固定实用的表述,比如“怀柔远人”“封贡体系”。如果能也以“佐米亚”这种本土的、带有自主意识的观点来看待本地,然后比较司马迁以来,包括徐霞客在内的他者眼光来看待西南山地,显然就会看到一些不同。
“佐米亚”的含义是什么呢?在本地民众的母语中,它的意思是土著、是山民,也就是“山里人”,跟普通民众不一样,他们需要反抗一些平地人的一种征服,或者一种强化、一种同化。我们可以考虑,司马迁在其中构建的结构是一种中心观,他没有多元观念,是“一点四方”,就是整个帝都,然后周边都是蛮夷,需要去帮助他们扶贫教育、改造蛮荒,是这样一个天子式的四方图。但是在“佐米亚”这个概念中,每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的主,他们跟天地打交道,跟后辈打交道,在传承自己的文化,跟邻邦友好相处,跟他者相处,都是一种邻居式的概念。
最后,我想以贵州为例提一下山地学者的本土表述。其中一位是侗族学者潘年英,他是学者也是作家,文章写得很好,在他笔下,西南山地被表述为家乡、故土,而不是古汉语中的蛮夷处所或现代的旅游目的地,既拥有独特的传统遗产又面临严峻的发展难题[15][16]。
另一位是我的好朋友,苗族学者游建西,从贵州到深圳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博士,也是作家,出版过新武侠小说《龙吟苗疆》。游建西把苗族视为“温和民族”,称苗族文化是“温和文化”,由此与中原不断涌现的暴烈类型相区别[17]。他的论述早在斯科特之前,可惜没被注意。他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演变进程中,越往上的高级层面,政治就越体现为暴力机器。在此过程中,居住山区的苗民长期保持“低等级”类型,未能进化到城市和国家阶段,因为不需要。这样的论述已进入到很深刻的分析之中,提升了山地研究的表述类型,丰富了相关的话语遗产。
六、结语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话语”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关键词。它的含义可理解为与特定对象相关并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产生主客体连接及权力关系的某一类知识谱系*有关“话语”的论述庞杂繁多,此不展开。作为源起开端,可参阅福科1970年12月就任法兰西公学院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Foucault,Michel ,L’Ordre du discours,1971 .Paris:Gallimard.)。相关评论参见张汉良《话语的秩序与所有权——重读福科的法兰西公学院就职演说》,《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1期,第10-19页。。这种谱系既由现实的生活世界产生,又能反过来对生活世界造成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由此而论,有关西南山地的古今论说可谓已积淀成了满足上述界定的表述话语,可归为记忆与档案式的遗产类型。
大致说来,山地研究的表述话语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作为地理学概念的自然区域,即山脉、山地和山区。我们对这样的区域类型研究不够,从徐霞客等前人著作里即发现还有许多内容有待发掘。其次是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山地治理,涉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创建和沿革。第三即为人类学表述中的山地文明。在相互关联的整体中,地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各有不同的重点。相比之下,地理学提出的是一个客观概念,政治学聚焦于一个社会范畴,人类学则要考察一种文化类型。彼此指向也有所不同:一个强调自然空间,一个突出实践性的权力布局,最后一个则关注具有地域性的多元文明。三层含义组成了山地研究较为全面的整体结构。如今有学者提出建立多学科的“山地学”。我想若要实现这样的构想,无疑需要认真梳理并继承以上三个层面的表述遗产。
由此可见,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展开的山地研究已呈现为多种多样的话语类型,不同学科交互展开的相关成果已积淀为丰厚的表述遗产,值得深入辨析和承继。
参考文献:
[1]陈刚,徐杰舜.人类学与山地文明[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张伟.基于DEM的中国山地空间范围定量界定[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5):58-63.
[3]钟祥浩.20年来我国山地研究回顾与新世纪——纪念《山地学报》创刊20周年[J].山地学报,2002(6):646-659.
[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
[5]蒋应镐.绘图本《山海经(图绘全像)》[M].聚锦堂刻本,明万历二十五年刊行,图2:54.
[6]徐新建.西南研究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1-7.
[7]司马迁.史记:本纪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徐弘祖.徐霞客游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18.
[9]樋泉克夫.民族之间的跨国联系——西南、东盟与华人圈//文化遗产研究[M].关杰,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76-88.
[10]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M].刘愚山,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1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考古与文物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91-201.
[12]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J].云南社会科学,1982(2):41-45.
[13]徐新建.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14]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15]潘年英.传统村落保护——黔东南样本的隐忧与希望[N].贵州民族报,2017-05-12.
[16]潘年英.扶贫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17]游建西.从苗族古歌看苗族温和文化的底蕴——值得深入认识的一种农业文化遗[J].贵州社会科学,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