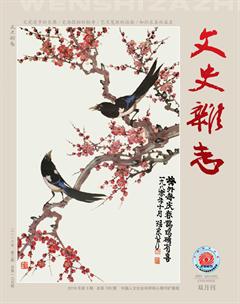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胥吏制度??
赵映林
摘 要:胥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级行政衙门中的具体办事人员,是官民交接的枢纽,须臾不可或缺。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政府、国家。因此胥吏之优劣,办事之行为、效率,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可是,由于顶层制度设计的缺憾,造成胥吏操纵行政事务的“吏治”大坏,损害了政府形象。背后的缘由则是人性理论的缺失。
关键词:胥徒;吏员;师爷;低俸;顶层制度设计;人性理论
胥吏之称与构成
对历史上的那些政府衙门中的公务人员,人们统称之为官吏,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以前,一直是这么叫的。这并不奇怪,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在《礼记·王制》的注释中说:“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是干什么的?孔颖达说:“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官是从事管理的,掌握着权力,管事也管人(管老百姓、管比他职务低、权力小的官)。总之,官是“与人主共理天下者”。[1]既然有管事的,就得有做事的。做事的衙门中人是什么人呢?做具体事的,肯定不如动嘴不动手的地位高,《辞海》将这些做具体事的衙门中人定义为“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不过直到汉代,对官与吏,人们还是将其联系在一起,统称官吏。如汉代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的高官被称之为长吏,百石以下的官员则被称之为少吏。如司马迁的《史记》有《酷吏列传》《循吏列传》,新旧《唐书》亦有《酷吏列传》《良吏列传》,而上述“酷吏”“循吏”“良吏”的“吏”指的都是官,而非“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那个时期,政府各部门除主官外,大家都要具体办事的,都可以目之为吏。汉朝时的很多官员都是从政权底层的吏一路打拼上来的,直至丞相。如著名酷吏宁成原“为人小吏”,受到另一酷吏郅都的欣赏,汉景帝时调任首都长安中尉(首都警察局局长),汉武帝时升任内史(首都市长)。[2]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将两汉时期的官与吏区分出来,界别的标准就是俸禄。《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这百石以下的少吏就是“各署曹掾史”[3]。这里说的“署曹掾史”就是吏。这些人在地方衙门就被称之为令史、主吏、书佐,幹(门幹、门下幹)、小史,虽称小吏,其中有的实则乃后世所说的胥徒,地位卑贱。这里的“小史”即是。再如,史籍所记的有秩啬夫与无秩啬夫,前者是官,后者是吏。
官与吏的分途经魏晋唐宋尤其是宋朝的演变,到明清时已是泾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语了。官与吏有了区分以后,一般說来,官就是专指各级政府、各部门中有品级的长官,有决策权与管理权的;吏是专指各级政府、各部门中无品级,既无决策权也无管理权,在官的指挥下专事各种具体事务的办事人员。《大清会典》卷一十二说:“设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而且宋时已开始将吏称之为胥吏,宋人程大昌《演繁露续集》说:“案牍、法令、书判,行移悉仗胥吏。” 元人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说:“夫吏,古之胥也,史也,上应天文,曰土公之星,下书史牒,曰刀笔之吏。” 按此说,胥就是吏,吏就是胥。所以世人往往合称之胥吏或吏胥。但实际上,并不尽然,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吏主要是从事案牍文字工作,如令史、典史、知印、司吏、功曹、宣使、奏差、书吏、狱掾、仓吏。《水浒》中的宋江上梁山前是押司,是书吏中的一种,负责办理案牍文书。那么在案牍文字等工作以外还有从事杂役的,这批人称之为差役、衙役,如捕快、牢头、看守、皂隶、门子、听差、仵作,他们“任奔走服役”。[4]这批人不需要什么文化,略识些字甚至不识字就能充任,称之为“胥徒”。[5]胥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在政府中跑腿听差。因此,胥吏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事案牍类的吏员,一是从事杂役的胥徒;前者有文化的要求,后者无文化方面的特别要求,甚至文盲也可充任。至于将胥吏称为“刀笔吏”则更早。秦国—秦朝自商鞅变法后,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是必须懂法,会用法处理事务。只有符合这一要求的人才有资格做官。由于法又称“文”“文法”,于是这些懂法的做官的人就被称之为“文法之吏”“文吏”;又由于“文法之吏”必须制作文书(公文与法律文书),那时还没有纸张,是在竹木简上用笔写或用刀去刻写修改,因为经常捉刀弄笔于竹木简,故称之“刀笔吏”。这不同于后世理解的讼师。其实,这时期的“刀笔吏”既有官也有专事文书的吏。所以,汉代有“秦尊法吏”、“秦任刀笔小吏”、[6]“专任狱吏”[7]之说。不过,这一时期的“吏”地位并不轻贱,因为秦朝的政治制度是按照法家的那套理论建立的。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就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8],即从基层干起的。因此,法吏、刀笔小吏、狱吏是受到朝廷器重的。懂法的吏在当时被目之为“良吏”,不懂法的被目之为“恶吏”。[9]更何况这支“吏”的队伍中有许多本就是中高级官员。
胥吏是衙门中的最底层,自从有了国家,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主要是胥吏,而不是官。清人梁章钜说:“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10]国家形象是通过胥吏的办事行为反映到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因为在老百姓眼中,在政府衙门中做事的不论是吏员衙役,总之都是公家人,是官,是官家人。因此,胥吏形象就是国家、政府的形象,只不过胥吏们并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也不认同这一点。至少古代社会的胥吏们无一不是如此的认知水准。
宋及之前的胥吏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特别是西周时代,政府官职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基本是DNA说了算。这种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遭受到有力冲击,这是由于兼并过程中要解决人才问题。秦在这一过程中对在DNA基础上构建的世卿世禄制的否定最有成效,使得它终于得以统一全国,使郡县制随后在全国确立。秦汉时期,因职务不同,工作内容、方式有不同,但官与吏没有什么区分。虽然汉以后,士人进入政府会被称之为官,庶人进入政府被称之为吏(所谓“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可是因吏而入官者并不在少数。如前所述,汉代的许多官员都是从政权底层的吏一路打拼上来的;更不用说汉朝的开创者刘邦乃是秦朝根本不入流的小小“亭长”,既不是官,而且连吏都不是,属于胥徒,不过却管着两个地位更低的胥徒:亭父、求盗。[11]至于追随刘邦的这批人,未战死者皆成为开国元勋的大多或吏或胥出身,如萧何是沛县主吏,司马迁说“(萧)何于秦时为刀笔之吏” ,[12]曹参是狱掾,夏侯婴是厩驺(管一县之车马)等等,无一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故有“布衣将相”之说。如前所述,汉与秦一样官与吏仍旧相通。然而,在政府做事,不论是官也好,吏也好,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没文化当然不可能做官,无文化也承担不了大量的案牍文字工作。只不过比较起来,对吏的文化程度相对要求低一些。秦朝“以吏为师”说明官与吏是合一的,同时也都是有文化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盛行,入仕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3],到东晋时完全固化。做官尚且分上品下品,就愈加不屑为吏。这种情况下,吏的地位更加低下,官与吏的区分明显了。在官的眼中,吏役属于同类,受到轻视。但由于吏与役的分工明确,“服役吏”(衙役)地位日益低贱,与从事文牍之吏的距离也随之迅速拉开了。
隋唐时期,官与吏开始分途。区分二者之间的一条界线就是“流”。流就是品类、等级,所谓“不入流”“三教九流”就是此意。有流内之说当然也就有流外之说。“流外”之说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但在当时还未形成与有品级的流内官相对应的完善体系。隋炀帝推行科举取士,九品中正制逐渐退出选官舞台,唐朝继承了科举取士,并加以完善制度化。这使得在官制上形成了流内与流外官的区分。这是秦汉以来第一次在官吏制度上明确官员与吏员的区分。由于科举的盛行,使得吏的社会地位为士子所轻视。唐代明文规定,“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14]。
官吏虽逐渐分途,但吏通过积累年资,总有不在少数的吏能入“官”,成为低品(八品九品,少数七品甚至更高品级)官员。更由于唐代贞观遗韵,重视选用能官干吏,一批胥吏出身的人才得以进入政府,有的渐成为高官。
宋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未出现过梁唐晋汉周这样的局面,这是宋朝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结果。宋太祖、宋太宗为了消除有枪杆子就有地盘的五代割据,强干弱枝,同时不惜从中央到地方广设官职,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官员之间相互监视,相互牵制,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官冗官滥。有官则有吏,吏又往往是官的多倍。据学者研究,唐代中央政府有吏3000——4000人上下,地方政府有吏近10万人。宋代中央政府有吏在5000人上下,地方衙门有胥吏约22万。[15]
宋朝胥吏,包括中央机构如省、曹、寺、监和地方行政机构诸路监司、州县的各类僚属,名称繁多。《云麓漫钞》卷一:“下至胥吏,则有通行官、专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则有散从官;流外有梓官、阴阳官;军校有辇官、天武官之号。”常见的还有曹司、令史、书吏、掌库、典库、吏人、役人、公人、录事、守当官,等等。宋代胥吏最初无俸,遂靠索贿为生,办事必先行贿,“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16]此后,朝廷不得不更弦易张,给吏俸禄,而且与官员俸禄一样优厚有加,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在朝为官的右司谏王岩叟说:“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管卒,郊礼沾赐赉,又许引有服亲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异。”[17]可惜的是这种优厚待遇并没有“尽禄天下吏人”,而是将天下胥吏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取俸禄的,称“重禄公人”;一类仍是没有俸禄的,称“无禄公人”。唯有中央各部门胥吏享受到最优厚待遇。“无禄公人”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索贿,不给钱不办事。
宋朝科举受重视。宋朝科举共进行118次,取进士42577人,平均每次约361人。[18]倘若加上落榜士子,这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自从有了科举取士制度后,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科举出身者。其次则是恩荫制的推行,中高级官员子弟纷纷得以进入官场。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进入政府机构的这两类人,原先只习经书、诗赋,基本不熟悉典章刑律,不谙行政事务。但法律、条例又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基本遵循,恰恰这是吏的强项,于是官员们不得不依靠胥吏,形成宋朝特有的官弱吏强的行政局面。顾炎武评论说:“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19]
与宋并存的金朝,因有史料记载,使我们得知,金代吏员是有俸禄的。中央各部门的吏员皆有俸给,最高的可以支正六品俸,每月计有“钱粟二十五贯石,麦五石,绢各十七匹,绵七十两”[20];最低的是胥徒,如驼马牛羊群子、挤酪人,仅有钱粟三贯石而已。中央吏员出差另有补贴,而且规定的比较详细,便于执行。
元明时期的胥吏
胥吏左右公事,控制衙门,最典型的是元朝。元朝号称“以吏治国”,就是指由吏出身的官来治理管理国家。元世祖忽必烈时,全国官员总数26000余人。[21]据当时人的记载,由吏出身的官员在元朝占到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22]“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23]。地方胥徒中的吏员有10万人之众,中央政府有正式吏员3000人。[24]实际数字当过此。
元朝主要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知印、宣史、司吏、书吏、奏差、狱典等。元朝对胥吏实行俸给制,“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禄。”[25]其俸禄由俸钞与禄米构成,标准是每月“每一两与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支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与米一升”[26]。俸禄最高者是行省的令史、译史、通事、知印,月俸鈔35两,米1石;最低者狱典中的司狱史、县衙门司吏、巡检司的司吏、录事司司吏,月俸钞6两,米6斗。元代通行纸币,可元代的通货膨胀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严重的一个,纸币不断贬值。
元代虽然没废科举,但科举选官制度不受重视,几被统治者束之高阁。元朝统治全国89年,共举行16次科举考试,取士1139名,平均每年仅12.8人。[27]在一个有着若干万官员的国家,一年却仅有不到13名的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政府,这真令人不可思议。在这种尴尬背景下,吏便自然地成为元政府各级衙门官员的主要来源。
这就构成元代官制的一大特点,即政府官员不由科举取士而主要是由吏员升职构成——“官由吏得”。当时,吏员脱离吏职出任官职,专称“出职”。这是唐宋以来的独有的一种任官制度。其原因一是如上所述,不重视科举,士子很难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到官员队伍中。二是官员不熟悉典章制度,官员的不足恰恰又是吏员的长项。吏员熟悉旧律,无人能取代他们。元代法制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差的。蒙古贵族入侵中原后,一直没有颁布过正式法律。官吏审案断案,有的沿用金代的“泰和律”,有的援用“蒙古祖宗家法”。忽必烈禁用“泰和律”,几次要制定新律代替它,都未能实现。于是将建国以来历来先后颁布的“敕旨条令,杂采类编”,编成《至元新格》一书。继忽必烈之后的几代皇帝先后颁行的《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都是将“敕旨条令”加以汇编。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遇事有难决,则捡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在旋行议拟”。[28]旧例就是宋、金旧律和“蒙古祖宗家法”,熟悉这些的只有吏员。由吏迁官,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