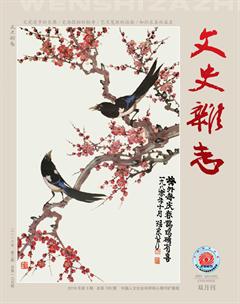李白的神仙信仰
贺兰山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是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所云“杖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那一年。岁末,李白在江陵(在今湖北)长江边的一处驿馆与年近80的道士司马承祯相遇,两人相见恨晚,很快成为忘年之交(时李白大约25岁)。鹤发童颜的司马大师极为欣赏眼前这位年轻的信徒,连连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并序》)。司马承祯在江陵停留数日后,即乘船顺江而东,经洞庭入湘江南下去游衡山。李白则在驿馆作短暂盘桓,回味大师金玉般的教诲、点拨,遂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广为宣传。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自号白云子,为道教义理化进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曾亲授唐玄宗法箓。他的道教理论视野宽阔,兼采儒家正心说和佛教止观学说,重视人生,强调把握自我而顺应天道,主张“道”(在人身则谓之为“气”,由“道”所派生)乃主宰人体生命的决定性物质。这种物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是可以实在感觉到的,是能够通过后天修炼与蓄养的。而修炼与蓄养到高级阶段,就叫做“得道”。司马承祯在《坐忘论·得道》里是这样描绘的:
是故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
在司马承祯看来,凡“得道”者,必为“凝神宝气”而与道相合者。这时已是“身与道同”,“心与道同”,“耳则道耳”,“眼则道眼”,“六根洞达”了,成为长生不死,“智周万物”的仙人了。(参见《坐忘论·得道》)倘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来观察,司马承祯的“得道”论固然荒诞无稽。可是,他却继葛洪、陶弘景等之后,又一次地高标起“仙道贵生”的生命大旗,并将这杆大旗交给处于现世中的人们,引导人们脚踏实地,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将人生(包括人的健康与长寿)自信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司马承祯的道教理论的一个核心点是“守静”,以“藏晖”(“藏身”)而致“道”。这对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道经以圆成仙之梦的李白自然会有重大影响。李白尔后的不少涉道诗便谈及对“藏晖”“藏身”的体会。他有《沐浴子》歌云: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
处世忌太洁,志人贵藏晖。
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
又有《拟古十二首》其八云:
……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
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
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
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
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两诗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人貴于“藏”,即随俗而处,不露锋芒。这就是《老子》第五十六章所谓:“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此二诗当是李白不得志时(可能是在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赠金放还”后)之作,在政治上颇有逍遥于世之意。这与司马承祯哲学与养生学意义上的“守静”“藏晖”虽有不同,但仍合道家本义。
上引《拟古十二首》其八,还提及李白平生的两大嗜好——服丹(或称服药)与饮酒。而服丹乃属道教徒修炼的内容。道教养生修炼分外丹和内丹。外丹为金石烹炼成丹,即长生不老药。葛洪《抱朴子·金丹》说:“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内丹则属司马承祯所主张的“守静”范畴,其原理完全仿照炼外丹而来。《谷神论》说:“含精炼气,吐故纳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谓之内丹。”炼外丹要用炉,炉上要用鼎,鼎中要装药(黄金、朱砂、雄黄、雌黄、硝石、云母等),炉中要烧火;炼内丹也是一样,要有炉、有鼎、有药、有火。人体的炉就是阴穴,又称会阴。人体的鼎在脐以下到阴阜的部位,形状好似一只反扣的半边锅,故被称做“半边锅内煮乾坤”。炼丹者的药就是精、气、神这生命“三宝”。道教养生家认为“生命三宝”在后天人为的作践中会消耗殆尽,从而短寿,因此须得将它们凝炼成“丹”。炼丹者的火就是意念。李白是深谙内丹之道的。其有诗赞道:“喘息餐妙气,步虚吟真声。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题随州紫阳先生壁》)这里的“喘息餐气”,即指内丹吐纳之法。
《抱朴子·论仙》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所指大概就是外丹和内丹。而饮酒与服丹(指外丹之丹药)在李白来说,都是入梦成仙的路径,饮后、服后均飘飘然有升天的感觉,所以李白有很多饮酒买醉的诗,服丹、求药的诗。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的“玉浆”、《游太山六首》其一中的“流露”、其四中的“不死药”,都指的是丹药——李白眼中的仙药。
李白相信服了仙药可以长生不老,继而进入仙界,成为神仙中的一员,所以到处求药寻仙。他在《感兴八首》其五中说:“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在《古风五十九首》其四中说:“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在《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中说:“昆山采琼蕊,可以炼精魄”;在《留别广陵诸公》里说:“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说明他不仅不辞万里,踏遍千山万壑地去求药寻仙,而且还就地动手采集药石、药草,亲自烧炉炼丹。在这方面,他也有诗纪其事:“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避地司空原言怀》)……由此表明李白的神仙信仰是极虔诚的,追求仙人之梦是坚定的,费材耗力而在所不惜,甚至倾家荡产,还将妻(宗氏)女(平阳)一同拉来“访神仙”,“炼金药”(参见《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这还不算完,他又将家僮唤作“丹砂”(参见《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四)。按:《抱朴子·金丹》云:“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草木远矣。故能令人长生。”这就是道教所谓的“还丹”。王琦《李太白文集辑注》引甄鸾《笑道论》说:“《神仙金液经》云:金液还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烧水银,还后为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所以李白“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落日忆山中》)。李白将家僮取名为丹砂,以示时刻不忘炼丹服药,并最终达到白日升天这个神仙梦想的最高境界。
李白因为有了炼丹求仙的美丽梦想而时常处于幸福中。他在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为将离金陵南游的好友权十一(即权昭夷)写的饯行诗序中说:
……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之子也,冲恬渊静,翰才峻发。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舍我而南,若折羽翼。时岁律寒苦,天风枯声。云帆涉汉,冏若绝电。举目四顾,霜天峥嵘。衔杯叙离,群子赋诗以出饯,酒仙翁李白辞。(《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
是序在回顾诗人与权十一(也在一起炼丹求仙)的友好交往外,还涉及诗人自己的学道炼丹历程及对神仙(如1200岁而未曾衰老的广成子)的仰慕向往,有怡然自得之状。序中还提到14年前贺知章呼他为“谪仙人”的事,余美未歇。原来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李白在京师长安被唐玄宗命为翰林供奉后,得以与秘书监贺知章(659—约744)相见。这位当时已是83岁耄耋老翁,也是狂人(自号四明狂客)、本身亦有“仙”号的太子宾客一见到李白便惊呼他为“谪仙人”。李白一下子便觉血液沸腾,飘飘然了。这感觉比他当年在江陵被司马承祯夸为“有仙风道骨”还要好。李白从此也便以“仙”或“谪仙人”自居,四处自美,在后来的诗文中屡屡提及,念念不忘。他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末尾也是以“酒仙翁”自称。这说明天宝十四载的李白(离他辞世还有6年光景)依旧痴心于学道炼丹,追求成仙之梦。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李白在安徽宿松长江边上写下《江下望皖公山》诗,其中有云:“但爱兹岭高,何由讨灵异?默然遥相许,欲往心莫遂。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皖公山为道教名山,为道教徒眼中灵异(神仙)出没而“巉绝称人意”的地方,李白一心向往之,却又感叹自己尚未“还丹成”。这表明李白对自己“谪仙人”的身份已有了怀疑,知道自己毕竟还未成仙,还须继续努力炼丹服药,待真正得道之后,才有资格去长驻仙山。
李白此时的动摇,或与其时身体渐感不适,自觉开始走下坡路有关系。他在此前两年,即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冬《与贾少公书》中便已透露出这信息。那上面说:“白绵疾疲苶,去期恬退”。疲苶,困极之貌,疲惫透顶,打不起精神,所以才有“恬退”(不事奔竞,安于退让)的想法。至德元载冬,永王李璘慕李白才名,辟其为幕府僚佐。李白虽已应征,但却深感力不从心,处于犹豫之中,故在给一位做县尉(县尉别称少公)的朋友贾少公的书信中说了那些话。不过,李白最终还是被永王李璘的诚意(三次遣使征召李白入幕)打动,出山追随李璘。孰料不久却因此获罪。他在宿松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判决(年末即以“附逆”罪被判“长流夜郎”)时,便有了上述《与贾少公书》。他同时还有《赠张相镐二首》,其一中的“卧病古松滋(宿松山)”“枯槁惊常伦”句,则明白说明当时疾病已很严重。[1]尽管如此,李白仍不愿停止炼丹、服药(丹),依然做着期望“还丹成”而加入神仙队伍的美梦。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从夜郎(治今贵州正安西北)流放途中遇赦折返,经江陵、江夏(治今湖北武汉之武昌)而游洞庭,再还至江夏,因作《望黄鹤山》诗,其中有云:
……
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
一时向蓬海,千载空石室。
金灶生烟埃,玉潭秘清谧。
地古遗草木,庭寒老芝术。
蹇余羡攀跻,因欲保闲逸。
观寄遍诸岳,兹岭不可匹。
结心寄青松,永悟客情毕。
黄鹤山又名黄鹄山,即今武昌蛇山。其长江边黄鹤矶上有黄鹤楼。相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三国蜀汉大臣费祎也是于此处登仙,又驾黄鹤回来在此休息。诗中金灶指仙人炼丹炉,玉潭是仙人炼丹水,芝术为仙人所服仙药灵芝与白术、苍术等。黄鹤山即是仙人升天和往来的地方,亦密集金灶、金潭及众仙草,令李白羡慕死了。他大概是望仙山而心飞天外,悠悠然又以为自己是仙了。明人严沧浪、刘会孟评点《李太白集》引明人评语说:此诗“大指在求仙,亦生峭,有气概”。李白作此诗时已是花甲老人,且疾病缠身,可求仙之心不改,依旧兴致勃勃,情趣盎然。
李白写《望黄鹤山》的翌年,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夏天,他将夫人宗氏亲自送往庐山屏风叠北女道士李腾空处学道(这离他辞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李腾空即宰相李林甫之女,在庐山出家为道,以丹药符箓救人疾苦。李白将夫人送抵目的地后,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纪事: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
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
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其一)
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
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
一往屏風叠,乘鸾著玉鞭。
(其二)
二诗一任李白道家韵致,风骨泠泠而神采粲粲,虽因对宗氏的依恋而有些怅然若失的意味,但给读者更多的却是对爱妻的衷心祝福与钦羡。宗氏或要在庐山成道,可本身就是道士的李白却不能与之携手成仙。对此,他不能说心中不起波澜。然而,此时的他的确是心似镜湖,澄净如洗。正像他在《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中所说:“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他早晚总是要回归山林,专心修炼,与同道中人共享仙境之乐的。然而,这一切都要待他再次报效国家之后。这是因为上元二年五月,朝廷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出镇临淮,以平定安史之乱。消息传到他暂栖的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夫人宗氏居此),他又跃跃欲试,全然忘记了四年前从永王璘的那份不堪回首的伤痛。他将宗氏匆匆送上庐山后,便兴冲冲地赶往宣州投军去了。只是这次投军还是因病躯拖累中途返回金陵。他不禁抚剑长叹:“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同时也便最终死了从戎的念头,重新将人生的目光投向道山:“因之出寥廓,挥手谢公卿。”(均见《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表示从此真的要高飞远举,去与“道”合,与仙人群了。
其实,李白的心一直围绕着“道”、围绕着仙在转;只是有时走得近些,有时处得远些罢了。郭沫若先生说李白暮年在宣州当涂横望山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郭沫若系于宝应元年即李白去世当年春天),“是他和道教迷信的最后诀别”,“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2]。其实不然。郭沫若指证的核心句子是:“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揖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如果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些句子遵循的乃是告别友人包括道友(郭沫若说是吴筠,郁贤皓、刘华云、李从军等则认为是元丹丘)时的一般思路,是对人对物不对事,说的是对过往人物的历历在目,对告别友人的凄苦与依恋,丝毫没有轻慢宗教、否定迷信的意味。倒是其中“羡君素书常满案,含丹照白霞色烂。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俯仰人间易凋朽,钟峰五云在轩牖。惜别愁窥玉女窗,归来笑把洪崖手”等许多句子,传递出已接近人生终点的李白始终不忘学道游仙,回忆起他当年孜孜以求的神仙梦时,仍满怀幸福、温馨、愉悦与美好的憧憬;尽管他临死也未成仙。
什么叫神仙?《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曰仙。”《抱朴子·对俗》说,仙人的基本特征就是长生。闻一多先生在《神仙考》里则换了个角度说:神仙“实即因灵魂不死观念逐渐具体化而产生出来的想象的或半想象的人物”[3]。总之,憧憬长生和成仙,乃是道教神仙理论的首要特点。为了实现长生和成仙,道教徒们在方仙道的基础上,寻药、炼丹、行气、导引、远游、饮露、餐霞,倾全身心地忙个不停,从汉代一直忙碌到明代,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写下了最为荒诞离奇而又神秘诡谲的一章,并留下诸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类的许许多多撩拨人心的美妙杜撰。虽然如此,道教的长生和成仙欲望,仍荡漾着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难能珍贵的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人定胜天精神与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把握自我的思想。这在世界其他宗教中是没有的,亦是几千年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主流思想难望项背的。这是道教(包括其神仙信仰)在旧时能够吸引许许多多中国人,包括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国文化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李白之所以读儒、学佛,但更崇道,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求道寻仙,其奥秘也在这里。
注释:
[1]郭沫若先生引晚唐皮日休《七愛诗》说,李白当时得的是“腐胁疾”,即慢性脓胸穿孔。他分析李白身体由壮转衰,并最终因“腐胁疾”死去的原因中,有嗜酒一项;而“长期炼丹、服丹,以致水银中毒”,“是更重要的一项”。参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9页、第145页。
[2]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49页,第155页。
[3]闻一多:《神话与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