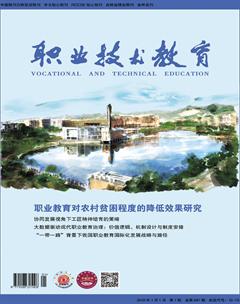多元治理结构视域下中高职衔接的利益主体与路径框架
方绪军 王敦 周旺
摘 要 应然的教育状态跨越至实然的教学状态是一种内生性的教育发展表征。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生性的核心指标、教学模式衔接内部结构性错位、多元治理结构中多元主体治理复位等三个层次的内生性诉求为逻辑出发点,深入剖析中高职衔接中政府、高职院校、中职学校、企业等各利益主体的辩证关系。并以各主体利益博弈和融合域为逻辑基点,确立了构建中高职衔接多元治理的路径框架,包括做好政策、制度的制定和教育资源分配;加强内在衔接要素的对接、构建衔接实施平台;鼓励企业实施主体介入、多层次参与衔接项目;以教学模式衔接为内核,规范各要素结构性标准的制定等。
关键词 多元治理结构;中高职衔接;利益主体;路径框架;高职院校;中职学校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01-0033-05
中高职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打通职业教育独立的学制体系、实现职业人才一贯制培养具有深远意义。由于构建中高职衔接体系存在着多元化的治理结构以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衔接过程中便会出现“利己主义”倾向,导致中高职衔接停留在“学制化”衔接的实然状态,结构内部各因素缺乏有效的、无缝的衔接。因此,基于多元治理结构视域对中高职衔接的利益主体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建设路径框架便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应然—实然:中高職衔接的三层次内生性诉求
从教育伦理的价值取向看,应然的教育状态是教育理想化的精神追求,是对教育本质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实然的教育状态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教育状态,是对教育现状进行的一种复制性表述。根据英国学者G.E.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提出的“自然主义谬误”理论,从实然陈述推论出应然论述是一个谬误。但现实化的教育状态与理想化的教育形态形成鲜明对比时,就要深刻反思教育理想与教育行为鸿沟的起源。基于此,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学制衔接建设的背景下,理顺各利益主体错综复杂的关系与追求应然的衔接状态已应为政策设计层面、实践层面和治理层面等三维内生性诉求。
(一)政策设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生性的核心指标诉求
在国家顶层设计中,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学制发展的重要环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从学制衔接角度看,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中高职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从内生性的体系衔接来看,还存在着一定的阻隔,导致衔接路径不畅,特别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中教学模式衔接不畅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实训等内部因素的不对称衔接或错位衔接,这与中高职衔接的应然状态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相对于其他衔接要素,教学模式衔接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关系到职业教育属性的应然归属,也是中高职衔接体系构建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因此,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探索期,职业教育中高职衔接要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为指南,不能仅仅是学制层面上的衔接,更为重要的是教学模式内生性要素之间的衔接。事实上,多元治理结构视域下,由于中高职学校在地域范围、学校传统、管理体制、隶属系统等社会固有属性实现原因,加之有些学校出于功利主义,重学制衔接而轻教学模式衔接,其实质就是重形式上的衔接而忽视实质上的衔接。这往往导致中高职衔接简单化、形式化。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呼唤的衔接不仅仅是学制上的外在衔接,更要重视学制之间的内生性衔接。
(二)实践诉求:教学模式衔接内部结构性错位的诉求
教学模式衔接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同时也是中高职衔接可持续开展的核心元素。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教学模式衔接就是中高职两种教学模式之间的衔接。但从广义角度来看,教学模式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其运行模型结构不仅涉及专业衔接、课程衔接、师资衔接、实训衔接等显性的衔接因素,还包括校园文化衔接、课程文化衔接、技术文化衔接等隐性衔接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在相互冲突、融合、共生中建构的和谐衔接整体,构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学模式衔接的内在机理。虽然我国各省市普遍实施了中高职衔接工程,实现了学制层面上的初步衔接,但从学制的内部结构来看还存在着衔接不对称的问题,特别是以教学模式衔接为核心的人才培养衔接还存在着目标不明确、结构不对称、课程设置重复、教学方式迥异等问题。事实上,多元治理结构视域下,由于各利益相关主体缺乏统一管理、统一指导、一贯制衔接等原因,而导致教学模式衔接的实质主体——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衔接常态屡屡发生。总之,应然的衔接状态应该是中高职有效的、无缝式的衔接,然而却被实然的“学制化”衔接所占据。
(三)主体要求:多元治理结构中多元主体治理复位的诉求
在多元治理结构视域下,中高职衔接工程需要政府、高职、中职、企业等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构建。但多元化的主体基于核心利益博弈的考虑,极易使中高职衔接陷入以单一利益主体为核心的“利己主义”怪圈。这必然使中高职衔接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产生利益空间地带,特别是在政府、行业和企业缺位状态下,中高职衔接俨然演变成中高职学校各自主导下的一元衔接治理模式,引发了各利益主体在衔接内部结构运行中“各自为政”,导致在逻辑目的、逻辑内容、逻辑系列以及逻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与错位。究其原因:事权是由多元主体构成,而各个主体在内部与外部双重因素交织下,缺少有效的学制贯通平台,导致内部结构处于无序化衔接状态,进而造成中高职内部结构的衔接陷入低效、不对称衔接的实然状态。这不仅影响到中高职衔接项目的数量、质量与效益,同时也危害了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贯制和学制的无缝衔接。
二、多元治理结构视域下中高职衔接的各利益主体分析
在中高职衔接多元治理结构内部存在着各利益主体(stakeholder),从利益主体角度看,中高职衔接可以被视为各种利益主体与客观交织存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处于各种利益交织的各主体在客观上会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国内学者对中高职利益主体的客观存在个体观点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从分类结果上看,各利益主体大同小异。其中,政府、高职院校、中职学校、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四个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本研究认为,各利益主体内部结构也存在着一种层次性和權重,按照衔接维度划分,政府属于上层利益客体,权重比较低;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是属于中层利益主体,权重较高;企业属于低层利益主体,权重也比较低。基于广义逻辑方法论中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手段,本研究基于多元治理结构视域,针对中高职衔接的应然状态进行辩证逻辑研究,并对多元主体结构的实然状态进行形式逻辑研究,以此构建多元治理结构视域下中高职衔接的逻辑结构,从而为疏通中高职衔接中的多元治理结构性不畅提供支撑。
(一)政府——公共利益为使命的利益主体
政府可以作为利益主体出现吗?关于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观点,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包括公共利益学派的政府利益观和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利益观两种学说。不过,后者主要是适用于经济学等领域,而前者广泛适用于教育学领域。有学者认为,政府利益就是全体人民公共的利益,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做好一定的社会服务。例如,亚里士多德基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提出了“凡是正宗政体,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自然是公共利益;只有‘变态政体行为的价值取向才是统治者个人的利益或部分人的利益”[1]。法国卢梭指出:“政府作为全体公民权力的委托行使者,除了公共利益以外,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不会追求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利益,也就是说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完美的利他主义者。”[2]美国学者詹姆斯·E·安德森也认为,“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3]。由此可见,政府的价值取向和任务是“公利”而非“私利”。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来看,中高职衔接工程是政府顶层设计中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社会服务为利益点的战略性工程,其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具有一定的法理性依据和教育体制运行上的考虑。基于多元治理结构视角,本研究认为政府的利益主体体现在公共服务职能、宏观管理职能两方面,其中,公共服务职能在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学制上实现中高职贯通纵深发展的服务职能,这也是为解决中职生的升学问题。同时,政府也在履行宏观管理职能,主要是通过行政指导式的命令加强政府对于教育的方向性指导以及部门职能的行使,其方法包括宏观政策引导、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在客观上影响到微观领域。总之,政府具体的利益诉求包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优质职业院校的建设、中职学校学生学制提升与就业、人民对于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需求等。
(二)高职院校——人才需求的利益主体
高职院校在中高职衔接中存在什么利益?处于职业教育学制高层次的高职院校,由于其特殊的教育学制类型和教育目标属性,即使面临着学制上移和生源减少的大背景,其招生人数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那么开展中高职衔接的利益点何在?基于利益层级角度,高职院校是直接实施和落实中高职衔接顶层设计的利益主体,是上位机构利益下移的主体机构;同时,也是中高职衔接中作为主体地位直接参与中高职衔接的执行者,是中职学校利益上移的主体。换言之,高职院校的利益主体地位不仅仅体现在衔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同时也是相关利益主体“利益输送”的目的地。因此,从多元治理结构角度看,高职院校是中高职衔接的直接执行者,其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切合点集中在政治属性、本体利益属性以及社会效益属性三个方面,其中政治属性主要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开展工作,主要包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践经验的探索、教育行政部门的任务、高职教育的社会使命和培养任务、学制上移的实践;本体利益属性主要是以高职院校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开展工作,主要包括拓展生源范围和人数、特色人才的培养、校际之间的利益以及教学模式衔接的探索等;社会效益属性主要是高职院校对社会稳定和美誉度等产生积极的正向效应,主要包括接收中职毕业生,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以及增强学校在地区范围内的美誉度等。
(三)中职学校——人才供给的利益主体
中职学校在中高职衔接中能获得什么利益?按照我国的学制体系,中职学校属于中等教育,处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层次。因此,相对于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在招生生源、学生质量、学生就业以及社会服务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从多元治理结构角度看,中职学校是中高职衔接的直接参与者,其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焦点集中在学校生存压力上,这是中职学校实然的发展状态。长期以来,我国中职学校沿袭着发展轨迹“重复往复”、学校建设“亦步亦趋”、专业建设“一拥而上”、课程结构“人云亦云”,重复性建设屡见不鲜……县级中职校以及优势特色不明显中职校的处境每况愈下[4]。由此可见,中职学校办学特色不突出和优势不明显是限制其发展的症结所在。因此,从多元治理结构角度来看,中职学校作为利益主体开展中高职衔接时,其利益结合点在于学校生存压力所迫、职业人才发展两个方面。其中,现在国内有些中职学校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特别是县级中职学校。由于生源自然减退、学历教育上移、传统观念偏见等因素的影响,中职学校面临着“无生可招”的窘境,因此中高职联合办学,提升学历层次,也是吸引初中毕业生就读中职学校的优势所在。同时,职业人才发展也是中职学校开展中高职衔接的驱动力之一,中高职衔接打通了中职与高职之间的学制阻隔,实现了人才培养的一贯制培养,对于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进阶有着非凡的意义。
(四)企业——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参与中高职衔接有什么利益可寻?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筛选和聘用合适的高技能人才,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5]。2017年2月15日,全球招聘专家瀚纳仕(Hays)在北京发布《2017年瀚纳仕亚洲酬薪指南》,对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3000多位雇主、涉及600万名员工和1200个职位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90%的中国受访雇主表示很难找到所需的技能人才,中国企业非常担心持续的技能短缺问题会严重影响其业务发展[6]。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智能化时代的日益临近,中国企业在不断的技能升级下实现了发展的结构性转型,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能够承担一定技术研发和改造的技术人员,而现有的中职或高职院校单方面都无法满足企业对于人才培养数量和规格的需要。中高职衔接所培养的人才与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耦合性,集中在岗位胜任度、岗位工作认同度以及岗位融合度三个方面。除此之外,在技术操作、技能潜力、团队精神以及工匠精神等方面也是单一学制很难培养的。因此,企业迫切需要打通中高职衔接学制的障碍,参与职业教育中高职衔接的全过程,以培养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总之,从多元治理结构角度看,企业是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往往将校企合作为主要载体,属于低层利益主体,主要是因为企业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中高职衔接学制建设中来,而是在参与中职或高职合作项目中间接参与中高职衔接。
基于上述对于各权重利益主体的分析,从现行各主体实然的衔接状态可知,中高职衔接是一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顶层设计下,多元治理视域中各利益主体在“利己主义”驱动下开展的一种人才培养一贯制学制衔接形式。为什么各利益主体保持持续的衔接?第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需要,中高职衔接是职业教育发展趋势中必须尊重的客观规律和主观驱动,虽然早期中高职学校是被政府裹挟着开展相应的探索,但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中高职衔接已经成为各利益主体基于本体核心利益而开展的社会性活动。第二,各主体之间寻求利益的结合点或利益空间域。中高职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助推各利益主体本体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多元利益主体在中高职衔接中已经找到了利益的结合点或利益空间域,这也是中高职衔接处于可持续发展常态最为有力的佐证。
三、中高职衔接多元治理路径框架构建
多元治理结构源于多元治理理论,强调多元化的结构和多样性的治理。其中,多元化的结构强调利益主体以利益为出发点,可以在同一个框架内实施治理的职能,主体包括政府、高职院校、中职学校以及企业;而治理是一个具有持续性、互动性、融合性和共生性的发展过程,强调在利益为逻辑归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协调、分配等手段实现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共生。本研究以各主体利益博弈和融合域为逻辑基点,提出在多元治理结构框架内以利益主体的地位和属性开展多元治理的路径框架。
(一)顶层设计:做好政策、制度的制定和教育资源分配
从多元治理结构角度看,政府的职能往往定位在宏观调控层面,而且在多元治理结构中处于顶层地位,因此政府要从微观治理结构的职能解脱出来,加强宏观管理的职能。首先,做好中高职衔接政策层面上的设计和规划,通过促进、引导中职、高职和企业三方主体介入中高职衔接工程,为开展衔接工作提供科学性与法理性依据。其次,要制定好制度性规范。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中高职衔接工程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一项长期性与探索性、艰巨性与责任性相结合的工作,因此政府要做好具体制度上的设计和规划,为中高职衔接项目提供具体性指导意见和制度层面的保障,包括政策解读、经费来源、技术保障、制度支撑、人员体系和实施明细等,并为开展衔接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政府应以社会服务职能以及利益主体介入为逻辑出发点,积极做好教育资源的宏观调整,科学、合理、有序地分配教育资源,包括专项经费、生源数量、试点单位、定向政策等,这样才能在中高职衔接的框架结构中整合利益主体机构,规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责任关系,实现结构内部的合理配比。
(二)中端实施:加强内在衔接要素的对接、构建衔接实施平台
作为中高职衔接中层利益主體,中职、高职对于中高职衔接工作的落地、实施、诊断、整改具有直接性的功效。但长期以来,中高职衔接陷入了片面“学制化”衔接的尴尬境地,出现了低效衔接等办学窘境,影响了中高职有效性衔接、深化式衔接和拓展性衔接。因此,中高职学校应加强对衔接工作的全过程管理。从学制衔接的角度看,中高职衔接是一种定向培养、定向升学、定向育人的一连贯人才培养行为,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与连贯性共存现象。从哲学角度看,阶段性与连贯性是对立的两个概念,阶段性强调学制的分离,属于中高职衔接的实然状态;而连贯性强调学制间的衔接,属于中高职衔接的应然状态。中高职衔接的实然状态不应该是碎片式、割裂式的衔接表征形式,而应该是全方位的立体衔接,具体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衔接、教学衔接、课程衔接、实训衔接、教学标准衔接、课程标准衔接,甚至还包括文化衔接、心理状态衔接以及职业教育认同感等多种结构性的衔接,而这些衔接形式势必是有效的、无缝的,这样才能实现衔接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同时,从多元治理结构看,中高职学校在地缘等客观因素存在的背景下,中职与高职多层次、内部结构性衔接缺少衔接媒介,导致衔接不畅、低效等问题。鉴于此,中高职学校应搭建开放式衔接平台,既可以是实体的平台(组织机构、定期会晤机制、互设办学联系处等),也可以是虚拟的平台(中高职衔接精品课程共享开放资源平台、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资源共享库等),这样才能使双方衔接的各要素在同一平台上实现共建、共管、共享。
(三)多方融合:鼓励企业实施主体介入、多层次参与衔接项目
从多元治理结构角度看,相对于中高职学校,企业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中高职衔接的具体治理中去,而是通过对适配性人才的诉求来表达一种社会认同感。同时,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看,绝大多数企业是通过校企合作等形式参与职业教育的建设,而大多数校企合作呈现出低效的发展状态。究其原因,校企合作的深入程度还远远不够,有深度、有温度的校企合作依然凤毛麟角。因此,在多元治理结构框架下,企业要实现对适配性人才诉求的愿望,就必须要以主体角色介入到中高职衔接中去,并开展深度合作。同时,为了实现深层次合作,企业要在合作内容的结构上实现多层次、立体化的衔接。多层次指企业在参与中高职衔接中需要连贯性地开展校企合作,以实现人才培养理念、目标、定位、能力结构的一贯畅通;而立体化强调企业要与中高职学校协同构建以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内涵建设、课程内容设置与配比、实训教学体系、人才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式衔接结构。唯有如此,才能使中高职衔接与企业无缝链接。
(四)结构建构:以教学模式衔接为内核、规范各要素结构性标准的制定
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是职业教育特有的教育属性,而人才的培养往往取决于教学模式的科学性和适配性。教学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教学过程或教学结果,而是基于特定教学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有一定逻辑线索、相对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8]。这种教育活动结构是一个系统性与复杂性并存的合理结构,包括组织教育教学在内的所有要素,在一定的结构性和系列性相结合的条件下开展。因此,在多元治理结构下,中高职学校负责微观层面的衔接,以教学模式衔接为核心的衔接尤为重要。同时,在地缘、空间和时间等客观因素存在的背景下,中高职教学模式衔接还需要规范各要素结构性标准的研制工作,尤其是教学标准衔接、课程标准衔接等核心要素的标准。因此,构建以教学模式衔接为内核,规范各要素结构性标准化的研制便是中高职教学模式衔接的关键因素。衔接结构性标准可以使中高职学校在标准化教学模块中实现无缝式链接,而不至于由于标准各异而产生衔接上的“水土不服”或是“错位前行”。
参 考 文 献
[1][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3-134.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2-83.
[3][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
[4]王屹,方绪军,李春春.广西中职示范特色学校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1):50-56.
[5]洪贞银.高等职业教育校企深度合作的若干问题及其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0(3):58-63.
[6]2017年技能人才短缺将影响中国企业发展[J].职业技术教育,2017(12):9.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116.
[8]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大辞海(教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125.
Analysis on Interests Subjects and Path Framework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vergence from Multipl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Fang Xujun, Wang Dun, Zhou Wang
Abstract The state of the education state to the actual teaching state is an endogenous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presentation. From higher vocational policy design, practical demands, and body three levels of endogenous demand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n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businesses and so on. And interest game from the main body and the fusion domain into logical basis points, from the top design, the implementation, fusion, structure construction, such as level, put forward to higher multiple governance path in the framework.
Key words multiple governance structure; connection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enefit subjects; pathway framework
Author Fang Xujun, lecturer of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Law Research of Nanning College for Vocational Technology(Nanning 530008);Wang Dun,professor of Nanning College for Vo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Zhou Wang, Nanjing College for Vo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作者簡介
方绪军(1982- ),男,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所负责人,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南宁,530008);王敦(1972- ),男,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周旺,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重点项目“广西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立交桥模式的机制与实践研究”(桂教职成[2015]22号),主持人:王敦;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广西职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广西职业教育学生培养标准研究”(2016ZZC002),主持人:周旺;2017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公共决策中高职院校新型智库建设研究——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创新研究(研发)机构为例”(2017KY0993),主持人:方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