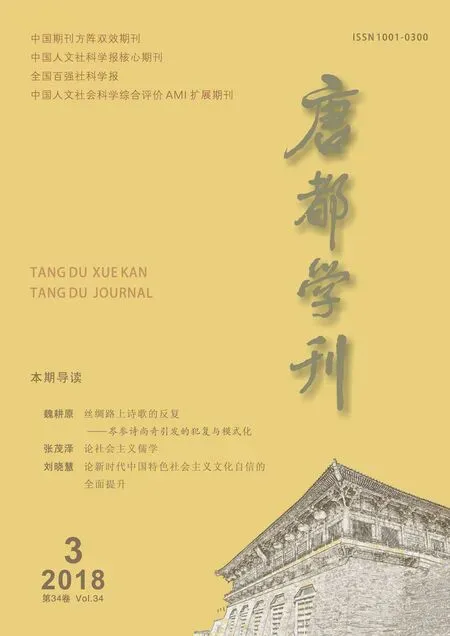天主教徒王徵和《西儒耳目资》:从关学到天学
谢明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
1623年10月,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独自前往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传播教天主教*金尼阁独自西行的原因是他已经能够流利地运用中文,参见1624年10月30日金尼阁所写的一封信。在这封由绛州寄给德国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573—1651)的信中,金尼阁写道:“就我自己而言,尽管长期的遗忘,我已经克服这种语言的困难。向上帝祈祷;我已经可以与任何人自由地交往而不需要通事;已经一年有余,我独自一人前往边远的省份,传布天主教信仰。”(“quod ad me attinet,jam hujus linguae difficultates oblivione diuturna obliteratus,Deo laus,et in hac aetate resarcivi; jam expedite sine interprete cum omnibus ago,et jam annus est ubi in remotissimis provinciis solus peregrinor,Christi fidem disseminans”)参见Nicolas Trigault,“Ex litteris P.Nicolai Trigault,ad serenissimum Electorem Bavariae et alios Bavariae duces,datis 30 octob.1624”,in Appendice,in C.Dehaisnes,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Paris,Leipzig,1864,275页。。途中,他携带了一部尚未成稿的字典,用于学习中文[1]109-110。1626年,这部手稿在陕西刻印,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西儒耳目资》。该书在中国辞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使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字音的字典。1627年9月13日,金尼阁在一封写给欧洲天主教神父的信中谈到了这部字典:
在中国天主教徒的要求之下,我已用中文(我已很容易地使用这种语言)完成一部字典,三卷。在其中,我把汉字和我们的元音和辅音进行比较。如此,这个国家的人们能够三天之内掌握我们的书写方法。语法家的这项工作激起了中国人的尊敬,他们好奇地发现,一位外国人校正了他们语言中的缺点。这是一个他们要竭尽全力去完善的问题。这部书也像精致的鱼饵一样,吸引了很多异教徒到天主教的网中。一位老迈的尚书兴致勃勃地对它进行编辑,并给它增加了一篇显明的前言。现在,人们驱使我编写第二个版本,以增加一些卷册,使很多中国人所写的有关此题目的研究,相形见绌。[2]282,293
与这部字典相关的一些讯息在这封信中被金尼阁揭露出来:比如这是一部由他完成的三卷本字典;它是在中国天主教徒的要求下完成,并用拉丁文字表示汉语音韵;这部字典出版后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其中就有年迈的尚书,即前吏部尚书张问达(1554—1625)。金尼阁也提到这部书有可能会被重印。简言之,这部书是成功的。通过它,欧洲的读者将会知道,金尼阁如何利用书籍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进而让部分中国人成为天主教所网罗的鱼。然而,金尼阁在信中所提到的内容,并非都确凿可信。事实上,《西儒耳目资》不是由他独立完成,而是和许多在中国出版的天主教典籍一样,是中西文人合作的产物。在中国方面,至少有王徵、韩云、吕维祺、张芳、卫子建、陈鼎卿、来临、陈宝璜、李从谦、李灿然等人参与了它的创作。张问达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西儒耳目资》的创作中,他是在王徵的介绍下,知道了这部著作,并为之写了一篇序言[1]30。他的序言,是1616年“南京教案”之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政治人物之关系恢复的重要见证,对传教士而言,意义重大。不同于张问达,其他参与者在政治上并不显赫,但他们是促成这部字典诞生的主要人物,特别是王徵,他“周旋终其役耳”[1]48。对此,学者也多有论述,但对于王徵和其他中国人参与该项活动的思想原因,却语焉未详*比如杜松寿《罗马化汉语拼音的历史渊源——简介明季在西安出版的〈西儒耳目资〉》,载于《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卷,第64~70页;计翔翔《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载于《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4期,第51~57页;金薰镐《〈西儒耳目资〉的成书及其体制》,载于《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第72~82页;邱光华《〈西儒耳目资〉的第一功臣——王徵》,载于《语言研究集刊》第13辑,第270~281页;谭慧颖《关于〈西儒耳目资〉的著者问题》,载于《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6年第4期,第87~95页;毛瑞方《王徵与〈西儒耳目资〉》,载于《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23~29页。。
事实上,王徵是“关学”之重要人物之一[3]78-79*此外,还请参见林乐昌《前言》,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关学”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主要是指北宋张载(1020—1077)以来在陕西关中所盛行之理学。明末大儒冯从吾(1557—1627)曾编有《关学编》,依次介绍关中的诸理学名家。尔后,王心敬在《关学续编》中也将王徵名列其中。然而,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之后,为强调天主教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一致性,却对理学展开了猛烈抨击。显然,金尼阁在关中传教时,以王徵为代表的理学家对金尼阁和西学的态度,并未受到利玛窦之思想的影响。相反,在天主教传行中国的过程中,这些中国士大夫的立场,成为天主教能否在中国顺利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王徵如何从“关学”代表转变为天主教徒,参与到《西儒耳目资》的编纂之中,并由此来探讨中国士大夫如何接受西学。
一、王徵生平*王徵的生平简介,请参见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林乐昌《年谱》,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375~397页。
王徵(1871—1644),字良甫,号葵心,中年之后自称了一道人[4],1571年5月12日生于陕西泾阳。1577年,王徵七岁,始受业舅父张鉴(1545—1606),后者亦为晚明“关学”代表。1594年,王徵二十四岁,中举。随后,他连续九次参加会试,均落榜,直到第十次,亦即1622年,他才考中进士。1623年,他被派往广平府(在今河北省)任司理;一年后,由于继母过世,他回籍服丧。正是在此期间,他与金尼阁相遇,并陪随其左右,一直到他离开。1626年末,王徵被派往扬州府任司理。1628年冬,因其父亲过世,王徵再次返籍服丧。1631年,由于徐光启(1562—1633)的学生孙元化(1581—1632)的推荐,王徵任“山东按察司佥事辽海监军道”,负责山东海防。在徐光启的建议下,他与登莱巡抚孙元化一道,积极采购西洋兵器,任用洋人武装,防御关外的后金政权以及明朝内部的农民叛乱。同年十一月,明军将领孔有德在山东吴桥发动兵变,孙元化、王徵等人为叛军所执,虽之后获释,但被押解至北京,孙元化被处以极刑,而王徵则被判“戍近卫”,之后不久,被遣返至原籍[5]76。
王徵自从被罢官后,便隐居不出。王介写道:“归来闭户著书,日译西文,阐扬圣教,以为老来功课”[6]425-426*同时请参见韩霖《守圉全书》卷末《赠策篇·王佥宪征来简》,第1页,转引自汤开建《明清天主教史论稿二编·圣教在中土》,澳门:澳门大学,2014年版,卷上,第241页。,他认为王徵欲以西学了却余生,但对有关王徵侍奉西学的论断过于笼统。王徵弘扬圣教的宏愿,从其接触天主教时便已开始,而且也不仅限于翻译西文。我们可由王徵与西学之接触的过程观之。
1598年,王徵第二次赴京参加会试。由此,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1571—1630)[5]11*另外两位分别是徐光启与杨廷筠(1562—1627)。。1615年,他从一位好友那里获得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所著的《七克》。读毕,王徵为该书所信服,想见其作者。一年之后,王徵再次赴京赶考,虽又落榜,但终于见到庞迪我。西班牙神父带领他参观了耶稣会在北京的寓所、图书馆和所藏图书,而王徵也借此机会瞻望了耶稣会士悬挂在那里的天主圣像。不仅如此,两人还展开对话,讨论天主教的相关教义。从此以后,王徵“是洗然若有以自新也,洒然若有以自适也”[6]118-121。也许就在该年,庞迪我在北京为王徵受洗,并取圣名“斐理伯”(Philippe)[5]25*方豪认为王徵受洗时间为1615年或1616年,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1,第227页;以及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1116~1167页.焦仰先神父认为王徵受洗一事,可能发生在1601年与1602年之间,参见Fortunato Margiotti,Il cattolicis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Roma:Edizioni “Sinica Franciscana”,1958,83页。德礼贤认为,王徵甚至早“在1603年就已经接受洗礼”,参见 Pasquale M.D’Elia S.I,ed.,Fonti Ricciane,Roma:La Libreria dello Stato,1942,II,593页,note 1。需要指出的是,王徵直到1636年,都未真正解决妾的问题,参见王徵《崇一堂日记随笔》,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177页;丁锐中《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0卷,第25~30页。另外,宋伯胤也指出,直到1638年,王徵才开始在其著作中使用受洗之名“斐理伯”(参见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第85页),因此,王徵之受洗亦有可能发生在1638年左右。另外,由于1617年3月18日庞迪我神父被驱逐出北京,而王徵于1617年与1618年,均在泾阳(参见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第23页;以及L.Pfister,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on de Chine,1552—1773,Chang-hai,1932—1934,71页),是故,王徵若在1617年之前受洗,则只能发生在1616年,亦请参见林乐昌“前言”,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7页。。
1619年,王徵可能是在北京再次参加会试之际,第一次邀请传教士到陕西开教。但中国官员沈漼(1565—1624)于1616年5月在南京发动的反天主教运动,令在华耶稣会士感到“暴风雨的狂烈”[7]。是故,王徵的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对天主教的热情并未减弱。1621年,王徵为杨廷筠的《代疑篇》作序,强调“信”德在天主教信仰中的作用[5]25。1624年9月12日,王徵与张问达的儿子张芳——当地的秀才,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共同写信给天主教中国副省阳玛诺(Manuel Diaz,1574—1659),第二次邀请传教士到陕西传教,并为其家人领洗[8]。因此,正在山西传教的金尼阁受命,于1625年4月从山西绛州,经过河南新安,前往陕西泾阳。金尼阁在关中传教时,王徵不仅帮他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还陪同其前往西安,视察刚被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9]*See also Dichiaratione di una pietra antica,scritta e scolpita con l’infrascritte lettere,ritrovata nel Regno della Cina,in Annue Giappone,MDCXXV-MDCLV,in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ARSI),Hist.soc.,I.50,2页。。
1626年冬,王徵前往北京补铨之际,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1559—1654)、奥地利籍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北京的寓所中相见,朝夕相谈。在他们的帮助下(“分类而口授”)[6] 192,王徵完成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他选译了西方巧器中与民生“最切要者”,工费“最简便者”,制作“最精妙者”的部分,编辑成册,并于1627年刻印出版。该年,王徵还在西安为在此传教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雅谷(Giacomo Rho,1593—1638)修建了一座教堂,“以为朝夕钦崇天主上帝之所”[6] 161。后来他在该教堂向在此传教的汤若望神父请教天主教历史,完成《崇一堂日记随笔》一书,并于1638年正式刻印出版。在书中,王徵记录了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圣人以及其他的圣经故事*关于这所教堂,请参见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第64页,同时参见C.Dehaisnes,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188页。。1634年,王徵依据罗雅谷的《哀矜行诠》(1623),在家乡建立起天主教慈善组织“仁会”,以实践天主教义中的“畏天爱人”思想,并借此来传播天主教[6] 139-140*同时请参见Erik Zürcher,Christian Social Action in Late Ming Times:Wang Zheng and his “Humanitarian Society”,in Jan A.M.De Meyer & Peter M.Engelfriet,eds.,Linked Faiths:Essays on Chinese Relig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nor of Kristofer Schipper,Leiden:Brill,1999,269-286页。。1637年,王徵在法国籍耶稣会士方德望(Etienne Le Fèvre,1598—1659)的帮助下,将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杜奥定(Agostino Tudeschini,1598—1643)的《渡海苦迹》译成中文,题为《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王徵在该书中记录了杜奥定神父东渡,向中国人传播天主教的伟大事迹,并借此强调“敬天爱人”的思想[6]157-160*同时请参见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第83页。从1637年到1639年,杜奥定在山西和陕西传教。。1640年,王徵编写了《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一书,这是他所编写的最后一部有关西方器械制造的书。书名中的“额辣济亚”为拉丁文“gratia”的音译,这意味着该书与天主教有密切之联系[5]87。
王徵丰富的人生经历,可简要地分成为两个阶段:一是他饱读诗书、十上公车而进入仕途的阶段。在该阶段,王徵颇为不顺,中途又遭罢官,仕途累计不足三年。故后人为他立传时,常为其未能完全施展治国才华而深感遗憾。但细观王徵的政绩,并未超出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平常职责。而且这些人也并未从王徵本人之立场,分析其仕途平常这一现象及其原因。因而,他们也无法认识到王徵之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即他作为天主教徒,专心于中国天主教事业的建设时,与他作为士大夫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虽有重叠,但更多的则是一种继承关系。前一种人生经历为王徵接受天主教徒这一身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后一种则弥补了王徵在仕途上的遗憾。两者最终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尽管它们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思想背景。
二、王徵的思想世界
1643年冬,李自成攻陷西安,欲网罗关中大儒,以为大用。王徵担心受辱,故手书一联,贴在墓门上。他写道:“自成童时,总括孝弟忠恕于一仁,敢谓单传圣贤之一贯;迄垂老日,不分畏天爱人之两念,总期自尽心性于两间。”[6]399之后,他便执剑坐卧在其所建立的天主堂中,静候李自成派来的使者。最后,他绝食七日而亡,时在1644年4月10日*有关王徵最后生平与事迹,各家所言,均有差别。本条史料引自张炳璇《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398~401页。。王徵手书的这副对联,正是他对其一生思想之自道。上联所讲,为其尚幼时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统一于“仁”;而下联中的“畏天爱人”,则来自于他所受的天主教义,该思想一直影响其后半生。这两种源自不同文明的思想,以前后相继的方式主导着王徵的不同人生阶段。
王徵的启蒙老师张鉴,字孔昭,别号湛川,是“关学”代表人物之一。“关学”强调“学以致用”,重视兵法、井田法、自然科学之流[10]。在历史长河中,“关学”思想的核心并未发生过根本的变化。黄宗羲在《三原学案》中写道:“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11]158文中所讲的“薛氏”,即山西大儒薛瑄(1389—1464),他向来主张“学贵践履”[11]3。这一精神亦为张鉴所坚持。王心敬在张鉴的传记中写道:
先生好学深思,诗、古文、词皆成家。然所深嗜者关、洛之学,而初不执宗旨为谈柄,尝以为“圣学关键要在此心不自欺,吾辈但从行事起念时一一点检无愧,便是圣贤人路,若徒事语言而自欺不除,君子耻之。”故生平不多著书。在家,则日用伦常事事求慊于心;历官所至,则念念切于民生国计。利不兴不已,害不除不已。以故,官虽不逾五品,而功绩则卓乎古循良之遗征。[3]78-79
张鉴的思想是强调“心不自欺”,也即在“起念”与“行事”之间保持一致。因此,张鉴无论“在家”或者“历官”,都戒空谈而重实行。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历官”时悉心于地方治理;“在家”则悉心于各种奇器的制造,但皆以民生为根本指导。因此,不同于那些依靠“得君行道”以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士大夫,张鉴认为,作为“循吏”也可以实现“圣贤人路”*关于“得君行道”,请参见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载《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北:云晨文化,2004年版,第250~332页;同时请参见Cynthia J.Brokaw,Introduction of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order in Late Ming Imperial China,Princeton,New Jersey,1991,3-27页。。
张鉴殁后,王徵得其心传。尽管在王徵一生中,他为实现其“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曾十上公车*1639年,王徵在庆贺其表弟张炳璇受任河北满城县令时,曾说他自己“未尝不动圣主贤臣之想”,参见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第86页。另外,有关张鉴为“循良”的说法,请参见王心敬:《关学续编》,载冯从吾《关学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第78~79页。。然而,与他的舅父一样,王徵坚信,通过制作巧器也可以成为有用之人,进而成为“圣人”,甚至超越他们。因此,他一反传统社会所谓的“君子不器”,反而兢兢业业于器物的研究和制作*王徵曾引《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为其行为辩护,参见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193页。。在接触天主教教义之后,这一信念变得更加坚定。在解释为何出版《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时,他写道:“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于技艺一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5]116正是在此种情怀的影响下,王徵对传统士大夫的“正经学业”并无太多热情[5]163。
换而言之,王徵同情天主教,并从中发现政治的出路,首先与其所受的儒家思想或者说“关学”思想有关。1628年秋,王徵完成《畏天爱人极论》一文。在其中,他谈到其人生不同阶段的思想转变历程。他说自束发以来,解读圣贤书,以寻求解决“天之所以命我”(即人生价值)的困惑。为此,他曾求助于释、道两家,但未有所获,故“屡学之而屡更端”[6]118-119。直至有一天,他偶尔读到孟子的三乐书,突然有所感悟,认为孟子书中所讲的“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就是“天之所以命我”的理由。然而,如何作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则又一直困扰他。解决此困惑的基本方向,直到他读了庞迪我的《七克》之后,才有所获。他称道此书为“是所由不愧不怍之准绳乎哉?”[6]119此后,王徵放弃此前之所学,特别是佛学,转而投身于西方天主教。到1637年,天主教已成为王徵之日常生活的指导。同年,他在《山居自咏》组诗中写道:“糊涂账,何须算?神明镜,乐有余,分明认得来时路。半生潦倒从人笑,百样颠危赖主扶。自在乡,由人住,洒圣水消除了白业,叹南柯劳攘杀玄驹。”[6]328*1636年,王徵在其所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即已将人生际遇都托付于天主,他写道:“况百危百险中,赖主佑而生还”,请参见王徵《崇一堂日记随笔》,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177页。。王徵把潦倒不堪的余生都托付给天主,最终完成其身份认同的转变。这一过程,一波三折。王徵的人生困惑,首先来自于他对儒家典籍的理解。在释、道两家无法解决其困惑之后,他最终从天主教那里得到慰藉。其身份认同的转变表明,在关学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方面,源自儒家的人生哲学问题,成为天主教在中国被理学家接受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主教义,为王徵和其他士大夫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当西方传教士以西学为手段,传播天主教义时,王徵的政治抱负也开始在天主教教义的指导下展开。
在王徵处,这种途径便是“畏天爱人”*王徵有时也用“敬天爱人”,请参见王徵《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160页。。该短语包含有两层含义:“钦崇一天主万物之上”与“爱人如己”[6]121*在别处,王徵又将其归之为“爱慕天主万物之上,与夫爱人如己”,请参见王徵《畏天爱人极论》,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136页;在《仁会约》中,王徵写道:“仁之用爱有二:一爱一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请参见王徵《仁会约》,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139页。。王徵在创办“仁会”时,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梳理。他写道:“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然必真真实实能尽爱人之心之功,方是真能爱天主。”[6]139这种“畏天爱人”观,来自于王徵对天主教义的理解。他依靠圣经、《哀矜行铨》和《七克》等天主教著作,获得天主教知识,并建构起“畏天爱人”的内在逻辑。
首先,王徵认为天主对普世世界握有赏罚大权,人类会因为行善事而升入到天堂,也会因为行各种恶而坠入地狱,接受惩罚。其次,由于天主赋予人类“亚尼玛”(anima),所以人类能够分辨“善”“恶”。不仅如此,“亚尼玛”是“灵性一赋,常存不散”,所以,尽管灵性有向善和向恶两种,但通过圣礼和自省可以抑恶扬善,可以“恒见天主于心目,俨如对越至尊,不离于心,狂念自不萌起”,亦即能够对天主产生真爱[6]136。由此,便可以培养起天主教徒的德行。而作为天主教徒,他有多种德行,其中起总领的德行便是“仁”德。“所谓仁者,爱人。”所以,爱天主必定会爱人。而对人之爱,则又不能虚爱,而是要实践之,也即王徵后来通过“仁会”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因而,“爱天主”最终归于“爱人民”。不仅如此,王徵还进一步认为,人人皆有“畏天爱人”的念头。对此,他说得极为明白:“本人人原具之良心,亦愚夫愚妇所可与知与能之平常事,而实千古希贤、希圣、希天者之真功用,只在吾人一提醒转念间耳。”[6]137-138这一论断,也可以在王徵的另外两篇文章《学庸书解》和《士约》(1628)中得到类似的回应。但在这两篇文章中,王徵是以儒家之立场,强调士大夫应坚守尧舜之道,并指出,尧舜之道“时时见在,人人各足,诚匹夫匹妇之所可知可能”[6]110。所以,不管是在儒家经典之中抑或在天主教文本中,王徵都发现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理。同时,王徵又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起点,追溯至“格物致知”。在儒家思想中,特别是在宋明理学中,由“格物致知”能够产生出“治国平天下”的终极政治理想。对天主教徒王徵而言,“格物”与西学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王徵曾说:“格物者,即格究物有本末之物也。盖吾身本万物皆备之身,格者直向未发前乍见时体认本来面目,知其孰为百体之君,孰为万事之宰,孰为精一纯粹虚灵而不昧,灼见原头,专务大本,方为知至。”[6]109而王徵也同样在入华耶稣会士所编写的各类著作中,发现天主教同样重视“所以然”。既然由“格物”可知万物的本来面目,知“孰为百体之君”,那么,由“所以然”也可以实现终极的政治目的。
因此,对于王徵而言,即便是在器械制作中,也隐藏着实现终极政治理想的途径。所以,在政治上颇为平凡的王徵,并未为其荒废当时所谓的正经事业而难过。相反,他总是从天主教中获得力量,凭着自己的想法而践行生平的事业,并不为那些正经事业的荒废而有所动,“独时时将畏天爱人念头提醒,总求无愧于心”[6]1。对他而言,“爱民”即为“爱国”*王徵认为:“重国即亦重民,爱民即亦爱国。”请参见王徵《贺张仪昭授满城县令序》,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353页。,如同王阳明的“视国犹家”,王徵把对民众之爱,视为天主教徒所应承担的职责[12]。因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人痛痒”的关注,便具有了崇高的政治意义[6]1。只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指导理论已经由传统的儒家思想转变为天主教义。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王徵通过“畏天爱人”这一观念,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转移到天主教徒身上。所以,当金尼阁携带《西儒耳目资》这样一部介绍西方知识的著作,前往关中传教时,王徵才会“周旋终其役”。
三、王徵与《西儒耳目资》
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共三册,依次为《译引首谱》《列音韵谱》《列边正谱》。其中第一卷为总论,介绍如何利用罗马拼音查阅文字和如何利用汉字笔画查阅字音;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分别介绍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它正式出版之前,这部字典便已经以手稿的形式在耶稣会内部流传。金尼阁所携带者,便是其中一部。由于它的便捷性,这部字典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纷纷要求将其出版。在这些人中,就有来自山西绛州的天主教徒韩云。金尼阁同意了这些人的请求,于1624年开始编纂此书。1625年4月,他携带书稿,由河南新安转道陕西泾阳时,也得到了当地文人吕维祺的帮助。

名理如渊,正汇字学之海。学海不澄,名理奚自而流。西儒殚竭心力,急急成此书者,政欲资之。徧阅此中文字,可为后来翻译西学,义理之渊海耳。况此中世代相传,音韵诸编,种类虽多,都从一路所出。细勘厥路,路多有差,但差之或近或远焉。今《西儒耳目资》一书,独关直捷之路,不左不右,绝无一毫之差。其中种种名理,相逼而出,若海错争奇,鲜新可味。细相较勘,西儒创发此中向来所未有者,盖至五十余款之多。观者肯一细心理会,自见良工苦心,应不疑余有偏嗜矣。[1]37
王徵提出了刻印此书的两点理由:首先,《西儒耳目资》属于事天之学,包含有西学的精神。对于事天之学与字学的关系,韩云在其《西儒耳目资序》中曾有所讨论:“西庠天学,修身以事天人学,格物以穷理;字学乃文学之一,为天人学之基。”[1]3王徵也有类似的看法。尽管他视《西儒耳目资》为金尼阁之学问的余绪,但这些入华传教士放弃了一切名利婚宦,“独嗜学穷理”,而他们所刻的书“莫不各殚奥妙”[1]18-19。因此,由《西儒耳目资》,中国人也能获取对天学的认识。王徵在其后来所写的组诗《山居自咏·五煞》中,更是直接将《西儒耳目资》与天学联系在一起*王徵写道:“诗酒场,兴颇豪。性命关,心肯粗?奇人幸得多奇遇,资人耳目元音谱,启我灵函圣迹图。但开口,皆奇趣。情知道天花香艳,那怕他世路荒芜。”请参见王徵《山居自咏》,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327~328页。。
其次,《西儒耳目资》可以修正中国音韵书中的诸多错误。明末以来,中国的音韵学家和文字学家已意识到中国固有之音韵书和字书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明末大儒吕坤(1536—1618)曾批评中国人所编写的各种韵书:“余少从里儿游,读边字。长而耻之,积韵家书卢数十,浩浩茫茫,未知所入也。”[13]吕坤为此编写了一部《交泰韵》,试图进行改革。然而在金尼阁看来,中国韵书的诸多问题,唯有通过西法,也即西方音韵之学,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受此影响,王徵也相信《西儒耳目资》可以用来弥补中国传统音韵学所存在的不足。不仅如此,王徵在通读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之后,也对中国之学习音韵的人提出批评。他认为:“本国之人,未知元音元韵所以然之理,真聋而自以为聪者,可惭也。”[1]243。这种对“所以然”的强调,正是王徵接受《西儒耳目资》,并支持其在中国出版的根本原因。于是,他向张问达和张芳父子寻求资助,出版这部著作。
四、总结
王徵利用其西学知识,评价中国固有之学问,并积极以西学来改进或代替之的立场,事实上也出现在王徵对中国的其他事物的认识之中*自信奉天主教之后,王徵便从天主教的视角来批评和反思中国社会和政治,请参见王徵《贺张仪昭授满城县令序》,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353页。。尽管如此,这不意味着王徵彻底与儒学断绝关系。其最具意义的体现,便是他绝食七日,以死反抗李自成的招安。这件事在后世的文人中间影响颇大,被冠以“杀身成仁”之美名*方豪在为王徵作传时,似有意避讳王徵自杀一事,请参见方豪《王徵》,载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第419页。王徵因绝食而死的最可信证据,来自王徵的墓志铭,请参见丁锐中:《张炳璇〈王徵墓志铭〉点校及初步探析》,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8~125页;另请参见林乐昌《王徵死因订正》,载《唐都学刊》1998第2期,第39~40页。。然而,作为天主教徒,王徵的行为却违背了天主教教规。而“绝食”一事却深刻地反映出王徵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作为天主教徒的王徵与作为士大夫的王徵,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天之所以命我”的人生疑惑。所以,他才会坦然接受西学,并积极为其奔波,以服务于这个即将倾倒的大明王朝。于是,当西儒金尼阁携带西学进入关中地区传播天主教义时,也便得到了王徵和他的“关学”乡党们的积极呼应和支持。
(拙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比萨高等师范学校Stefania Pastore教授、美国哈佛大学Peter Lieberman先生和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教授和孙海棠女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2] C.Dehaisnes.ViedupèreNicolasTrigaultdelacompagniedejésus[M].Paris,Leipzig,1864.
[3] 王心敬.关学续编[M] ∥ 冯从吾.关学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丁锐中.张炳璇《王徵墓志铭》点校及初步探析[J].世界宗教研究,2012(1):118-125.
[5] 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林乐昌编校.王徵全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7]Relationedellecosepiùnotabiliscritteneglianni1619,1620,&1621dallaCina[M]. Roma,1624:38-39.
[8] Fortunato Margiotti.IlcattolicismonelloShansidalleoriginial1738[M].Roma:Edizioni “Sinica Franciscana”,1958 :91.
[9]Letteredell’Ethiopiadell’Anno1626.finoalmarzodel1627.EDellaCinadell’Anno1625.finoalfebrarodel1626 [M].Roma,1629:119.
[10]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45-550.
[11] 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2[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86.
[13] 吕坤.交泰韵·序[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5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