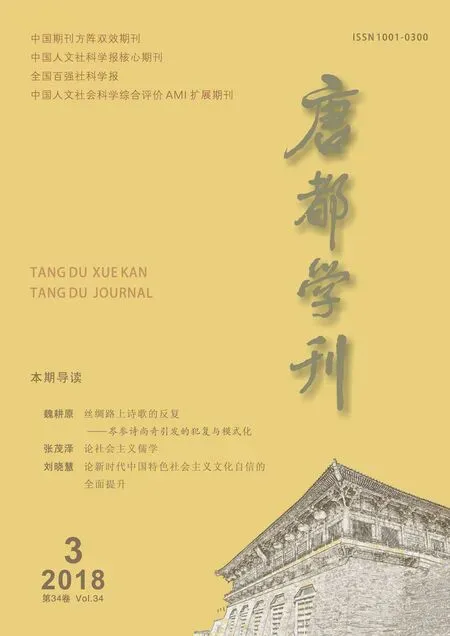善的型与幸福
——解析两种考察“好生活”的路径
卢明静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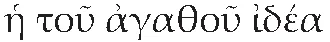
一、生活中的聪明人与好人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写作方式来看,通常会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们都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讨论主题,即考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也就是好生活。他们都注意到了生活中那些影响年轻人的意见和那些被认为聪明的人和善良的好人。
生活中有一些被看作是聪明的人,他们相当精明,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这些精干的人,可以洞察事态,选择利己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的理智思维相当的发达,具有能够很快完成既定目标的能力。那些聪明之人很多也是狡猾的人,通常设法避开法律,不惜伤害他人,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正如柏拉图所言,他们中的最强者,有能力避人耳目地做不正义的事情,甚至获得统治城邦的权利。正常状态下,对于两个好人而言,健全的理智更有利于做高尚的事。但从这些聪明人的所作所为来看,理智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道德行为的发生,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柏拉图认为,这样的人只拥有卑微的小灵魂,他们的灵魂专注于不确定的、生成变化的东西,也就是单纯财产的增加、权力的获取等方面,缺乏对善的型的关照(519a)[1]326。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没有高尚的目的。
同时,我们也发现生活中有些人是善良的,他们心肠好,常常为别人着想。在他们中间,可能大部分的人不具备任何较高的理智,他们的行动仅仅顺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根据一些朴素的想法做出很多让人感动和受人称赞的事情。这些朴素的想法或许来自父辈母辈的教导,或者由于受到良好风气的熏陶,他们可能没有过多地反思过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但是,他们能够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并且为此感到快乐和心安。亚里士多德认为好人的行为方式,似乎就可以作为道德的标准。一个好人出于本性就会做高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人仍然需要明智,因为,明智能够确保我们出于好的考虑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明智作为理智德性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
二、善的型与幸福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思考何为好生活的过程中,都关注着当时围绕年轻人的流行意见,但是由于他们的不同气质,前者注重数学,并由此开始考察解决自然、伦理等问题,而后者注重经验现象,以此为基础朝向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问题的讨论。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对柏拉图的一些理论进行批判,正如他所言:“虽然友爱和真两者都是我们的所爱,爱智慧者的责任却首先是追求真”(1096a17)。[2]13因为柏拉图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明确地分科,他在《理想国》一篇对话中讨论了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所讲的“善的型”,不仅是可见领域即可感世界中一切正确和美好事物的原因,也是思维领域的主宰者。而亚里士多德将理智分为沉思的理智和实践的理智,只有实践的理智关系人的实践活动。我们将从他们的研究方法出发,解析这两种不同的考察好生活的路径:
关于理性论证应该从原理出发还是走向原理,亚里士多德说这个问题由柏拉图提出,确实值得考虑。他认为对于打算成为高尚正义的人,应该从对我们而言已知的事情出发。也就是说,早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对一件事有基本正确公正的判断,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始点。正如很多学者所言*J.A.Stewart和J.E.C.Welldon认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特指柏拉图的某一篇对话,他可能仅指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的总的方法倾向(参见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10页注3)。Burnet建议将这个结论理解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讨论的回忆,参见由C.Rowe译、S.Broadie注释的《尼各马克伦理学》第266页。,柏拉图没有在对话中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探索事物定义,要求认识善的型的人返回洞穴,才能对洞穴里的所有东西有真正的认识。也就是说,正确的理性论证必须以认识善的型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是从原理出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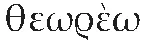
2.作为原因的善的型与作为目的的幸福
柏拉图没有正面回答善的型本身是什么,而是连续用三个比喻即太阳喻、线段喻和洞穴喻解说它。柏拉图称太阳是善的型的孩子。在感觉世界中,如果是白天,也就是有太阳撒下的光,我们就能用眼睛看到周围的事物。所以说视觉能力汲取于太阳,就像从太阳那流溢出来的(508b)。这里柏拉图的意思应该是,视觉能力是眼睛所具有的,即使在黑夜,眼睛仍然具有这种能力,但不会是清明的,就如同瞎子没有视觉是一样的,只有太阳才能使视觉能力起作用。人的灵魂也一样,善的型给被认知的东西以真而使认识者的认识能力得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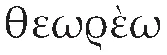
正如太阳不仅给可见的事物以可见的能力得以实现,而且促使它们产生、生长和养育。同样,善的型不仅使被认识的事物被认识,而且还使它们“是”、被称为“是的东西”。但善的型不是“是的东西”,它在位阶和能力上更卓越*通常认为,柏拉图区分了两个世界即可见世界和型式世界,其实他并没有“世界”这个术语,仅是用与格表示不同的领域,并不具有任何空间意义上世界的含义。正如陈康先生所言,“柏拉图在《费都篇》和《国家篇》中并没有讲分离,只有差别,没有距离。如果误解为空间的距离,便成为分离。这是从古以来对柏拉图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他的学园中便已经产生”,参见陈康《柏拉图哲学研究》,载于《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10页。。善的型可以说是最高的“是”。
亚里士多德从四个方面否定了柏拉图善的型的存在*这个讨论集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1卷第6章。具体来讲,这四个方面是:(1)柏拉图对于有次序的事物没有提出型式却用善表示不同等级的范畴;(2)不存在同一个善,因为善在不同的领域被使用并表达不同的含义;(3)属于同一个型式的事物应该由一个科学来研究,但实际上,对于不同领域,只有那个领域的人才研究并知道什么是善的;(4)善不会因为是永恒的善就更加的善。,这种否定是源于他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首先明确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的实践活动。而且人的实践同技艺与研究相同,都是以善为目的的。而幸福是实现所能达到的最高善。从良好教养获得的正确意见开始实现把握幸福这一最高的善。“幸福”这个最高善是对一个人一生的完善的实践活动的评价。面对三种主流的生活,即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快乐和荣誉,都不能囊括人生的幸福。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
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理解为是合乎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所以,我们生活的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少年时是否受到了良好的教养。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灵魂合德性的实现活动,这里的德性应该包括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不同的题材需要不同的科学以及我们的灵魂用不同的部分考察不同的事情。所以可以推断,作为可变化的实践活动,灵魂理智部分只有明智是与此相对的,合于德性指的应该是伦理德性和明智。
幸福是人生所朝向的目的,这种目的是指人们实践最终达到的状态。合乎德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我们不能说只有一个人过完一生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是幸福的。面对现世各种偶然的变故,那些幸福的人总是在思考着合德性的事情,他们能够以最恰当的、最高尚的方式接受并处理它们。
3.对善的型的观照与最高的实现活动沉思
既然善的型是思维领域的主宰者,是实践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原因,因此我们的灵魂一定观照于它。在柏拉图这里,对善的型的观照已经成为理论上顺理成章的事。而此处我们主要来讨论一下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最高的实现活动沉思。这个与观照同样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整个思考好生活的路径中,似乎不是那么明确。
正如前文所言,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1卷,已将最高善幸福看作一种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而在第6卷和第10卷,亚里士多德讨论了灵魂中确定真的理智德性,其中沉思是思考不变的作为原理的东西,并说沉思对应灵魂中最高等的部分,因此努斯的活动沉思是最高的实现活动,作为连续的沉思比任何其他活动都更持久。亚里士多德最终将合于德性的生活看作第二好的生活,第一好的生活是努斯的活动沉思。因为努斯是人似神性的东西,它不属于混合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努斯的德性是可以分离的。在《论灵魂》430a15-17处,他说明努斯像整个自然界一样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料的、被动的,另一方面是形式的、技艺的、主动的。主动的努斯造就万物,“它就像光一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光使潜在的颜色变成现实的颜色。这样的努斯是可分离的、不承受作用的和纯净的”。所以,努斯的德性像努斯一样也是可以分离的。参见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第308页注4,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合于伦理德性的生活完全是属人的,因为这些德性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在沉思的过程中,人可以获得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其他任何属于享福祉的人的特性。沉思这种实现活动不需要任何的外在东西,而合于德性的活动则需要。
然而,亚里士多德强调,对于人来说,属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西。因为人的本性对于沉思是不够的。亚里士多德没有讨论沉思对于人在世的实践活动有怎样的影响,他仅仅分别述说了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和沉思,在二者中,沉思因为属于人中似神性的东西,因此是最幸福的。而人由于本性的缺陷不能只完全处于沉思的状态,必须拥有合于德性的实践活动。这就像柏拉图所言的,走出洞穴的人必须回到洞穴。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是:柏拉图明确表示善的型是一切正确行为的原因,因此,要想做高尚的事,必须对善的型有所观照;而亚里士多德则没有说明沉思的对象是什么,也没有明确说明这种沉思对于合德性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作用,仅仅表明理智德性中的明智是保证道德行为正确的品质。亚里士多德这样处理的原因,有可能是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属于伦理学讨论的题材,应该在形而上学中进行思考*因本文仅是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好生活两种路径的初步探索,讨论的范围基本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他们的其他著作包含的思想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讨论。此处涉及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以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不变事物的思考是否有益于对可变事物的考察。。
三、具有观照能力的灵魂之眼与能够保证选择正确的明智
柏拉图认为我们的灵魂有观照善的型的器官,正如我们身体的眼睛一样,可以保障我们行为正确,做高尚的事。每个人的灵魂都具有那个犹如眼睛的“器官”,可以说这种器官是自然赋予我们的,造物主给予我们的*参见《蒂迈欧篇》。,而这种器官所具有的能力不是通过如智者们的教育就能具有的。我们应该关注的只是这个器官如何才能朝向正确的方向,注视它所应该注视的东西——善的型。灵魂有四种获取认识的状态,面对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见事物即各种影子和自然的东西以及人造物,灵魂形成臆想和信念。可思维的事物,前一部分是以可见事物中的部分作为映像,它的方法是从假设出发,推出相应的结论,灵魂是通过思想而不是感性知觉观照它们来获得思想;另一部分是“是的东西”和作为一切事物本原的东西即善的型。灵魂中的理智,可以借助辩证的力量,考察作为一切事物本原的善的型。灵魂之眼具有辩证能力,能力抛弃一起假设,根据“是的东西”不断地论证和探索,一直向前分析,最终对善的型有所观看。辩证科学能够使灵魂之眼得以净化并复燃而重建光芒。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中欲求引起实践,欲求中的追求与躲避便相应于实践理智中的肯定与否定。
如果伦理德性是灵魂的进行选择的品质,如果选择也就是经过考虑的欲求,那么就可以明白,要想选择得好,逻各斯就要真,欲求就要正确,就要追求逻各斯所肯定的事物。这种理智和真是与实践相关联的。而沉思的理智同实践与制作没有关系。它的状态的好坏只在于它所获得的东西是真是假。获得真其实是理智的每个部分的活动,但是实践的理智的活动是获得相应于遵循着逻各斯的欲求的真。选择是实践的始因(选择是它的有效的而不是最后的原因),选择自欲求和指向某种目的的逻各斯开始。所以,离开理智和某种品质也就无所谓选择。理智本身是不动的,动的只是指向某种目的的实践的理智(1139a21-35)。[2]168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指理智德性中处理实践题材的明智。“明智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140b6)[2]173。明智是灵魂中有逻各斯部分中构成意见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处理实践事务。而且,明智不是一个纯粹的逻各斯的品质,它是运用在行为的选择中,在生活中,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亚里士多德认为努斯是用来考察第一原理,但他没有专门讨论第一原理与明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首先辨明了努斯和明智所考察的对象,“努斯相关于始点,对这些始点是讲不出逻各斯来的。明智则相关于具体的事情,这些具体的东西是感觉而不是科学的对象”(1142a24-26)[2]179。明智的主要因素是好的考虑、好的理解以及体谅。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将德性等同于知识,有对的一面即离开了明智所提供的正确道德选择是不能存在的,但将知识都等同于明智则是错误的。因为伦理德性不仅是合乎逻各斯的,而且是与后者一起发挥作用的品质。离开了明智,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伦理德性,也不可能有明智。因为伦理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智使我们选择朝向实现目的的事物正确。
四、小结
在寻求好生活的过程中,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回应了所有柏拉图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在对它们的态度上,二者也是极其相似的。柏拉图通过对话,由对话者言说了具有代表性的常识观点,而亚里士多德也是从日常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出发;柏拉图讨论了早期的音乐和体育教育,培养推理、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德性,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将这些定义为伦理德性,也对它们做了详细的考察;柏拉图接着讨论了善的型和灵魂之眼具有的思辨能力,而亚里士多德也讨论了灵魂的理智德性,此处的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的研究之初就对其研究对象和目的进行了限定,将伦理学的目的定位在属人的最高善即幸福,因而所有理智德性中,亚里士多德将明智作为一种实践智慧,是理智德性中思考实践活动并确保做出正确选择的品质。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的结尾也讨论了幸福与沉思的关系,在柏拉图那里沉思就是对善的型的观照,人最高贵部分努斯的实现活动沉思是最幸福的,合于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并没有说明沉思的对象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应该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探求好生活的路径,虽然有两个不同的始点,但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用范畴、分科的讨论方法将柏拉图的理论进行了细化。就目前的讨论来看,我们可以说他们面对人的实践,态度是一样的,行为的正确需要理性思维的保障。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用范畴来诉说事物,其中“实体”为最重要的范畴,这样他就用范畴将柏拉图所言的“是的东西”与“可见的事物”放在一个视域来讲。而且,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对不同事情的研究来界定不同科学,因此,他明确区分了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在这种区分的研究中,柏拉图的善的型在不同的领域代表了不同的东西,伦理学中是个人的幸福,政治学中是城邦的幸福,形而上学中则是第一推动者。由此看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有很强的内在相关性,但由于采取的方法不同,所以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理想国[M].顾寿观译,吴天岳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
[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以《对传·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