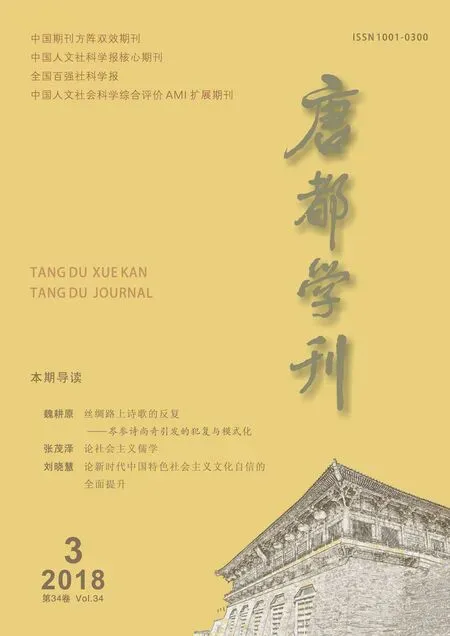唐代进士浮薄之风新探
陈飞飞, 李宗俊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大创举,隋唐则是它萌生与发展的第一阶段,因此其优点与不足能够在这一时期得以充分显露。科举制与进士科的发展脉络及其进步意义,相关论著作已然汗牛充栋,而且对于这项选官用人制度存在的漏洞与不足,学术界亦不乏深入的研究*相关的研究很多,如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专著,荟萃了作者20多年研究科举史之心得,堪称国内科举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主要讨论科举制的起源问题;许友根《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主要研究进士科考试的时间设置。刘杏梅《论唐代进士科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指出进士科从唐代学校教育、学术文化如经学、史学、文学、法学乃至书法等方面促进了社会学术文化的繁荣。,但学界就唐人对于这项制度的褒贬态度尚且关注不够,如史籍中存留的时人的一些诸多负面性评价,比如“浮薄”“词薄”,即指进士个人品行或文风轻薄、浮华等相关现象的研究仍留有很大的空白*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1~283页)曾提及;韩宾娜《从进士科看唐代科举制的流弊》(《松辽学刊》,1994年第3期)是从进士科的角度讨论唐代科举制的流弊,其观点较为新颖,但重点仍然在于科举制的本身,并没有深入到进士群体的研究;杨伟威《进士浮薄与亡唐政治研究》(《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其文主要论述晚唐时期进士浮薄的原因和影响,且主要集中于晚唐,但是作者的相关结论和阐述方面稍有欠缺,未能全景而清楚地展示科举浮薄与唐代兴衰的内在关联。,故本人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进行考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表现
隋炀帝于大业年间创设进士科,自此科举取士成为中央王朝选官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至唐代因之,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1]1159。诚如史家杜佑所言“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2]353,故而唐朝的取士制度只是在隋朝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与完善。唐代的秀才科几乎消亡,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虽是大唐首创,由于有较强的专业性,且不为社会所重,故而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明经和进士两科是最重要的入仕途径。
唐中叶以后,进士特重,俗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在录取的人数方面,“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2]357。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不过只有百分之一二而已,考中明经者的则达十分之一二,从录取比例和人数上来说,进士科录取更加困难,录取人数更少,也就更加受到时人的推崇。宰相薛元超就曾“不以进士擢第”[3]而深以为憾。唐朝社会崇重进士可谓空前绝后,当时就有“焚香礼进士,设幕试明经”[4]8293之别;甚至贵为天子的文宗皇帝也自称“乡贡进士李道龙”[5]371,故时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虽然唐代进士备受尊崇,但是唐朝史书中屡屡见到有关进士浮薄的记载,尤其是集中于唐晚期,这样的现象令人深思与不解。是故,弄清有唐一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具体表现的阐述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唐朝初期就已经出现了进士浮薄的迹象。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文辞俊雅,声振京邑”,但员外郎王师旦将他们的文策考为下等,举朝震惊,不知所由。唐太宗得知此事后责问王师旦,师旦回言:“此辈诚有辞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太宗听后“深然之”。后来张昌龄做长安尉,因受贿而免,王瑾“亦无所成”[6]15,这不能不说王师旦确有先见之明。
唐玄宗统治时期,士子袁映上策反映铨选之弊,建议玄宗“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前弊”[7]3556;名相张九龄也曾上书议论铨选浮薄之事,指出“假如今之铨衡,欲自为意,亦限行之已久,动必见疑,遂用因循,益为浮薄”[7]2926。可见,玄宗朝铨选中也存在着浮薄之风,急需进行矫正。此后,肃、代朝的宰相杨绾也曾上疏论贡举之事:

杨绾深言唐代以来进士、明经科考试内容的调整与流弊,对于进士浮薄之风大加斥责。中书舍人贾至也赞同杨绾所奏,以为实情。且说“今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科,只足长浮薄之风,开侥幸之路矣”[9]1395。
德宗建中二年(781)改革进士科,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且皆试策三道”,说明德宗已经认识到了进士文词浮薄的现象。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敕令中书舍人王启、主客郎中白居易重新考核“今年礼部侍郎钱徽下进士郑郎等一十四人”,结果“覆落十三人”。针对这种情况,四月,穆宗为此专门下诏重申“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眷言败俗,深用兴怀”[8]488。表明当时的进士之浮薄非常严重,由于卷入当时的朋党之争,已经对穆宗朝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文宗也曾对侍臣说:“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下诏令礼部每年取科举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宰相郑覃以通经入仕,位至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文宗废除进士科。文宗认为“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1]1168。说明文宗也了解进士浮薄之风,但他认为这只是进士群体中的部分现象,不能因此就贸然废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进士科。
武宗即位以后,宰相李德裕秉政,他尤恶进士。根据前代的“故事”,进士及第之后有一系列的章程与宴集,由于其深恶进士浮薄,奏请皆罢,德裕奏曰:
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1]1168-1169
可见李德裕厌恶进士,是由于其互为朋党,过于浮薄,而非因中进士者皆出寒门而敌视。宣宗喜欢读书作文,曾赋诗一句“金步摇”,众臣未能续对。进士温庭筠以“玉跳脱”应对,宣宗十分高兴,“宣皇赏焉,令以甲科处之”[10]50,其文词轻浮,可见一斑。晚唐五代词人牛希济在《贡士论》中宣称:
浮薄之子,递相唱和。名第之中,以只数为上,贱其双数。以甲乙为贵,轻彼两科。题目之间,增其异名。至于傅粉熏香,服饰鞍马之费,多致匪人,成于牧宰。取资货以利轻肥,朋党比周,交游酒食。乱其国政,于斯为盛。[7]8892
可见晚唐进士浮薄,互结朋党,追逐私利,严重扰乱国政,危害深远。唐代进士浮薄之风,无疑是真实存在的,且唐初太宗朝就已初见端倪,历经中、晚唐非但未有减弱的迹象,危害还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故史载:“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1]1169。
二、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原因
唐代进士浮薄既然一直存在,那么探究其浮薄之风产生的原因就显得很有必要,结合相关典籍的史料记载并进行钩沉、梳理,现分析、总结如下:
(一)南朝浮华风气的残留
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堂取士各有侧重,对此唐人杜佑指出:
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梁、陈之间,时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于文帝曰……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2]409-410
唐立国于隋末战乱,隋祚短促,唐朝又距南朝未远,虽李唐皇室出自北朝,但南朝对其影响仍不能忽视。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渊源略论稿》中曾指出隋唐的政治制度渊源有三,其中文化制度方面多来源于东晋与南朝;而南朝尤以梁、陈时期最为突出[11]3,其文辞淫靡、骈俪,其政治文化之虚浮已为众人所熟知。就唐初而言,这种绮丽文风的遗风流韵依然浓郁。为此,陈子昂首举诗文革新的大旗,其针对的目标正是唐初文坛浮薄的不良风气。可见,唐初的进士浮薄与其特有的时代文化背景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二)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流弊
根据《通典》的记载,唐朝初期,进士科主考时务策;武则天统治时期,始重进士科,以杂文和诗赋应试[2]357-358;玄宗天宝年间就有“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2]419之语。考生们为了蟾宫折桂,迎合皇帝的意志,专注于一字一句的音韵格律,而忘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爱民之初衷,因此唐朝的诗歌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进士们也日渐沦为帝王之家专门写诗作赋的御用文人,而缺乏治国安邦之才,唐朝的翰林待诏等也因此得以出现。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12],而据有关研究统计,唐代的应制诗达八百余首,涉及作者两百余人[13],我们清楚地看到应制诗及涉及作者在整个收录诗集所占比例之大,令人惊叹。而且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传唱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并非都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唐代以诗赋取士而造成的进士浮薄是不可轻视的。
(三)进士朋党与朝臣朋党的勾结
朋党流毒遗害于李唐王朝,此前史家多有论及,兹不赘述;然而进士与朋党之关系,尚需作更进一步的考究。进士朋党之事,起于玄宗,当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6]16。此为馆生之间互结朋党,即尚未考中进士之前就已经拉帮结派,奔走于权贵之门,其考中进士之后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中晚唐以后,进士朋党之风盛行,当时进士“多务朋游,驰逐声名……唯追奉宴集,罕肆其业”[8]3976。柳宗元也曾提到:“今夫取科者,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沛焉而有余,吾无有也。不则餍饮食,驰坚良,以欢于朋徒,相贸为资,相易为名,有不诺者,以气排之,吾无有也。不则多筋力,善造请,朝夕屈折于恒人之前,走高门,邀大车,矫笑而伪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14]
更为严重的是,进士朋党与朝臣朋党互为表里,为满足一己之私,而堕坏朝纲。杨虞卿,元和五年(810)进士,“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8]4563杨虞卿与牛党交结,而且掌握科场选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科举的结果,据《新唐书》记载: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1]5249进士与朋党互相勾结,干扰朝政,所以文宗于大和九年(835),贬谪三杨及李宗闵,削弱了牛党与进士朋党的势力。但是武宗之时,此风复炽,“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开成、会昌中,又曰:‘鲁、绍、瑰、蒙,识即命通。’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厚徒’,多轻悔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赋》讥之”[5]378。这里的鲁、绍、瑰、蒙与郑、杨、段、薛分别指郑鲁、杨绍复、段瑰、薛蒙,四人中,杨绍复与薛蒙为大和、开成年间进士,郑鲁与当朝宰相崔铉相善,于是相互结党与李德裕对抗。对于中晚唐的进士朋党问题,金滢坤曾说:“中晚唐举人结为朋甲,相互延誉,干挠视听,无论士族与寒素,还是奥学雄文,凡是驰骋名利,欲谋取科第者,就不能避免受朋甲的影响。”[15]
(四)进士与宦官之相通
唐代的宦官专政之盛不同于东汉与之后的明朝,在于其掌握军权。德宗朝以神策、天威等军设置护军中尉、中护军,且都以宦官担任此职,“宦寺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之死,遂操其手”[16]481。宦官由于控制朝政,对皇帝屡有废立之举,甚至谋弑皇帝,其迎立的新君也多以幼冲皇子为之,以便于窃权乱政。中晚唐以后,宦官掌控仕途,科举进士若想入仕,就不能不谄媚以求。懿宗咸通年间,建州进士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遇见一监军便马上作揖,阿谀奉承之态深受同僚谤议[4]8216。同时出现所谓的“芳林十哲”,更是游幸中贵,干挠主司。由于宦官权势熏天,进士如果想要入朝为官,或为了尽快获得升迁的机会,不可避免地要交好宦官,一些心术不正之士,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宦官的怀抱。如“芳林十哲”之一的秦韬玉,史称其有词藻,工长短歌,却累举不第,后谄附晚唐的权阉田令孜,充当其幕僚,“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17]101浮薄进士依附宦官以求显达,宦官也因此获得了对抗南衙的政治工具,而且借助于进士在文学与社会上的声誉,能够进一步扩充权势,产生有利于宦官的社会舆论氛围。
(五)进士金榜题名的途径
由于唐代进士录取名额少,且极为时人所重,故而士子们趋之若鹜,至死方休。为了得中科第,士子们纷纷奔走于权贵之门,求得社会明贤的举荐以及主司的赏识。其中有自荐者,亦有奔走求谒者,时人谓之“名刺奴”[18]308。当然,也有拉关系,冒充同族、同宗者,极尽承奉拍马、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丑态;又有以退为进,归隐山林,沽名钓誉,求取功名利禄,走“终南捷径”[18]314。此外,由于进士科重诗赋,主司且以此为贤[2]419,故而产生“行卷”之风,即士子们将自己所作的诗文写成卷轴,献给主司求得赏识和推荐,行卷一旦产生,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士子们绞尽脑汁以达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文,权贵世家门庭若市,世风大坏。元人马端临感慨唐人科举“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19]士子们为考取进士已然行事若此,进士浮薄的记载就并非是空穴来风。
(六)进士及第之后的困境
据前文分析,唐代的进士科录取人数屈指可数,中进士者,如果不借助于父祖的门荫,释褐一般才“从九品上”,而且多数情况下需要“守选”三年左右才有机会获得官职[20]的实缺,从基层做起,一时还难以进入权力高层,这与为中进士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完全不成正比。另据美国学者姜士彬研究,认为“由于唐朝的科举制排斥商人等特殊群体,加之其录取的人数远远少于政府每年所需要的新官僚,故而进士及第的士子只能担任非常官卑俸薄的低级官员,只有屡经迁转之后才能掌握要职。”[21]因此,唐代初中进士者大多只享有名誉上的优待,可并不可能立即获得高官厚禄,这对于本以为“登龙门”的进士群体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现实。费冠卿,元和二年(807)进士及第,因所得俸禄不能够赡养亲人,便“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九华”[17]92。古文大师韩愈虽考中进士,但三试博学宏词均告落第,无法入仕,因此他在文章中表达了“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辛酸,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说“以至辱于再三”[22]155,166,深有一种虽中进士却长期无法得官入仕的苦闷之情。由此推测,进士的浮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对现实充满无奈的消极之举。
综上所论,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出现与深化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中晚唐以来,进士与宦官、朋党,甚至与藩镇的交往,都对于其浮薄之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三、唐代进士浮薄之风的影响
封建官僚系统一直以来都是古代王朝进行政治统治的基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唐代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样的辉煌局面,与当时朝堂上的“明君良相”“骨鲠之士”咸集有着莫大的关系。唐初继承并发展隋代科举制度,是为了更多地吸收人才,更好地治理国家,时人看重进士,也是因为考中进士是一种才华与能力的象征,希望进士们能够担负起为朝廷和百姓谋福祉的重任。只是中晚唐以后,进士日渐浮薄,对于唐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首先,进士浮薄造成了唐人对进士、乃至于科举士子群体的厌恶与鄙薄,甚至敌视,最典型的便是李德裕。李德裕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数次为相,政绩斐然。李德裕深恶进士,曾有人劝李德裕参加科举,李德裕不以为然,称“好牛马不入行”[16]489。又如杜牧,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进士,以诗文闻名于世,陈寅恪先生指出杜牧虽以进士擢第,然而“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且推断“其家风固习于浮薄,不同山东礼法旧门”[11]283。又如苏楷,乾宁二年(895)进士,“物论以为滥”,且楷“目不知书,手仅能执笔”[8]800,可见其浮薄之情态。唐人笔记中屡载进士的浮薄行为,如进士杨光远,常“游谒王公之门,干索权豪之族”,时人多鄙之,皆云“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铁甲也”[23]12。正因如此,才有代宗、文宗两朝都有大臣建议废停进士科,但都是因其施行已久,并且以为只是部分现象而未采纳[1]1166-1168。进士结朋党、附宦官、终日游宴咏诗,浮薄之风大兴,深为时人所不耻。
其次,进士浮薄与社会上的浮薄之风沆瀣一气,严重影响了唐代的优良文风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论及唐代进士科与倡伎文学的关系,而且称言“关系密切”,举出孙棨与其《北里志》为一例;又举出韩偓一例,韩偓虽然以忠节著闻,但他的著述《香奁集》内含大量的淫艳之词,“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11]281。不仅是进士,当时整个朝堂都弥漫着浮薄之风,哀帝在天祐二年(905)四月的敕书中承认:“近代浮薄相尚,凌灭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8]791。钱穆先生也认为晚唐以“轻薄”“浮薄”为诟詈朝臣之口头禅,故朱温斥御史大夫赵崇,谓为“轻薄之魁”;李振劝朱温杀朝士,亦以“浮薄”为罪名[16]490,理由便是“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4]8762所致。当时有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等十余人,每逢新春,“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籍草裸行,去其巾帽,欢笑喧呼”[23]27,这种近乎癫狂的行为严重加深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最后,进士浮薄严重损害了中央政权的政治统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唐朝中央政府权威的严重削弱,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朋党、宦官和藩镇,其中进士与朋党、宦官的关联,前文已述,兹不复言;而进士与藩镇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说明。唐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藩镇割据,唐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11]203。它们不仅在政治、军事上与中央政府对抗,其在人才方面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中央政府浮薄进士与朋党、宦官互相勾结,造成政治黑暗,奖惩不公,为了寻求发展,施展抱负,一些进士和士子不得不另谋出路,奔走河朔。同时,藩镇也积极延揽人才,礼贤下士。“诸使辟吏,各自精求,务于得人,将重府望”,使得“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藩镇”[8]3778。韩愈曾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邵南虽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南游河朔。可见董生虽举进士,尤不得志而南奔,韩愈也相信其必能找到合意的归宿[22]。又有李益,“大历四年等进士第,授郑县尉”,然而由于长期不得升迁,“益不得意,北游河朔”,被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8]3771。针对这一现象,陈寅恪先生说,进士不得志者北游河朔是“当日社会之常情”,并不新鲜[11]212。由此可知,当进士们在中央政府受到排挤,或者仕途不顺、抑郁不得志之时,就会选择去河朔地区寻求发展,而藩镇对于这些进士或者士子也予以重用,这样中央政府与割据藩镇的平衡局势慢慢翻转,在中央政府因朋党与宦官互相斗争以致筋疲力尽时,藩镇却得到了长足发展,等到时机成熟,朝官外结藩镇谋诛宦官,藩镇势力入朝,又诛朝臣,“白马之祸”即由于此。唐王朝逐渐成为各地藩镇利用的工具,朱温和李茂贞各欲“挟天子以令诸侯”[4]8676,唐政权也就名存实亡,被藩镇取代只是时间问题。
综括以上所论,虽然科举制在唐代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进士科也的确为政府吸收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在看到进士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各种贡献时,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进士浮薄之风的存在,甚至于唐晚期,进士浮薄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对于唐朝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唐代承东晋、南朝淫靡、骈俪文风之后,唐代初期虽然已出现进士浮薄的迹象,但其时君明臣贤,尚能够辨人识才,及时退黜浮薄之士,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国家统治力的衰退,社会日渐动荡,而且朋党相争、宦官专权,以诗赋取士的流弊日益显现,进士浮薄的幼苗便在这样的土壤下迅速滋长、不断壮大,严重堕坏了社会风气和士民的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刘餗.隋唐嘉话[M].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28.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见闻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 钱易.南部新书[M].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2] 彭定求.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3] 李玲.唐代应制诗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14]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655-656.
[15] 金滢坤.论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87-91.
[16]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7] 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 徐连达.唐代文化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9]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74.
[20]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51-55.
[21] 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M].范兆飞,秦伊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194-195.
[22]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3]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曾贻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