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的历史叙事重构
——浅析胡性能小说《消失的祖父》的叙事策略
农为平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互文互现的对应关系,一定的文学文本总是映照着相应的历史阐释,而且任何历史建构都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叙述者的个人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性能的小说《消失的祖父》正是从一种个人化的视角呈现了一段既波澜壮阔又诡谲沉重的历史风云,从其裂缝中书写小人物随时代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和悲剧命运,折射大时代对普通人命运的裹挟与掌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并没有采用常规的直面历史的叙事方式,而是巧妙借助一种新颖别致的“陌生化”手法,将一段原本已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以另一副“新奇”面貌呈现,既使故事产生引人入胜、曲折生动的艺术感染力,也潜在地达到了借助小说载体回顾并反思历史的深层诉求。
“陌生化”是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认为对于习以为常的存在,人们总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机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方式去把握,而陌生化则是对日常话语以及前在的文学语言的背离,它会不断破坏人们的习惯性反应,使人们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重新调整心理定式,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艺术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事物“陌生化”,正如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说,“作家或艺术家全部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使作品成为具有丰富可感性内容的物质实体,使所描写的事物以迥异于通常我们接受它们的形态出现于作品中,借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延长和增强感受到时值和难度。”在《消失的祖父》一文中,正是由于极为出色的“陌生化”策略和手法的运用,从而使小说在故事讲述、历史构建、文本形态等多方面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审美感受。
一、人物传奇的陌生化处理
语言学家热奈特将文学叙事具体分为三个层次:故事、叙述话语和叙述行为。而故事是其中的基础、出发点,是叙述的目的所在,在小说中尤为重要。《消失的祖父》首先吸引人的一点是讲述了一个曲折而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主人公聂保修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众所周知,对人物传奇的摹写是小说中的一种重要模式,尤其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极为普遍常见,因而如何跳出窠臼,写出新意和特色,自然是这类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在《消失的祖父》中,作者有意设置了一种远距离、散点式的观察人物的叙述方式,使一个原本寻常的战争年代的人物传奇故事,变得扑朔迷离、悬念频频,从而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显示了“陌生化”效果的独特魅力。
先看看主人公聂保修的人生经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青年时代留洋日本,后从昆明陆军讲武堂毕业,之后投身行伍,随远征军赴缅甸抗击日军,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野人山大撤退,负伤回国;二、伤好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战争期间受命潜伏进国军第六十军作特工,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夕随国军残部撤入缅甸,与组织失去联系;三、在缅甸漂泊十余年后冒险越境回国,因无法证明自己地下党身份而锒铛入狱,被关押十多年后释放,在申诉无望及亲人的误解、冷漠中离家出走,从此杳无踪迹。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果按传统的叙述方式来进行讲述,也足以吸引人,但作者大胆摈弃了常规的手法,另辟蹊径,用一种陌生化的手法予以讲述,为读者呈现一种新奇独特的阅读体验。
首先,对主人公一生的叙述并不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或是由熟悉他事迹的人来讲述的,而是由一个对他知之甚少的他者——主人公的孙子来承担的。在叙述语境中,主人公是缺席的,他只是一个被人追述、回忆的不在场当事人。而且不同于一般的祖孙关系,聂保修和孙子之间是隔膜的,他在孙子成长历程中长期缺席,虽然出狱后回到老家与孙子有过极短暂的相处,但孙子对他显然是不了解,二者间也甚少感情。一直到聂保修失踪多年后,已步入中年的孙子出于本能的亲情,才开始了对祖父人生的探寻。因而,不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都是疏离的,他们已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讲述者只能依借自己并不可靠的记忆和祖父残留下来的各种支离破碎的蛛丝马迹,透过重重迷雾去追踪祖父的人生轨迹。这种叙事者的不可靠及叙事本身具有的可疑性,显然使得整个故事在叙述视角上充满了陌生化的特质。
其次,与传统的人物传奇故事有头有尾、环环相扣,并试图全景式呈现人物事迹经历的叙事方式不同,《消失的祖父》采取了散点式的取舍策略,这与叙述者受限制的观察视角正构成逻辑对应关系。祖父戎马半生,漂泊、入狱半生,既享荣耀,又饱尝艰辛耻辱,一生的经历可谓纷繁复杂,若要全部展开叙述,足可敷衍成一部洋洋长篇。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仅有选择性地选取一些重要的事件作为叙述对象,并且有意打乱前后时间顺序,以跳跃式的思维来勾勒祖父的人生轨迹。这从揭示内容主旨的各部分的小标题即可反映出来:
二○一五年:照片;
一九八一年:丹城;
一九八二年:申诉;
一九九九年:寻找;
一九八三年:重逢;
一九五○年:逃离;
一九六六年,回国;
二○一五年:补记。
这种跳跃式、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必然对读者惯有的渐进式线性阅读思维构成阻碍和挑战,造成阅读上的新鲜体验。这就好比玩一个拼图游戏,作者不再按顺序把图片一一呈现出来,而是有意打乱顺序,读者要把错乱的图片按其内在逻辑关系重新进行组合,最终才能获得对图画的完整印象。更何况,作者并没有把所有的图片都显露出来,而是有所取舍,并且有意设置一些悬疑、空白,从而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滋生对人物对情节的好奇心和新奇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陌生化效果。
最后,与上一点相适应,小说既有选择性的以一些主要事迹为重点,以点带面铺陈人物的人生轨迹,同时又有意略去一些关键点,以造成悬疑,使通向真相的路途困难重重,使主人公原本就复杂朦胧的人生再生疑团,从而为聂保修的人生传奇更添神秘色彩。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不仅需理顺前后关系,通过逻辑推理来推测缺失的情节,而且也在无形中被作者所导引,跟随叙事者一起去深入探寻主人公充满谜团的一生。这时,读者实际上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参与者、探访者,与对祖父并不了解多少的叙事主人公一样根据不断显露出来的各种信息去判断、推理、思考,无意识地共同参与到主人公命运的构建上。其中,最大的一个叙事空缺就是祖父当年是否是打入国军队伍里的地下党。对于整篇小说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逻辑关键点;对祖父一生来说,这更是最为至关紧要的事件,因为这决定了他的入狱从政治层面来说是否是冤屈,甚而决定了他后半生所有行为的价值走向。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节,小说中却没有正面提及,仅仅是从侧面提供一些相关事件、情节,让读者自行去拼接、推断。其中包括祖父多年后分别向安青、父亲的口头陈述,他身上携带的当年的上线黄敏文给他写的证明材料,他一次次给有关部门写材料申诉,等等。但另一些材料也不免令人产生疑惑,比如他当年是如何从一名国民党军官转变为中共地下党?其上线黄敏文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潜伏进国民党六十军的任务是什么?云南解放时他为何不选择留下来,而是要随国军撤入缅甸?……再加上作者有意在文中设置一些“迷魂阵”,比如聂保修的孙子在这件事上模棱两可的态度,“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疑祖父如他所说的是潜伏在国军里的地下党。是,或者不是,也许都不太重要了。”通过这些叙事上的“障眼法”,祖父的一生行迹虽然基本上被勾勒出来,但一些关键的局部依然悬而未决,读者最终无法如愿以偿获得全部真相,文本留下了丰富而意味深长的想象空间。
二、叙述视角的陌生化设置
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从戏剧理论角度提出了“间离效果”说:“把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性格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在《消失的祖父》中,对主人公传奇人生的追怀,对过往历史的再现,不是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运用了第一人称这一限制性人称,——而且是他者第一人称,即由恰恰是对聂保修知之甚少的孙辈“我”来进行讲述。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当下与特定历史年代之间的隔膜,消解了人物、历史事件的“前在性”,从而成功设置了人物之间远距离的对话模式,达到了以一种新奇视角进行历史扫描的艺术效果。这种巧妙的叙事人称设置无疑是文本取得的陌生化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来,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人称的使用往往能使叙述事件显得真实具体而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和艺术感染力,而在本篇小说中,这种叙事人称不仅丧失了其固有优势,而且更加深了的故事的陌生感。对“我”而言,从小未曾谋面的祖父仅仅是一个能指符号,既是从大姑妈嘴里听说的那个“聪明、帅气,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抗日英雄,也是被父亲埋怨害了一家人的“反动旧军官”,所以“我”对祖父的认知是遥远、模糊、碎片的;当1981年祖父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第一次见到祖父的“我”,看到的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苍老憔悴的白发老头,和他之间也始终保持着一种疏远关系。主人公跌宕起伏且充满谜团的人生,由对他知之甚少的孙辈来讲述,本身就充满了难以跨越的隔膜。而且,这一叙述行为是从聂保修失踪23年后才开始,也就是说叙述者完全失去了与主人公交流的机会,因而只能依借记忆、相关人员的陈述、一些残留资料,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间接来拼接出聂保修的人生镜像。
在这种不确定叙事中,作者还常常有意加入主观臆测、判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看法,不仅使事件更显扑朔迷离,也进一步加大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比如在上文提及的祖父是否是被安插进国军队伍中的地下党这一核心事件上,祖父自己的陈述,安青的寻访,黄敏文的证明等等,本来已使事件真相趋于明朗,而就在读者以为真相大白之时,叙事者又冷不防地跳出来说:“有迹象表明,祖父当年参加国民党中央军,之后的行伍经历远不像他档案里记录的那样简单,就在祖父失踪后不久,有人曾给家里送来过一笔钱。”还有在去缅甸这件事上,“祖父当年选择离开昆明,跟随国民党残部南逃缅甸时,究竟有多少是组织的安排,又有多少是自己的个人选择,已经不得而知。”这就使得聂保修的行为变得暧昧不明而又无迹可寻。另外,小说利用第一人称的特性,在一些细部将现实与想象、真实与幻觉杂糅起来,营造出一种虚虚实实、似幻似真的氛围,与主人公充满神秘传奇的人生相得益彰。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后,由于祖父及时提供情报,解放军将撤退的国民党部队阻击于云南元江一代,双方在此地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战,多年后,当“我”来到当年的战场,“身穿国军上校军服的祖父在我的大脑里清晰起来,我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了半个世纪前,他穿越这条河谷之后远去的情景。”就在当晚,我睡下后不久,“我看见祖父从窗子外面进来,穿着照片中的那套国民党上校军服,面目慈祥,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那情景更像是我镜中的自己,穿了戎装。我仰躺在床上,望着浮在空中的祖父,他在一点点变小,又一点点靠近。当他缩小到只有两寸照片大小的时候,我感到他像雪花一样,渐渐融入我的身体。”“那一瞬间,我仿佛成了祖父,亲历了1950年跑到缅甸,以及十多年后,从缅甸潜逃回国的情景。”这原本不无梦魇色彩的场景,却因接下来的一句话变得虚实难辨、神秘莫测:“这种灵魂附体的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曾数次发生。”
对于聂保修的人生经历来说,“我”不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而且“我”所获得的信息又主要是通过其他人而得到的,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小说的“陌生化”距离。并且,几个方面汇总起来的与祖父相关的信息是不同甚至互为矛盾的,这些不同的人的叙事既起到互补作用,也使得祖父的形象更为扑朔迷离。“我”的大姑妈是提供祖父正面形象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是祖父几个孩子中唯一对祖父有印象并且在情感上与祖父亲近的人,她话语中的祖父是俊朗的青年才俊、受人景仰的抗日英雄,她以这样的父亲为荣,并乐此不疲地对“我”讲述祖父的辉煌事迹,幸运的是,大姑妈在祖父出事前就病逝了,她得以永远保留对自己父亲的崇敬之情。而“我”父亲对祖父则是另一种态度,他尚未出生祖父就离开家乡上战场了,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具体的父爱,相反,在他成长的岁月里,祖父的存在像一块顽石,一次次阻挡他的前途和人生:考上大学却因为政审不过关而被卡,工作后积极进步,每年都工工整整地递交入党申请书,但由于祖父的影响而发展缓慢,一直到三十八岁才被提拔为文化馆馆长,入党问题,则拖到四十岁才解决,因而不难理解他对自己的父亲更多的是埋怨甚至是怨恨的情绪,他与祖父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对立状态,这也是导致祖父晚年出走的重要原因。安青则是所有叙事者中最重要的一个,她17岁时在战地服务团与祖父相识,爱上了这个右手负伤的帅气的战斗英雄,祖父曾与她在昆明置屋同居了多年,直到被迫撤离。“我”手中保留的祖父唯一的一张照片,祖父生前的诸多秘密,如他中共地下党的身份,他当年如何撤离昆明,他在缅甸九死一生的漂泊经历,他所写的申诉材料内容……这些关系到聂保修命运的重要信息,“我”都是通过安青获得的。应该说,安青的存在,更增添了聂保修人生的传奇色彩,同时,从叙事立场来说,这个人物为“我”的限制性视角开辟了一道通向聂保修人生秘密的便捷途径。
总之,小说既设置了主观性强的第一人称视角,但又通过“我”来回溯、展开另一个他者——聂保修迷雾重重的一生,使得第一人称丧失了自身的优势,“我”和读者一样,对祖父所知甚少,只能借助其他人、其他途径来找寻关于祖父的种种蛛丝马迹,在判断、猜测、臆想中拼接起祖父的人生轨迹。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本能地产生了似幻似真的参与感,在文字的导引下,仿佛随着“我”一起去探寻一个被历史烟尘所遮蔽的神秘人物的人生历程,好奇心、新奇感自然而然被激发出来,进入了一种“陌生化”的境界。不用说,这种“间离”的手法将叙述者、读者皆排斥在主人公的世界之外,他们只能隔着一道道藩篱窥见、猜测聂保修的遭际经历,却无法顺利走进他的人生和内心世界,无法抵达一般文学作品惯常会提供的“真相大白”境界,从而保证了新奇感、陌生感的始终存在。
三、历史叙事的陌生化构建
为更好地达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形式主义倡导者们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尽量取消文本经验的前在性,“瓦解‘常备的反应’,创造一种升华了的意识”,“最终设计出一种新的现实以代替我们已经继承的而且习惯了的(并非是虚构)现实。”《消逝的祖父》虽以人物叙事为中心,但文本同时呈现出一种厚重的历史质感,或者说聂保修复杂跌宕的传奇人生正是依托于纷繁动荡的特定时代才得以发生。小说将人物命运置放到波澜诡谲的宏大历史场景中去展开,既彰显时代洪流裹卷下小人物的身不由己,又从一种私人化的视角建构了独特的解读历史的视角,使一段早已被意识形态所定性的历史呈现出某种引人沉思的诡吊色彩。
从时间维度上看,《消失的祖父》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最动荡复杂的一段历史作为叙事对象:从1937年抗日战争横贯至叙事当下(2015年),时间跨度前后绵延近80年——这样巨大的时间容量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展现并审视历史的视野及诉求野心。小说中具体指涉的历史事件主要有:抗日战争,具体写到滇西抗战,缅北野人山大撤退;国共内战,包括云南和平解放,国民党残部撤入缅甸;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的诸多政治运动。在一部中篇的篇幅内容纳了如此繁复的历史信息量,这是使小说血肉丰满、丰赡充实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负载了阐释历史的重任。当然,由于涉及政治、时代等特殊语境,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对于以上在史书、史料中均有大量详细记载而且广为人知的历史,作者刻意避开与历史的正面遭遇,别出心裁地转换视角,选择从主人公聂保修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生际遇来作侧面呈现,同时也放弃家族叙事、性格叙事等传统叙事立场,一意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建构、观察,从而将人物命运与历史风云紧密勾连起来,尽写处于历史激流中小人物身不由己的沉浮和跌宕,使人物命运尽悉统摄于历史不可捉摸的戏剧性变迁之中。可以说,小说中聂保修及其家人、相关之人的遭际无不是时代使然,他们自身无法挣脱的人生、命运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注脚而已。借助这样的视角与手法,小说在主题命意上达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历史的高度融合,写人即是叙史,二者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给予读者一种新奇、陌生的历史体验感,完成了“一种新的现实”的“设计”。
小说以倒叙手法,在开篇首先营造了一种充满神秘悬疑色彩的氛围:作为小说叙述者的“我”——主人公聂保修的孙子,在一个即将辞旧迎新的岁末寒夜中追想已失踪32年、生死未卜的祖父。在故事尚未正式展开的狭小叙事空间里,作者倒豆子般将一堆陌生信息向读者倾泻而下:失踪,身着国军上校军服的老照片,上线黄敏文,喜欢黄色“懒梳妆”菊花的安青的坟墓,愧疚的父亲,印有上海外滩图像的手提包……对于一无所知的读者而言,这些信息的所指是不明确的,充满着疑问,而它们综合叠加起来明显带有浓厚的旧时代气息,小说的叙事时间指向隐隐闪现。在一堆充满悬疑色彩的疑团面前,读者的好奇心自然而然被调动起来,产生了欲从文本中追寻答案的兴趣。这样,一条进入主人公身世、进入历史的叙事途径就成功地搭建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小说以几个时间、地点、事件上的节点作为线索来串联起祖父时而明朗、时而模糊的一生,而且在排列顺序上并非线性行进,而是打乱的,一会儿是“1981年:丹城”,一会儿是“1999年:寻找”,下一节则“1950年:逃离”,在这种时而当下,时而回忆的混杂叙事中,祖父扑朔迷离的一生通过一些并不连贯的时间和事件片段得以部分呈现。只不过这个呈现的过程始终笼罩着一层面纱,读者只能窥见部分细部,更多的部分则像历史真相一样永远逝去,留下的只有不无沉重的思索和遗憾。而重要的是,祖父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和转折,无不与当时的时代紧密勾连,甚至可以说,他所迈出的每一步关键步伐,都是为时代大潮所驱动:在清末民初的留学大潮中赴日学习,在军阀混战的乱世进入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因抗战爆发而奔赴战场,在国共纷争时作为地下党打入敌军内部,反右运动中因身份不明入狱……祖父波澜起伏的一生实则正是那段纷繁动荡历史的真实写照,作者欲借人物传奇来重构历史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
纵观聂保修的一生,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精忠报国的人生追求。他前半生戎马沙场、舍家为国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履历,不论是从价值评判还是道德评判的角度,都可称得上是一个大义凛然的时代英雄。然而,历史却与他开了一个荒诞的玩笑。宁聂保修九死一生、忍辱负重,最终赢得的不是鲜花、掌声、功勋、奖章,而是异国漂泊、锒铛入狱,后半生一直顶着“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在古稀之年凄凉地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家人也因为他的历史问题饱受牵连:母亲、妻子先后自杀,儿子因他而在上大学、提拔、入党等人生大事上受阻,不仅将他视为路人,还从心里怨恨他,不正常的家庭氛围又造成孙子人生、心理上的失格……亚里士多德以艺术是对人生的模仿的观念入手,第一个提出了悲剧的定义,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称“悲剧是人生中的可怕事物”。在乖戾无常的时代面前,聂保修及其家人的命运注定了是一出他们无法选择也无法挣脱的时代悲剧,而同时,他们的人生遭际也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时代的凛冽寒光。
有几个细节尤其耐人寻味。1966年,聂保修在大批国民党残部撤回台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穿过国境线回国,四处寻找当年介绍他入党的上线黄敏文——黄是唯一能证明他地下党身份的人。但当时国内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运动,讽刺的是,黄敏文早已被划为右派而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当聂保修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他时,在这个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终于与自己的上线再次见面了,祖父拉着黄敏文的手,激动得想哭,可黄敏文却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祖父。得到消息的农场场长赶了过来,用鹰一样的眼光审视着祖父和黄敏文。场长问黄敏文:‘你认识他?’黄敏文盯住祖父望了又望,摇摇头说:‘不认识!’”于是,聂保修就成了一个国民党的反动军官被投入监狱。多年后,黄敏文的右派帽子被摘除,释放之日前去探望聂保修,“面对祖父的质问,黄敏文沉默长久之后,承认自己认识祖父”,他后来还专门写了证明聂保修身份的材料交给组织,聂保修也以此为据一次次写申诉材料,但都如石沉大海。“那一段时期,全国都在落实政策,那些此前几十年走背运的人迎来了一个人生的小阳春。只有祖父例外。”平反的无望,亲人的冷漠,最终,无路可走的聂保修只能离家出走——这样的选择显然与他早年热血慷慨的形象更相符。叶歌苓在《陆犯焉识》中也设置了一个类似的结尾,但陆焉识的去向是明确的,而且他身边还有笃爱他的冯婉如相伴,多少有一抹暖色调,而祖父是真正的孑然一身,不知所踪。这个不无残酷的结局将聂保修的人生悲剧推向了极致,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也升华到了一个令人沉重的高度。
与聂保修的悲剧命运相映照,小说中还安插了一个似乎与故事关联不大的情节:身为历史教师的“我”曾去采访一个叫李茂的抗战老兵,但老人三缄其口,当“我”为了消除他的顾虑说“您是打小日本的,是抗日英雄”时,95岁高龄的老兵放声嚎啕大哭,“‘我不该参加国军抗日!’老人说,他的眼泪顺着满是沟壑的脸慢慢地往下流淌。”后来“我”才知道,抗战胜利以后,李茂,这个曾经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因为历史原因三次被判刑,一共在狱中度过了二十六个春夏秋冬。是什么令历史蒙尘?是什么让聂保修、李茂这些曾为民族命运而以命相搏的人遭受命运屈辱的戏弄?行笔至此,小说的用意已经不仅是要探寻某一个人飘忽的踪迹,讲述一个传奇故事,而是努力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一个已经远去的特殊群体的过往——哪怕只是支离破碎、只言片语的残留,哪怕只是一些模糊的身影——透过他们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这潜埋于文字下的深沉诉求,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厚重的历史质地,充分显示了作家鲜明的历史责任感和难能可贵的历史求索意识。
“祖父颠沛流离,辗转一生,最后概括为短短的几行履历,就像一根吃剩的齿刺不全的鱼骨头。仅凭这个残损的鱼骨,我们无法想象这条鱼活着的时候,它身体的流线、完整而闪耀着光泽的鳞片,更何谈它曾游过的江河、寄身的水草、经历过的炽热或寒冷的岁月。”作者在结尾处不无感慨地如此写道。聂保修们残破不全的人生,充满了历史不可捉摸的戏剧性和时代荒诞色彩。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形式主义主张陌生化,是为了将读者的注意力引至文本即“文学性”本身,而《消失的祖父》中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却是反其途而行之,很显然,它欲令读者关注的是一段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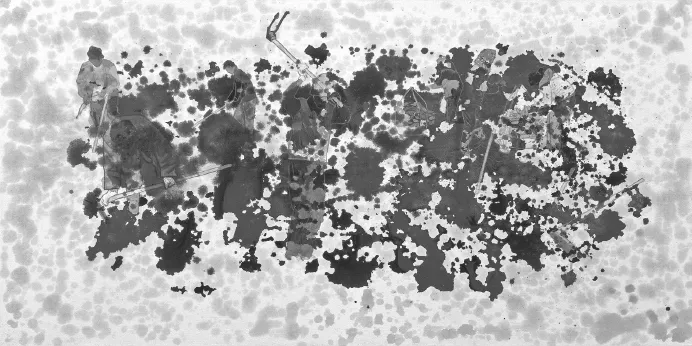
陈玲洁 冬至 布面丙烯 2015年
【注释】
[1] 登载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4期。本文所引例文,均出于此处。
[2] 转引自张冰《陌生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3] 张黎编,《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4页。
[4] 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翟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61~62页。
[5]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8页。
[6]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
【参考文献】
〔1〕 张冰:《陌生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3〕 方珊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
〔4〕 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