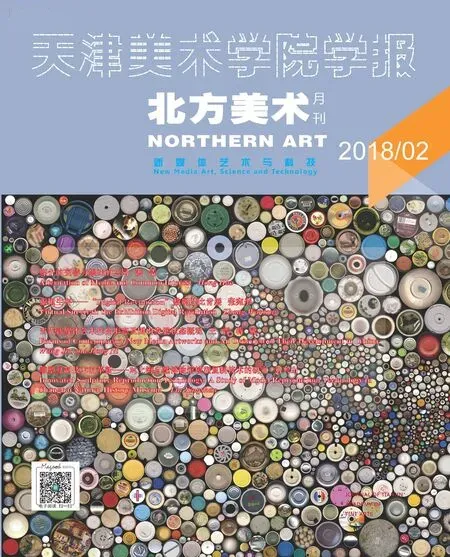文化记忆视角下木版年画技艺传承
邵卉芳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集团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非遗”中饱含历史文化记忆的诸多信息,因此“非遗”归根结底保存和保护的是“技艺”与“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纲领》强调了文化记忆的重要性:“记忆对创造力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对个人和各民族都极为重要。各民族在他们的遗产中发现了自然和文化的遗产,有形和无形的遗产,这是找到他们自身和灵感源泉的钥匙。”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所含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人记忆的基本特征,加之该记忆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笔者坚持认为,深入的“非遗”文化记忆研究非常必要。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凤翔木版年画为视点,结合文化记忆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一、木版年画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
“文化记忆”概念首先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仪式和文本是文化记忆传承的两个重要载体,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并列而被看作“集体记忆”的下位概念。集体记忆源自于法国的社会年鉴学派,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则被公认为是集体记忆的首倡者。哈布瓦赫这样描述集体记忆:“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①他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②。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区别于历史和“传统”,③他强调集体记忆的变迁特征而忽略了集体记忆的连续性和传承特征。正是看到了哈布瓦赫的这一理论缺陷,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提出了“社会记忆”概念,并从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两个角度强调了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很好地论述了记忆的连续性和传承性,他的社会记忆理论关注了权力的作用且探讨了人们对权力影响下的社会记忆的接受。他认为,我们对于现在世界的体验和认识深受我们所掌握的过去知识的影响,这就是文化的连续性,它使我们在一个与过去事件和事物有因果关系的脉络中体验和认识现存世界。不过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侧重于讨论政治层面的社会记忆,而忽视了其他大量存在于民间的社会记忆现象,这就为笔者从民间木版年画视角考察记忆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一个民族或族群的记忆与该民族或族群的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作为传统文化的独特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记忆。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人类记忆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有些内容被记忆,有些内容则被忘却,或者可以说,记忆容易被忘记或忽视。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就是对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基因和文化记忆的传承和保护。也可以说,“非遗”项目中保护的其实就是“记忆”,既有“物质上的记忆”也有“身体上的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技艺”,又是“记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涵盖的内容有: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凤翔木版年画于2006年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表面上看来,木版年画隶属于手工技艺类“非遗”,但因其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密切联系,故可从节日遗产和仪式的视角进行解读。又因“节日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④,“节日本身就已带有强烈的历史意义,担当着文化记忆载体与媒体的功能”,⑤故这里将木版年画这一年节符号与文化记忆理论联系起来似乎又显得顺理成章。
凤翔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关于其起源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说起源于唐宋,有的说起源于明代,但对其繁盛年代的认识比较统一,基本认为木版年画印制、销售和使用是在清代走向兴盛。凤翔木版年画采用彩印与手绘相结合的印制方法,色彩主要以红、绿、黄、紫为主,线条刚劲有力,造型夸张,题材以人物为主,花鸟虫鱼为辅。题材方面,凤翔木版年画有表现民间神话故事的,如《封神演义》《白蛇传》《西游记》等;有表现历史故事的,如《三国演义》等;还有专门表现当地戏曲秦腔的戏文画,如《狮子洞》《水淹金山寺》及《求真经》等。其中表现完整人物故事的,多以墙画的形式出现,如《西游记》(36幅)和《白蛇传》(1套)等。凤翔木版年画便是通过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古典小说、地方戏曲等故事画面的描述和记载,很好地将文化记忆记述和传承了下来。因为“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 ”⑥。在传统社会里,每年到了祭祀、谷雨和年节时分,人们便会选择相应的年画张贴,尤其是年节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张贴门神。“大小门神多画历史人物,如商代的方弼、方相,唐代的秦琼、敬德、魏征、盖苏文,宋代的包拯,还有神话人物如天官、三星、刘海、钟馗等。……中型墙画有历史、戏曲小说人物故事、民间传说、风俗、花鸟、草虫、走兽等三百余种。”⑦长辈手指着门神和墙画,向晚辈讲述画中的人物和故事,木版年画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对晚辈尤其是儿童进行着历史文化记忆的熏陶,关中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色彩方面,喜用红色,这与凤翔的地理位置有关,其地处关中平原,古称“雍”,是周秦发祥地。《礼记》曰:“夏后氏尚黑,牲用玄。周人尚赤,牲用骍。”另据文献记载,秦人尚黑尚红,红色代表秦人的刚烈与正义。因此说凤翔木版年画的用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历史文化记忆的呈现。因此说,“凤翔木版年画不仅是很好的艺术作品,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文化风貌的珍贵资料”⑧。
另外,凤翔木版年画还有对现代历史记忆的描述,最为人们熟知的是《白朗过秦川》,这幅画描述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第三年,白朗响应孙中山、黄兴发起的“二次革命”号召,率领农民起义军继续同袁世凯做斗争,坚决反对封建卖国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的阴谋。但是,《白朗过秦川》这幅木版年画上呈现出来的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事实”:该墙画高约二十六厘米, 画中是两支武装激战争城,城上官兵用火炮向城下轰击,督战者是清朝老官吏,其身后站立一位着洋服的谋士,城下大军云集,气度非凡的农民军“白元帅”骑在马上,其带领的士兵气意高扬,画面情景预兆了他们攻无不克的胜利前景。而实际的历史事实却是:白朗军抵凤翔时,驻凤翔的甘肃四军统领崔正午早已弃城鼠窜,起义军也置府城于不顾绕城而过,后奔袭千阳、陇县,驱进陇西。然而木版年画的绘制者偏偏要“杜撰”两军正面对杀的攻守戏剧。年画作者可谓发挥了绘画艺术的特长,从而歌颂了起义军的勇武,鞭笞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阴谋。这里便典型地表现出记忆的选择性,年画绘制者选择了“杜撰的记忆”或曰“人民群众期望的记忆”,而没有选择“历史事实的记忆”。

贴在门上的年画(门神)
二、木版年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
木版年画是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美术形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传统年节中,家家户户门上贴的几乎全是木版年画,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胶印年画方才逐渐取代木版年画。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及以冯骥才为首的年画普查运动的推进,历史上的木版年画产地又开始红红火火地生产起了早已不再张贴的木版年画。较为著名的年画产地有河南开封朱仙镇、河北武强、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陕西凤翔、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等地。
统观凤翔木版年画的整个发展历程,有兴盛也有衰落,有欢乐也有沮丧,兴衰成败无不对当时当世的历史事件、民风民俗、时代观点等进行了记录,可以说,这些记录本身就是木版年画对文化记忆呈现的重要方式。换句话说,凤翔木版年画的发展变迁过程就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再现,也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记录和反映。譬如,传统年画中的《岳飞传》《精忠报国》《包文丞》等记录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岳飞保卫祖国的故事,宋代清官包拯秉公断案的故事;《女十忙》《男十忙》则表现了男耕女织、捕鱼打猎的农家生活的恬淡美好;新年画中的《丰衣足食》《兄妹开荒》《纺线线》表现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搞生产的喜庆场面;《男女都一样》《娃娃少而康》则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年画制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响应;还有世兴局创制的讽刺年画《爱钱钻钱眼》《东头吹胀西头捏消》《扶上杆儿掇梯子》《见了旋风竟作揖》等,这些年画形象鲜明,语言通俗,揭露了时代弊病,起到了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作用。另外,已在有关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新木版年画作品《再想想》《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羊乖乖》《我爱小花鹿》《雏食图》《人欢马叫》《和平友好》等,也都是时代风貌的真实再现。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通过木版年画认识了守护宅院的秦琼和敬德,认识了精忠报国的岳飞,认识了秉公为民的包拯,也是通过木版年画了解了代代承传的神话故事,学会了中华民族勤俭持家、智慧勇敢的民族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总之,可以说凤翔木版年画是延续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传统文化符号之一。通过对凤翔木版年画的实地调查得知,木版年画的民俗背景已经不复存在,笔者认为,民俗背景不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记忆链的断裂,关于记忆链断裂的问题,笔者将另行文论述。
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面临着人亡艺绝的濒危境遇。历史上的凤翔木版年画生产确出现过繁盛时期,“清末民初时凤翔年画逐渐发展提高,从光绪十年(1893年)到1929年, 三村从事年画生产者发展到六七十家,其中南肖里的世兴画局、忠兴画局、树德画局,北肖里的复胜画局、兴盛画局、新盛画局,陈村镇的张记、李记画局等都具一定规模”⑨。但到了近代,凤翔木版年画与全国其他产地的木版年画一样走过了起起伏伏的道路,直到21世纪初冯骥才倡导的年画普查运动的到来,凤翔木版年画方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经过十几年的普查、保护、研究和展演,很多产地的木版年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称之为“裂变”——木版年画由年节的民间消耗品摇身一变而成为高贵珍稀的艺术收藏品、纪念品和礼品。尽管单幅木版年画的市场价格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木版年画从业者尤其是绘制者却越来越少,原本制作凤翔木版年画的艺人们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蹲守在家中做年画。历史上的南肖里村是家家会丹青,“南肖里村娃娃一丁丁,自小就会画‘门神'”的民谣便是明证。但现在的南肖里村跟其他普通村子别无二致,只在邰江平家里能见到木版年画的制作,邰江平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终止年画制作,他的爱人和儿子会在空闲时印画,儿子邰伟同时负责凤翔县的木版年画传习所,作为凤翔木版年画制作者中为数不多的80后,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年画的制作和销售事业中来。另一位传承人邰立平致力于凤翔木版年画的印制,算得上是当地年画艺人里销售业绩最好的一个。邰立平也曾为木版年画的继续人问题殚精竭虑,他曾在宝鸡招收了6名徒弟,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2名,且把木版年画制作当作业余爱好,一个卖扯面,一个在工厂上班。邰立平的子女中,目前只有小女儿从事木版年画相关行业,凤翔木版年画昔日的繁荣不复存在。
凤翔木版年画和全国其他产地的木版年画一样,都不能恢复历史上的繁盛场景,究其根本,是因为木版年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社会中适合木版年画生存的土壤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筑格局变了——传统木版年画无处张贴,审美习惯变了——朴拙的木版年画不再好看,消费观念变了——胶印年画取代了木版年画。上述各种变化导致木版年画传承的记忆链发生断裂,尽管如此,凤翔木版年画并没有因土壤变化而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经历了1929年到1932年的关中自然灾害,经历了1938年到1949年的连年战争,经历了“文革”被界定为“迷信品”的打压,经历了胶印年画的巨大冲击,凤翔木版年画曾多次面临奄奄一息的濒危境遇,但凭着民间年画艺人的执着坚守,凭着王宁宇、张仃、王树村等年画研究者的大力支持,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凤翔木版年画终于在南肖里村迎来了它最后十年的辉煌,正是那时,一向不为人知的凤翔木版年画进入了学者和外地游客的视线。直到今天,邰氏家族的后人们仍秉持着这份执着,传统年画样子依然年复一年地印制,与此同时反映新时代新风俗的新年画也一幅接一幅地问世。传统文化记忆的承传虽然遇到了障碍,出现过断裂,但新年画的问世却以现代文化记忆的方式做了相应补充。

年画艺人邰江平的家

木版印刷年画
笔者认为,凤翔木版年画要想在不太景气的现代社会里得到有效传承,需要在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两个层面上寻找路径。根据保罗·康纳顿的理论,体化实践通过亲身在场参与具体活动来传达信息,刻写实践则通过记录来捕捉和保存信息。⑩他指出,体化实践的特别记忆效果依赖于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它们的获得方式,影响体化实践的因素——习惯不仅仅是一种符号,而且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⑪凤翔木版年画制作技艺本身比较复杂,学习起来不那么容易,尤其需要耐心和定力。制作技艺的传承其实就是体化实践的典型表现,而木版年画画面内容(包括图像和文字)的传承则是刻写实践的表现。体化实践层面的传承,需要有兴趣有耐心有担当的年轻人的积极加入,刻写实践方面的传承需要具有创作才能的专业人士的鼎力支持。
三、木版年画的开发利用与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要为其所在地民众及其他地域的民众服务的一种文化资源,“非遗”的价值是要在为人类所利用的过程当中实现的。对负责“非遗”管理的政府部门而言,在做“非遗”保护的工作中不可武断地拒绝商业旅游。旅游的重要分支“遗产旅游”在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状态中诞生了,但目前的发展现状是,旅游在给“非遗”所在地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不少负面作用,如生态的破坏、空气的污染和治安的压力等。但笔者认为,不能因为遗产旅游产生的负面作用而对其完全否定,凤翔木版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完全可以在做好传承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得到良好的开发利用,因此,处理好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关系十分紧要。
(一)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前提
对木版年画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一切形式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之上。这里特别强调研究保护的重要性,学界对木版年画的研究,就是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形式。1977年,王宁宇作为陕西省轻工业局下属的工艺美术公司的干部,来到凤翔县南肖里村邰立平的家中,鼓励邰立平父子搜集传统年画资料以恢复邰氏家族的木版年画制作技艺。后来,国内外学者的先后到访以及众多高校师生的采风和教学实践基地的设立,尤其是冯骥才倡导的年画普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以及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大力推进等,这些来自学界的鼓励、研究和帮助,无疑对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除了研究保护之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对其进行资料性的保护。但“非遗”的保护研究不只是记录和整理,以往对“非遗”的保护多局限在记录与整理层面,在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观念并不太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研究必须超越传统的记录和整理,将口述史等记忆资料存档并不等同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只堆积资料而缺少甄别筛选环节,缺乏感情与历史的投入,就很难搞清楚其与当下的联系。
对于凤翔木版年画这种手工技艺类的“非遗”,除了上述提到的研究保护、资料整理保护之外,最为紧要的恐怕还必须进行生产性保护。笔者认为,生产性保护模式比较适合木版年画,因木版年画在传统社会中本就是年节消耗品,其本质就是消费品,木版年画作坊赶在春节前加班加点大量生产年画,其目的就是获得更多更高的利润,这是无可厚非的。现代社会里,木版年画虽然失去了昔日的民俗背景,但将其看作消费品,创新后进行生产销售,理论上是可以找到一定市场的。事实上,收藏市场已经对木版年画伸出了橄榄枝。

年画创新样式:兵马俑
(二)适度进行旅游开发
对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当地民众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但是近年来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因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收益,或可看作是当地民众的权利。一直以来,学界对“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持不同意见,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笔者认为,“非遗”的保护与开发(主要为旅游开发)完全可以做到相得益彰,“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旅游开发离不开“非遗”。“非遗”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没有“非遗”的旅游便缺少了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其次“非遗”离不开旅游开发。旅游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在很多“非遗”产地已得到证实。当今社会,“非遗”通过与旅游消费的结合,逐渐以商品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正是借助于现代商品包装的手段,“非遗”方能得到大众的认识和认可,逐渐靠近甚至是走上“流行”文化的方向。“人们对遗产的追逐是因为他们想去寻找与‘后现代支离破碎'生活的相同之处。”“非遗”是一个社会或民族文化记忆的象征。游客可以通过“非遗”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等,加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另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非遗”看作是其所在社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非遗”已被各地政府利用和开发。
1.重视传承主体
凤翔木版年画的记忆传承离不开对传承主体的重视,一方面,传承主体需要主动提高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意识,在凤翔木版年画这项“非遗”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方面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在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为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考虑到传承主体⑫的重要性和应得收益,应给予传承主体一定的经济分红。前述为传承主体的狭义解读,广义层面上的传承主体,还可以将木版年画的保护者、研究者和收藏者等包括在内。一般而言,保护者多为“非遗”项目的申报单位或个人,这类主体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保护主体在做“非遗”项目的宣传、策划、展销等工作时,不妨适当引入记忆理论,多从记忆角度进行探讨,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大量重要的文化记忆,记忆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研究者可以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为凤翔木版年画的有效开发提供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理论指导。总的来讲,笔者强调将传承主体单列出来加以强调,就是要打破以往非遗保护传承见物不见人的屏障。在年画的旅游开发中,同样要重视传承主体的存在和作用,要从生活和生命视角层面深挖,做有深度的旅游规划。
2.平衡权利与义务关系
与其他旅游开发成熟的地区相比,陕西凤翔旅游开发的意识相对薄弱:规模小、项目少、文化体验游不多、游客参与度不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旅游开发中的运用还有待加强。但目前的发展现状是,旅游在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从根源上来说,负面影响的产生就是旅游参与者主体没有处理好相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如果各个主体能从理念上深刻认识到自身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承担的义务,那么“非遗”旅游开发的负面影响将会逐渐减少。具体到凤翔木版年画的旅游开发,就是要处理好旅游公司、政府部门及年画艺人等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
3.培养文化时尚
凤翔木版年画目前的传承面临危机,多数木版年画用于研究和收藏,其消费品的本质特征不再凸显,缺乏受众和市场。如何扭转这一传承危机,是凤翔木版年画从业者应该直面的重要问题。笔者以为,培养文化时尚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让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找到重生之路,就要在年轻人中寻找合适的受众,就要使木版年画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文化艺术品,就要使木版年画及其衍生品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对象。要想使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像日韩文化时尚一样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就要在文化产品创新上下功夫,就要找到木版年画这些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年画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与诉求,反映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审美习惯。新年画和年画衍生品的设计和生产,也应该把广大民众的期望、诉求及审美习惯考虑在内,甚至是放在首位。
余论
凤翔木版年画不仅是凤翔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民间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花园中的重要一簇,它凝聚着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由于凤翔木版年画题材内容广泛地取材于民间百姓的真实生活,年画艺人大量地运用写实手法进行创作,使得木版年画成为关中历史珍贵的风情画卷,成为关中历史民俗记录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凤翔木版年画是对关中文化的高度概括,是记录关中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手工技艺类“非遗”明显属于“技艺”的传承范畴,其实此类“非遗”在进行“物质技艺”传承的同时也发生着“身体记忆”的传承,身体记忆具有主体间性和复合型双重特征。⑬陕西凤翔木版年画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表面上可看作传统手工技艺类的“技艺”传承,但其背后却蕴含着较为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传承。凤翔木版年画画面内容丰富多彩,有历史人物、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这些均是民族记忆的承载体,对木版年画这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本质上就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传承,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
“研究、搜救、颂扬集体记忆不再是在事件中,而是指在经年累月中,寻找这种记忆也不再是在文本中,而是在话语、图像、手势、仪式和节日中,这是历史视角的一种转换。广大公众也参与了这种转换,这是害怕失去记忆、害怕集体记忆缺失情况下的一种转换。‘怀旧'是害怕失去记忆、害怕集体记忆缺失的一种拙劣的表现,且被记忆商贩无耻地加以利用,记忆变成了消费社会的消费品之一,而且销售势头良好。”⑭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显然对将集体记忆消费品化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但事实上,我国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因此成为各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和消费品,商人们对“非遗”商品的生产销售乐此不疲。其实木版年画这些“非遗”中,也有很多已经变成了消费品,在变成了消费品以后,很多“非遗”才有了发展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并不能否认其消费性。因木版年画在传统社会里本身就是消费品。那么有个问题值得思考:如何看待文化记忆变成消费品这种现象?笔者以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留住传统以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是为了合理地利用传统,让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于现代生活。
注释:
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②同上,第24页。
③哈布瓦赫把那些有组织的、被客体化的回忆形式称为“传统”。
④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1页。
⑤同上,第44页。
⑥同上,第41—42页。
⑦邰怡:《凤翔木版年画见闻记》,《美术研究》,1985年第2期,第73页。
⑧党天才:《凤翔木版年画论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97页。
⑨同⑦。
⑩[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⑪同上,第40页。
⑫这里特指传承人一类的传承主体。
⑬邵卉芳:《记忆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87页。
⑭[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说明:文中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山西木版年画展在山西美术馆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