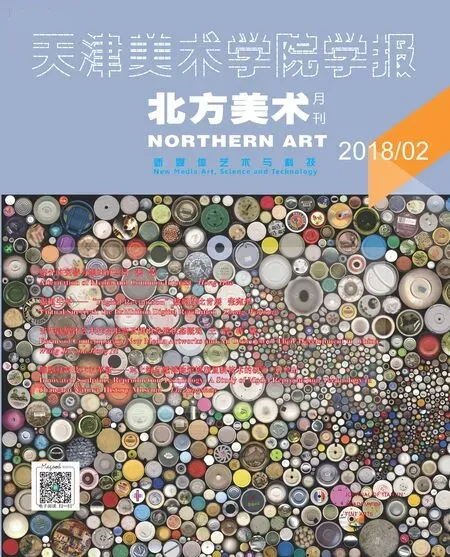早期西方影像艺术语言述略
——兼谈艺术家的影像记录与表达
祁 震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二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在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开始了对旧有规则的反思,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向多元化发展,这也必然导致了艺术创作的多元化。这一时期,欧美艺术正在向观念靠拢,观念逐渐成为艺术的核心,而作品的观念又都体现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之中。正是影像所具有的独特的记录过程的功能,使影像在这个由现代主义艺术向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过渡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像艺术的早期语言的形成就是艺术家们在记录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艺术家使用影像媒介由自发变成了自觉,影像语言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它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类型:艺术行为的主观记录、身体本能实验的记录、艺术家工作室中的影像表达、带有自我意识的影像叙事、艺术家的影像日记。在这些影像语言的形成中,记录,是艺术家所使用的影像的最基本功能,在客观的记录中夹杂着叙事,而在叙事中又隐含着表达。
一、艺术行为的主观记录
艺术家行为留下的痕迹或行为本身都在事先被艺术家认真地思考,在创作中,艺术家用影像去拍摄整个过程,拍摄地点被反复测量,拍摄角度被反复试验。当艺术家按下快门,摄影机就开始工作,开始记录镜头前所发生的一切。因此,艺术家在使用摄影机拍摄他们的行为作品时,所使用的正是影像的记录功能,这种记录功能在反复实验中逐渐成为一种创作语言。
1969年,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电视台与八位艺术家合作制作了一个系列节目,取名为“大地艺术”,节目播放的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作品《10英里的直线行走》(图1)中,作者首先展示了一张他将要行走区域的地图(地点位于英国的达特摩尔),然后,画面转换到现实场景,一片广阔荒芜的开阔地,艺术家在远处,就像一个黑点一样,摄影机镜头慢慢推近,推近的速度等同于艺术家向前行走的速度。然后艺术家再反向往回走,摄影机再以相同的速度拉远镜头,缩小画面。背景声音是艺术家行走的步伐声和他的喘气声音。理查德·朗的艺术是在行走中完成的,过程是被摄影机客观记录下来的,作品结果的再现是通过电视信号传播到四面八方的。
同类型的作品还有,瓦尔特·德·马里亚(Walter De Maria)的作品《沙漠中的两条线,三个圆》(图2)。就像作品题目表明的,艺术家在美国加州的沙漠中画了两条直线和三个“圆形”,但“圆形”并不是在地上画的圆形,而是镜头进行了三次360°的旋转,这是真实图形与影像拍摄(记录)技巧的巧妙结合。艺术家把摄影机固定在两条平行线中间,画面中艺术家开始沿着平行线朝远方行走,然后镜头从左向右开始慢慢旋转,每当镜头回到起点,观众都可以看到艺术家在两条平行线中间越走越远,当镜头旋转最后一圈的时候,艺术家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严格地把动态、时间过程和空间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传统透视方法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将自己的身体消失在自己建构的透视图里面。

图1 理查德·朗 10 英里的直线行走 1969年
由于当时艺术家考虑到影像在大众媒体中传播的广泛性,所以他们在记录自己行为的时候认真考虑了如何能让观众更清楚地了解作品,因此在使用影像记录功能时,他们自觉地去选择最佳的拍摄角度、位置和光线,甚至可以说摄像机代替了观众的视角,参与到了艺术家的行为中。所以,这一类型的影像不应该再被看作是艺术行为的副本,也不仅仅是一种关于行为的视觉和声音的传达。他们使用影像媒介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状态,带有艺术家强烈的主观色彩,他们所使用的影像的记录形式则成为一种艺术化的表达“语言”。
二、两种艺术家工作室行为的影像记录语言
人的身体一直是艺术家创作实践的重要再现对象,这里有艺术家可以比较方便地观察自己身体的原因,也有艺术家自我反省、自我证明与自我肯定等心理因素。艺术家的身体在这些艺术实践中充当工具、媒介、材料等不同角色,而影像艺术的早期形态则是作为以上这些艺术实践的记录工具才进入到艺术领域的,影像与艺术家的身体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关联。影像艺术语言中的“记录语言”逐渐走向成熟,并在艺术家的工作室中发展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1.身体本能实验的记录

图2 瓦尔特·德·马里亚 沙漠中的两条线,三个圆 1969年
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开始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创作媒材来使用,他们把身体当作感知器官,当作动作的主导,当作性别和身份的携带者,还当作心理活动的表达载体。艺术家的这些用身体进行的艺术探索经常触及人类肉体和精神所能够承受的底线,身体的疼痛与扭曲往往能够带来对伦理和道德的挑战。他(她)们做着各种挑战身体机能的实验。20世纪60年代末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在他的工作室中就做了大量的身体行为实验,而且都是使用影像来作为记录工具。如《工作室中的压力行为》《颠倒的旋转》《调好琴弦的小提琴D.E.A.D.》《在一个正方形边界以夸张的方式行走》等作品,都是瑙曼一个人在工作室完成的。在实施这些艺术行为的时候,没有观众,也没有助手,因为瑙曼的行为影像记录不需要有人来操控,他经常是架好摄像机,按下拍摄按钮,他就可以走到摄像机前去表演。瑙曼为了使他的影像比单纯的行为视觉记录走得更远,经常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拍摄方式,或者把摄像机的拍摄功能使用到极限,就像他自己说的:“摄像机经常被我旋转90度来拍摄,甚至整个颠倒过来,或者我干脆使用一个广角镜头,这样可以把影像画面拍得扭曲变形。”①瑙曼在拍摄《调好琴弦的小提琴D.E.A.D.》时,他根本不会拉小提琴,但是他有10分钟的带子可以使用,即使他在第7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感觉累了,但瑙曼就一直坚持快速重复一个简单的演奏动作直到录像带结束。
布鲁斯·瑙曼以及当时的一大批艺术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做着类似的行为实验,如维托·阿孔西(Vito Acconci)、德尼·奥芬海姆(Denis Oppenheim)、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克里斯·博登(Chris Burden)等艺术家。摄像机好像一台监视艺术家行为的机器,记录着艺术家们重复做着的相同动作,直到身体承受的极限或者拍摄的录像带结束时才停下来,但是身体动作本身的含义在重复中慢慢消解掉了。正如弗朗索瓦·帕尔费所说的:“早期艺术家工作室的行为包含三个层次的消解:一个是艺术家身体体力的消解;一个是影像载体(录像带)的消解;另一个是动作含义的消解。”②艺术家把影像介入到他们的挑战身体本能与极限的实验中,把影像记录的语言推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即艺术家身体本能实验的影像记录。摄像机代替了观众的“在场”,在艺术家进行实验的时候客观地记录下全过程。艺术家们就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重复着自己的动作,专注而持久,动作在这种机械的重复过程中不再具有更多的指向性含义,而是一种接近舞蹈般的肢体语言,具有一种神秘的仪式感。

图3 维托·阿孔西 主题曲 黑白,有声,33分15秒 1973年
2.艺术家工作室中的影像表达
影像记录语言在艺术家工作室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记录艺术家在工作室中的自我表达,艺术家通过影像表达他们当时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艺术家的这种自我表达也具有一定的行为性,但是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作为身体本能实验的记录语言。在这种影像语言中摄像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观众对影像的审美活动也不是单纯的观看了。
维托·阿孔西在他的创作中总是把摄像机想象成未来的观众,在影像中让自己与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把自己的性幻想与观众的性幻想相融合。阿孔西的作品《主题曲》(图3)中使用影像试图与观众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直接与观众进行交谈。他躺在自家的客厅里,头部靠近摄像机,眼睛直视镜头,脚下是一个沙发,阿孔西点上一支烟,跟随着背景音乐暧昧地唱了起来。但是他改变了原歌曲的歌词,把歌词变成了邀请观众进入他的私密空间:“我不能看到你的脸,我不知道你看起来像谁,你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但总会有人看着我。有谁愿意来靠近我……来吧,我独自一人,我会跟你说实话……”阿孔西一个人在工作室中面对摄像机,想象着摄像机镜头背后存在着观众,试图与将来观看影像的观众进行交流,向其表达着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交流。当观众看到这个影像时,观众就与阿孔西相互对视了。
艺术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观众有一种现场参与其行为的感觉,观众面对影像中的艺术家时就产生一种与艺术家现场对话的感觉,这并不是观众走进了影像,而是影像里的艺术家走出了影像,在展厅中“出场”了。阿孔西以后的艺术家也在工作室中进行影像自我表达的实验。他们使用的都是影像的记录语言,但是把记录语言提升到了一个心理学和美学的层面,摄像机不再是一个冰冷的物体,而是一个可以倾听艺术家诉说的“人”,而影像也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客体,而是一个艺术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窗口和工具。

图4 皮皮洛蒂·莉斯特 我不是那个有太多牵挂的女孩 彩色,有声,4分30秒 1986年
三、带有自我意识的影像叙事
当艺术家们把摄像机的镜头对着自己后,他(她)们也在试图通过叙事性的方式向观众展现自己的形象和身体,去寻求自我与对外部世界的思考相交融。这种带有“自我意识”的影像叙事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影像的表现语言,不断被艺术家们所使用。
皮皮洛蒂·莉斯特(Pipiloti Rist)是一位喜欢走到摄像机前面的艺术家,她的作品《我不是那个有太多牵挂的女孩》(图4)中使用自己的形象和身体作为材料,并用影像叙事来进行情感的表达。她把自己化身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女权主义者形象,这个女人有着强烈的愿望想成为一个有主见的、独立的现代女性,但是却不得不受制于来自男性主权社会的控制,而不能实现其美好愿望,最终导致心理的失衡。整个作品是艺术家运用了带有自我意识的影像叙事语言来创作的,艺术家从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和体验出发,通过所唱的歌词,叙述了一个社会生活中真实的女性的心理故事。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的形象丢失了“物质性”,身体不再是有血有肉的躯体,被塑造成一个会动的“图像”,而这个图像又是模糊的、残缺的、被肢解的。皮皮洛蒂·莉斯特在作品中表达了一种令人忧伤的悲剧式的状态,即“我是谁”和“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常常不能一致。在这种带有弗洛伊德“自我”认知式的创作中,艺术家运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个体叙事的载体,并借助了影像这个媒介来实现的。
四、艺术家的影像日记
“影像日记”,即作者把摄像机当作一种记录载体,代替了书写文字的日记本和笔,作者面对摄像机把心里话和情感都倾诉出来,摄像机成为其想象中的亲密知己。“影像日记”并不是作为艺术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它是一种借由影像媒介而达到记录与表达目的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个体与社会发生关联的特质,“日记”记录者所讲述的个人经历都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虽然具有极强的私密性,但是当影像公开后,封闭的个体又重新回到了社会群体关注的视野。

图5 苏菲·卡尔 昨夜无性 彩色,有声,72分钟 1992年
法国女艺术家苏菲·卡尔(Sophie Calle)在1992年和她即将分手的男友进行了一次横穿美国的长途旅行,在旅行途中他们用摄像机拍下了共同经历的事物,这些影像就是他们旅行时的“日记”。虽然这些都是私密性的影像,但还是被艺术家编辑成了一件题为《昨夜无性》的影像作品(图5)。苏菲·卡尔梦想着要嫁给这个男人,但是却很清楚两人已经约定在旅行结束后会分手,因为这个男人有自己的梦想要去实现。现实对苏菲·卡尔来说是残酷的,即将到达的旅途的“终点”标志着两人爱情关系的结束。虽然两人共同完成旅行,但是两人分别拍摄的影像是以两种不同的视角进行的,记录了二人对事物的不同反应。苏菲·卡尔想用影像留住他们美好的旅行,而她的一心想成为导演的男友则常常以一个电影导演视角去拍摄。在影片中,苏菲·卡尔一直都流露出对谢帕尔德的爱恋,这是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感。虽然生活和艺术有的时候并不总能够完美地结合,但正是这种生活与艺术的相互撕扯,使得这件作品充满了力量和感动。
结语
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将影像引入到创作中的时候,使用的是影像的记录功能,记录是冷静的、客观的,但是艺术家们并不满足于只是客观地去记录,他们在记录的同时加入了个人主观的情感和观念的表达。这种表达的需求推动了艺术家对影像在语言层面的实验,创造出来很多新的影像语言。影像是一种媒介,在艺术学研究的框架中,我们的目的终究是探讨艺术家使用这种媒介的文化创造,其背后艺术家个体起到了极其核心的作用。这就让我们再次想到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的《导论》中的一句话:“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③。
注释:
①布鲁斯·瑙曼接受《雪崩》杂志的采访(Avalanche N°2,1971年),后重新刊登于瑙曼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个展的图录。
②[法]弗朗索瓦·帕尔费(Françoise Parfait):《影像:一种当代艺术》,法国Ragard出版社,2001年。
③[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杨成凯校,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