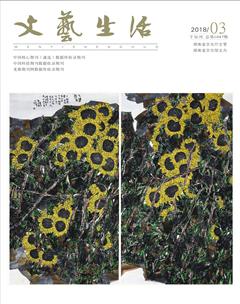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看丁玲对身体的描写
王刘梅
摘要:丁玲写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两部短篇小说都是以妓女为主体,对女性身体进行描写,尽管分别写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里,但是它们都展现了女性在以男性构建的权利话语下的艰难处境。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女作家,从始至终都在关注女性,关注她们真实的想法和境遇,深入到妓女的内心世界中去,通过描写女性身体,打破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从而争取让女性获得话语权。但是又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受到男权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丁玲在创作过程中感到无奈的原因。
关键词:丁玲;女性主义批评;身体;主体意识
一、前言
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将妓女分为低级妓女和高级妓女。在笔者看来,波伏娃说的低级妓女就是指那些迫于生活压力的低级妓女,而高级妓女往往包括上层社会的舞女,比如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以及特殊政治环境下的间谍,如张爱玲《色戒》中的赵佳芝,丁玲笔下的贞贞。这两篇小说都是描写女性由最初被迫失去贞操,到最后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出路。丁玲旨在从女性身体出发来反抗男性的权威地位,从而张扬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但是通过深度阅读发现,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当时还是微弱的,她们的身体描写最终还是建立在男性权利话语之下的,这也是丁玲为女权主义一直奋斗却感到无奈的原因。
二、从《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谈生存与贞操的关系
丁玲在《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正面描写男性的外貌以及行为活动,而是通过妓女阿英的心理活动得以展现。阿英甚至对服侍过的嫖客进行比较,她认为穿洋服的后生“人虽说干净,斯文,只是多么闷气啊!”而那穿黑大布长褂的瘦长男子“人是丑,但有铜钱呀,而且……阿英笑了。”有文化和社会地位的男性在这里遭到了女性的歧视,并且只是被看做满足对于金钱和性的需要。阿英由最初怕丈夫嫌弃自己而另有所爱,到无所谓婚姻的轻松,这种前后心理的变化无疑都体现了她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为什么定要嫁人呢?吃饭穿衣她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负担了。说缺少一个丈夫,然而她并不虚过呀!而且这只有更觉得有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阿英不管是选择留在妓院还是嫁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做判断,此时的她获得了一个主体的地位,也是一种不自觉地对社会较为消极的反叛。
尽管丁玲竭力表现女性主义,使女性获得解放。但是笔者发现,丁玲在努力刻画阿英这一形象时,为了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时刻意将男性地位贬低。丁玲一方面想努力摆脱男权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其影响。
这篇小说似乎向人们传达了一个特殊的观点:对于一个年轻且懂得如何讨好男性的妓女来说,妓女生活比倍受压迫的婚姻生活更加自由。丁玲通过阿英这个身处屈辱境地却心存希望的女性,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对妓女的印象。这个拒绝被拯救的妓女形象,真实地传达了在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并未真正觉醒、反抗。其实庆云里这一妓院场所也是一个束缚女性的牢笼,即使她在以后的某一天选择离开庆云里,已经惯于那样生活的她,走投无路时也许会选择一个男人作为依靠,也许会孤苦无依,始终会受到周围人的冷眼旁观,这个男权社会是很难接受她的。“娜拉出走”事件也许就重演,阿英的悲剧即是所有处于同样位置的女性的悲剧。
三、从《我在霞村的时候》谈革命与贞操的关系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去延安之后写的又一部有关妓女的短篇小说,反映的其实仍是女性的贞操和革命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根源还是在于男权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包括女性自身对女性不幸的漠视。
《我在霞村的时候》整篇文章都是霞村人对贞贞的议论,尤其是那些村妇不但没有站在同是弱势群体的角度同情贞贞,反而麻木的将贞贞的事情作为谈资,女性本身也就成了残害自身的同谋,帮助男性和整个社会,吃掉这类自愿或被迫失去贞操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叙述视角,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虽然不能简单地将丁玲本人与“我”进行联系,但是笔者认为这也是丁玲体现自我意识的途径。“我”与身周所有人的距离感——鲜明体现在与霞村村民的距离感以及对贞贞的態度上,并不认为失去贞操就不贞洁,依旧将主角叫作贞贞。“我”反感霞村人对贞贞的流言蜚语,但是生活于霞村一个环境中,立场与情感态度,不知不觉受到大众价值观的影响。当贞贞决意治病到延安时,“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感到惊讶,就说明还是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平等看待她,丁玲自身在极力摆脱旁人的束缚,又在文字中反反复复体现出受到男权主义的影响,这就是笔者认为丁玲在创作中的矛盾所在。
不过,丁玲在对女性身体描写时,还是寄予一定的希望。因为不管是阿英还是贞贞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曹禺笔下的陈白露被生活逼到绝境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张爱玲笔下的佳芝单纯的相信爱情,最后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丁玲笔下的阿英是享受生活,自愿留在庆云里;贞贞被拯救回来,最后去延安治病。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笔者认为,活着,或许给人的震撼感要深沉的多,有勇气背负沉重的负担,才是最难做到的。
四、结语
每一种文学现象都与它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丁玲所宣称的女性主体意识不仅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世界上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一直以来,男性都掌握着社会的主要话语权,女权主义者将“身体写作”作为对抗男性的武器,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如伍尔夫等。但是她们在实践中有意的弱化男性,其实本身也说明了女性的处境,女性所宣扬的“平等”实际上是社会上对于女性的“不平等”,越是抵抗,越是挣脱不了男权社会的束缚。
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登上文坛,她从一开始就以女性的视角,进行女性身体的描写。在前期塑造了莎菲、阿英等形象来寻求女性的生存价值。30年代后期,丁玲投入到民族革命当中去,她的小说中女性意识明显减弱,试图颠覆男权文化的中心,求得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但是在与政治话语相结合下,丁玲更多地倾向于国家话语,她并不是对女性的关注减弱,而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让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丁玲后期的创作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坚持为女性发声,维护她们的权益。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丁玲的创作发展变化以及她内心矛盾困苦的心境,丁玲在女权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后来的女性作家开辟了道路。在当时社会,女性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不得不采用身体叙事或者女权主义的方式去写作,以便更好的提高女性地位。我们应该理性对待这种身体叙事,包括后来的女作家上海宝贝,还有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这类作家塑造的作品,暴露女性的身体其实只是作为一种反抗男性社会束缚的工具。事实上,不含任何功利性目的,不需要故意博取社会对于女性的关注,用女性身体叙事,才能反映出男性与女性处于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