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系统结构探析“文化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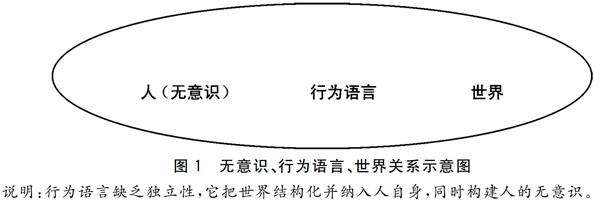

摘 要: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系统就是“文化基因”,它由性质及功能迥然不同的两种行为(语言),即“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共同构成。这两种行为(语言)共同建构了人与世界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由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互结合、相互协作的整体结构存在民族差异性,由此形成的张力结构及倾向性决定着不同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着中西方对世界的解释,并为思维方式和文化生产打下鲜明的民族烙印。
关键词:符号系统;行为语言;言语行为;文化基因;世界观;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4-0163-10
卡西尔把符号活动视为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认为文化的所有发展都依赖于这个条件。格尔兹继承了卡西尔的观点,他对文化的解释“代表了人类学内部的一种发展,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某些其他发展的汇合”,汤普森将其概括为:“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包括行动、语言和各种有意义的物品)中的意义形式,人们依靠它相互交流并共同具有一些经验、概念与信仰。”① 这也就意味着,文化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即象征符号,符号系统的特征就决定着文化的特征。或者可以进一步说,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系统就是“文化基因”,正是它决定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定着人对世界的解释,决定着文化的发生、创造和发展,而一个民族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系统的独特性就决定着这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抓住“文化基因”,我们就可以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就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更加自觉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开展新的文化创造。
一
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系统是由行为语言(动作、姿态、表情、声音)与言语行为组成的,② 这两种性质及功能迥然不同的行为(语言)相互协作、相互博弈,共同构建了张力场。
人与世界的关系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作为生命存在,人与其他生物体一样,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活动与环境建立物质及能量交换关系,以此维持自身生存。在此过程中,那些有益于生命的行为方式在群体间得到不断模仿和重复,并被结构化而具有群体共享的意义,由此形成一种广义的语言:“行为语言”。因此,行为语言实即“被结构化的行为”,它以“身体信息”(动感)来建立差异性。由于行为语言是在身体与环境打交道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不仅密切关联着身体和环境,而且本身就是特定环境中的身体状态,它积淀为生物体的共同经验,同时成为关联世界、表征生物体的内在状态及生物体与世界之关系的方式,成为生物体享有的“语言”,一种身体行为与表征相合一的特殊“语言”,它在前人类时期就已经形成。
行为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只能依附于身体,是身体表演,行为与身体之间并没有分界线。这种缺乏“独立性”的语言无力把人与世界相分离,无力把世界构建为人的明晰的“对象世界”,而是以行为关联世界,在与世界打交道(此在在世)的过程中,以行为语言的结构将世界结构化并纳入己身,以此领悟世界,协调身体行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初模式。既然行为语言无法构建人的对象世界,反过来,也就不能构建人类意识,而只能构成无意识经验(行为语言记忆),造就无意识的结构。医学中“裂脑人实验”证实了人类行为与无意识直接关联,话语则与意识相关。详见Susan Blackmore: Consciousnes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2005. pp.72-73.因为任何意识都是关于对象(包括虚拟对象)的意识,离开对象,意识就无所附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由行为语言记忆所积淀的经验只能是无意识经验。人类这种通过行为语言来直接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直觉”或“悟解”。人以行为语言将世界结构化,实质上,也就是把人自己的生命形式和情感形式赋予世界,世界因此具有了生命性、情感性,这就是“移情”。这种通过行为语言把世界结构化并纳入己身,与世界融合一体,建立非对象性关系来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正是我们所说的“体验”。在这种物我一体的关系中,人无需把世界對象化,无需经过自己的意识或意志,而是直接地做出身体的“本能”反应。因此,我们所说的直觉、悟解、移情、体验、本能就建立在行为语言的基础上,是种种人与世界相融合的“非对象性”活动。正是行为语言建构了人与世界间最为原初的关系,而直觉、悟解、移情、体验、本能则是我们对行为语言的性质、施行方式及功能的描述。
图1 无意识、行为语言、世界关系示意图
说明:行为语言缺乏独立性,它把世界结构化并纳入人自身,同时构建人的无意识。
言语行为是在行为语言,特别是发声行为基础上生成的。随着活动领域扩大和相互交往日益复杂,人不能不将行为语言所构建的无意识经验加以归类和概括,凝聚为更加抽象的概念,言语行为就此诞生了。发声行为既与身体密切关联又相对离散的双重性,使得它有可能演化为“概念/音响形象”,并以“概念/音响形象”来建立自己的差异性,最终因日趋抽象化而脱离身体,获得相对独立。这是人之为人极其关键的步骤。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言语行为,其性质、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已经迥然不同于行为语言,它以其差异性把世界与人相区分,进而把万物相区分,并构建了人的“对象世界”,与此同时反身构建了人类意识。人类意识、对象世界是在言语行为的生成过程中同时形成的,三者间存在同步建构的关系,言语行为的结构就决定着人的意识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人与世界间一种崭新的对象性关系形成了,世界开始以意识“对象”的方式明晰地呈现在人面前,这正是西方现代哲学所说“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根源。“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和“世界是由各种符号建构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哲学主流。这并非说世界原本不存在,而由语言和符号凭空构建,而是说世界本来不是作为人的“对象世界”而存在,只有当无意识经验经过归类、抽象,凝聚为具有独立性的语言概念和符号,人类意识才形成,世界才开始以人类意识“对象”的方式呈现。西方现代哲学所忽略的是:在言语行为出现之前,行为语言就已经存在,并且由于行为语言的非概念性、非独立性,以致它只能以行为关联世界,以行为语言的结构把世界结构化而纳入己身,建立生物体与世界相统一、相融合的浑整关系,并构建无意识经验。当代认知科学家瓦雷拉等人提出的“生成知觉观”就认为:“知觉就是身体行动,知觉的过程就是身体行动在环境中的不断生成,在这个连续过程中,知觉不仅通过身体行动嵌入于环境,而且还参与了环境的生成。”(孟伟:《身体、情境与认知——涉身认知及其哲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实质上,当前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具身(涉身)认知”就建立在行为语言的基础上。在世界成为人的对象的过程中,人自己也就开始成长为具有自觉行动能力的主体,主客体关系就在言语行为中逐步确立了。可以说,言语行为原本就是对无意识经验自动归类而构建起来的,也因此成为人类有意识地用以给世界分类的差异性系统。从此,人不仅可以能动地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大为提高了自身的认识能力,而且同样可以把自己的行为同身体强行剥离开来,抽象出来,作为认识对象和阐释对象来看待;可以把行为与目的、后果及环境相结合来审视和反思,进而调整和掌控行为,不断改善人的实践能力。在言语行为中,就孕育着人的观察、认识、反思、批判、分析和推理的能力。也正是在对行为与目的、后果及环境关系的审视和反思中,人对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做出了判断,开始向着理性主体迈进。于是,人类不再是自在的存在,而成为自觉自为的存在,摆脱了盲目追随自然界的本能活动,展开了有目的的文化创造活动。
图2 意识、言语行为、对象世界关系示意图
说明:言语行为因其相对独立性,在构建人的对象世界的同时构建了人类意识。
言语行为既割裂了人与世界原本一体的关系,造成人与世界间的裂罅,又重新关联着人与世界,以言语行为的结构来重构世界、重组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起主客二元的对象性关系,使人可以把自身从固有的、直接的、狭隘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赢得巨大自由,有力扩张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开阔了人的视野,拓展了人的世界,人终于从有限的亲身所在的空间和绵延不断的当下时间中超脱出来,有可能同时占有现在、过去和未来,占有真实和虚拟的无限空间,而言语行为本身则成为人用来表征世界、相互交流的最为灵活、最为有效的工具。我们所说的分析思维其实就扎根于语言的区分功能,而逻辑推理则离不开语言概念运演。与之相应,行为语言的地位却因此被贬低和边缘化了,行为语言的无意识特点似乎就注定它被忽视和遮蔽的必然命运。
然而,言语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取代日趋蛰伏的行为语言,两种行为(语言)仍然同时并存,共同建构着人与世界间极其繁复多变的关系。在《我与你》的开篇,马丁·布伯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因之他必持双重态度,原初词是双字而非单字。其一是‘我—你。其二是‘我—它……由此,人之‘我也是双重性的。”[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页。马丁·布伯所说人与世界的双重关系,其一是指人与世界相浑融的原初关系,即非对象性关系,也即“我—你”关系;其二是指人与世界间主客二分的关系,即对象性关系,也即“我—它”关系。实质上,这种双重关系就是由两种行为(语言):言语行为或行为语言所构建的。正是这两种行为(语言)赋予人以双重态度,并与世界建立双重关系。马丁·布伯敏锐地注意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可惜限于西方思维习惯,他仍然从语言中心主义出发去探寻原因,无可奈何之下生造了双字“我—你”,试图以此摆脱语言困境。
言语行为的区分功能让自己赢得了巨大力量,在把一个千姿百态的对象世界奉献给人类之后,它仍然凭借其惯性分割着各个领域和对象,不止息地为世界祛魅,构建起一个个学科、一门门知识,扫除着种种神秘和神圣。从本质上来看,知识就是利用语言的区分功能来“分类”:对动物的分类、对植物的分类、对天体的分类、对人的身体器官的分类,就产生了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医学,等等。所谓科学范式的变革,从根本来说,首先是分类原则的变更。但是,语言同样可以被用来制造假象,制造神秘和神圣,蒙蔽人心,只不过这是对语言本性的扭曲和滥用。就在各个领域和对象被不断分割之际,神灵被驱逐了,神圣也被剥除了庄严的外衣,灵韵也消散了,世界因此变得毫无生气和诗意,颓圮为散乱的残砖碎瓦。甚至连人的生命,以及由言语行为亲手构建的人的主体性也被语言自己所肢解,凋落为一堆遗骸和空壳。从终极动因来看,正是言语行为在把人带入现代性之后,又凛然地把他投入后现代的碎片之中。无论启蒙所肇始的理性抑或启蒙所遗留的后果,其背后都潜隐着言语行为的踪影。
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性质差异,致使两者间发生了分裂,双方虽然相互沟通、相互协作,却不能通约,并造成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理性与感性的分裂,精神与身体的分裂。尽管如此,行为语言仍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符号活动,它始终静默无声地伴随着言语行为,共同参与人类活动,共同構建人与世界的关系。只不过在两种行为(语言)的博弈关系中,言语行为以其喧嚣的姿态日益夺得主导性地位。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分裂开始压倒融合,冲突压倒和谐,生态平衡日渐被打破了。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其实就隐含着对行为语言的召唤,意图借助于行为语言来弥合人与世界不断加深的裂罅,重建人与世界相融洽的亲密关系,重新找回失落的原初神秘体验和诗意存在。
人类的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分别塑造了人的无意识结构和意识结构,并共同成为人类最为基本的符号系统,人的所有感觉,无论视觉、听觉、触觉,其背后都潜隐着这两种行为(语言),其他各式各样的符号活动都以此二者为范型,只不过是媒介的延伸和拓展。参见马大康《多模态符号·具身性·审美活动》,《当代文坛》2017年第6期。人无法脱离这两种行为(语言)直接与世界建立关联,凡是不能被这两种行为(语言)所结构化的,就不能不被排除于感觉阈限之外。
在《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中,西恩·贝洛克具体阐述了“具身认知”,他指出:“当我们看、听、读,甚至想到任何不好的事情时,我们自己就会‘体验这样的经历。这些反应不光出现在大脑中;它们也延伸到我们的面部表情和姿势上。身体的姿态反过来也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告诉大脑我们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阅读一则悲伤的故事或者观看悲伤的电影时,总会把情感表现在脸上。但是当我们无法感受到这种经历时——当脸部没有发出能够改变想法的反馈时——情感的处理过程就被阻碍了。解读情感信息的重要一环就消失了。”[美]西恩·贝洛克:《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李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具身认知理论借助于实验发现了身体与人类认知活动的关联性。其实,身体之所以能够介入人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身体是通过行为语言来构建世界,进而直接悟解世界并为认知活动提供基础的。贝洛克所说在阅读故事或观看电影时我们对作品情感的接受总是与脸部表情,也即行为语言密切关联、相互影响,则进一步说明:对于感觉和认知活动来说,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双方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具身认知理论备受质疑的焦点在于否定认知过程中“表征”是不可缺少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理论忽视了身体行为同时是一种特殊的表征方式,是身体行为与表征符号相合一、相重叠的表征,一身而兼二任,是一种非中介的中介,一种非离散的特殊“语言”。
人与世界的关系最初就是由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这两者共同建构起来的,人的生存活动和思维活动就处在这两种行为(语言)共同构建的宇宙内,所有活动都离不开这两种行为(语言),人类经验就建立在两种行为(语言)协同作用的基础上。这两种行为(语言)所构建的人与世界之关系,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决定着人的感觉,决定着人的思维,决定着人类的所有活动。人类文化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两种行为(语言)的张力结构中,由这一“文化基因”所决定。
二
然而,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互合作而形成的整体结构却并非恒定不变,在这两种行为(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其张力结构及倾向性,就决定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及思维活动的独特性,决定着不同的观看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
索绪尔把语言视为由词汇与语法共同构成的两极,而各民族的语言就处于其间的不同位置。实质上,这种两极关系是由两种行为(语言)相互结合的关系结构所造成的,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两极关系更换为由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构成的两极,而不同民族的语言就因所处不同位置(不同的分类方式和抽象程度)而与两极发生不同关联,体现着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间不同的整体结构及倾向性。抽象程度程度越高的民族语言,偏离行为语言就越远,独立性越强,所具有的反思性也越强,并因此在对语言自身的反思过程不断完善语言表达的精确性和逻辑性,强化语法结构。相对而言,抽象程度较低的民族语言,与行为语言的关联就相对密切,并偏重于词汇。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就藏匿在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互关联的整体结构中。
在两种行为(语言)相结合的整体结构中,强调言语行为的重要性,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特征和思维的特征,影响着对世界本源的看法。古希腊时期,泰勒斯提出“基质”、阿那克西曼德提出“元质”、毕达哥拉斯提出“数”,以此来思考世界的本源和万物的基础。但是,种种思考本身就预先把世界设定为“对象”来看待,也就是说,在哲人们开始哲学思考时,就已不经意地运用“对象性”思维,落入言语行为布下的陷阱了。因为只有在言语行为的作用下,世界才呈现为人的“对象世界”,才有可能进而思考诸如“基质”“元质”“数”等问题。只要为世界“是什么”做出命名,就已经进入了语言“概念化”。至于柏拉图则直接把“理念”与“概念”(名称)相关联,借助于概念来思考理念。柏拉图说:“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的。”([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1页)这些以世界本源、本质、结构为探讨对象的本体论思考,其实质都是“对象性”思维,是以言语行为作为前提和基础的,这就注定了西方思想难以逃避语言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宿命。
当人们发现单纯从客观对象去认识世界、寻找真理并不可靠,因为这种认识和寻找本身就受到人的主观性的制约,从而转身去拷问人自己,探索人的主观认识能力,试图建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就导致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因此,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固然和宗教变革及社会历史境况演变分不开,但是,这种种因素还只是外因,它们只是从外部共同促成学者们把目光转向人自己。可是,尽管思考对象变了,而思考的基础和方式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把人、人的心理、人的能力、人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对象”来考察和分析罢了,譬如康德就是依据语言划定的范畴:知、意、情,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
胡塞尔的现象学似乎要摆脱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对象的分裂状态,然而,他把“先验的普遍意识结构”设定为研究目标,并主张通过“第一人称”主观描述的方式来揭示这种结构,也就显示着他仍然没能跳出言语行为的泥潭。至于现象学所说的“主体间性”也绝非“物我合一”的混沌状态,无论这个“主体”是先验的或是心理的或是交互共在的,它都只能是语言对人与世界做出区分、定位和建构的结果。而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则是直接去探讨作为审美“中介”的语言,分析“意向性客体”的层次结构。海德格尔曾以惊人的胆魄宣言传统本体论的谬误,并把问题的核心“存在者”(是者)置换为“存在”(是),从人的生存活动(此在在世)中探索真理,这确实隐含着对语言概念的疑虑和规避。因为哲学一旦思考“存在者”,也就涉及“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势必落入语言概念的圈套。海德格尔把问题转向“存在”,也就避开了“是什么?”这个问题,避开了“概念化”。与现象学有所不同,海德格尔贬斥“主体性”,认为主体性正是人与世界相分裂的根源,因为有了主体,也就有了对象,分裂就在所难免。为了避免这种分裂状态,他提出了“此在在世”的结构来描述存在状态,认为人原本是与世界一体的,人只能在世界中生存,在与世界打交道中有所领悟,大地也因此而敞开,真理因此而显现。“我们在理解和谈论物时,会插入我们与物之间的所有东西必须事先悬搁。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沉浸于物的無遮蔽的现身。”海德格尔把这种“与物直接遭遇”视为阐释的首要条件。[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这似乎暗寓着对语言的贬斥,因为一旦语言介入,也就必然凭借其差异性实施区分,又重新在人与世界间造成裂隙。但是,海德格尔毕竟未能跳出西方的语言中心主义,最终他还是把真理与语言相关联,把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园”,由此造成理论内部的矛盾。人是无法避免这种悖论式的生存境况的:语言是人之为人的依据,人离不开语言;语言却又分裂了人与世界,造就人的生存困境。海德格尔虽然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营养,却因文化差异仍然与中国文化隔着一层,他依旧信赖语言,尽管他所说的主要是诗性语言,是“原语”,而老庄虽然深知人无法离开语言,却始终不信任语言,始终怀着对语言的警惕。或者说,他只是对“概念化”(存在者)抱有戒心,而并不是否定言语活动,甚至是醉心于富有诗意的言语活动,醉心于“原语”(Sage)。正如佩尔尼奥拉评论海德格尔时所说:“因为语言的本质正是‘让实体自我被见到。现象学之所以是解释学,是因为它是与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马里奥·佩尔尼奥拉:《仪式思维》,吕捷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7页。
针对西方的理性中心主义,胡塞尔指出:“西方的一切非理性主义归根结底仍然是理性的,只是未达到某种(更深层次的)理性的自觉而已。没有理性便没有整个西方文化。”邓晓芒:《胡塞尔现象学导引》,《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我们可以更深入一步说,没有对语言核心地位的重视,就没有对理性的重视,没有整个西方文化。在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结合的整体结构中,强调言语行为主导作用这一倾向,构成了西方文化基因的独特个性,它决定着西方人的思维特征和文化特征。
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现象学的崛起,把人自己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推到理论关注的焦点位置,学者们这才发觉,在人与世界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障,一直来遮蔽着世界真相的竟然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语言,在人类呱呱坠地之初就始终戴着这副有色眼镜在看世界和人自身,无法离开语言来认识和思想——这就是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语言终于从思想舞台隐蔽的幕后走向前台,从载体和工具升格为主角,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这种现代主流哲学始于康德用心灵的结构取代了世界的结构,继之于C.I.刘易斯用概念的结构取代了心灵的结构,现在则进一步用科学、哲学、艺术、知觉以及日常话语的很多符号系统的结构取代了概念的结构。”[美]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序言》,姬志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古德曼高度简练地概括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问题在于: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即便存在着许许多多种符号系统,他们也仍然是依照言语行为的范型来看待和解释这些系统,这就势必障蔽了行为语言的独特性质和重要作用,陷入了语言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既然遮蔽世界真相的罪魁祸首是语言,分析哲学也就把锋芒直指语言。在他们看来,症结就在于人们天天使用的语言概念。大量的日常概念并非经过严格的逻辑设定,而是日常习得的,它边界模糊,意义迁移不定,恰恰需要分析哲学支清晰和治疗,可是以往我们竟把它们视为天然的合法性依据,由此出发去思考世界的本源,思考万物乃至各式各样的语言衍生物的本质,这岂不荒唐?也正是在语言符号中,隐蔽着种种权力操纵,暗地里造成遍及旮旮旯旯、根深蒂固的思想偏见和社会不公。于是,语言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为质询的对象。至此,西方哲学把自己的思考推向极致。它质疑语言,却并未逃出语言的樊笼。他如约翰·塞尔以言语行为来阐释文明结构的做法;叙述学溢出文艺学的边界,被简单套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及其他诸多领域,其实都根源于语言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根源于西方文化基因的独特个性。
三
在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本源问题上,中国古代哲人似乎站在西方学者思考的巅峰上,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轻信语言,而是既尊崇语言,又看到语言的局限性。老子深谙其中奥妙,时刻保持着对语言的警惕。在谈论世界本源和法则时,老子不得不使用语言來表述,不得不勉为其难地以“道”来命名。“道”,《说文》解释为“所行道也,从辵、首,一达谓之道。”(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6页。这种象征性、隐喻性说法强调了关联、贯通着人与世界的“行道”的重要性。唯有借助于道,人才能通达世界,才与世界建立关系,才能与世界打交道中解悟和把握世界,人的种种行为都发生在道上,也只能发生在道上。同时,老子又明确意识到这种命名是不能为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02页。世界的本源和法则是道、大、逝、远、返,而同时它又不是任何一个语言概念所能表达的,它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用概念来限定,甚至不能用广漠无际的“大”来说明,只能在与人的关联中,在逝、远、返的行动中去领悟。世界本身就是非概念、非语言的。老子将自己置身于悖论式的困境中,试图通过语言来超越语言,通过既命名又否定命名来启示读者亲身去接近道。语言不仅如分析哲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值得怀疑的,需要清理和治疗,它本身就是横亘在人与世界之间必须跨越的壁障,要真正把握道,就不能不超越语言。
道不仅是非语言、非概念的,而且是非具象的,人的感官无法把握道。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朱谦之:《老子校释》,第52-53页。这里所说的“混而为一”并非指世界自成一统,而是指人与世界相混成、相合一,世界并非人的对象世界。当人与世界融合为一,进入与物俱化、无物无我之境,所有的语言壁障都自行坍塌了,所有的概念界限也都被取消了,世界已经不再作为“对象”而存在。此际,一切声音都将成为希声之“大音”,一切形象都化为无形之“大象”。处于这种“非对象性”的浑融状态,人实际上就已然置身道之中,道也同样置于人之中,人与道相同一了,感官也成为毫无必要的虚设。
对语言的不信任必然导致对感知的不信任。人类所感知的世界是经由语言区分而构建的对象世界,在人类将无意识经验归类、凝聚、抽象为语言概念之际,既流失了许多珍贵经验,又夹带进不少偏见,并将人与世界的亲密关系拆解开来且重新固化了,这就决定着这个由语言区分和构建的对象世界本身并不可靠,那么,人的感知又怎能可靠呢?人类的感官是无法摆脱语言纠缠的。设若我们弃绝语言,那么人与世界就无法被区分,世界就无法被构建为人的对象世界,人类意识也无从产生,尽管世界依然故我地存在着,却只能是以“无”,即无言、无声、无形、无像的方式存在。世界并非因此缺席,而是它不再是人的意识对象,感觉对象,它本身就是“非对象”。这种非对象性的世界就是老子所说的“无”,是物我一体、唯恍唯忽的混沌状态,它无处不在、周行不殆,却又不可言说、不可感知,唯有借助于行为语言所构建的物我相融关系,人才可以绕开言语行为径直去把握世界,把握“无”(道)。正是行为语言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与世界的关联,其非概念性、非独立性就决定着它可以将人与世界相融合来体验世界、悟解世界;又由于行为语言只能建构无意识,因而,尽管对于人的意识来说世界依然是“无”,而事实上却已然构成了无意识经验,并在直觉上悟解了道。一旦言语行为介入,人与世界之间的裂罅就形成了,世界则成为人的意识的对象、感知的对象,“无”也就转变为“有”,万物也由此而生,而道却隐失不彰了。
在谈到王弼《老子指略》时,牟宗三做出这样的阐释:“道有双重性,一曰无,二曰有,无非死无,故由其妙用而显向性之有;有非定有,故向而无向,而复浑化于无。其向性之有只是由‘关联着万物而欲使之然而凸显也……而向非定向,有非定有,故可浑化于无也。有与无,母与始,浑圆而为一,则谓之玄。”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牟宗三准确地指出了道的双重性:“无”与“有”相共存,“有向”(对象性关系)与“无向”(非对象关系)相变换,并且有无之变化起因于“向性”(意向性关系)的转化,然而,却仍然没有揭示造成“向性”变化的原因。其实,根源就在于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之间主导关系的变化。随着两种行为(语言)主导关系的转换,对象性关系中有形之“象”转而成为非对象性关系中无形之“大象”,“有”转化为“无”。
庄子和老子一脉相承,同样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清)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2页。。《庄子·天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郭嵩涛注曰:“知以神索之,离朱索之形影,吃诟索之声闻,是以愈索愈远。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眸而得之。”(清)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第101页。“玄珠”即喻道,而人的智慧、感官、言语都无法求索它,唯有若有形、若无形的“象罔”才可得之。显然,这种脱离理智、感官、言语的“象罔”,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象”,是一种人与世界间非对象性的浑融状态,它只能由独特的符号系统,即行为语言所建构。在庄子笔下,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削木为鐻等等,都反复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那种出神入化的技艺恰恰需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清)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第29页。甚至应该达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境界。(清)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第69页。这也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境。只有搁置理智和感知,超越现实语境,排除种种外在干扰,彻底改变人与世界的分裂状态,臻于这种至境,无意识经验(行为语言记忆)中蕴蓄着的创造潜力才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喷涌,而这恰恰又是中国古代哲人不懈求索的至美状态。
对世界本源及道的看法,孔子及儒家与老庄之间并没有根本性分歧,他们同样主张“天人合一”观念。“中国人的现实,只是‘浑全一整体,他看‘宇宙与‘人生都融成一片了。融成一片,则并无‘内外,并无‘彼我,因此也并无所谓‘出世与入世。此即中国人之所谓‘天人合一。”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7页。可以说,对“道”的理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而强调人与世界之非对象性关系,强调符号活动中行为语言的基础地位,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独特个性。
在阐述庄子美学思想时,彭锋指出:“道”是一种非对象性存在。“正因为道不是一种对象,因而任何将道当作对象追求的活动,都是背道而驰。道也不是一种特别的事物,任何事物的自然存在都是道,这在庄子‘天籁概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彭锋:《从浑沌、象罔和鸿蒙看庄子美学思想》,《中国美学》2004年第2期。林光华对《老子》中的“道”也做了意义相近的解读,他说:“在道家看来,工具性的语言恰恰会遮蔽‘道。因为工具性的语言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只要开始用它言说,就预设了主客的二分,此言说一定有明确所指和目的的,是出于人认清对象的需要,因此是对象化的。‘道不是与我们主体相对的对象,在人没有产生时,它的存在与语言无关;在人产生以后,它是我们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人无法从这个‘世界中真正挺立出来,回过头来看‘道,如同我们无法点燃一盏灯看看黑暗的模样。否则,我们就像是骑驴找驴,永远找不到‘道。道的玄妙正在于此,在这一意义上,本文用一个现代术语去描述它,即‘非对象化的道。”林光华:《非对象化之道:再读<老子>第一章》,《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彭锋和林光华正确地把握了老庄所谓“道”的“非对象化”特性,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这种非对象性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究竟如何把握非对象化之道?追根究底,离开行为语言,人与世界间的非对象性关系就无从构建,人也就无法领悟非对象化之道。
同彭锋、林光华的观点相类似,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则阐释了中国古代绘画“非客体”的特征。在谈到笔墨与形色时,她进而认为,在绘画过程,占据至高无上位置的并非目光的敏锐和心灵的规划、构思,而首先是内在的聚精会神、洗练雅化、精致真纯的功夫;并且其成功并不怎么取决于执笔之手的敏捷、精确和出色的笔法,而更取决于这样一种运动原理:“它开始于更上游的阶段,将心脏脉动毫无损耗地一直传递到激活形式的张力,操画笔与操斧头或操刀属于同样的操作技艺。”在这一过程中,“身体语言与气息相关,它操控着绘画。”[法]朱利安:《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张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5-406页。朱利安敏锐地感觉到“身体语言”与气息相关联,与绘画的笔墨及非客体性相关联,但是,可惜她未能进一步深入探析身体语言(行为语言),没有发现身体语言(行为语言)独特的性质、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没有觉悟到正是身体语言(行为语言)的独特性致使画家与自然相契合,令笔墨成为身体语言(行为语言)的自然延伸,并最终赋予画作以“非客体”特征,由此造就中国绘画的独特性,而是把中国绘画归结为“意”的图像,并将根源落实到“气息—能量”。尽管这种“气息—能量”同样是无形无迹、流动转化、生生不息的,却已经沦为朱利安眼中的客观实在,而区别于中国文论画论中那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若有若无的 “气”,更远离了不可道之“道”,偏离了中国艺术精神,重新落入语言逻各斯的圈套。朱利安似乎将要逾越中西方艺术的疆界,洞悉中国绘画的真谛,而最终却仍然被阻挡在语言的魔障内,与真相失之交臂。
四
在比较庄子、玄学、禅的关系时,李泽厚做出这样总结:“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中国哲学思想的形成道路不是从认识、道德到宗教,而是由它们到审美,达到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这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区别于逻辑认识和思辨理性,也区别于事功、道德和实践理性,而且也不同于脱离感性世界的‘绝对精神(宗教)。它即世间而超世间,超感性却不离感情;它到达的制高点是乐观积极并不神秘而与大自然相合一的愉悦。”李泽厚:《漫述庄禅》,《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中国哲学思想形成路径的独特性,就根源于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系统结构的独特性:在这个系统结构中,行为语言起着基础性作用,由此决定了天人合一的觀念,决定了哲学思想的趋向和顶峰。
在此,我们并非要比较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优劣,而是辨析双方的差异性,并认为中西方文化和思想差异的根源在于符号系统的差异,在于两种行为(语言)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及倾向性的差异,由此形成中西方文化基因的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决定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定着人的生存活动的宇宙和生存活动的方式,从而影响着对世界的认识。卡西尔说:“全部理论认知都从一个语言在此之前就已赋予了形式的世界出发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以至哲学家无一不是按照语言呈现给他的样子而与其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这一直接的依存性,较之于任何其它一种由心智所间接创造的东西,都更难为意识着的思维过程意识到。”[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5页。本维尼斯特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他说:“象征化,就是说语言恰恰就是意义的领域。并且,归根结底,文化的全部機制都是一种象征性质的机制……就好像有一种语义学贯穿着文化的这些所有要素,并且将这些要素组构起来,在多个层次上组构起来。”[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8页。对于西方民族来说,言语行为在符号活动的整体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因此遮蔽了行为语言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西方学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行为语言,而是不可避免地以言语行为的范型来看待和阐释行为语言。本维尼斯特就曾武断地说:“任何音响、色彩和图像的符号学都不会通过音响、色彩和图像本身来表达。任何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学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因此只有通过语言符号学,并在语言符号学之中才能存在……语言是所有其他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的解释项。”[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第133-134页。用语言范型来解释所有其他语言系统或非语言系统,固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却唯独抹杀了行为语言的独特性,简化和扭曲了人与世界间复杂多变的关系,这才是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的真正根源。然而,言语行为是人获得认识能力、反思和批判能力的根据,也正是对言语行为的倚重和强调,致使西方人能够在反思、批判中突破原有思想,构建起一个个宏大的思想体系,把理论认识不断推向新的高峰,并迎来了自然科学的繁荣。
在中华文化和思想中,行为语言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地位,正是这一特点使古代哲人没有堕入西方的语言中心主义,精当、正确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领悟了人与道的关系。唯有借助于行为语言,人类才能真正悟解道,并且行为语言的独特性也不是单纯靠逻辑分析来发现的,它必须借助于直觉和悟解,也就是说,要借助于行为语言自身。因此,正视言语行为的局限性,重视行为语言的特殊性,试图通过大象、象罔来把握不可言说、不可感知之道,让我们的先哲们在一开始就赢得了先机,但是,也因为反思和批判有所欠缺而迟滞了思想的后续发展。中华民族早在先秦就创造出极其灿烂的文化思想,其后却高峰不再,学者们往往述而不作,这固然与秦汉及以后的思想统制相关,但更主要的是这种靠悟性获得的思想成果无法借助于悟性自身来作出反思批判和逻辑推演。人的认识能力需要依仗批判的砥砺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悟性则难以与反思、批判相联姻,更无法与逻辑推理兼容,需要让无意识直觉冲破理智的压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朱谦之:《老子校释》,第192页。这不能不窒息思想批判和新的创造,更为严重的是会阻碍理性主体的建构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要弘扬中华文化,就必须真正认清中华文化的实质,这首先就要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然后才谈得上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当我们从最原初、最根本的符号活动中找到中华文化的基因,也就有可能辨识、厘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改变古代文明与现代的断裂状态,给已成遗迹的古代文化重新注入新生机。文化生成、创造和发展离不开两种行为(语言):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协作,双方不可偏废;也只有从符号系统整体结构这个文化基因入手,我们才可能更加深入地比较中西方文化,从而博采众长,充分发掘两种行为(语言)永不枯竭的潜能,把行为语言中蕴蓄的创造动力与言语行为的反思、批判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双方的协调和互补中,在新的文化创造中,也使人自身日臻完善。
(责任编辑:李亦婷)
Analysis of Cultural Gene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Symbolic System
Ma Dakang
Abstract:The most primitive and basic symbolic system of human beings is the cultural gene, It consists of two kinds of acts (languages), i.e. behavior languages and speech acts,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in nature and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combination of behavior languages and speech acts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distinc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but also determines the distinction in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words: Symbolic System; Behavior Languages; Speech Acts; Cultural Gene; World View; Nation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