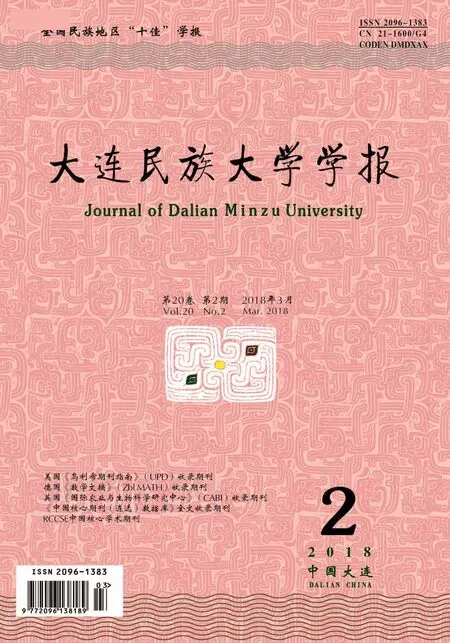诗意的远方: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 寻根文学”之民族美研究
——以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为例
李珂玮
(大连大学 教育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文化寻根”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反现代性思潮,是各国、各族群、各地域传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的思想博弈,各界学者以不同形式自觉进行了“文化寻根”,以抵御日益明显的文化整合、文化趋同效应。“文学的文化寻根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萌发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是一个跨文化、跨族群、跨体裁的文学、文化现象,如果我们再将其与更广泛的文化领域的相关情况联系在一起的话,完全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绵延不绝的泛文化寻根思潮。”[1]这股泛文化寻根思潮一直蔓延至21世纪,从而形成了“后寻根文学”,与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共同构建了新时期以来的“寻根”主题文学。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寻根”文学以其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在整个“寻根”主题文学中独树一帜。进入新时期,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身份认同逐渐复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对各族群文化的自觉关注[2]。此外,作家们自觉产生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从而出现了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这些少数民族“寻根”主题文学用独特的边缘叙事穿行在各少数民族的远古与今朝,为各少数民族追溯到了民族文化之“根”。如80年代 “寻根文学”中乌热尔图关于鄂温克族的小说集《琥珀色的篝火》、郑万隆关于鄂伦春族的小说集《异乡异闻》、张承志写蒙古族的小说《黑骏马》等,以及“后寻根文学”中,迟子建关于鄂温克族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关于蒙古族的小说《狼图腾》等。无论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本民族文化抒写,还是作家的跨文化抒写,都表现了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命运的共同观照。少数民族“寻根”主题文学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民族文化图景,其中的边疆自然美、文化风俗美、原始人性美等共同谱写了中华文化多元美。少数民族美作为中华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原始性、生态性、质朴性,他们是少数民族文化积淀的产物,印证了中华文化的悠久性、多元性。对少数民族美的尊重、礼赞、弘扬有利于建设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多元一体”国家。
一、少数民族“寻根文学”之边疆自然美
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地主要集中于边疆,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决定了其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亦远离中心。他们成为最后走进现代化的群体,这为少数民族的发展保留了相对独立的空间,最直接的表现是保留了边疆自然美。在少数民族“寻根文学”中,边疆自然美首先表现为和谐的生态美。回族作家张承志到内蒙古插队多年,他的代表作之一《黑骏马》*张承志.黑骏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文中所引均出于此处。是典型的跨民族抒写,他将故事置于辽阔的蒙古草原,那里是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根”,那里有一片宁静祥和的草原。“河湾里和湿润的草地上密密地丛生着绒花雪白的芦荻,大雁在高空鸣叫着,排着变幻不定的队列。穿行在苇墙里的骑手有时简直无法前进;刚刚降落的雁群吵嚷着、欢叫着,用翅膀扑楞楞地拍溅着浪花,芦苇被挤得哗哗乱响。”河湾、草地、芦荻、大雁、骑手、浪花……自然万物合奏一曲和谐的天籁之音。同样是张承志的作品,《顶峰》则呈现冬日里的风景:雪山之海一望无际,冰冷而又傲慢地向着彼岸连绵,在强烈耀眼的银光中稳健地升起一轮浑圆晶莹的蓝色冰顶。张承志的草原如此清澈明亮。与张承志细腻唯美的风格相反,汉族作家姜戎笔下的草原则是剑拔弩张的,人与狼、狼与马群、狼与羊群,还有獭子、黄鼠狼,等等,各种生物在生物链条中搏斗着、厮杀着。看似血腥的角逐,其实正是草原原始生态环境的真实存在,这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令自然生灵的优良基因不断延续,是生态和谐、平衡之美。如果说张承志抒发了草原的“诗意”生态,那么姜戎则张扬了草原的“血性”本色,他们均通过文学创作重塑了草原生态的多样性、完整性,也展现了原始草原的质朴与纯粹。
草原是辽阔无际的,而山林则是神秘深邃的,乌热尔图、郑万隆、迟子建等“寻根”作家再现了东北深山莽林之生态美、朴拙美。这里居住着从远古走来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斜仁柱”中,他们的生活伴随着俗称为“大烟泡”的狂风暴雪,伴随着出没于林野间的野兽,伴随着高山丛林、湖泊河流,伴随着永远不灭的火种。万物有灵思想以及图腾崇拜令这些少数民族敬畏自然、尊重生灵,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乌热尔图的小说不变的主人公是驯鹿,《七岔犄角的公鹿》中,在“我”与公鹿的较量之后,“我”被公鹿的勇敢精神折服,将它视为英雄,并尽力保护它,最终在险境中救了公鹿;《老人和鹿》中,老人将鹿看做是自己的老朋友,将鹿鸣当做最美的音乐。还有郑万隆小说中人与马、人与熊的故事……无数个人与动物之间产生的默契与温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表现。生长在中国最北村落——北极村的迟子建记忆中充满了童年的生态元素:广袤的原野、森林,还有寒冷冬天的大雪、炉火,故乡的木刻楞房子、晚霞、菜园……这些成为迟子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鄂温克民族史诗,更是一部生态小说。小说中没有大段对自然的独语,但是自然万物、气候流转始终影响着、伴随着鄂温克人的出生、成长、死亡。这些不是作家的诗意创作,而是原生态环境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真实再现,这是边疆特有的、未受现代文明侵袭的和谐生态美。
对于本民族作家来说,他们的创作动机源自“作家从自己民族母体那里传承过来的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民族情结”[3]。而对于其他民族的作家来说,他们描写的民族区域往往是曾经的故乡,他们对少数民族美的礼赞亦是怀有对故乡文化的留恋。与现代化刻意雕琢之美相比,边疆自然美具有原始、质朴、奇崛等特点。它是人类的童年记忆,犹如蒙古长调一般,高亢悠远而又舒缓自由,在叙事与抒情之间造就了人间壮美。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更是地广人稀,有利于保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我们可以领略中华多元自然美。少数民族“寻根文学”对边疆自然美的抒写一方面呈现绝域之圣景,另一方面展现了原生力量的自由与朴素。
二、少数民族“寻根文学”之文化风俗美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寻根”主题文学为重温少数民族文化风俗提供了土壤与空间,作家对各民族文化风俗之美倾尽心血与热情。韩少功认为“寻根文学”是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对少数民族“寻根文学”来说,作品中记录的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美更是对民族审美意识潜在因素的唤醒,尤其是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图腾文化、图案纹路、民间风俗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都很注重对本民族独有习俗风物的表现,刻意将与习俗有关的诸多意象融入叙事,使作品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之外又多出了民俗风情画的文本属性,形成了一种习俗化的叙事模式。”[4]不独是少数民族作家,汉族作家在进行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时也采用了习俗化叙事模式。在现代文明对人类多样文化进行“格式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美令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岩层下涌动的原生岩浆,文化岩浆的喷发迸射出各民族文化的绚烂姿态。
文化风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或者传承下来的活动仪式而构成每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而文化风俗通常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又通过人自身的活动形成人们的风俗习惯。蒙古族逐水草而居,他们的民俗便源自草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张承志的《黑骏马》中有这样一首古歌:“伯勒根,伯勒根,姑娘涉过河水,不见故乡亲人……”讲述的是草原独特的风俗:远嫁他方的姑娘,跨过伯勒根河,便永远与亲人、故乡告别了。小说中的老额吉,便是无数个告别故乡的姑娘之一,她不希望心爱的孙女索米娅也这样永远离开自己,但是索米娅最终还是跨过了这条别离的河。可以想象,这种草原风俗源于草原的广阔与辽远,离别是忧伤而又凄美的,但是这种离别的风俗又令草原女性具有了大爱之情,因为她们不仅仅属于亲人,更属于草原。张承志笔下的蒙古族风俗像一首情诗,而郑万隆、乌热尔图笔下的少数民族风俗是一个个神话。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都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因此很多文化风俗都与宗教密切相关。萨满教崇拜火神,认为火是神所赐,最圣洁,最亲切,火神可以降魔捉鬼,任何仪式都离不开火,各类祭品也要先给火神献一点儿。乌热尔图运用儿童视角写出了祭祀火神的完整过程,体现了火崇拜的神秘与神圣,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以火来象征着民族的命运。火崇拜直接反映在人们的风俗习惯中就是对灯火、对红色的推崇。郑万隆的《三块瓦的小庙》记录了黑龙江地区这样的过年风俗:二十五点冰灯,二十六给树挂红。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的共同图腾为熊,他们认为熊和人是同一个祖宗。郑万隆与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处处投射着熊的影子,熊成为鄂伦春人与鄂温克人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猎熊的过程以及猎熊之后人们都怀有几分敬畏,并举行隆重的仪式。乌热尔图在《棕色的熊——童年故事》中详细描写了鄂温克人猎到熊后的隆重仪式:首先割下熊头,嘴里插根木棍防止它再进攻人类。猎人下跪祈求熊的原谅,并保佑他们多打猎物。接着把熊驮回住地,大家围坐在一起将猎刀与熊肉摆放在桌子上。长老先用熊肉与熊油祭祀火神,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学乌鸦叫,以表示是乌鸦在吃熊肉,而不是人类,随后要给熊举行风葬仪式。无论火崇拜还是熊图腾崇拜,都是通过仪式呈现出来,体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质朴与浪漫。“寻根”作品的少数民族风俗记载是从前的记忆,呈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有的以器物的形成存在。原始生活中的器物通常就地取材,从而形成了少数民族朴素的审美心理和地域性生活习惯。在鄂温克、鄂伦春民族艺术中,桦皮艺术堪称一绝,他们将桦皮制成容器、餐具、酒具,还能制成桦皮帽子、桦皮鞋、桦皮船。乌热尔图、郑万隆、迟子建的小说中桦树遍及鄂温克人的世界。另外他们的作品中还记录了鄂温克人居住的“撮罗子”与鄂伦春人居住的“斜仁柱”,所用材料在整个树林中俯拾即是。这些民俗器物充分战现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以及朴素的审美心理。由于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的远古历史、祖先故事完全凭借着文化风俗以及神话传说流传下来,世代相传,形成了各民族特有的性格与特征。中国有56个民族,文化风俗各异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寻根”主题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描写在审美情调与美学形态方面有效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元美。这种“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学作为本民族与本地区人们思想感情的体现,还可以有效地激发群体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思乡情怀、寻根崇宗意识等等”[5]。
三、少数民族“寻根文学”之原始人性美
少数民族文化心理,除了表层的民族风俗文化,更积淀在少数民族原始、野性、充满大爱的人性之中。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美则是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内在品质与情操。“寻根”主题文学中,作家着力塑造了少数民族原始人性之美,他们的人性美跨越民族,跨越血缘,是人性之“大美”。这种人性美首先表现在对生命的尊重。对于蒙古族来说,对生命的尊重主要源于蒙古人游牧的生活经历,张承志曾在《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想》中写道:“在北亚游牧世界中,人所经营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畜群。由于历史的迟滞循回,这种生活和生产在千百年中制造了人们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观,那就是相当平等地看待牲畜的生命。”[6]人与牲畜生命的平等体现了蒙古人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成为蒙古族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张承志的《黑骏马》用细腻多情的笔触叙写了蒙古青年白音宝力格和牧民姑娘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在小说中爱情是凄美的,但是草原人性却是淳朴、宽厚、博爱的。无论是额吉,还是索米娅,她们都具有大地母亲般的宽阔胸怀与人间大爱。父亲将白音宝力格寄养到毫无血缘关系的蒙古额吉家时,额吉待他同自己的孙女一样,用同等的爱呵护着他们。奶奶不但收养了白音宝力格,还收养了一匹快要冻死的马驹,最终这匹幼马成长为白音宝力格胯下一匹健硕、高贵的黑骏马。当索米娅早产下一个“勺子大”的孩子时,老额吉并没有听从牧民们的劝告将其抛弃,而是坐在门槛上,对牧人们说:“这是一条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扔到野草滩上。不管是牛羊还是猫狗……把有命的扔掉,亏你们说得出嘴!”生命,无论多么弱小、多么卑微,在额吉的心里都是世间最珍贵、最不可亵渎的,更是不可抛弃的。这种对生命的敬重在索米娅身上得到延续,索米娅带着卑弱的孩子被迫远嫁他方,在没有爱情与浪漫,只有现实与生活的日子里,索米娅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与粗朴、豪爽的大车夫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岁月的洗礼,索米娅早已褪去了年少时的羞涩与朝气,而变成了勤劳、热情、坚韧、淳朴、慈祥的草原成熟女性。草原两代女性的宽厚与博爱孕育了草原上的生命,哺育了草原后代,令草原生生不息。张承志对蒙古族人性美的描写,不是在用技巧,而是在用心、用情、用热血。《狼图腾》中毕力格老人是草原民族的象征,他具有着蒙古族的勇敢、宽厚、博爱、智慧。毕力格老人爱着草原,爱着草原上的所有生命,他懂得草原规律,尊重草原生存法则。在对待狼的问题上,老人恨狼,但更爱狼,蒙古草原与骏马赋予了蒙古人民野性、勇猛,同样也赋予了他们慈爱、宽厚的胸怀。
除了对生命的敬重,少数民族人性美还体现在对他人的“兼爱”。新中国成立之前,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还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他们群居、共猎,且平均分配。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人性美在乌热尔图、郑万隆、迟子建的文学中是善良、质朴、厚重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真实记录了鄂温克人的温暖人性: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丛林中,树间常常会有风葬的棺木和储物的“靠老宝”。“靠老宝”便是鄂温克族在迁徙的过程中,为自己,也为陌生的后来者储存食物、皮张、衣物等的装置。乌热尔图的小说《琥珀色的篝火》中猎人尼库为了救山外迷路的城里人丢下了自己病重的妻子,义无返顾地两次搭救傲慢而一味索取的城里人。鄂温克人的人性美绝不止于“小善”,更有大爱。《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妮浩萨满具有超验的神性,但是为了救赎部族中的病弱,为了保障部族的生存,她每一次施法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她用法术救了别人的生命,上天就会夺走她的一个儿女,直到她的儿女全部归天。最后妮浩仅剩下自己一条生命,为了祈雨,她又使尽全身的力量
舞蹈求神最终力竭而亡。妮浩萨满是宗教领袖,她身上闪烁着神性,但是更多闪烁的是人性奉献的光辉。。妮浩身上流淌着鄂温克民族的血液,她秉承着鄂温克“大爱”的民族基因。
在这些少数民族族群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良、淳厚、郎健,它们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存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原始人性的美丽令我们感受到天之广博,地之宽厚,这种人性构成了各民族的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心理。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主要分布于中国边陲,他们粗犷豪迈、耿直健朗的民族性格有效地补充了中原地区汉族的温婉、柔弱、细腻,这股硬朗强劲的民族风为中华民族性格的健全注入了一注强心剂。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民族性格多元的情况下,各个民族能够和谐是一家,凭借的也正是宽广、厚博的民族胸怀。
四、结 语
1990年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民族文化观,有利于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寻根”主题文学创造了一个封闭的美学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恬然自守、文化自足、信仰源远流长[7]。其中抒写的民族美,无论是边疆自然美,还是风俗文化美,亦或是原始人性美都烙印着民族的印记。对少数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岩层下的原生力量与文化基因,源自作家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少数民族美属于小众之美,但却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大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示多元文化之美,尊重欣赏多元文化之美,繁荣发展多元文化之美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姚新勇.多义的“文化寻根”—广谱视域下的“寻根文学”[J].暨南学报(哲社版),2008(4):98-103.
[2] 杨红.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6):90-94.
[3] 尚正宏.从民族性看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实绩[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140-142.
[4] 王晓恒.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J].贵州民族研究,2015(11):133-136.
[5] 宋贵生.新时期少数文学的繁荣与发展[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6(10):52-53.
[6] 张承志.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想[J].读书,1985(9):25-30.
[7] 吴雪丽.再寻根: 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10):184-189.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