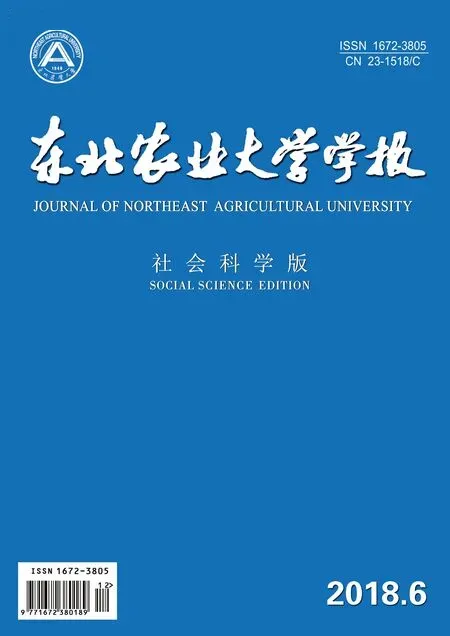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建构之现实审思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在我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吸引艺术家、教师和相关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等助力乡村振兴。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艺术介入途径建构文化认同规范,唤醒村民归属感、责任感和认同感,继而形成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引发学术界广泛讨论。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艺术介入研究
有关艺术介入研究在国际上跨越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文献较分散,研究成果缺少综合性。截至2018年6月,以“艺术介入”为检索词,检索文献共331篇,相关著作15部,其中,以“艺术介入乡村”为主题的相关文献27篇。依据现有资料积累,艺术介入研究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其一,关于艺术介入的理论研究。文艺理论界对于“介入”一词关注始见于1947年萨特《什么是文学》一文,表达文学艺术要介入社会现实的核心观点,强调文艺在“介入”社会过程中,人的自由本质将得到最大程度凸显。彼得·比格尔在其先锋派理论中也深刻揭示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和强大社会批判功能。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具有较强敏锐性与前瞻性,他意识到艺术领域中的美学思潮正逐渐涌向日常生活空间,但对艺术如何介入社会实践继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在西方,“艺术介入社会”概念源于现代艺术。强调艺术介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从而使艺术成为与社会平等的感知领域。1978年,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社会雕塑”概念,即把感觉转换成对艺术或社会的思考及对人性的关怀和分析,为后来艺术从业者提供新路径——艺术介入社会空间。国内对于艺术介入的思考与研究至今尚处于探索阶段,方李莉提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在于通过艺术复兴传统的中国生活式样,修复乡村价值,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发展之路。”[1]刘姝曼则从人类学视角予以补充,并深入探讨人类学与艺术乡建的相互关系[2]。来洁与一木分别介绍许村“许村计划”和龙溪乡的“美丽乡村·动漫花谷”两个艺术介入项目,顾骏对这两个农村公共艺术项目的实施给予理论上的充分肯定[3]。
其二,关于艺术介入的社会实践。人类对于艺术介入社会的实践活动自上世纪开始从未停止,国内外诸多学者在田野乡村开展实验,继而引发后续理论界对艺术介入社会的广泛探讨。芝加哥大学学者Sol Tax于1948年率领一支人类学家团队在印第安人中实行福克斯计划,呼吁人类学家应以当地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为其行动指南;次年,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Alan Holmberg在维柯斯地区开展“自由社区”实验。在与受访者交流中不断获得其文化价值观念反馈,并有意识地完成介入式引导过程。我国艺术史很早即有“介入”传统,1931年初上海发起木刻运动便是艺术介入现代中国政治的发端。木刻运动关注时政和底层民众生活,很快使艺术成为大众公共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艺术经历从文人化到民众运动,再到政治运动转变。当代典型案例是1986年至2004年期间,美国费城艺术大学终身教授叶蕾蕾通过艺术教育与园林建设相融合,将一个肮脏的美国费城贫民黑人区,变成全国知名、生机勃勃的美丽社区,这是一次成功的艺术介入社会实践。二十世纪以来,我国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逐渐兴起,从2010年“台北国际艺术村”团队正式成立到2017年艺术家渠岩在顺德青田正式发布“青田范式”,越来越多艺术家通过艺术实践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现阶段,对于艺术介入问题研究侧重于乡村公共空间改造实践,艺术行为多以公共设施、装饰艺术等形式介入乡村文化,缺少对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全面清晰的理论研究与多元化实践探索。
(二)文化认同的研究
有关文化认同研究文献较全面。截至2018年6月,以“文化认同”为检索词,检索文献共15 697篇,相关著作1 112部,其中,以“乡村文化认同”为主题相关文献73篇,著作73部;以“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为检索词,检索结果为0。依据现有资料,文化认同研究可分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文化认同概念研究。关于“认同”(identity)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近代意义上的“认同”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1990),而有关“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概念目前还未形成一致结论。郑晓云指出,“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4]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文化认同是个体将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种文化中多数成员保持一致,表现为个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同程度。综上,当代理论界对文化认同研究往往从个体认同(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维度展开,其观点大致可归结为主观体验说与客观存在说,前者认为特定社会文化资源,包括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个体精神需求带来的主观体验是其获得文化认同的根源,具有稳定性与独立性特征。后者认为文化认同具有生存适应价值,这一独特文化系统客观存在于个体或群体的自我意识与先天气质结构中,人们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规范,影响其自身行为与观念。
其二,文化认同现状研究。文化认同现状研究,主要聚焦于单维与双维结构模式下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泰勒认为:“认同与道德方向感具有本质关系,个体缺失认同的同时则‘认同危机’得以产生,由此导致个体出现严重的无方向感和不确定性。”[5]曼纽尔·卡斯特则分析网络化社会中人们遭遇的文化认同问题,以及“认同危机”背景下如何让“认同的力量”在个人成长与企业中发挥作用。赵旭东将研究视域聚焦乡村社会,分析乡村潜在的认同危机的社会根源。石勇在研究中发现,文化认同危机促使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乡村普遍出现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与文化上的自我否定。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扩张与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
现阶段国内外对文化认同研究较充分,理论界在不断整合概念过程中逐渐丰富文化认同内涵,建立了清晰研究脉络。立足历史新阶段,将文化认同危机作为时代课题,从城市、乡村不同领域展开策略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大多局限于自上而下理论层面探讨,缺少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实践验证,尤其对艺术审视与观照不足,对艺术介入文化认同能力认识不够。随着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如何与时俱进走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乡村文化发展特色之路?如何正确审视艺术介入与文化认同之间内在关联?如何规范这种关系使其在乡村振兴之路上实现效能最优化?是时下亟待开展的课题。
二、艺术介入与文化认同之耦合关系
作为协同学的基本范畴,“耦合”一词特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元件或运动形式之间密切合作且相互影响的一种协同效应。20世纪60年代初期,德国物理学家Haken·H将这一蕴涵“协同”“合作”之意的物理概念引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以此描述自然界整体环境中不同属性与结构的系统间,或同一系统不同要素间通过非线性互动结合继而形成彼此作用与影响的关系,即“耦合关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等基本特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性质相近似的生态系统具有互相亲和的趋势,当条件成熟时,它们可以结合为一个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6]艺术介入与文化认同具有天然互动耦合关系,主要表现在艺术介入对文化认同功能的感性显现及文化认同对艺术介入形式的多元创造两方面。
(一)艺术介入对文化认同内涵的感性显现
文化认同即个体或群体在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从属于某一特定地域或集体的归属意识。其内涵表现为内部结构中个体或群体对相对稳定的文化资源、社会生态的亲近感,包括价值观念、民俗风俗、宗教信仰、审美取向等构成的身体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这种“自我”意识主导下产生的文化认同感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可以不受地域、环境、语言等限制而独立存在。”[7]此外,文化认同还表现为经由本民族文化价值标准校验后而产生的对于“他者”文化,即群体外部异质文化的认知判断与情感接受,其实质体现为“把人的主体性投射到文化认知活动及其成果中,将特定的民族文化认同对象的存在方式转化为主体的观念性存在[8]”,由此便为艺术介入与文化认同的耦合互动开启了通道。艺术以其形象性、主体性、审美性特质介入乡村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有助于通过艺术的认知功能,完成乡村文化认同内涵的感性显现。
艺术的认知功能自两千多年前便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论说中得以揭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行为产生于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本能模仿,模仿的相似程度越高越易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而这一“本能”模仿的前提便是认知。孔子曾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思想是对艺术社会功能较为全面的概括,其中“观”,即“观风俗之盛衰”,体现为人们对自然界及社会人生的观察、认知与理解,并将艺术视作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精神情感状态在心理层面的直接显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艺术(即审美)的方式是除却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及哲学之外的人类认知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作为人类认识社会的一种特殊途径,艺术认知功能不同于自然科学理性严谨的逻辑推演,而是将认知融汇在艺术的审美鉴赏过程中,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生活本质、展现民族历史与地域文化。如敦煌石窟壁画中描摹的亭台楼宇、历史传说、飞天佛像及劳动图景,是古人借以绘画艺术生动再现绵延千年的民俗风貌与历史文化。纪录片《丝绸之路》《唐蕃古道》通过影像艺术,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采撷璀璨的文化瑰宝予以展示、传播,以丰富的视听语言与结构形式彰显抽象民族文化精华,满足文化主体情感需求,继而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艺术介入行为建立在艺术认知功能基础之上,强化艺术在认识社会层面上的主导性意义,使艺术成为与社会平起而坐的感知领域,体现具有时代性、变革性、突破性的前卫精神。如景德镇宋代陶瓷文化村落的营造,以艺术介入重塑古镇特有的民族文化发展逻辑,将“忙时种田,闲时做陶”的生活方式传承于陶瓷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融中,瓷石古道的修葺、瓷器绘画的培育、宋代作坊的还原……在青山绿水间锁住乡愁,于真实体验中感知“水土宜陶”的文化意蕴。艺术家以敬畏之心介入乡村,以村民作为创作主体参与式艺术改造,将乡村文化主体精神融汇于本土传统文明复兴的内在逻辑之中,通过介入行为与文化认知的互动关系调整对话策略,激发在地村民的文化认知与主体意识,在改善乡村文化形貌的过程中理性面对外来文化移植与浸透,重建乡村本真的精神家园,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乡村修复计划”构想:“希望在尊重传统营造法式的前提下,用当代的技术手法修复传统民居和村落,在收集和整理传统手工艺基础上,找出与今天生活关联部分加以发挥推广,并与今天生活相通。复兴和传承传统节日与仪式,融入今天的生活方式与文明习惯,建立起一个全新和完整的活动空间系统以及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恢复一个有精神灵性、有伦理规范、彼此关怀和仁德本性的现代中国乡村。”[9]
(二)文化认同开启艺术介入模式的多元通道
内在于心理与人格结构中的文化认同归根结底体现在人们对其地域文化精神的认同,这种文化精神渗透在礼仪风俗、道德伦理、服饰工具等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中,外显为诸多艺术形式,并为艺术介入模式开启多元化通道。
梳理大量实践案例可见,时下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建构模式包括单线式与复线式两类,其中,单线式介入模式主要指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影像等单一艺术门类对在地乡村文化认知的非政策性介入,其艺术创作主体大多由艺术家或村民自发构成,这种自下而上式的介入模式极大程度地保持对在地文化的尊重。2018年4月,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十余所美术院校30余名艺术家组成涂鸦团队,汇聚山东寿光田柳镇东头村,用艺术和涂鸦方式重新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动力,村落民宅的墙体、房门、树干在艺术家的心灵点化下绽放出耀眼光彩,村民自发参与实践创作,其对家园的热爱与艺术家的愿望交织出灵感火花,最终完成绘画艺术改造乡村计划。同年5月,日本本州岛新潟县越后妻有地区举办了第十七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活动由著名策展大师北川富朗先生于2000年发起,作为生长于新潟县的本地人,北川富郎亲眼目睹了城市化严重破坏了越后妻有古老而传统的日本民间乡村文化,面对故乡的衰败与凋零,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佛像雕刻史专业的北川富郎希望借由艺术力量春风化雨般介入家乡文化复兴中,在越后妻有760平方公里土地上重新找回乡民共有的精神寄托。艺术家以破败老屋、古朴农田、纯净生态作为创作舞台,利用艺术设计作品传达乡村重建声音,这种将艺术创作融入日常生活常态的方式使新潟县村民在艺术体验中重拾文化自信。此项活动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北川富郎因此被誉为日本“艺术振兴乡村之父”。在我国,以村民为主要创作主体的艺术介入见于2000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郭净等人在当地三个藏区村庄——汤堆村、茨中村、明永村开展的“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艺术家指导村民掌握摄像机拍摄及后期基本编辑技术,通过参与式影像记录生活的途径激发村民认同并表达乡村文化,第一部作品即纪录片《黑陶人家》,展现汤堆村做陶工艺与日常生活,在“云之南”记录影像展放映后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与单线式介入模式不同,复线式介入模式是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元化的政策性介入,这种自上而下式的介入方式大多表现为政府主导的乡村旅游文化开发,借由“乡村意像”的建构满足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原生态文化心理期待,“宁静致远”“返璞归真”等典型乡村精神特质成为乡村旅游文化开发的心理基础,易唤起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艺术介入作为现阶段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必要手段,在乡村景观修复、传统民俗展演、文创产业建立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广西红瑶村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开发,以自然景观梯田耕地与人文景观民居村寨结合为基础,融汇民族歌舞表演、手工艺产品销售、木瓦民宿开发及民族传统节日之一——晒衣节的宣传推介等;哈尔滨市阿城区泉山下貌溪河边建立的满族风情园毗邻红星镇北赵村三合屯,园中随处可见极具满族特色的民间陈设——炕桌、炕柜、搁板、火盆……并将满族杀年猪的民间习俗重构为具有仪式感的祭祀活动,通过萨满舞蹈完成祭天、祭神、祭祖先的传统民俗事项,杀猪前将温烧酒倒入猪耳中,猪耳晃动意味着祖先、神灵已“领牲”。具有旅游开发性质的艺术介入行为,通过建构清晰的乡村景观意象与乡村文化意象实现乡村资源旅游化,对于恢复乡村传统文化与民族风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如美国学者乔治·马尔库斯与米开尔·费彻尔所言:“一种文化或者一个社区不是自在的、同质的,而应当被看做是不断流动的状态,是出于既外在于又内在于地方场合的广阔影响过程之中,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具有历史敏感性的抵制和兼容状态。”[10]因此,复线式介入模式下乡村旅游文化再建构是新时代条件下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加强乡村文化认同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文化认同主客体错位是现阶段广泛存在的问题。在复线式艺术介入过程中,村民由乡村建设主体——创造者、引导者变为参与者、服务者,乡村文化认同建构背后隐含着外来资本主导下经营管理模式与营销策略,因此,该模式下文化认同更多体现为“他者”认同,即城市人群对乡村景观意象与乡村文化意象的概念化理解与接受,并以此产生归园田居愿景及可持续消费动机,对乡村文化真正主体——村民而言,被动式接受文化修复与空间改造未能从根本上锁住“乡愁”,乡村也由此成为“他者”眼中的理想家园。
三、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建构规范
现阶段,通过艺术手段增强乡村文化认同模式在备受关注之余屡受质疑,原因在于尚未形成严格规范,导致在不同介入模式开展过程中,因艺术行为主体认知差异、动机差异带来诸多争议。因此,适时建立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的外部规范,有助于引导两者间耦合关系优化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乡村复兴。
(一)艺术介入的身份规范
马克思曾言:“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只有“行动着的‘群众’才能决定历史。”[11]在乡村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勤劳质朴的农民群众以其生生不息的劳动实践活动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乡土文化,同时也为其文化主体地位确立打下坚实根基。十九大以来,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战略进入具体实施新阶段,从改造农民到激发农民自主性,人们已充分认识到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是乡村振兴关键。作为乡村文化承载者与主力军,艺术介入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使其真正成为乡土文化创造的主人,在农民重拾历史记忆的过程中重构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用文化力量召唤远走他乡的村民复归山野田园,共同完成“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图景。在艺术介入过程中,艺术家是另一重要参与主体。艺术家以指导者角色参与其中,有利于倾听农民声音,激发农民创作热情与表达欲望,从专业角度解决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技术瓶颈。此外,政府角色定位应由传统领导者转变为服务者,在艺术介入的整体规划、资金投入及主流价值观引导等方面发挥有效服务与引导作用。挖掘乡村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宏观上把控单线式与复线式艺术介入模式的正确方向。推动民间文化组织发展,为乡村文化人才培育搭建平台。投资商在介入过程中应避免强行植入式的“他者”乡村建构,在政府监管下平衡乡村原生态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关系,继而保障农民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主体权利。
在农民、艺术家、政府等主体参与下,通过艺术介入手段建立高度地域文化认知,在古老民族文化基因基础上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的滋养,锁住“乡愁”,使其成为乡村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艺术介入的形式规范
传统乡村文化认同的形成经历漫长且不断支解与离析的适应过程,因此,时下农民文化认同的重构绝非一蹴而就,需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弥合传统文化裂隙,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开展介入式引导。艺术介入必定是持久、循序渐进的局部介入,而非“填鸭式”或“移山填海式”的表面粉饰,不能追求文化大繁荣表象,而忽略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的根本诉求。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江西村的文化认同建构中,艺术行为历经十余年渐入式介入,最终从村民自发性单线式介入模式自然演化为多元主体参与的复线式介入模式。每年阴历6月15日流头节,江西村朝鲜族民众自发地聚集到小河边开展“东流水沐浴”仪式,祈求洗去污浊之气换取幸福安康。此方式在时代演进中不断汇入新的艺术形式。从2005年至2018年,流头节开始由传统单一的“东流水沐浴”仪式逐渐恢复祭拜农神、农乐舞表演、朝鲜族竞技比赛、流头宴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吸引在外务工的村民及朝韩友人纷纷返乡庆贺,引发艺术家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纷纷出资献策助力江西村文化建设。这种以局部带动整体的艺术介入策略在横跨十余年的持续建设中,避免了简单的大规模乡村“翻新”给村民带来的陌生感与排斥感,是完全依靠农民心之所向完成的从单个民族仪式认知到整体文化认同复苏的蜕变。
(三)艺术介入的文本规范
对“艺术文本”概念的描述始见于20世纪初诸多文艺理论研究中,大多以“作品”形态供接受者认知与解读,并通过不同艺术语言阐释具有整体性意义的组织系统。对文本的阐释直接影响接受者认知其在地文化,需在艺术介入之初对其进行文本规范。
首先,日常化组织建构。乡村艺术形式根植于漫长的乡村生产实践活动,人们在日常劳动中发出有规律节奏、韵律逐渐形成民间音乐的根基;鱼皮、兽皮、树皮等劳动成果成为绘画艺术的天然载体;庆贺丰收或祭祀祖先时的肢体动作演化为传统舞蹈进而表达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均离不开以实用为目的的乡村日常生活,借由不同物质载体表达作者审美情感。艺术介入文本建构应延续古老民族文化融汇于日常生活的叙事机制,通过裹挟情感与意愿的符号体系唤醒村民历史集体记忆,在天然、朴实、纯粹的审美视域下实现当代乡村文化认同的话语表达。
其次,类型化文本书写。乡村传统艺术是由村民集体创造,表达其生活趣味、风俗信仰等广为流传的综合形态,是乡村典型文化标识,具有类型化、程式化、仪式化等审美特征。通过师徒传授、家门传承等世代沿袭的传统艺术具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从创作思维到技艺手法均呈现出对前人成果的遵从与效仿。类型化文本书写造就不同乡村社会文化符号的差异性,在艺术门类选择、艺术语言运用等方面彰显“自我”之于“他者”的独特魅力,以此增强本民族文化认同。
最后,在地化场域选择。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市场经济因素制约,乡村传统价值观念日渐消解的同时也吞噬着曾滋养民间艺术的肥沃土地。伴随乡村旅游热潮兴起,艺术文本成为“他者”凝视下满足其消费欲望的无生命力的文化景观形态,传统文本组织结构在此权力关系运作中发生变异——斩断了根,失去了魂。“对民间艺术的意义把握不能简单地单纯地将其从当时当地的情境中剥离,而应该注意其表征意义的语境化特征,提倡‘介入性审美’,在具体的活动场域中体验民间艺术的丰满意义。”[12]艺术文本在现代建构过程中应充分凸显在地化场域的重要职责,努力谋求乡村文化再生与认同间的平衡。
四、结语
艺术介入乡村目的在于重建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在两者不断优化的耦合关系中修复历史集体记忆,用青山绿水留住原汁原味的乡愁,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重拾乡村文化自信。以艺术介入手段重塑民族文化形象,在美丽乡村建设道路上营造诗意栖息的文化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