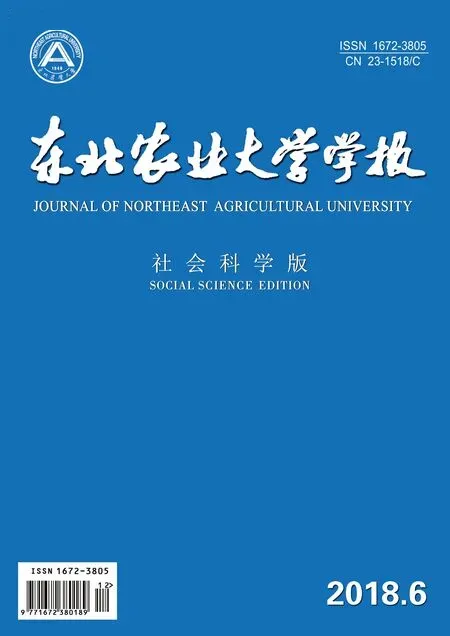《死魂灵》的庄园文化时空观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洛特曼在研究文化符号学时,指出“空间不只是看待问题的一个视角,而是一种根本的方法论。”[1]在时空问题上,洛特曼认为:处于一个时空中的物体,并非静止物质,而是带有自己记忆的活的因素。因此完全可通过时空中的可见物透视地主的不可见灵魂。
1809年,果戈理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素罗庆采镇。作家从小在地主家庭中长大,地主的生活环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842年出版小说《死魂灵》,果戈理描写了五个地主,嘲讽其丑陋行为,揭示俄国社会弊病。读者在嘲笑之余,也发现作者笔墨中不乏同情,此与作家出身有关。众所周知,果戈理的地主出身使其“在对俄罗斯农奴制的腐朽充满仇恨之时,又难以割舍一线希望”。[2]本文以地主生活的庄园作为分析对象,剖析地主性格特征及其成因。
俄罗斯庄园文学是俄罗斯文化史中独特现象,有特殊美学含义。文化意义上的庄园主要兴起于18世纪中叶,庄园保存人们的记忆,让庄园主人感受其在世袭高贵家族中的地位。庄园主题源于19世纪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描写。果戈理在小说第六章开头部分写到:“我可以根据宅地样式猜测这家主人是什么样人,长得胖不胖,有没有儿子,还是一口气生了六个女儿,个个笑声清脆,喜欢玩耍。”[3]可见,居住环境对果戈理建构作品的作用。
一、庄园的空间形象:房屋及外部景物描写
果戈理关注社会日常环境,他精心设计主人公所在地周边环境,借助主人公生活的物质世界展现其精神面貌。环境描写则集中于房子外部环境和屋内装饰上,并非简单陈述地主的居住条件,而是具有一定情感评价和内涵。在果戈理笔下,“对环境的描写,无不鲜明而恰当地映衬出主人公的形象特征,成为刻画主人公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4]
洛特曼研究但丁《神曲》时指出,垂直的轴线“‘上—下’组织了整个文本的意义构造。”在《死魂灵》中,作家将乞乞科夫拜访五位地主的路线设为从玛尼洛夫到泼留希金,正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精神堕落走向。
乞乞科夫拜访的第一个地主是玛尼洛夫,玛尼洛夫庄园具有“英国风景”特点,因而玛尼洛夫其人被印上人类精神文化承载者的记号。两层石头房子矗立在“光秃秃的山顶上,不管刮什么风,都没有遮挡。山坡上铺着草皮,剪得倒也整齐。草坪中间仿效英国式修成两三个花坛,上面种有丁香和黄槐。有些地方长着白桦,五六棵长在一起,树梢上叶子细小,稀稀落落。”[3]此情景可见庄园无人经管。“幽思之所”证实玛尼洛夫有高远思想和理想追求。玛尼洛夫在五个地主中第一个出场,他既不行善也未做恶,毫无个性,而其他人物则表现出鲜明个性。
果戈理描写贵族地主庄园,揭示主人公性格特征,展现其心理活动状况,具有讽刺性。庄园场景布局体现主人公受过教育,但附庸风雅。玛尼洛夫庄园并不小,通过地主和民房描写,发现农奴同玛尼洛夫一样懒惰。因而果戈理对地主们高声疾呼,“离开大城市,你们总在那里挥霍钱财,回到上帝赐给你们的田地里去。上帝给你们天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你们能变得像黑土地一样富饶;在你们慈爱的监管下,农奴们将精力充沛心情愉快,他们会满怀感激地劳作。‘地主们的事业是神圣的’——这就是果戈理布道的主旨。”[5]玛尼洛夫身上不见剥削和残暴特征,反而若隐若现地显现出良好品质,他的农奴虽不富有,却也未曾遭受苦难,生活很自由。
乞乞科夫来到玛尼洛夫房前,发现共济会两个象征物:公鸡和题词“幽思之所”。“公鸡”预兆变化了的政治气候,1789年革命之后,公鸡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徽章。凉亭上“幽思之所”同共济会对真理的理解及自我完善的事业吻合,玛尼洛夫庄园里的英国式花园设置,旨在赋予主人公自由主义思想,果戈里借此讽刺盲目的西欧自由主义。
乞乞科夫拜访玛尼洛夫后来到科罗博奇卡院落,女地主庄园简朴,领地不大,但生机盎然。女地主凡事亲力亲为,关心一切可获利之事。院子里到处是家禽和家畜:“火鸡和小鸡数不胜数,它们中间还有一只大公鸡迈着方步走来走去,不时摇摇冠子,歪歪头,仿佛在倾听什么。还有一只母猪带着全家也来到这里”“栅栏外面是一大片菜地,种着圆白菜、洋葱、土豆、甜菜和其他蔬菜。菜园里还零散地长着几棵苹果树和其他果树。果树上面用网罩住,防备喜鹊和麻雀来吃。这里的麻雀像一大片斜飞的乌云飞来飞去。为赶跑麻雀还在长杆上立了几个稻草人,伸开两臂,其中有一个戴着女主人的睡帽。菜园对面就是农民住的小木房,木房虽然修得零零散散,构不成整齐的街道,然而据乞乞科夫观察,倒也证明他们的住户生活充足,因为这些木房维修得很好,房顶的旧木板都换成新的,家家的大门都不斜歪,他还发现朝向他这边的带顶棚子里都放着几乎崭新的大车,有的人家甚至有两辆。”[3]因科罗博奇卡专注于庄园管理,她的农奴丰衣足食,同玛尼洛夫形成鲜明对比。
诺兹德廖夫是乞乞科夫拜访的第三个地主,他们在驿站相遇,诺兹德廖夫劝说乞乞科夫到家中做客。刚进院子,诺兹德廖夫就立刻展示他的马厩,“里面有两匹骡马,一匹是菊花青,另一匹是金栗毛马,另外还有一匹枣红色马驹,样子不起眼,可诺兹德廖夫却诅咒发誓说,他是花一万卢布买的。”[3]诺兹德廖夫既爱吹牛又爱说谎。乞乞科夫参观养鱼池时,诺兹德廖夫说:“池里的鱼非常大,两人抬一条都难以抬出来。”[3]然后去看水磨坊,“魔盘上缺少磨脐,就是磨扇按上去就可以飞快旋转的铁垫,按照俄国农民的绝妙叫法,就是‘转子’。”[3]这样的磨盘无从磨磨。诺兹德廖夫又带乞乞科夫参观他的田界,“可是地里很多地方都是草墩子。客人不得不在休耕地和刚翻过的田地里绕来绕去。”[3]主人公展示的只是田地边界,而非庄稼。经此一番折腾,乞乞科夫感到疲倦。诺兹德廖夫庄园几乎完全荒废。作家叙述由近及远,延伸读者空间视野,让人很难捕捉诺兹德廖夫的真实生活。
乞乞科夫又拜访索巴凯维奇,不像其他地主,索巴凯维奇精打细算,是个狡猾吝啬的商人。他同爱幻想的玛尼洛夫、喜怒无常的科罗博奇卡及愚钝爱攒钱的诺兹德廖夫不同。索巴凯维奇家所有布置均很牢固,以突出其性格特征。
索巴凯维奇田庄各角度均展示出坚固特点。“左右各有一片树林,像翅膀向两边伸开:一边是白桦林,颜色浅些,一边是松林,颜色发深。正中间是一座带阁楼的木房,红屋顶,深灰或者说暗灰色的墙,样子很像军屯或德国移民住的房子。”[3]房主人为求方便改变房屋结构,“一眼就看得出来,当初修房子时建筑师曾和房主人的爱好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建筑是墨守成规,样样都讲对称,而房主人只讲实用,显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房子两侧本应该都留窗户,但有一侧却被砌死,只留一扇小窗,大概为了给昏暗的仓房透些光亮。”[3]就连正门上的三角楣饰都没安放在正中,“因为主人下令把边上的一根圆柱取消,于是原定的四根柱子只剩下了三根。院子周围的栅栏也是用非常粗的木头修的,显得非常结实。”[3]这位地主极其讲究坚固耐用,连马厩、仓库和厨房皆以又粗又沉的圆木修建。村中农民木房也盖得很结实,“一色用圆木垒的,既不刨光,也没有雕饰或其他装潢,不过房子盖得倒也结实,严丝合缝。井台也是用最结实的柞木修的,这种柞木一般用于修磨房或者造船。总之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有一种既结实又笨重的特点。”[3]稳固结实正是索巴凯维奇的特点,生活环境展示其性格特征,也揭示其畸形生活,四根柱子只用三根,本应有窗的两侧被砌死。果戈理总结道:“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非常坚固而又非常笨重,跟这家主人相似到令人奇怪的程度。”[3]笨重的物品体现索巴凯维奇求实的生活态度,但也因此失去生活之美。
乞乞科夫最后拜访的地主是泼留希金,他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的只是一个居住空间,而非“家”。他不知何为美,何为丑;他丢掉有价值之物,留下无用之物。果戈理对泼留希金庄园描写极其出色,展现的庄园景物“都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活动的需要,经过精心安排,由远及近,由外到内,升堂入室,逐层刻画出来的。”[4]
乞乞科夫发现所有建筑物均很破旧:“房子的窗户都没有玻璃,有的挡块破布或一件粗呢子上衣。有些俄国式木房不知为什么在房檐底下修阳台,还带栏杆,可是已经歪歪斜斜,甚至黑得难看。”[3]可见房屋年久失修,就连屋后的麦垛,皆因放置很久而变色。随后看到泼留希金如同行将就木的老者般长长的宅地,“屋顶发黑,已经不能处处庇护老屋的平安,屋顶上耸立着两个望楼,彼此相对,也已歪斜,从前刷的油漆都已剥落。房子的墙壁有些地方裸露出抹灰的板条,显然由于天气恶劣、风吹雨淋和秋天气候多变而备受摧残。只有两扇窗子开着,其他窗户或关上窗板,或甚至钉上木板。连这两扇开着的窗子也黑糊糊的:其中一扇糊着三角形的蓝色糖纸,显得发黑。”[3]作者多次使用“黑”字,有意呈现一个密不透气的空间,让读者迫切想进入这座废弃城堡一看究竟。善于卖关子的作者有意拖长叙述,读者跟随乞乞科夫脚步来到泼留希金宅地门前,看到一片凄凉景象,“院墙和大门的木头都长满青苔。院子里簇拥着各种房子,有下人住的屋子,有仓房和地窖,显得破旧不堪;左右两侧还有大门通向别的院子。”[3]说明此处曾经繁华,如今冷冷清清,一切了无生机。“平时正门也是紧紧关着,因为铁门环上挂着一把巨大的锁头。”[3]锁头象征地主的腐朽生活已被封存。
泼留希金花园是唯一有些生机之处。地主庄园和村子似乎已无生命迹象,与之对比,花园令人联想美和生命。“茂密的绿色的树丛有的地方也有空隙,阳光可以照射进去,中间找不到的凹处形成黑色,好像野兽张开的大嘴。凹处完全被阴影所笼罩,从它那黑糊糊的深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些东西:一条小径、一片倒塌的栏杆、一座摇摇欲坠的凉亭、一颗带树洞的老柳树,从柳树后面伸来颜色发白的灌木,密得像猪鬃枝叶虬结,并由于生得过密而干枯。还有槭树的一根嫩枝也从一旁伸出巴掌似的绿叶,其中有一片叶子不知怎么竟然有阳光钻到后面,把它照得火红透明,在浓荫之中放出异彩。”[3]果戈理将内在精神注入花园,将泼留希金歪歪斜斜的房舍与室外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对照,将日常生活与具有精神象征的花园先后置于读者面前,让读者从死气沉沉之地步入一派生机的大自然。花园象征心灵空间,高大的杨树、嫩枝、绿叶、阳光,无不使花园增添生命活力,花园的纯真与浪漫是人的心灵诉求。不由令人感悟:与其为追求物质财富耗尽一生,不如重归朴素无华的大自然,那里才是心灵的归宿。
二、庄园的时间物语:画及其他物品
画卷及一些特殊物品成为被凝固的时间、被凝固的情感、叙事发展的见证。果戈理向读者展示地主房间时,读者常把目光放在地上物品,然而墙上的画作也不容小觑,它如同历史文献,告诉读者地主也曾渴求艺术和美好生活。一幅发旧变黄的画,将作者叙事空间延伸到主人公过往,深入其灵魂深处。乌克兰文学理论家别莱茨基(А.И.Белецкий)在《艺术家的作坊中的词语》使用“静物画”(натюрморт)一词。别莱茨基写道:在现实主义文学中,静物画完成背景功能,能够反映人物内心状况,此观点有助于分析果戈理的《死魂灵》。“静物”在法文中指无机界。静物画在造型艺术中指“描绘没有生命的事物,如花、果实、猎获的野物、器皿、用具、标本以及蒙上各种织物的台子、背景等等。静物画体现物质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它肯定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环境绕着人们的普通的、平常的事物的美学价值。”[6]
果戈理细致描写了书房。玛尼洛夫书房不大,“墙壁刷成淡蓝色,又好象淡灰色,里面有四把椅子,一把圈椅,还有一张书桌。桌上摆着前面有幸提到的那本书,还夹着书签,另外还有几张带字的纸。”[3]当进入他的书房中,立刻会发现,作者一直关注蓝色,暗示玛尼洛夫善于幻想且具感伤情怀。
科罗博奇卡屋内装饰既朴素又老套,“墙上糊的带斜纹的壁纸已经很旧,挂着几幅花鸟画;墙壁中间挂着旧式小镜子,深色镜框刻成树叶形状;每块镜子后面都放着书信、旧纸牌或袜子;还有一个挂钟,表盘上画花。”[3]第二天早晨乞乞科夫醒来时,发现墙上的画不都是花鸟,“其中有一幅库图佐夫的肖像,还有一张老者的油画像,他穿着保罗一世时代的制服,镶着往外翻的红袖头。”[3]墙上表盘上画花的挂钟也很奇怪,“挂钟丝丝作响。”[3]这些花鸟画及镜子、纸牌具有虚空静物符号特点:“虚空静物画主要描绘的是颅骨、沙漏、怀表、镜子、烛光、肥皂泡、花、水果、蔬菜、动物、乐器、武器、纸牌、骰子等等。”[7]花朵美丽,但生命短暂,象征女地主早已远逝的青春,“静物画中,花卉常常象征着青春易逝、岁月无情。”[8]小说中,果戈理并未描述女地主容颜,但从乞乞科夫反应可猜测,科罗博奇卡是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女性。科罗博奇卡生活殷实、富足,但很低级,因此作家总把女地主的生活环境同动物(很多家畜)和植物(挂钟表盘上画着花,树叶形的镜子)联系在一起:客人因苍蝇侵扰而醒来,钟表发出可怕的声音,院子里挤满动物,发出嘈杂的声音。
当乞乞科夫来到诺兹德廖夫家时,“家里并没有一点准备待客的样子。餐厅正当中摆着木头架子,有两个庄稼汉正站在上面刷墙,还没完没了地哼着歌;地板上洒满白灰浆。”[3]地主带乞乞科夫参观他的书房,这是与人的精神灵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可“他的书房丝毫没有一般人家书房的样子,也就是说,既没有书,也没有纸,只是墙上挂着两把马刀和两支枪,一支枪花了三百卢布,另一支花了八百卢布。”[3]而后诺兹德廖夫又带他看土耳其匕首,“其中有一只刻得不对头:萨韦利·西比利亚科夫制造。”[3]他的书房表现出军人气质。马刀、枪和匕首象征诺兹德廖夫好斗性格,其难以抑制情绪冲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房间布置充分反映主人性格,书房与其精神世界完全隔离。诺兹德廖夫爱好打猎,具有军人气质,这与其爱赌博爱闹事的性格相得益彰,“在冒险中寻求刺激,喜爱冒险本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9]无论打架还是牌桌上对峙,同样需旺盛精力和超人胆识,因此诺兹德廖夫的“率真”竟有些可爱。作家用“手摇风琴”巧妙揭示主人公性格的另一侧面。“没等玛祖卡舞曲响完,就放出《马卡菠萝出征歌》,没等出征歌完,又突然响起一支非常熟悉的华尔兹舞曲。诺兹德廖夫早已不摇了,可是风琴里还有一根管子怎么也不肯停下来,还独自响了很久。”[3]手风琴在此处起象征作用,诺兹德廖夫变化无常的性格如同频繁更换曲子一样,说变就变。
果戈理在描写索巴凯维奇时,把读者视线吸引到很多英雄画像上,作家对画像的处理较为复杂。画像一方面成为买卖死魂灵卑劣行为与英雄丰功伟绩的对照,另一方面表现索巴凯维奇尚对美好事物心存向往,其心灵与英雄窃窃私语。当乞乞科夫进入客厅,看到墙上的画,“画上全是英雄人物,全是希腊将领的全身版画像。其中有马夫罗科扎托斯,穿着绿制服、红裤子,鼻子上架着眼镜;有米阿乌利和卡纳里斯。这些英雄都长着挺粗的腿和没人见过的胡子,真叫人不寒而栗。”索巴凯维奇本身“长得健康结实,便希望他的房间里挂的画像也都结实健康。博别丽娜的画像旁边,紧靠窗户挂着一个鸟笼,里面养着一只黑毛带白点的鸫鸟,样子也极像索巴凯维奇。”[3]索巴凯维奇房间所有东西均与主人相似。“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非常坚固而又非常笨重,跟这家主人相似到令人奇怪的程度。客厅的墙角上放着一张胡桃木写字台,肚子特大,腿特粗,跟熊一模一样。桌子、椅子、圈椅——一切都显得又笨重又不安生,总之,每件家具、每把椅子都仿佛在说:我也是个索巴凯维奇!”[3]当乞乞科夫和索巴凯维奇商谈死魂灵价格时,“鹰钩鼻子的巴格拉季昂从墙上聚精会神地看着这场交易。”[3]英雄画像装饰着索巴凯维奇的客厅,果戈理同时代人很了解且尊敬为自由而战的英雄,英雄形象与一心谋私利的地主商人形成鲜明对比。
当乞乞科夫进入泼留希金住地,他看见“外屋昏暗而宽敞,就像进地窖似的让人觉得浑身发冷。”[3]然后他从外屋进入房间,这是一间“黑屋子,里面略微有点亮光,是从另一扇门底下的大风子露出来的。他推开门,终于走到亮堂地方,不过眼前的杂乱景象令他大吃一惊。这家似乎正准备擦地板,把所有的家具都堆到到这个房间”。[3]
柜橱里和桌子上物品如同静物画般突显文化记忆,物品记载着泼留希金的生活历史。“桌上放一把破椅子,椅子旁边放着座钟,座钟停了摆,摆上挂着蜘蛛网。桌子旁边放着柜橱,侧面朝墙,里面装着古旧的银器、中国瓷器和几个长颈瓶。还有一张螺钿写字台,台面有的地方贝壳脱落,露出一道道小沟,里面涂着胶因而发黄。写字台上也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堆布满细小字迹的纸片,上面用发绿的大理石镇纸压着,镇纸带有一个小圆把手,有一本皮封面的旧书,裁口刷成红色,有一个柠檬,干皱得榛子大小,有一个圈椅的破扶手,有一只高脚杯里面不知装的什么液体,却落进三个苍蝇,上面用信封盖着,有一小块火漆,一块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破布,两只鹅毛笔沾满墨水痕迹,干巴得像得了肺痨病,还有一根发黄的牙签,大概主人还在法国人攻打莫斯科之前就用它剔过牙。”[3]古旧的银器、中国瓷器和几个长颈瓶、螺钿写字台,这些物件象征着财富,与尘世存在紧密关联;布满细小字迹的纸片,大理石镇纸,皮封面的旧书,这些物品暗示泼留希金尊重知识,受过良好教育,也曾有求知欲;柠檬、高脚杯则表示主人也曾幸福、愉快地生活;而如今落进三只苍蝇的杯子和一块不知何处捡来的破布,两支干巴鹅毛笔则反映泼留希金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停止摆动的座钟,仿佛暗示时间已经凝固,生活的快乐和低沉以此时间为分界。果戈理犹如画家,通过描述主人公家中代表性物品,让读者感受泼留希金生活的动态过程。“文化是记忆。因此文化总是与历史相连,总是意味着个人、社会和全人类的道德,智力与精神生活的连续性。”[10]泼留希金家墙上也有画。“墙上只挂了几幅画,却挂得挺满,而且杂乱无章:有一幅版画挺长,已经发黄,镶着红木框却没有玻璃,木框用青铜丝嵌着,四角还嵌着铜环。画面上是一场激战,战鼓画得老大,士兵头戴三角帽,正在呐喊,战马纷纷落进水里。旁边是一大张大幅油画,已经发黑,上面画的是花卉、水果、一个切开的西瓜、一个猪头和一只倒挂的鸭子。”[3]第一幅画凝聚动作和声音,表现战争画面的戏剧性和灾难性,呐喊中死去的士兵和落入水中的马暗示战败。果戈理采用存在于一定空间中,以静止形式表现动态过程的造型艺术,具有俄国画家勃留洛夫启示录风格。“水中或泥坑”象征地狱。斯米尔诺娃在《果戈理的诗学‘死魂灵’》中指出,小说第一卷全部思想均被俄罗斯现实映照,现实同最阴暗的地方一起,就是地狱。在小说中,常见“向下陷和向下去”的画面,如乞乞科夫和他的马车先后两次掉进泥坑:一次在科罗博奇卡家门前,他从马车掉进泥坑,后又在诺兹德廖夫家附近陷入泥潭。泼留希金家中悬挂马被淹死的画作,再次阐释“地狱”般从昏暗到漆黑的次第光谱。
三、结语
果戈理是杰出的艺术语言大师,其代表作《死魂灵》以庄园内部和外部景物描写,展现生活其中的人物性格。地主彼此类似而又不尽相同,果戈理赋予每位主人公以日常生活的最明显特征,他的小说如镜子般反映地主阶层的精神贫乏和道德堕落。实际上,《死魂灵》欲表现人类所有缺陷。作者讽刺为权利和金钱而生活的人,他们忽视了“永恒”的价值。他们看似活人,但灵魂早已死亡。此类问题产生不仅源于人自身,还有社会和时代的影响。类似于小说中的人类愚昧和贪婪的缺陷尚未消除,因此《死魂灵》在当今仍具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