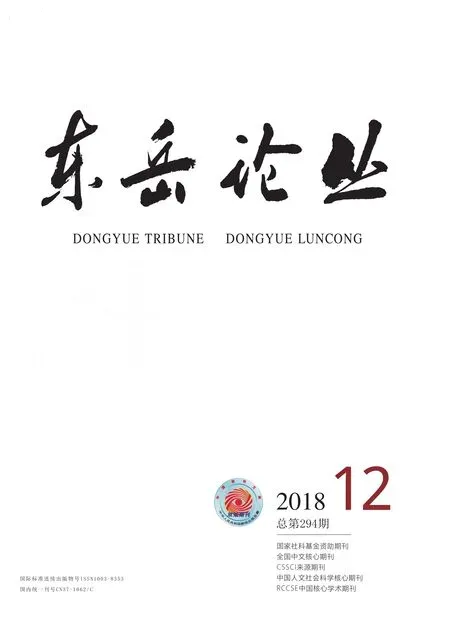叙述分层与主体分化
——论一种小说叙述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邓 艮,乔 琦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从古希腊《荷马史诗》、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印度故事集《五卷书》、清代《豆棚闲话》《红楼梦》,到现代小说如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黑塞《荒原狼》、莱辛《幸存者回忆录》、门罗《孩子的游戏》、麦克尤恩《赎罪》、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谭恩美《接骨师之女》、阎连科《炸裂志》、莫言《蛙》等,小说的叙述分层可以说已足够支撑起一种小说叙述传统。而且越到现代,小说的叙述分层现象越普遍。目前学术界对叙述分层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较多,但对分层的原因和意义尤其是它与现代主体分化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论文在参阅中外学者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尝试从言说空间的拓展、自我之谜的揭示和人与世界之关系建构三个层面,揭示叙述分层这一小说叙述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一、叙述分层及其形式结构
在现代小说中,随着显身叙述者和限制性人物视角越来越多地在叙述中被巧妙使用,小说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等主体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分歧。比如黑塞的《荒原狼》,开篇“出版者序”的部分,在显身叙述者和次要人物视角构成的叙述方位当中,推出的是一位神秘主角,以不合群的狂傲为特征。主体部分“哈里·哈勒尔自传”则在显身叙述者和主要人物视角构成的叙述方位中展开,“我”是一个患有痛风和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极度痛苦和孤独,甚至想以自杀获得解脱。从整部小说倒推回来,隐含作者似乎想给我们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反启蒙精神和反二元对立之后,归还世界它本应拥有的经验性和当下性。显而易见,《荒原狼》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像“灵魂从来不是统一的”[注][德]赫尔曼·黑塞:《荒原狼》,赵登荣、倪诚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这种不统一,确切地说文本中因冲突对抗和不确定性而形成的张力究竟源自哪里呢?笔者以为,除了上面提到的基本的叙述声音、叙述视角以及由此组合而成的叙述方位带来的影响,更要注意叙述结构的非平面化对文本深层意蕴的激发。“出版者序”“哈里·哈勒尔自传”以及该小说中嵌套的一篇文章“论荒原狼——为狂人而作”等,这些叙述在空间化的时间中,错落有致地架构起立体结构,使我们可以直接感觉到叙述层次的区隔。
关于叙述的层次问题,国外学者如普林斯的《叙述学词典》中至少有以下词条指向叙述层次的区隔:转叙(metalepsis)、嵌入式叙述(embedded narrative)、套层结构(mise en abyme)、框架式叙述(frame narrative)、元故事叙述(metadiegetic narrative)等。热奈特、内勒斯等叙述学家分别以不同的术语论述叙述层次问题,但都没有清楚地给出不同叙述层次之间的生成关系。国内学者赵毅衡明确提出“叙述分层”[注]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并指出叙述分层如何成为可能:“当被叙述者转述出来的人物语言讲出一个故事,从而自成一个叙述文本时,就出现叙述中的叙述,叙述就出现分层。此时,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变成另一层叙述的叙述者,也就是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注]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仍以《荒原狼》为例来说清这一问题。“出版者序”为第一层叙述,也是最高层次叙述,通过显身叙述者兼次要人物“我”引出神秘人物“哈里”;而“哈里”在第二层叙述中成为主要人物兼显身叙述者,在“普通人/狂人”的二元对立格局中质疑第一层叙述带给我们的“狂人”印象;“哈里·哈勒尔自传”中嵌套的“论荒原狼”的文章构成第三层叙述,以清醒的理性反驳前面两层叙述中共有的非此即彼逻辑——狼性和人性、欲望和精神、圣人和浪子等任何一组二元对立都只是人类灵魂的一小部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多元而复杂。《荒原狼》解构了歌德的“浮士德难题”中所包含的启蒙精神,最终以充满狂欢意味的“魔剧院”揭示出生活流当中主体性的萎缩。小说文本中隐含的戏剧性翻转之所以能够被解读出来,显然与“叙述分层”理念的引入有重要关系,正是在“分层”思路层层剥茧式的推进中,多种共存的思路和意蕴才得以浮现。
20世纪以来,小说形式技巧花样翻新,如若不注意叙述形式,只把小说当作整一的故事来读,就可能会读不通或者捕捉不到文本意图。叙述分层对平面化阅读挑战最大,各层次叙述的区分不只是把故事分装在不同的容器里,形式本身往往有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多丽丝·莱辛、爱丽丝·门罗、伊恩·麦克尤恩等都在小说中对叙述分层做了精彩演绎。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通过叙述分层这个形式框架,自然而然地跨入未来世界。“当我再度发现自己站在家里的客厅,一支香烟已燃烧过半时,留给我的是对一个许诺的坚信,无论以后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和那些隐藏的房间里,情况变得多么艰难,这种坚信都不会离开我。”[注]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朱子仪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页。这个句子标示出回顾讲述即将开始,在此之前的叙述讲到过去的某个时代,特别细致地描绘了客厅的一面墙,没有门没有窗,再普通不过的一面墙,即使写到“我”穿过这面墙去看墙后面的世界也显得极为平常。《幸存者回忆录》被称作幻想小说,当然也只有在认识它这个型文本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解小说中那个混沌的时代。叙述时间永远指向过去,未来小说也一样,只不过以时间参照系的方式显示叙述的事件发生在叙述行为之前,小说第一部分恰好构成第一层叙述,解释“回忆录”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这里的第一层叙述也是超叙述层。借助叙述分层,《幸存者回忆录》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和未来小说结合的范例,以现实的笔法写虚幻,扰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时间铺展,逼真的危机感迎面而来:幻想世界中的灾难也可能随时爆发在现实世界中!
虽然叙述分层到了现代才较多出现,但也并非现代小说所独创。事实上,古代叙述文学中早已存在这种形式结构,并呈现出三种发展脉络。第一种,古希腊史诗《伊利昂纪》对阿喀琉斯铠甲上的图案进行的详细叙述,已经显示出“故事中套故事”的分层雏形。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俱卢族和般度族的主故事之外有大量插话,如“蛇祭缘起”“金翅鸟救母”“沙恭达罗”“罗摩传”等都作为独立故事而存在,这种模式发展到后来就是“故事中套故事”的叙述结构;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戏中戏”也属于这一模式。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里谍战和侦探的故事嵌套着迷宫的故事,在极其紧张的情节中凸显了网状的时间迷宫,“时间是永远交叉着的,直到无可数计的将来。在其中的一个交叉里,我是您的敌人”[注][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第二种,《奥德修纪》中,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历尽艰辛漂泊海上的故事是他自己讲述的,这种模式在后世文学中延续下来,形成“隐身叙述者”+“显身叙述者”或“显身叙述者a”+“显身叙述者b”的层次组合,在讲述个体人生经历的小说中比较多见。比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两层叙述都由显身叙述者讲述,第一层叙述是“显身叙述者a+次要人物视角”,“我”在叶蓝卡河的渡口碰到一个极度悲痛忧郁的男人,他对“我”讲述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第一层叙述中提到的人物成了第二层叙述中的叙述者,形成新的叙述方位——“显身叙述者b+主要人物视角”,经历过战争痛苦的“我”讲述自己的经历更有信服力。
第三种,印度故事文学《五卷书》、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均是在开头有个引子,引出后面的主要故事,此为后世总结的“框架结构”。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果戈里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等小说都是框架式叙述分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会饮篇》大致也属此类,在层层转述中所谓真实早已无据可考,而这一叙述形式与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无得亦无失的爱与美的最本质存在完美契合。
叙述分层从古至今在世界各国文学中都有发展,目前至少可以总结出上面提到的三种发展脉络,足以称之为一种小说叙述传统。而现代小说在形式上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分层传统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管分层形式如何千变万化,究其根本,乃出于复杂化的现代世界中主体的不统一。下面将围绕主体问题讨论叙述分层的深层意义。
二、叙述主体权力分化与言说空间的拓展
西方文论的“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中,最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影响可谓深远。1969年福柯在题为《作者是什么》的演讲中激烈驳斥作者中心,他指出:“我们很容易设想这样一个文化,在那里,话语可以无需任何作者而流通”,谁是真正的作者并不重要,另外一些问题更值得期待:“这种话语有哪些存在模态?它从哪里来?它如何流通?它受谁控制?针对各种可能的主体将作出怎样的安排?谁能实现主体这些各不相同的功能?”[注][法]福柯:《什么是作者》,见唐纳德·普雷齐奥西主编:《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7页。的确,意义难以统一于单一的作者主体,一旦进入叙述,主体必然发生分化,人物主体和叙述者主体之间的权力互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本的形式风格。小说中的不同转述语很能说明主体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间接引语中叙述者主体强度最大,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多通过间接引语的方式转述人物的话;而直接自由式的转述语当中人物主体强度最大,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形式特征就是直接自由式转述语的大量使用。实际上,转述语足够长就会形成叙述分层;分层伴随主体权力的分解而产生,高层次叙述向低层次叙述提供叙述者,也正是高层次叙述者主体对人物主体让渡权力,赋予人物话语权,使其成为另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叙述主体。
尽管我们知道虚构叙述中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等同于叙述者,但现实中也不乏作者为叙述者承担责任的例子,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昆德拉等都曾因其创作而受到威胁。叙述者和作者容易被混淆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韦恩·布思在2005年发表的《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一文中重申设立“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对学生们混淆第一人称叙述者和作者感到忧虑”[注][美]韦恩·C·布思:《隐含作者的复活》,申丹译,《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叙述者只有和作者拉开距离,叙述才自由,尤其在处理尖锐的政治、道德、伦理等直指人性深渊的问题时更需要淡化作者意识和现实指涉。那么如何以相对平和自然甚或充满诗性的方式言说人们难以直视的恶的世界?叙述分层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言说的可能性,分层越多,权力分化越多,承担责任的叙述主体也就越多,曲折迂回中形成的虚构世界及活跃其中的人、事自有一套解释其存在的逻辑,而不会过多附着于作者。
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孩子的游戏》写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的三重回忆,环环相扣,最后道出一个惊人秘密。三重回忆对应着叙述的三个层次:第一层叙述展现“我”从童年到老去的生活图景,涉及“我”(马琳)、沙琳和维尔娜的关系,叙述者显得冷静而充满理性。第二层叙述中“我”回忆童年时代的一次露营,也即小说的核心事件,回顾讲述之叙述者“我”借助经验之“我”的视角,以十几岁孩童的经验来还原露营,整个过程似乎只笼罩着小女孩之间单纯又善感的情绪,成功避开了第一层叙述中“我”的清醒审视。第三层叙述中“我”讲维尔娜的故事,叙述者是第二层叙述中的孩童,讲述的是七、八岁间“我”对维尔娜的各种不喜欢。叙述分层使得回忆中无法直面的东西得以隐藏,“我”和沙琳溺死维尔娜的事情如孩子的游戏一样普通,“我想我们并没有罪恶感,也没有为我们的邪恶得意洋洋。感受得更多的是,我们仿佛正在做神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儿,仿佛这是我们这辈子当中,让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一个最高点,一个巅峰。”[注][加]爱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第二层叙述和第三层叙述分别通过对“夏令营/特殊营”和“正常班级/特别班级”的强调,刻画出维尔娜的异常,因而成为被嘲笑、排斥乃至仇视的对象。第一层叙述中“我”出版过一本题为《偶像和白痴》的书,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精神或身体异常的人”的态度。《孩子的游戏》中三个层次的叙述者都尽量淡化“罪”,而“赎罪”意识很清晰,沙琳选择找神父忏悔,而“我”(马琳)专门研究维尔娜所代表的那类人,主动选择把自己的一生都浸泡在露营事件中,从来不曾得到解脱。《孩子的游戏》优秀之处就在于它写了人性中可怕的恶,却让人在不觉其恶当中感受到灵魂的震动,从而引发现代人的深度反思。
通过叙述分层,在叙述中分化主体权力来智慧地揭示世界中的暴力冲突或人性中的阴暗面,这样的小说佳作还有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莫言的《蛙》等。甚至电影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维伦纽瓦执导的《焦土之城》,在不断切换的叙述层次间隐藏着宗教冲突和母子乱伦的主题。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叙述分层为不方便言说之物提供了被言说的空间,使文学艺术的表现领域得以向纵深拓展,同时对伦理和美学的冲突起到缓解作用。
三、叙述分层对自我之谜的揭示
叙述分层和叙述主体分化本质上都对应着现代文明语境中,人的主体性的破碎,外在身份与内在自我难以统一,自我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身份认同危机、自我焦虑、文化冲突等问题大量渗透于现代小说中,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等小说都包裹着对自我的追问与探询。
《接骨师之女》出自华裔美籍作家之手,在异质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中凸显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其间充满自我的不确定性。第三代女性露丝是个写手,鬼写手(ghost writer),代人写书在某种意义上对自我是一种摧残,因为在写作中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自我而代之以他者的灵魂,这恰好是露丝多种身份虚弱的一个隐喻。露丝的婚姻家庭生活构成主叙述层的主要内容,叙述声音由隐身叙述者提供,而具有叙述能力的人物并没有像小说中经常处理的那样同时兼作叙述者,叙述形式进一步强化第三代女性因身份虚弱而无力支撑起自我。第二代女性茹灵在记忆衰退之前写出的文稿构成小说的次叙述层,“显身叙述者+主要人物(茹灵)视角”展示出一个灵巧、执拗、悲伤又坚韧的女儿,完全不同于主叙述层当中露丝注视下的乖僻、神经质的母亲形象。叙述分层同时分化了人物主体,身世飘摇的茹灵显得更加难以捉摸,多重身份冲突之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一个自我?没有鬼魂和毒咒的美国非但没能减少茹灵的痛苦,反而加剧了她的自我溃灭,不通英文导致她甚至无法和女儿沟通,异国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异域注定不能成为她的安全港。第一代女性宝姨,因新婚当天的惨剧而失声,同时失去的还有她真实的过往以及茹灵的身世。次叙述层因叙述者自限而无法叙述茹灵的身世,本可以由宝姨留下的厚厚一卷字纸来弥补,但茹灵拒绝接收这一重要信息,宝姨的母亲身份再次被悬置。内心千疮百孔的宝姨缺失的不止一种身份,然而她执着于单一身份——母亲身份,因此当她误以为茹灵获知了字纸中的真相而未对亲生母亲表现出丝毫认同之时,便彻底放弃了生。
在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之外,《接骨师之女》的尾声形成另一个叙述层,鬼写手露丝提笔创作自己的故事,“写给她的外婆,她自己,还有那个将成为自己母亲的小女孩”[注][美]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页。,似乎前面两个叙述层讲述的就是露丝所写的。尾声部分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的超叙述层,以叙述主体分化的形式制造出叙述者现实化、具体化的假象,“如果自我叙述能看出过去的谎言的真相,从而起到一种治疗作用的话,那也只能以牺牲这种叙事的自我意识为代价才能做到,因为它得以以可靠叙述的面貌出现,以便与被叙述内容的不可靠性保持距离。”[注][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写作者身份的强化拯救了露丝,获得叙述权力和确立自我胶着在一起。
人物通过叙述分层获得叙述主体权,分化了的言说主体凝视分裂的被言说主体,可以说是自我探寻类小说极绝妙的叙述形式。
四、叙述分层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建构
虚构叙述中被书写的世界不只作为对象而存在,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往往会搭建起另一种可能世界,行走于其间的人和他的世界享有一套迥异于实在世界中默认的逻辑。但丁的《神曲》在框架式分层叙述中描绘了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图景,正是在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的完美对接中宗教与世俗、理想与现实、人性与神性等各种冲突以狂欢化的喜剧形式被表现出来。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宗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当中提到“我——它”和“我——你”两种人与世界的关系,前者把世界对象化,主体与世界处于对立之中,后者将主体和世界放置在对话关系中,在布伯看来,“世界只可作为观念‘栖居’于我,恰如我只可作为物栖居于它。正因为如此,它并不在我之内,正如我不在它之中。世界与我相互包容。这种思之矛盾内在于‘它’之境况,消失于‘你’之境界,因为‘你’使我走出世界,以便我能与世界联接沟通。”[注][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1页。布伯所称颂的主体与世界的相互包容,只能在“我——你”这种充满诗性的相遇关系之中实现,堂吉诃德在他的可能世界中把想象当作解释世界的方式,荒诞而不滑稽,散发出无限激情和理想的光芒。
正像《堂吉诃德》所展示的那样,人面对的不是唯一、绝对的世界,多层次虚构叙述中既有实在世界的影子也有与之平行的充满骑士色彩的可能世界,人与世界在不确定性之中相遇,存在充满无限生机而并非重复陈旧的套路。诚如昆德拉所言:“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注][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都对存在做出过精彩叙述,往前追溯,雅典时期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已开始质询“我是谁”的问题,荷马时期的《奥德修纪》开了以人物回顾讲述的方式写个体漂泊的先河。但直到《堂吉诃德》,虚构叙述才以精致的分层形式把叙述文学从模仿现实的传统中拉回来,阿拉伯人西德、摩尔人翻译者和变身为小说人物的塞万提斯,共同为堂吉诃德提供了一个奇幻世界。延续下来,麦克尤恩的《赎罪》通过对两重世界的书写道出一个残忍的真相:罪之不可逆转,赎罪行为无法完成就如同小说中写到的破碎的花瓶无法复原。
《赎罪》主叙述层讲述布里奥尼从童年到老年的经历,次叙述层讲到布里奥尼向姐姐和托比道歉,“恐怖伊恩”在小说最后的超叙述层告诉我们次叙述层是布里奥尼写的小说,实际上罗比和塞西莉娅早已丧生,赎罪不可能实现。《赎罪》叙述出来的虚构世界又包含两个世界,一个是类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构世界,人物在叙述中的虚构世界进行赎罪以弥补无法在叙述中的类现实世界赎罪的缺憾。跨越四个世纪,《赎罪》和《堂吉诃德》的分层模式都以元小说的叙述形式为基础,消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世界的多种可能性被书写出来。元小说形式与叙述分层的结合,使分层在打破单一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同时,切实显示出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人性的复杂微妙。
综上论述,叙述中的分层意识伴随着人对自身认识的需要而产生,叙述者想要叙述自己就必须把自己变成叙述中的一个人物,上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又可以成为下一层叙述的叙述者,叙述层次不断分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物不断获得叙述权力继而彰显主体意识的过程。叙述分层的原理并不难解,但从古代史诗延续到现代小说的漫长过程中,分层的具体形式越来越复杂,这同样对应着现代人的主体性破碎以及人对世界认识的分裂。叙述分层以看得见的形式容纳了不可见的抽象观念,并层层撩起主体的神秘面纱;作为一个重要的小说叙述传统,还有着丰富而又广阔的阐释与探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