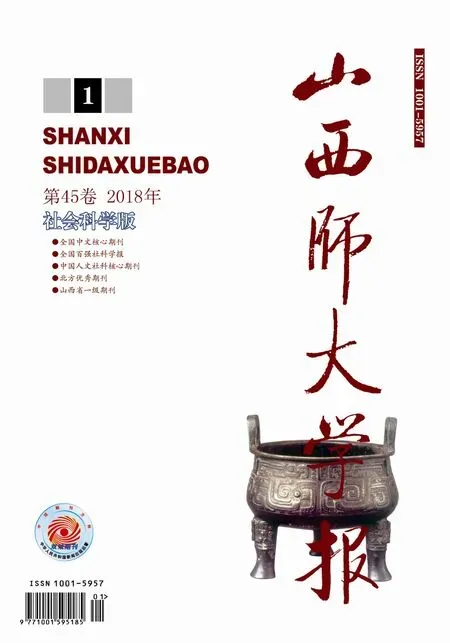诗性悬置与叙事诉求
——1930—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抒情文体”的悖论镜像
王 爱 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在总体上呈现出“诗意”隐匿的态势。[1]然而,在这种“常态”之下仍暗涌一股“反常态”潜流,即20世纪在三四十年代“写实化”文体潮流中,以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诗意体小说为代表的“诗意化”文体时有出现,但这类“诗意化”文体形式互文的却是“合理性”内容,或为群体话语的凸显,或为时代意识的溢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记体小说文本形态显然异于“五四”时期:“五四”日记体小说的“抒情化”文体呼应此一时期的“个性化”内容,而三四十年代日记体小说的“抒情化”文体承载的却是“群体”意识。穆木天于30年代中期即指出“现在的中国,写工农兵用自白与日记是不可以的”。[2]所谓“不可以”并非是反对作家采用此类文体互渗形式,而是认为“日记体”难以适应这一时期的“群体”意识,因为时代不容许叙述者的“自我”讲述,而是需要“群体”展示,“在主题上有一个从内向外的转变过程,封闭性和自我关照性主题渐渐地被搁置”[3]了。除了日记体小说,此一时期的书信体小说、诗歌体小说情形亦然,所谓抒情化文体形式难以承受时代之重。即使在风沙扑面的战时环境,创作主体也会情不自禁地顺从内心,以诗意化的文体形式表征生命的体验与感动,这原本无可厚非。然而,特殊时期的群体化意识必然会修正这种诗性感怀,导向从“‘自我的表现’转变到‘社会的表现’”,[4]且以速写、报告、评书等叙事文体取代日记、书信、诗歌等抒情文体为正则,于是呈现出三四十年代小说诗性悬置与叙事诉求的悖论镜像。
一、日记体小说与“时代”价值
1902年,佚名在《〈鲁滨逊漂流记〉译者识语》中说:“原书全为鲁滨逊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若改为中国小说体例,则费事而且无味。中国事事物物皆当革新,小说何独不然!故仍原书日记体例译之。”[5]66其强调现代“日记”文体中的“自叙”特征,读之有味,“味”即在于“日记”文体的表“情”性。“五四”时期,孙俍工在《小说做法讲义》中将小说体式分为四类,其中日记体位列于首,定义日记式小说是“一种主观的抒情的小说。是一种以自叙作为表现的样式的小说,借主人公自己底笔意语气,叙述自己底阅历、思想、感情以及周围之物象等”,[6]340这就进一步指认了“抒情”之于日记体小说的标识性。时至30年代初期,日记体小说的“抒情”倾向开始弱化,甚至明确表态“写工农兵用自白与日记是不可以的”。[2]然而,日记文体形式对现代小说的渗透融合并未止步,涌现了沈从文的《篁君日记》《呆官日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庐隐的《一个情妇的日记》、穆时英的《贫士日记》、丁玲的《杨妈的日记》、黄明的《雨雪中行进》、茅盾的《腐蚀》等一大批日记体小说文本。综观这些作品,它们与前一时期的日记体小说文本大异其趣,主要表现在以“诗意化”文体形式承载“合理性”时代内容。
20年代末,沈从文创作了中篇日记体小说《篁君日记》。其中,《记五月三日晚上》之前的篇幅最初分12次连载于1927年7月13日至9月24日的《晨报·副刊》,署名璇若,全文由北平文化学社于1928年9月结集出版。作者在《篁君日记》的“序”和“自序”中提供了两点内容颇耐人寻味:一是“这日记,是二哥临行留下的,要我改,意思是供给我作文章的好材料。我可办不到。我看了,又就我所知的来观察,都觉得改头换面是不必的事。——上面的话作为我这失了体裁的文章一点解释和此时一点见解”;二是“如今是居然说是有一千四百人马在身边,二哥已不是他日记中的模样,早已身作山寨大王了。——人民还未死尽房屋还未烧完的河南,兵的争夺与匪的骚扰自然也还不是应当止息的时期”[7]。从这两段话里首先可以见出作者清晰的文体意识。然而,“供给我作文章的好材料”又为何“失了体裁”?若按照叙述者的思路是应该写成一篇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小说,但成文之后却是一篇“日记式”的小说,这便昭示了叙述者的矛盾心态,即通过“我”记“日记”的形式来呈现已发生的“事件”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给读者尤其给妻子一种真诚感和真相感,为了“作为在妻面前的一点忏悔”。[7]237于是乎,这“事件”当然就不能算是主人公封闭性的内心世界和个人化的诗意情怀了,而是触及了大的时代内容,即在这“兵的争夺与匪的骚扰自然也还不是应当止息的时期”,主人公该如何决心抛却工作北上为兵的过程,终究“给她爱的认识以外再给她以对现世不满的指示”[7]。因此,《篁君日记》实质上是一部“讲故事”的小说,而日记式的“抒情”形式在时代“叙事”要求面前被消解了。
30年代,张天翼、丁玲等的日记体小说长于时代叙事,个人化抒情隐匿。由《鬼土日记》到《严肃的生活》,可以见出张天翼趋归时代的心路历程。《鬼土日记》叙述了韩士谦从阳世社会进入鬼土社会所经历的荒唐见闻,借韩士谦的眼睛讽刺了阳世社会有闲阶级的附庸风雅以及统治者的虚伪狡诈。该小说完全放弃了“日记体”所擅长的对于个性生命的开掘,而以嘲讽意味的粗线条叙述与描写来消弭“日记体”的独白和私语,从而大大强化了《鬼土日记》的时代叙事功能。作家采用这种文体形式的目的大概在于“日记体形式带来的似真性和文本世界提供的荒唐的内容之间形成的反讽张力”,[3]其能够凸显“合理性”的时代叙事内容,所谓讽刺“根本是理智的产品”,[8]因此,讥讽充斥全篇的《鬼土日记》可以说是“代表小说的理智方面”[9]了。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了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日记》,主编马国亮在后面写了“编者按”,称这是丁玲失踪后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该小说刊出后即惊动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潘公展,他随后批评良友公司经理余汉生及赵家璧不该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通过《杨妈的日记》发表前后的“事端”即可见出该小说被赋予的“时代”元素,因此,杨妈的“日记”定然不会是主人公杨妈的盈盈诗语。的确,该小说采用“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事,不但没贴近反而远离了主人公杨妈的内心世界,其原因就在于杨妈只是三四十年代群像的一个“符号”,她难以担任“抒情”角色,即如同时代批评家所言“杨妈的生活是可以客观地描写”与“展示”,如若采用“内聚焦”(以杨妈的视点)的主观化“讲述”,就显得十分“滑稽的了”。[4]穆木天指出了这类“农工”题材“日记体”形式的症结:“若是叫农工自己写呢,恐怕不成为艺术品,因为中国的农工都是文盲。若是知识分子去写他们的自白呢,情绪、口吻都是很难以逼真。”[10]也就是说,日记文体并非不能与工农角色结合,而是难以把握他们的“情绪、口吻”,那么采用“外聚焦”地客观化“展示”,即以叙述人的视点进行讲述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因此,30年代的“农工”题材“日记体”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文体形式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尴尬。
40年代初,七月派作家黄明的《雨雪中行进》是一篇速写式的日记体小说。[11]该小说由《是一条好汉子》《从几千里外家乡带出来的伞》《等打败了日本鬼子回来再下雨吧》《不光荣的流血》《血下苦行军》五小节按照时间发展线索进行叙事,标题中的“好汉子”“日本鬼子”“光荣”“行军”等词汇即已宣告了小说的“时代感”。文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是以主人公“我”(黄明)的视线所及来叙述,隐匿了主人公的个人化情绪,最大程度地凸现了时代的“合理性”意识。在第四小节《不光荣的流血》中,当“我”见到“一个刚刚枪毙的逃兵,曲着脚,还没有完全失掉知觉的躺在地上,鲜红的血从他的后脑流出来”这一场景时,“我”没有个人化情绪上的波动,没有同情和惊惧,有的只是鄙夷地骂了句:“不光荣的流血!” 这种源自时代“合声”的高姿态谩骂显然不合乎日记形式所能表征内容的叙述逻辑,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主人公形象的真实。小说最后一节叙述“我”的战友在叹息美丽雪景中兄弟们的寒冷之苦时,“我”立即说出“这还算不了什么苦”的豪言壮语,并挺起胸膛迈出轻快的步伐向前进,主人公形象被有意地拔高了。由此可见,《雨雪中行进》的日记体形式承载的是作者的时代价值趋归,文体形式与诉求内容不相统一,于是削弱了作品的深度。
茅盾的日记体小说《腐蚀》塑造了一位女特务赵惠明的形象。文学史家颇为欣赏《腐蚀》的日记体形式,认为“就表现一个身陷魔窟而不能自拔,参与血腥的勾当又蒙受着良心谴责的女特务的心潮起伏,矛盾错综复杂的心理来说,这种日记体无疑是最好的形式”[12]11。然而,茅盾后来否定了这种形式,他说:“如果我现在要把蒋匪帮特务在今天的罪恶活动作为题材而写小说,我将不写日记体 。”[13]300何故?文学史家是着眼于日记体形式对于人物复杂性揭示的适宜度,而茅盾的否定是因为“如果太老实地从正面理解,那就会对赵惠明发生无条件的同情”,[13]即茅盾担心读者若“太老实地从正面理解”,那就会和小说序言中故意渲染日记的真实性发生自相矛盾。本来,日记文体的“似真性”就是要求读者贴近主人公坦白的心灵,这无疑就是“从正面理解”,形成一种“情感”意义的真,但茅盾并不希望如此,因为“情感”意义的真势必会冲淡赵惠明的政治身份功能,从而会削弱时代价值意义。一言之,三四十年代小说的“日记体”形式总是难以承受时代的内容之重。
二、书信体小说与群体“意识”
“倾诉与倾听”是“五四”书信体小说的文体标识,它与这个时期表现自我的抒情小说潮流相吻合,诞生了《或人的悲哀》《一封信》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诉情”式书信体小说。随着普罗文学的兴起,特别是全民抗战和紧随其后的解放战争的展开,长于抒情的文体远远比不上街头剧、朗诵诗和小故事的鼓动效应。向内探寻的生命姿态显得不合时宜,主体势必要从“‘自我的表现’转变到‘社会的表现’”[4]上来,那么,“诉情”式的书信体小说这种主情主义的样式,“自然要被抛弃了。因为新的酒浆不能装在旧的皮囊,于是现实主义作家用了新的样式了”[4]。
华汉的书信体小说《女囚》(1928年)称得上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小说中充满着“控诉”话语,像女囚赵琴绮在信末呼吁:“亲爱的姊妹呀!你们何时才能冲破这狱门呢?你们何时才能冲破这狱门呢?我的手已经早张开了!” 即从早期书信体的“诉情”转变到此时的“叙事”,传达了一种合乎群体生活要求的“意识”,并流行于三四十年代,如京派作家沈从文的《八骏图》、林徽因的《模影零篇》、文学研究会作家徐雉的《嫌疑》、创造社作家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七月派作家张藤的《写给古城里的姐姐》、晋驼的《蒸馏》,等等。一直以来,这批文本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研究者主要还是从时代题材着眼,认为“书信体小说终于在1934年后悄然淡出时代文坛,让位于更适合时代需求的报告文学等新文体作品”[14]。这个判断显然不甚切合实际,但恰恰也道出了三四十年代书信体小说的生存状态,即在时代群体“意识”面前,书信体小说的文体特征亟需修正,以使它更加合乎特殊时期的内容需要。
“外倾型”视点是三四十年代书信体小说的主要叙述修辞。沈从文的《八骏图》(1935年)即是一篇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为主的信笺嵌入体小说。长期以来,研究者较多关注《八骏图》的主题意义,[15]往往忽略了这篇小说的文体形式功能,而恰恰是这类场景化“展示”凸显着一种普世“意识”:即以穿插主人公达士与未婚妻媛媛以及南京X之间的8封书信来表征一种“类性格”成长的意义。第一封信中“我窗口正望着海,那东西,真有点迷惑人!……我欢喜那种不知名的黄花”宣告了达士先生易于被迷惑的心性;第二封信中“那报纸登载着关于我们的消息。说我们两人快要到青岛来结婚。……我担心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找我”暗示了达士先生对于目前情感的不坚定性;第三封信中“X,您若是个既不缺少那点好心也不缺少那种空闲的人,我请您去看看她”,说明了达士先生为人处事的无原则性;第四封信中“我将把这些可尊敬的朋友神气,一个一个慢慢地写出来给你看”道出了达士先生的好奇性;第五封信中“不过我希望你——因为你应当记得住,你把那些速写寄给什么人”暗示了达士先生的非专一性;第六封信中“然而那一种端静自重的外表,却制止了这男子野心的扩张”道出了达士先生情欲的强烈性;第七、八封信以十分简短的文字赤裸裸地呈现出了一个喜新厌旧、感情不一的达士“类形象”。因此,信件内的达士先生与信件外的人生——八个教授的生活达成有效的互补,表征了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群体 “意识”,即“阉宦似的人格”,如作者认为“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16]205。达士先生和八个教授便是这些“类形象”的代表,这正是《八骏图》书信体叙述的价值功能。
七月派作家张藤的《写给古城里的姐姐》(1938年)完全是由一封信构成的书信体小说。文章开篇即是“亲爱的姐姐”的称呼,看似“内视点”叙述,实则承载了书信主人公藤弟的“外倾型”叙事内容,如呼喊“姐姐,勇敢点吧,我将会医好我的孤独症,在广大的人群里取得温暖,取得爱。……暴风雨生产了我们,斗争养育了我们”,“我”的行为完全与40年代的群体底色达成一致,“巨潮将我们冲散了,不久,我们还要汇合在一起,向前泛流”。因此,《写给古城里的姐姐》实质上是以书信的“内视点”形式凸显一种强大的外倾型群体“意识”,这从文末“附记”中还可以得以确证:“从北平流亡出来,辗转到了豫北,怀念着家里的人,北平的友人,偶然接到两封信,里面充满了无声的沉痛,悲哀,并且说来信不要加上‘娘’‘姐’等称呼,这是很危险的……我终于不知道怎么写给他们。”[17]609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写给他们,但还是以“亲爱的姐姐”称呼之,则说明“我”内心依然期待一种真实的情感,采用“书信体”形式最为合适。然而,“我终于不知道怎么写给他们”又说明在这一时期选择该文体形式的无奈与纠结。七月派作家晋驼于1947年出版的《结合》集,其中多篇小说皆以第一人称叙事,并融合了多种叙事技法,如《蒸馏》的书信体式、《结合》的评书体式、《我爱骆驼》的散文体式,等等。《蒸馏》中的第四节内容是小说主人公王发写给“我”的一封信。在“我”看来这是一封近似于“情书”的信,但也不是“诉情”,而是“叙事”,是群体化“意识”的一种形象“展示”,“不能写了,棉油灯太暗。这几天我的眼又有些花——在马上看书要不得!——这里离敌人只有八里路,机关枪又响了,怕是又要进入战斗了……”[18]748其“内视点”的运用同样不在于指涉主人公王发的形象,而在于传达一种特殊时期的群体“意识”。
此外,京派作家师陀小说《结婚》(上卷)是以六封信展开叙述故事。作者原本想借助信札的“内视点”抒情,但依然难以实现,同时代作家唐湜就认为此处“散漫、松弛、无力,虽还残存一些诗人过去有的宁静的气质,但多不调和”[19]。因为,师陀受群体“意识”的作用而合乎“左翼作家的创作路线”,使用“冷静而又稳妥”的讽刺笔调为“那个时候的上海状况,保存一部分的记录”[20]153。文学研究会作家徐雉发表于30年代初期的《嫌疑》,也是一部以“内视点”表征“外倾型”群体意识的书信体小说。
三、诗意体小说与“教化”功能
“五四”时期是诗意体小说的涌现期。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书写的内容也发生了位移,“宏大事件的叙述”越来越成为30年代以后小说创作的诉求目标,而“诗意的抒情”逐渐淡出。不过,“诗歌”从未与小说绝缘,它在任何时段都与小说发生着互渗交融的现象,但诗文互渗形式所表征的功能和意义却大不相同。别林斯基指出:“当诗人不自由自主地遵循他的想象的瞬间闪烁而写作的时候,他是一个诗人;可是,只要他一给自己设定目标,提出课题,他就已经是哲学家、思想家、道德家。”[21]24“五四”时期的一些“诗人”到了三四十年代便不由自主地给自身“设定目标”,以目标化的“诗语”渗入现代小说,此一时期渗入现代小说的“诗语”形式主要是民间歌谣,该文本样式完全隐匿了“五四”时期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的“嵌入”体式,于是从“内视点”转变为“外视点”叙述,叙述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思想家”、“道德家”甚至“说教家”。萧乾的《邓山东》、芦焚的《过岭记》《百顺街》、萧军的《鳏夫》《夹谷》、卞之琳的《山山水水》、胡正的《民兵夏收》、冯至的《伍子胥》、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村歌》、孔厥的《凤仙花》、路翎的《滩上》、胡田的《我的师傅》、林浦的《渔夫李矮子》、邢楚均的《棺材匠》等是为代表。
民间歌谣具有“外倾型”的叙事特征。《汉书·艺文志》言:“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於是有代赵之讴, 秦楚之风,皆感於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中曰:“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於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可见歌谣多“缘事而发”。罗吉·福勒认为,传统民谣“往往是一些家喻户晓的故事的片断,经过浓缩后再以客观的方式讲述出来”,具有“明理性”的讽喻特征,如“时政歌谣”即富有相当的讽喻性和批判性。[22]22至于民间的“爱情歌谣”,虽然表现了男女之间的微妙情感,但也全非个人化的,它往往是民间群体情感和心声的载体,具备一定程度的教化功能,如《探妹》《五更鼓》等。民间歌谣与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渗透融合,合奏了时代的最强音符。
芦焚的《过岭记》中穿插了两首歌谣,都是主人公小茨儿唱的,前一首是爱情歌谣,后一首是时政歌谣,如“两行杨柳一行堤,//开运河,就是隋炀帝。//野鹧鸪打它打也不去。//桃花开在二月底。” 这首时政歌谣篇幅很长,叙述人“我”一边听一边想:“同道德,习俗,一国的统治是不是有关系呢?我不说甚么,只默愿着,听那曲子自己煞尾。” 另一篇《百顺街》中穿插了一首当代民谣:“百顺街,百不顺://开家医院史和仁;//阎王的马,肥又肥,//踏人好比踏烂泥;//药材店,生意好,//一场大火烧。” 该小说嵌入的两首歌谣内容均关乎“政治”,仅仅以富有节奏韵律的“诗歌”形式作为载体,通过隐喻(“开运河,就是隋炀帝”)和双关(“开家医院史和仁”)的叙述修辞揭示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现实。因此,《果园城记》固然是“一篇朴素的诗”,但更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23]其教化功能不言而喻。萧乾的《邓山东》中穿插了六首当代民谣,其中一首是:“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学生吃了程度高呀!//中学毕业大学考呀,//欧美留洋好办学校!”歌谣形式同样是合乎诗的旋律和节奏,但内容具有明确的政治批判指向,该文体样式的好处在于向民众进行便利的传达与教化,正如作者评价乔伊斯说:“乔艾思走的死路是他放弃了文学的‘传达性’,以致他的巨著尽管是空前而且大半绝后的深奥,对于举世,他的书是上了锁的。”[24]言下之意,乔伊斯这种沉入“诗思”的创作风格不必赏识,萧乾认同的是小说终究不能“脱离了血肉的人生,而变为抽象,形式化”,[25]《邓山东》就是以“具象”传达“教化”的有效实践。同是京派作家的林浦和邢楚均,其诗意体小说中的“歌谣”均是寄讽喻和批判于一体,“合理性”企图消解了“诗性”的自适。林浦《渔夫李矮子》中嵌入一首当代歌谣:“月亮弯弯——哟咿哟;照破头——呵哟咿哟,//日本鬼子——是哥而梭,斯而梭,梭咯美,//宰耕牛——啰喂;//杀了牲口——哟咿哟;杀人口——呵哟咿哟,//男女老幼——是哥而梭,斯而梭,梭咯美,//都不留——啰喂!”歌谣虽然也采用了诗经中常见的“起兴”手法——“月亮弯弯——哟咿哟;照破头——呵哟咿哟”。然而,小说下文的“教化”叙述内容——“日本鬼子”的行为完全消解了歌谣铺垫的诗意情调。
七月派作家创作中也试图以诗歌嵌入营造诗意氛围,然而,批判向度使得这些歌谣成为教化的载体,每每稀释了诗意本然的“美”。孔厥《凤仙花》中穿插的民谣消解了凤仙花的优美,所谓“战斗的号声响亮!//战斗的旗帜飘扬!//战斗的火焰,燃烧在//大西北的原野上……”; 萧军《夹谷》中穿插的民谣由诗意徜徉突变为革命教育,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里反复回旋着一段沙哑的唱腔:“我们这些蠢货,//要拼命地开掘呵,//今天我们把工作做好了,//明天我们开到他妈的什么包家宅,//后天日本兵占领我们的阵地。”歌谣旋律带来的不是对于心灵的慰藉,而是对于现实的批判以及合理性的期待。孙犁的《村歌》从标题上即能领略到一种悠远的牧歌情调,小说中也穿插了许多诗歌,运用起兴手法,企图强化诗意效果,如“七月里来呀高粱红//高粱红又红//姐妹们呀//集合齐了//开大会呀//来斗争”、“风吹枝儿树猫腰//今年梨儿挂的好//上好的梨儿谁先尝哪//我提着篮儿上前方呀//送梨的人儿回去吧//前方的战斗正紧张啊”,等等。但很显然,诗意想象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貌似轻松快乐的备战和激情奋然的战斗与“诗意”不沾边,这是孙犁诗意体小说的通则,《荷花淀》亦然。师陀小说《牧歌》即使穿插了诸如“强盗来了!枪刀剑戟!”等战斗式歌谣,也还是受到王任叔的批评,认为“牧歌”款款不合时宜,因为这时代“需要的是叙事诗,是《浑河的激流》,而不是牧歌。作为一种寓言,一种情绪的激动,我们的作者是借这牧歌,做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我们却需要更有理性的反抗啊!”[26]“更有理性的反抗”——可谓一语道破了三四十年代民谣体小说的文体表征。为了合乎这种“理性”的教化功能,便在语体形式上追求篇幅简短,少则两句,多则六句,以方便民众的接受,“长短是大可成问题的。如为教育大众起见,太长是尤当切忌的”[8]。一言之,此一时期的民谣体小说创作为了“教育大众起见”,甚至于闯出一条新路,将传统民谣“演化出煤矿工人的歌谣、劳动号子、示威抗议歌曲,以及为政党斗争服务的歌谣”,并要“努力化除个人的意气,坚定思想上的立场,作时代的前茅”[8]这就与“五四”时期诗意体小说的文体价值功能大相径庭了。
钱理群先生说:“文学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形式的变化,如果说注重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的‘五四’是抒情的时代,着重社会解放的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就是叙事的时代。”[27]211的确,“五四”时期的日记体、书信体、诗意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文学内容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实绩,但到了以“叙事”为潮流的三四十年代,这些文体的内聚焦叙述方式必须服从于时代意识和说教功能的客观化呈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形象的饱满度。如若这三种体式的小说既要保持自身的“诗性”自适,又要符合时代的“叙事”诉求,就会使它处于二难之境。因此,形式与内容不可二元对立,抒情必需抒情的文体形式,叙事必需叙事的文体形式,“咱们只能够作一元论的想法,内容寄托在形式里头,形式怎么样也就是内容怎么样”[28]2。随着时代布幕的完全拉开,日记体等抒情化文体形式就逐渐退出,甚至于1945年后很长时间淡出公众的视线,这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1] 王爱军.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互渗”现象:以小说为中心进行考察[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4,(1).
[2] 穆木天.谈写实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N].申报·自由谈,1933-12-29.
[3] 张克.论中国现代日记体小说的文体特征[J].东方论坛,2008,(1).
[4] 穆木天.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N].申报·自由谈,1934-1-10.
[5] 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 沈从文.篁君日记[A].沈从文文集(第2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8] 郭沫若.郭沫若诗作谈[N].现世界(创刊号),1936-8-16.
[9] 叶公超.写实小说的命运[N].新月(创刊号),1928-3-10.
[10] 穆木天.关于写实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之最后答辩[N].申报·自由谈,1934-2-10.
[11] 吴子敏.七月派作品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2] 荒煤,洁泯.序言[A].杨继业,范文瑚.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年·长篇小说卷(一)[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3] 茅盾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4] 韩蕊.现代书信体小说文体特征论[J].社会科学辑刊,2010,(5).
[15] 刘艳.自卑与超越——从《八骏图》反观沈从文[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4).
[16] 沈从文.《八骏图》题记[A].沈从文全集(第8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7] 张藤.写给古城里的姐姐[A].吴子敏.七月派作品选(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8] 晋驼.蒸馏[A].吴子敏.七月派作品选(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9] 唐湜.师陀的《结婚》[N].文讯,1948-3-15.
[20] 尹雪曼.师陀与他的《果园城记》[A].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C].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
[21] (苏)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A]. 满涛.别林斯基选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2] (英)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3] 唐迪文.果园城记[N].大公报,1946-7-12.
[24] 萧乾.小说艺术的止境[N].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1-19.
[25] 萧乾.詹姆士四杰作[N].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9-20.
[26] 王任叔.评《谷》及其他[J].文学杂志,1937,(4).
[27]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8] 叶圣陶选集·自序[M].北京开明书店,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