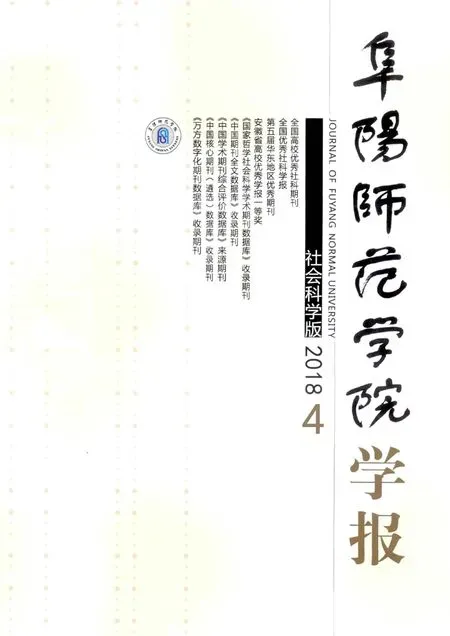从“情”的向度看《老子》
宋德刚
从“情”的向度看《老子》
宋德刚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老子》中无“情”字,却蕴含着“情”的向度。这种“情”的向度主要是道德情感,它关乎他者的存在、生存、生活。在《老子》对现实境域的理性批判与诗意反讽的背后,涌动着老子的道德悲情,比如不满、失望、悲伤、悲悯、无奈等等;在《老子》对理想境域的建构过程中,圣人的道德温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圣人的“爱”“慈”“善”等等,而民众也能够在理想社会中恢复孝慈。道德情感对于批判和建构而言是一种奠基,发现《老子》的道德情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无论是道德悲情还是道德温情,它们都意味着《老子》对他者的关怀。
“情”;《老子》;道德情感;境域
一、 “情”的向度
“情”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儒家对“情”十分重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颜乐处”“曾点气象”之中都蕴含着“情”。就道家而言,《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种“大美而不言”正是人向天地所投射出的一种美好情感,更何况还有“鲲鹏变化”“鱼之乐”“庄周梦蝶”“有情无情之辩”这些将思辨与情感融为一体的故事。竹林玄学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认为“名教”是对“情”的束缚,因此要“任情”。
那么,《老子》呢?《老子》中并无“情”字,当我们习惯于从理性的、形上的层面去看《老子》时,似乎觉得它是不怎么讲“情”甚至是“无情”的。有学者从“欲”的角度去分析《老子》的“情论”,“欲”在《老子》中固然突出,但“情”与“欲”在《老子》之时尚未有非常明确的联系,到战国中后期才有对两者关系的讨论。《荀子·正名》曰:“欲者,情之应也。”[1]“情之应”揭示出“情”是精神或内心对外在世界的感性反映,可以说具体情感的萌发、响应状态便是“欲”。但是,即便是今天我们仍难将“喜怒哀乐悲恐惊”这些具体情感的内在动因归之于“欲”。一个人欢喜可能是因为欲望得到满足,可是和朋友的日常聊天而心情愉悦,就很难说是欲望得到满足的缘故。因此,“情”与“欲”其实都有各自的独特性,“情”是情感,“欲”是欲望(古人所理解的欲望侧重于对某事物的“获得”,比如功名利禄、权势地位)。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按照《荀子》的解释将“欲”作为《老子》“情论”的核心部分,而是应当单列为“欲论”。
将“欲”放在一旁,《老子》中仍蕴涵着“情”的向度,主要是道德情感。道德是个人内在的品质、品格,并与“他者”关系密切。徐向东指出:“一般说来,道德关系到考虑别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考虑一个人自己的利益。”[2]那么,道德情感一方面是与个人内在的品质、品格相关的情感,另一方面,它具有关怀他者的存在、生存、生活的意蕴。从这层意蕴出发,一个人的道德情感在现实中最一般的表现是:“我”意识到他者的存在、生存、生活处于“好”的或“合理”的境域,“我”会因此而产生某些积极性情感;倘若他者没有处于“好”的或“合理”的境域,“我”便会产生某些消极性情感。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我”意识到。这就是说“我”是注意到、认识到他者处于某种境域中。第二,(现实的)境域。境域的不同——即“好”的或“合理”的与“坏”的或“不合理”的——所引起的情感也就不同。第三,积极性与消极性情感。看到他者生存得好,“我”会感到高兴、愉悦等等;相反,“我”会感到难过、痛苦等等。这样的道德情感当然是现实性的、经验性的。
其中,“境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现实的境域,也有理想的境域。道德情感同样也寓于基于现实的理想境域中。思想家、哲学家一方面关注、批判现实境域,另一方面也建构理想境域,在他们的论述中对理想境域的建构,通常是要由某个或某类人起主导作用,而道德情感就蕴含在建构过程中。就这一方面而言,现实中的“我”意识到(思想家、哲学家意识到)就转换成了理想境域中的某个或某类人意识到,而所意识到的就是如何将道德情感运用到境域之中。
《老子》中也分为现实境域与理想境域,在现实境域层面,“我”意识到就是《老子》的作者(主要是老子,后文有时以“老子”代指《老子》的作者)意识到了当时的现实境域是“衰”,于是老子产生了消极性情感,统称为“道德悲情”,它蕴含在对现实之“衰”的理性批判与诗意反讽中。在理想境域层面,主要是圣人意识到应以“爱”“慈”“善”等积极性情感营造境域,民众则在理想社会中恢复“孝慈”,这些情感便是理想境域中的“道德温情”。
二、 现实境域中的道德悲情
《老子》的主要作者是老子(李耳)。关于老子本人较为切实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对老子的介绍篇幅不多,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值得注意,原文曰:“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3]其中的“见周之衰”尤为重要。“见”就是意识到,老子意识到了“周之衰”,而“周”不能仅仅理解为“周王朝”,它实际上象征着当时的天下,“周之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秋乱世、礼崩乐坏,用现代的词语说,就是社会的沉沦。《老子》对乱世有着精练的描绘,所谓“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四十六章》)[4]125,“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4]149-150。这些内容无不体现着衰落或沉沦的景象:统治者发动战争,炮制出各种忌讳、法令,沉溺于伎巧中,使得民众难以安生,过着贫苦的生活,费劲心思地活着,甚至要去当盗贼。盗贼是春秋时期的一大社会问题,在《左传》中“盗”“贼”等字多有出现,鲁国(《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左传·昭公二十年》)都有盗贼横行的现象。
上述内容既是老子对实事的描述,也是对现实的批判。单纯的描述,可以隐藏或不带感情,而将描述与批判合二为一,就必然蕴含感情。这是因为批判尤其是对现实的批判不单单奠基在理性的反思之上,还奠基在对现实的不满之上。而“不满”这种情感,当它与他者不幸的境域密切相关时,就属于道德悲情。人在乱世之中容易动情,特别是对整个社会有所思考、关照的知识精英,不仅讲“良知”还讲“良情”。“良情”也就是将他者纳入其中的道德情感。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欺负弱小时,我们先是有情感的波动,再去采取行动(比如语言上的指责、批判,与弱小一同反抗等等)。
因此,在《老子》那些冷静的文字背后,涌动着老子内在的深情。当然文本和作者是有区别的,一本批判的书,有可能只是装装样子,历史上从来不缺乏伪君子。那么,因何而判断《老子》的批判为真意,老子的道德情感为真情?如果我们承认司马迁的记载,承认老子是因为看到了天下的沉沦而隐世,我们会很自然地倾向于这种“真”的确定性。以老子史官的身份而言,这种犀利的批判是具有危险性的,而隐世更具有一种牺牲的色彩,与后世的某些隐者之“隐”是为了求名利地位有明显的不同。有了这种确定性,进一步来看,“周之衰”所引发作者的道德情感首先是负面意义上的。当然,它不单纯是不满,从那些文字中还可以发现老子对统治者的种种昏庸、暴虐行径的失望,对百姓苦难生活的悲伤、悲悯。
《老子》还使用了诗意反讽的方式来揭示另一种“衰”的境域。《二十章》曰:“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4]46-48这是一段非常具有诗意的文字,其中并没有讲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充满嗜欲、谋划的“众人”“俗人”的熙攘生活与“我”的清冷生活的对比。这里的“我”其实就是老子的化身。在这段描述中,老子用了“正言若反”的言说方式,实际上构成了反讽。在最后,老子指出“我”与“众人”“俗人”不同的根源在于“食母”,也就是“我”用“道”来滋养自身。从另一个角度说,“众人”“俗人”就是“失道”或“无道”了。
诗意反讽式的批判,呈现的仍然是社会的沉沦,它同样内蕴着道德悲情,却更为复杂。诗意与反讽的融合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众人”“俗人”是被调侃的对象,调侃表现出轻松的情绪,然而这种“轻松”只是表面的,内在则是老子对他人“失道”或“无道”的不满、悲哀。而“我独”的一再确认突显了“我”与他人之间的某种疏离感。于是,这里的道德悲情可能还融入了“我”在心念他者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孤独”之情。“有道者”未尝就不能没有“无奈”“孤独”,因为将他者的境域纳入进来就是向他者敞开了一个关怀的世界,当他者执迷不悟愈陷愈深之时,从关怀的世界里流溢出“无奈”甚至“孤独”也是正常的。换言之,关怀可以导致特定的疏离。
将道德悲情揭示出来,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老子》与老子。当我们提及现实关怀时,不仅意味着理性,还意味着情感。现实的沉沦、道德悲情、批判与反讽,三者呈递进关系。以往的研究者关注《老子》对社会政治的反思批判,而往往忽略道德悲情,这就容易将《老子》与老子固着为理性的符号,从而使文本与作者缺乏弹性、情感活力。概言之,《老子》中有悲情,老子是一位兼具悲情和理性的隐者。
三、 理想境域中的道德温情
现实境域的衰败或沉沦使得老子着手构建一个理想境域,这时就需要一个典范——圣人(优秀的统治者)。《七十二章》曰:“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4]179-180《五十七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150《三章》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4]8只有统治者做到了“自知” “自爱”、诸“无”、诸“不”,也就是统治者实现自身的生存合理性,从而将紧缩的生存空间释放出来,民众才能在潜移默化的引导中同样实现自身的生存合理性。此时的生存境域是“天下治”,从另一个方面说即是达到了一种“自然”。“自然”表示存在者的合理存在状态,《二十三章》曰:“希言自然。”[4]57蒋锡昌说:“‘希言’者,少声教法令之治……谓圣人应行无为之治。”[5]156这里的“自然”就是指统治者合理的存在状态,“自知”“自爱”、诸“无”、诸“不”都属于此。《十七章》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4]40这里的“自然”正是对百姓的诸“自”、诸“不”的概括。于是,“天下治”即是天下之“自然”。
这种天下之“自然”,落实到国家社会则形成了“小国寡民”的理想境域。《八十章》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190这段内容重点描述的是民众的生存境域,民众没有过度的欲望,所以虽有“什伯之器”“舟舆”“甲兵”但无所用之,甘愿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欣然接受简单的饮食、衣着、居所、风俗。在“小国寡民”中没有熙熙攘攘、喧嚣嘈杂的景象,国与国、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并不亲近。民众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一方面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圣人的“自然”,所谓“使民……”皆是圣人所为,尤其是圣人不去对内压迫对外征服。
《老子》中的理想境域也蕴含着道德情感,这在文本中有直接体现。由于沉沦中的道德情感是缺乏的,那么在理想境域中就要将其充实起来。道德温情主要体现在圣人身上,并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语词:“爱”“慈”“善”“不仁”。《老子》在积极和消极方面使用“爱”字,积极的“爱”有两种:一种是“自爱”“爱以身”;一种是“爱民”。圣人要“自爱”,字面含义是爱自身,似乎这只关乎自我,不能算作道德情感,但实际并非如此,《十三章》曰:“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讬天下。”[4]29这里有一个预设,“爱以身”才能去治理天下。换言之,“自爱”内蕴着对他者的“爱”,它是一个爱他人的“序曲”。具体来说“自爱”或“爱以身”也就是克制欲望、爱护生命,当圣人达成之后,自然就过渡到了“爱民”。《十章》曰:“爱民治国,能无知乎?”[4]23“爱民”的同时还不能动用智巧,这是防止智巧对“爱”的干扰,因为一旦动用智巧就陷入了算计之中,就会有私心杂念。
这种“爱民”之“爱”也就是“慈”“善”。《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4]170这里突出了“慈”的重要性。“慈”是一种关乎他者的道德情感,它将他者的生命、生存放在第一位,舍弃“慈”实际上就是对他者的漠不关心,即视生命为草芥,可以任意践踏,而有了“慈”可“以战则胜”。这里的“战”是一种不得已而战,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三十一章》)[4]80。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战事,就应以“恬淡为上”,即使胜利也不应当以此为美,喜欢这种胜利就是喜好杀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慈”。我们常将“慈”和“善”连在一起,组成复合词“慈善”,其源头可能正来自于《老子》对“慈”“善”的强调。圣人的“慈”可称为“善”。《四十九章》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4]129这种“善”或“德善”是以“百姓心为心”,用一种孩童般的纯朴之心去理解、关怀他人,可以说“善”“慈”就是圣人的同理心、同情感。圣人的道德情感完全是向他人敞开的,善待善人,感化不善的人,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力量。
“爱”“慈”“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具有“不仁”的色彩。《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4]13-14这里的“仁”指的是私欲、私情,“圣人不仁”是说圣人泯去了私欲、私情,而他仍是在讲情,不过其侧重点在于说明圣人的道德情感不是一种精心的安排,不是一碗有索取目的的迷魂汤药,而是发自真情实意。苏辙曰:“结刍以为狗,设之于祭祀,尽饰以奉之,夫岂爱之,时适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践之,夫岂恶之,亦适然也。”[6]5-6“以百姓为刍狗”表明圣人不向百姓索取,一旦索取就是将百姓当作可利用的对象。
从“自爱”到“爱民”,圣人实现了自身的同时,也为民众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宽松和谐的空间。当民众过上了良好的社会生活之后,其道德情感也被充实起来,最主要的就是“民复孝慈”(《十九章》)[4]45。孝慈是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之情,这是属于民众的道德温情。从“复”字来看,这种互相关爱在现实的沉沦中是缺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国寡民”中,我们能看到民众美好的一般性情感,甚至可以从中感受到某种审美性情感,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又提示出民众在道德温情上似乎不太需要过多的倾注。正是在这里,圣人与民众的道德温情是不同的:前者的道德温情的投射对象必须要扩充至民众,其要求高、内容也丰富;后者的道德温情的投射对象主要寄寓于家人,其要求和内容都较为简单,民众以家庭为单位过着自给自足、成员间相互关爱即可。
结语
首先,对生存境域的批判和建构都以道德情感为基。我们通常认为批判与理性、智识相关,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精神的体现。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真正的批判始于人(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感,而它主要是道德悲情。老子的道德悲情将对他者的关怀转化成一种理性的思考。同样,在建构之中,圣人的“爱”“慈”“善”是首要的,老子将“善”作为三宝之“首”,意在指明圣人的道德温情是其他内容的基础。特别是作为治国手段的“无为”,其底蕴是圣人的道德温情。王庆节指出:“老子‘无为’概念中的哲学真谛更在于:这是一种存在论上更基本的要求。它要求我对于作为我的行为之对象的‘受者’的他人或他物的存在与独特性,给予一种基本的承认和尊重,并因此反对任何这种‘他者性’的承认和尊重的外来强制和侵犯。”[7]这是从对“无为”的解读中阐发“他者”问题,或从“他者”的视域来理解“无为”。概念、思想的背后是道德情感,“无为”内蕴着圣人或统治者的道德温情。“无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中的方法论、实践论概念,它还是而且首先是对他者的关怀。如此,“无为”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抽象的概念,而是温情的生动的领悟。“领悟”始终是情理交融的,倘若没有情的注入,那么“无为”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也是一些统治者难以实践“无为”的深层原因,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者(即百姓)无足轻重。要而言之,老子与《老子》始终对他者抱有一种牵挂、关怀。
其次,从《老子》中发现道德情感具有一定的意义。这里的意义可分为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在学术价值方面,学界对《老子》的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道论、自然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等方面,未能对《老子》的道德情感作系统化的研究、梳理,这就使得《老子》过度抽象化,甚至变成僵化的文本。而对道德情感的观照为我们理解老子和《老子》,甚至理解道家的相关理论之基、思想之源提供了新的路径,恢复《老子》文本的生动性和鲜活力。在现实意义方面,《老子》告诉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不应忽视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不应成为时下颇有市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应当心怀他者,在道德悲情和道德温情的基础上通过知识、行动将自己的社会关怀表达出来,负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该批判的时候就批判,特别是要为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发声。对于执政者、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而言,对弱者、弱势群体抱有同情心,克服自己的欲望、私情,“以百姓心为心”,将此作为根柢,通过合理的施政,才能与民众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的境域。
本文侧重于在生存境域之中考察道德情感,实际上《老子》的道德情感还应当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可以继续研究。比如,《老子》与《论语》中的道德情感的比较性研究,老子与孔子分别具有怎样的道德情感,有何异同?道德情感与其他要素、内容之间的关联,包括与欲望、认知、知识、理性、态度、行为、意志等要素的联系,与道、德、自然等内容的联系,在《老子》中是否构成了一个以情感为重要基础的精神现象系统和精神-实践系统?前面提到了在《老子》中还有一般性情感、审美性情感,那么它们与道德情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老子》中的道德情感对后世有何影响,特别是在道家系统中,我们能否找到一条始于《老子》的道家情感主义路线?总之,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尚需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1]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428.
[2]徐向东.自我、他人与道德——道德哲学道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4.
[3]司马迁.史记(修订本)[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2603-2605.
[4]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5]蒋锡昌.老子校诂[M]//民国丛书·第五编.周谷城,主编.上海:上海书店,1996:156.
[6]苏辙.道德真经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6.
[7]王庆节.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4.
Looking atfrom the Angle of “Emotion”
SONG De-g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There is no such word as “emotion” in, but it contains the dimension of “emotion” The orientation of this “emotion” is mainly moral emotion. It is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survival, and life of the other. In’s rational critique of the realm of reality and poetic irony, the moral tragic feelings ofare surging, such as dissatisfaction, disappointment, sadness, compassion, helplessness, etc.; ins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realm, the sages’ moral warmt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such as the saints’ love, kindness, goodness, etc, and the people can also recover kindness in an ideal society. Moral emotion is a foundation for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moral emotion ofhas a certain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short, whether they are moral tragic or moral warmth, they all mean’s concern for the other.
“emotion”;; moral emotion; realm
2018-05-30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圆道’观念与先秦哲学之研究”(14YJC720024);2013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哲学视域下的先秦‘圆道’思想研究”(13DZXJ01)。
宋德刚(1984- ),男,山东青岛人,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道家哲学、观念史研究。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4.02
B223.1
A
1004-4310(2018)04-0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