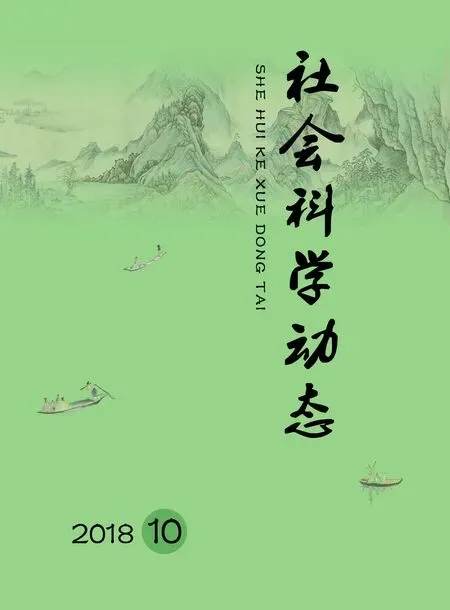《呼兰河传》与《一个人的微湖闸》比较研究
卢 姗
在新生代作家中,70后青年女作家魏微是独特的,她以怀旧、沉静、温良的细腻笔调书写着沉淀在时间深处那“暖老温贫”的日常生活。研究者注意到魏微作品风格与萧红、张爱玲等作家有相通之处,魏微自己也曾多次在作品及访谈录中谈及自己受两位作家影响:“我受张爱玲、萧红影响很大。张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技术上的,她的小说技法太娴熟了。”①
张爱玲的技巧,遮遮掩掩地浮动在魏微的笔尖。小说《化妆》里,挣扎在金钱与情欲中的大学生嘉丽,在看清情人面目后慨叹:“ 啊,这噩梦般的一切,让它结束吧。她今天一定是疯了!她为什么非要捅破!”这语调像极了张爱玲笔下另一个同样在金钱情欲中痛苦盘旋的女人——曹七巧,当她赶走自己暗恋的、上门来倾诉相思之苦的小叔子后,后悔自己的举动:“ 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 她又不是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戳穿他?”如此老练沧桑,对人情世故入木三分的刻画如出一辙。②
魏微自己曾表示,如果说张爱玲带来的是技术启蒙,那么萧红带来的更多是精神气质上的吸引:“精神上我离萧红更近一些,她身上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很本色。”魏微眼里的萧红“一生追求温暖,其实活得寒凉”,“她的小城背景,对穷人的态度,对日常的书写……这个也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其实萧红也是学不来的。精神这种东西你怎么能学得来呢,这是你天性里就有的东西啊。”③
诚然,萧红与张爱玲两位作家的人生虽然都是命运多舛的,但萧红比张爱玲幸运的是她有一位慈爱的祖父,给了她信任温暖,所以萧红比张爱玲笔下多一份温暖与爱,少一份绝望彻底。而有着完整亲情又不断把亲情当文学母体进行书写的魏微,显然更多的是继承了萧红的某些精神气质。
一、相通之处
对比阅读两位作家同题材文本《呼兰河传》 (萧红)与《一个人的微湖闸》 (魏微),笔者发现文本间抑或说是两位作家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确有相通之处:
1.写作背景中的寂寞心境与生死之思
《呼兰河传》是萧红1936年独居日本时开始构思,1938年在武汉时开始写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完成于香港的作品。独自身处香港,萧红内心感到的是难以排遣的寂寞苦楚。在写给密友白朗的信中她袒露道:“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抑郁……如今我却 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季红真分析萧红陷入忧郁心境原因“大概是由于写作和社会活动过于劳累。也由于初到香港,环境陌生,语言不通”④,萧红无法融入外界生活,加之其时与端木蕻良的关系也出现矛盾,“周鲸文夫妇得到一种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太关心”⑤。这是身为萧红好友的茅盾先生所不能预料的,萧红死后,他在《呼兰河传·序》中共用了28个“寂寞”形容身处香港的她。⑥寂寞的心亟待一首安魂曲,思乡的情绪空前磅礴,萧红开始在童年往事里翻箱倒柜,寻找遗失在记忆深处那片乡土之上令自己又爱又怨的那只蝴蝶,那朵黄花。
季红真分析认为,《呼兰河传》文本中有着浓郁的“祭奠性质”⑦,它通过生与死的意义追寻祭奠了所有的故土亡灵,不论是心爱的祖父,被众人折磨而死的小团圆媳妇还是王寡妇溺水而死的独子,而更本质的是,萧红由此祭奠了自己的童年。渴望返乡不可得,身体上的病痛又诱发生死之思,此时萧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需要的是一个出口,于是梦回呼兰变得顺理成章。
与萧红彼时心境相似,1999年,同样是30岁的魏微受邀创作《一个人的微湖闸》,她独自住在南京东郊一所大学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一整年。这一年,魏微感到的是与自己对话的宁静与寂寞:“有时候习惯性地望向窗外,目睹日光升起,盛大,衰落的过程,觉得伤心,并且很慌张……”外部世界被隔离在自我审视范围外,魏微“清晰地记得年近三十的自己,怎么样在偌大的校园里,走一两里路都看不到人”⑧。
或许这份寂寞与空辽为思绪的纷飞提供了场所,魏微选择回望自身,用回忆录的形式打量来时之路,思考生与死的意义。“走在陵园路,身处其中,很知道周遭一切是上了年岁的,安静的,苍老的。常常我会想到生死,想着想着就走神。不见天日的树林,思考生与死。”⑨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作家关于生死的思考都极具分量,而且在寂寞心境和独处带来的关于生命本质思考的催生下,同样三十岁的两位女作家都选择了书写一部个人回忆录,用孩童视角、回顾姿态与自己达成和解。
2.以亲情为母体,写非虚构童年
前文提到两部作品题材都锁定在纯真朴素的“亲情”和“童年”,且都以第一人称叙述六七岁小女孩“我”的故乡经验。对萧红而言,“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⑩。此外,贫穷的有二伯、悲惨的小团圆媳妇、生命力顽强的冯歪嘴子等童年时的街坊邻居、亲朋故友形象都在这部作品里鲜活着。而对于魏微,童年则是江淮之间名叫微湖闸的那个水利管理所日常生活的温馨小曲,不论是爱“我”的爷爷奶奶,生命力旺盛、跑步带风的储小宝,还是随年轻司机私奔的杨嫂,清朗英俊的叔叔,和大多数男人都睡过的小佟,都是这首小曲里不可或缺的音符。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家在关于童年的书写里都是越过了父母一辈,而将镜头对准祖父一辈。
众所周知,在《呼兰河传》里,祖父的爱是“我”永远的温暖回忆。而在《一个人的微湖闸》里,“我”同样对爷爷奶奶十分依赖。作者在开篇楔子里便表明:“那时候,我们住在微湖闸,我爷爷奶奶……过着幸福而枯燥的日常生活。”⑪文中有一章叫《怀念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日子》。那闲来无聊的读报岁月,“我”总爱洗漱后双手挂在奶奶脖子上吵闹着和奶奶“皮麻”(取闹,嬉戏),“我”喜欢在微湖闸的那段岁月,因为受到了爷爷奶奶的呵护,那是人世间最初的温暖。
除了写作镜头都对准在“亲情”,两位作家同样还注意到在回顾童年时都非常细腻且擅长捕捉记忆中的小城小街的样貌,它们都曾是作家真实生活经历的一部分。
《呼兰河传》开篇“严冬小城图”是一幅精彩的群像描写:年老的人,赶车的车夫,马行,卖豆腐的人沿街叫卖着,卖馒头的人跌落了馒头箱子……无独有偶,《一个人的微湖闸》开篇是“渔船人家图”:每年春夏照例停泊微湖闸的七八户渔夫人家,一群抽着旱烟的渔夫,渔舱里做饭的渔娘,无忧无虑嬉戏的孩子,一派闲适满足,俨然构成了微湖闸的一道风景。魏微说:“就想要把所看到的世界写出来”,“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却忘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⑫其实人物也好, 风景也罢,都因真实存在过而显得格外真挚动人。
3.存活在时间之外,与时代保持距离
萧红笔下那呼兰河城里的油店、布店门口挂着的布幌子,都是“自古亦有之”的,在这座小城里发生的故事,“过了三年两载,若有人提起那件事来,差不多就像人们讲着岳飞、秦桧似的,久得不知多少年前的事情似的”⑬。这里的人们始终如一地保留着古旧的生活传统:假如一个人牙疼了,即使街上出现许多新牌牙医广告,人们仍然习惯走进老旧的“李永春”药店,不管这老药店有没有招牌。萧红笔下呼兰河的故事几乎与时代没有任何联结,人物的命运和时代关系也不大,更多的是由于自然人性本身。
微湖闸何尝不是如此,那革命年代里的一切,在微湖闸的人们身上似乎都睡着了。时代以惯常的速度滚滚向前,而他们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那样的微小,谨慎,认真,永常。文中作者借长大了的小蕙子感慨道:“革命年代的种种风潮,并没有太大地影响到这个地处偏僻的水边大院”,“我看到的东西,就是生活。它跟时代没有任何关系”,“把她们安置在任何时代里,都显得再恰当不过”,“世界是完整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业社会的种种迹象,在那个年代已经初露端倪。可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人们还保留了从前的传统。这其中的空当被无限拉大了。最先锋的思想,最古旧的生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糅合进了那个激进的年代,竟然相得益彰,真是不可思议。”⑭
当70年代作家在书写风云际会留给自身或者社会的种种迹象时,魏微在时代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我的独特体验方式,即用日常生活的一套话语代替政治生活的话语:在《一个人的微湖闸》里记着这么一件事,当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到家里时,奶奶的反应先是惊讶痛苦,可之后又拿起土豆开始削皮了,“因为吃饭还是要吃饭,日子还是日子”。
4.人物的生死观与“逆来顺受”生活态度
此外,两位作家均对童年生活里的一些小人物记忆深刻,他们大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沉淀在人们日常生活深处的生死观,及对待生活逆来顺受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呼兰河传》里谈到小城人们的生老病死观:“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⑮
最典型的就是王寡妇独子掉到河里这件事。那曾轰动了一时家传户晓的惨剧,不久就被邻人街坊、亲戚朋友遗忘。王寡妇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者在庙台上狂哭一场,完了仍是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平平静静地活着。磨房的磨倌冯歪嘴子老婆因生产而死,留下一双孩子,所有人都以为冯歪嘴子要活不下去了,可生活硬是让这个男人经受住了一切,他自己拉扯大孩子。
而关于生死观,在《一个人的微湖闸》里是这么展示的:小蕙子回忆奶奶在五十岁时开始准备自己的丧衣,是因为“她要在生前看到死,死是具体的,穿红戴绿的,繁盛而热闹。一家人在丧礼上,大办宴席,笙箫不断”。因此,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时,奶奶的反应先是惊讶,而后“在哪一瞬间,她又拿起了刀,开始削土豆了,这对她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感情代替不了吃饭,悲伤是难免的,可是吃饭,它永远是吃饭”。借用小蕙子的话来概括最恰当不过了:“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走远了。我们掸了掸手掌心,非常不介意地,就这样走了”,“人世的魅力就在于,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跌宕起伏的戏剧化中,虽然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静静地过着日常生活。”⑯
5.片段式结构,多叙事描景
两部作者在结构上的相似更为直观:《呼兰河传》七章一个尾声,《一个人的微湖闸》九章一楔子一尾声,且尾声部分呈现出类似作用。
《呼兰河传》尾声中,成年的“我”在回望衰败的故土:后花园的主人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有二伯死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虽无一“想”字无一“爱”字,但思念与悲悯全然藏在这些文字里:忘不了,也难以忘却。
《一个人的微湖闸》的尾声与此极为类似:先是回望衰败的故土:“我永远的微湖闸……那遥远的年代,老人和孩子,妇女和青年人……他们渐渐老了,也死了……”再拉开审美距离,回望逐渐荒败的被记忆尘封住的空间,寄托无尽思念与悲悯:“我再也没有回过,我知道它还在着,是一个荒落的闸。”
此外,两个文本都存在大量片段场景式的描写,这也是众多研究者关注到的现象。《呼兰河传》每章都能独立成故事,彼此之间关联不大,也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一切都零零碎碎,看上去似乎不是一个有机整体。魏微在序里也坦言自己是“片断式的,浮光掠影的”。对此,魏微的解释:“因为小孩看世界大抵如此,一片片的,形不成一个整体。对于童年的回忆,就像老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⑰可见,两部作品都不是以故事情节的因果链条取胜,而是以流淌于各个章节间的脉脉温情为线索,娓娓道来。正是这份纯真的孩童般的审美打量,让这些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感动,萧红亦如此。
二、不同之处
《呼兰河传》与《一个人的微湖闸》两部文本虽确有相似相通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过《呼兰河传》就没有必要再读《一个人的微湖闸》,呼兰河水流淌过微湖闸,令微湖闸散发别样魅力。同类题材下两者的写作差异,让两部文本呈现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特点。
1.重叙述者视角与三重叙述者视角
《呼兰河传》作为一部自传体性质小说,叙述视角呈现出双重转换的特点:作品前两章是对呼兰城的全景俯瞰;第三章转为女童视角,描绘童年热闹的后花园,杂芜的储藏室;第四章起,叙事视角频繁转换,一方面是女童叙事角度,一方面是成人超然冷静的视角。女童视角奇异而有趣,成人视角却能看出家是荒凉的。在这种融合和旁观的双重审美视角中,萧红不仅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犀利与沉痛,而且在批判中寄予了对乡土、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人生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相对而言,《一个人的微湖闸》的叙述视角转换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叙述视角交织转换比《呼兰河传》更频繁,楔子是对微湖闸全景的俯瞰,对每年春夏停泊此处的船舶人家的描写,第一章起叙述视角之间开始频繁转换;二是《一个人的微湖闸》里有着不止“女童”及“成人”这两个叙述者,而新颖地加入了第三个叙述视角“中学时期的小蕙子”,这也是《一个人的微湖闸》带给读者最大的惊喜。
以第一章《杨婶》为例子:开篇是成人视角在回望童年:“我还能记得自己,那时候也不过才四五岁吧,穿着格子布的笼统的罩衫,方口布鞋,尼龙袜子,很安心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奶奶的手掌里,随她一起去杨婶家。”下一秒转换女童视角:“我低头看路,觉得自己是侉气而快乐的。……里面有许多喜欢的糖果/桃酥/各种花色的小饼干,绘有蓝色的小古人……”再次转换至成人视角:“许多年后,下午的阳光总让我想起杨婶……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许多年后,当他们回忆的时候……”
在第三章《储小宝的婚姻》和第九章《怀念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日子》中,则是三个叙述视角之间的自由转换。第三章开篇以成人视角进行回忆:“现在,让我再回到对于日常生活和人物的叙述上来。”随后进入女童视角回忆储小宝给“我”讲“爬灰”的事以及储小宝与小吴的恋爱故事。这次女童视角中间被一个成人视角的议论切断:“许多年后,我还能记得这一幕,我站在阴凉处,看见一个青年的身影,在太阳底下,飞速地移动着。”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进入的是特别的“小蕙子”视角:1987年,“我”回微湖闸过暑假与储小宝见了一次面,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成人视角触发回忆→女童视角储小宝讲“爬灰” →成人视角抒发议论→女童视角储小宝恋爱故事→中学视角最后一次见面
第九章这种转换更明显:开篇以女童视角回忆“我”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场景:奶奶做早餐,爷爷看报纸。随后跳转到成人视角,写长大后与亲戚们维持的只不过是客套,与曾经最亲近的奶奶也关系冷漠,“我没有气力,我继承了父亲的冷漠无情,我对我最爱的奶奶也不过如此”,甚至希望她死,“我嫌弃她,但更爱她,我希望她能死去”。此时,叙述者发生改变,追溯至中学时期爷爷死时的场景,“面对爷爷的死。我跪在一旁,迅速地闭上眼睛,心里默念着,爷爷,你走了,你能保佑我吗?你保佑我平安,幸福,不要早死,学业顺利。——一边祈祷着,一边也谴责着自己的麻木与自私”。
女童视角触发回忆→成人视角与奶奶关系不再亲密→中学“小蕙子”视角爷爷之死
其实作为特殊介质的“中学时期的小蕙子”叙述视角几乎贯穿了全文。例如第四章里“我”被叔叔说到掉眼泪,第五章中“茁壮地成长,听见骨骼在我身体里拔高的声音”,第七章写到1987年夏天中学时期的“我”对一个叫孙闯的男青年的单相思。1982年及1987年回微湖闸过暑假时与叔叔的故事,用她的话来说,“也没有什么故事,只不过是一些情绪。”学者魏天真在采访魏微时曾提出她作品中叙述者的一个特点:“一个成年的人在这里看她的少年时代,看到的是少年的她在回望她的童年,这很像两面对照的镜子形成了一个无穷的长廊,很清晰也让人觉得有点隔膜……给人的感觉,是你在回望过去,那个过去的你也在回望过去。”⑱
叙述者的转换不同,两次精神返乡意义也不同。《呼兰河传》显然更具文化批判性,当成人视角出现时,大多是对农村文化陋习的批判。而《一个人的微湖闸》则缺少这种批判性。魏微的文字更像是在照镜子,镜子里是过去的自己。当然这并不代表魏微没有批判性,其实,在魏微稍微晚一点的作品《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我们发现作者笔下的“我”开始呈现出精神返乡的“异乡人”身份——一种无法再融入故乡的无奈的自我反省,这里不展开论述。
2.反抗型人物塑造的有效尝试
诚如茅盾所说,《呼兰河传》的人物都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而怡然自乐。萧红并没刻意有塑造一个反抗这种日常生活的角色,这或许是后来的研究者对《呼兰河传》的一大失望。
令人惊喜的,生活的光亮在微湖闸开启。因为是闸,自然有冲出来的,也有失败的。在魏微笔下,是有人对这种“暖老温贫”生活不乐意的,他们忠于本心地去挣脱着、渴望着、奔走着,令人动容。如杨婶,微湖闸杨站长的妻子,一个众人心目中集齐各种美好品质、优越体面的主妇,四个孩子的母亲,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与路过的年轻司机私奔了。杨婶的行为打击了整个微湖闸,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丑闻”,所有人的道德天空都因此塌了下来。当一切人物都顺理成章地在自己的一方天地行走生活着的时候,杨婶的转变打破了这种灰蒙蒙的日常,或许多变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微湖闸的闸门逃出了一个惊喜的意外。
《一个人的微湖闸》中,人物的塑造是多元的,不再是脸谱化的单一性格,其前后行为的冲突极具张力,在杨婶身上生命的意识,身体欲望得到了唤醒,叫人怎能不爱?虽然魏微很不仁慈地给这个人物加上了一个不圆满的结局:她从日常生活里逃离出来,辗转起伏,最终又回到了日常生活里去。但这仍不能打破读者对这个惊喜的意外出现时候的激动。
三、余论
或许在某些重要时刻,我们都需要梦回故乡,去采撷那朵遥远清晨绽放在枝头的花,正如所有的鹿都会在清晨时分找到那条小溪,惟如此,才能与当下的自己达成和解,萧红如是,魏微亦如是。那人那景那城,在记忆中永垂不朽,在创作者每一次的精神返乡时复现,呼兰河如是,微湖闸如是。不同时段的两位小城姑娘,穿越不同历史的风尘,于文字与文字间相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
注释:
①③⑱魏天真:《照生活的原貌写不同的文字——魏微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②马琼:《金钱与情欲的纠缠——对〈化妆〉的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5年第20期。
④⑤⑦ 季红真:《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第97、121、93 页。
⑥ 茅盾:《呼兰河传·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1—18页。
⑧⑨⑪⑫⑭⑯⑰ 魏微:《一个人的微湖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9、121、143、92、102、213页。
⑩⑬⑮ 萧红:《呼兰河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0、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