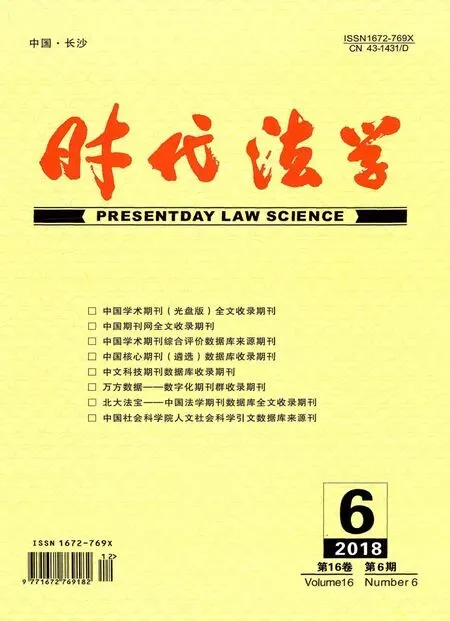论违规超额增持股票行为的民事责任
——以“ST新梅案”为分析样本
靳 羽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30120)
违反《证券法》第86条规定之“持股权益披露规则”(disclosure of interest in shares)、“慢走规则”[注]《证券法》第86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件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的违规超额增持股票现象近年来日趋普遍,据媒体报道,自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间,仅中国证监会发现并处罚的案例即达20多件[注]黄豪,张骞爻.违规举牌乱象频出,如何规范成为难题[N].证券时报,2016-06-29.。该违规交易行为之所以无法受到有效遏制,主要成因是违规成本与相应收益相比过于悬殊:从成本上看,执法机构往往依据《证券法》第193条[注]《证券法》第193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付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以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予以定性处罚,罚款上限为60万元;从收益上看,《证券法》第120条[注]《证券法》第120条规定:“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对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在违规交易中所获利益,依照有关规定处理。”赋予了违规交易等同于合法交易的法律效果。60万元的成本相较于违规行为得逞所获收益,二者孰大孰小可谓一目了然。行政处罚效果不彰客观上亟需民事责任“补位”,但在现有制度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以“ST新梅案”[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为代表的司法实践以《证券法》第213条“改正前,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规定[注]《证券法》第213条规定:“收购人未按照本法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收购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为违规行为民事责任的规范基础,并认为所谓“改正”就是指补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履行该义务对违规者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致使限制违规超额增持部分股票表决权法律责任形同虚设。可见,“ST新梅案”裁判规则实质上已异化为“漂白”违规超额增持股票行为的工具,与其说遏制毋宁说助长了违规现象。
“ST新梅案”裁判结果公布后,舆论普遍认为因“宝万之争”而衍生之“万科工会案”的结果亦不言而喻[注]梁梦雅.诉宝能案,万科胜诉为小概率事件[N].中国联合商报,2017-02-13.,该案所确立之裁判规则对于资本市场的标杆意义由此可见一斑。追问“ST新梅案”裁判规则“异化”的成因并探究司法审判实践的改进方向,即是本文的写作动因。
一、案情概要与裁判要旨
(一)案情概要
2013年7月至11月间,王斌忠实际控制开南公司、瑞邦公司以及胡飞、唐才英等法人、自然人的15个账户(以下简称账户组,其中公司法人6家,自然人9人)进行股票交易。截至2013年11月27日,账户组合计持有新梅公司已发行全部股份数的比例为14.86%。同日,开南公司发布《新梅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声明截至该日,其持有新梅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为5%。2014年6月6日,开南公司等6家公司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各方共同作为新梅公司股东,在行使股东权利时保持一致。
2015年1月20日,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向王斌忠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前述账户组未披露该账户组受同一人控制或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账户组在2013年10月23日合计持有新梅公司股票首次超过5%以及在同年11月1日合计持有新梅公司股票达10.02%时,均未依照《证券法》第86条规定,对超比例持股情况及时报告和公告。据此决定:责令王斌忠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王斌忠于1月22日缴纳该50万元罚款,并于次日与6家一致行动人共同发布《新梅公司祥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补充披露)》,详细列出各一致行动人截至该日所持有的新梅公司的股权比例。
2015年3月4日,新梅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兴盛公司以王斌忠等为被告、新梅公司为第三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各被告在持有新梅公司股票期间,均不得享有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提案权和投票权)等各项权利或权能;二、自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之日起,各被告不得以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以外的任何方式处分其持有的新梅公司股票[注]原告起诉时提出的诉求为五项,另外三项于庭审后撤回,分别是:一、自2013年10月23日账户组持有新梅公司股票首次达到5%之日起,各被告购买新梅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无效;二、依法强制各被告抛售2013年10月23日当日及后续购买并持有的新梅公司已发行股票(即超出5%部分),所得收益赔偿给新梅公司;三、各被告对上述第二项赔偿责任互负连带责任。。
(二)裁判要旨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归纳三项争议焦点,并分别分析认定如下:
第一,被告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超比例购买股票的交易行为是否有效。法院认为,原告虽在本案诉讼中撤回要求确认被告违规持股超出5%以上的股票交易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但该问题的认定结论与原告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依法予以审查。因王斌忠系以集中竞价的合法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故依据《证券法》第120条关于“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的规定,认定讼争交易行为有效。
第二,原告主张被告侵害其控制权及反收购权是否成立。法院认为,所谓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仅表现为投资者根据其投资比例依法享有的对公司管理事务表决权的大小,并非控股股东依法所应享有的股东权利。现行法律制度未赋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反收购的法定权利,目标公司管理层只有在为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采取合法的反收购措施。据此,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控制权和反收购权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第三,原告要求限制被告行使股东权利是否成立。法院认为,根据《证券法》第213条的规定,责令改正的事项应由证券监管机构依其行政职权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全面履行改正义务亦应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券监管机构予以审查认定。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作出处罚决定后,被告王斌忠已缴纳罚款50万元,并与一致行动人共同履行补充信息披露义务,证券监管机构并未进一步责令被告改正其他违法行为,或要求其进一步补充信息披露,故原告以被告改正行为尚未完成为由,要求限制其股东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违规超额增持股票行为定性
学术界普遍认为,“持股权益披露规则”的立法目的是通过对潜在公司收购行为的预警式信息披露,影响投资者对目标公司股票价值的判断,从而决定是否以及以何种价格进行股票交易。“慢走规则”的立法目的是赋予投资者以理解、消化持股权益变动信息的时间,据以保障其能够有机会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注]姚蔚薇.违反证券交易大额持股披露及慢走规则的民事责任探析[A].证券法苑(第二十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关于违反以上两项规则实施违规交易行为的定性,因原告撤回损害赔偿诉求,故“ST新梅案”受诉法院未做审查认定,本文尝试辨析如下:
(一)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不能成立
关于违规超额增持股票民事责任的可能性,依据《证券法》第120条第2款“违规交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以及“在违规交易中所获利益,依照有关规定处理”的规定,法院只是笼统地认为,此处的“民事责任”、“有关规定”是指《证券法》第69条、第76条和第77条分别规定的证券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民事责任,故并未给出最终结论。有学者从以上三种证券违法行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加以分析,认为违规举牌所可能引起的唯一民事责任是内幕交易责任。因为王斌忠持有新梅公司股票比例达到5%即成为新梅公司大股东,此后继续“秘密”增持至14.86%,属于《证券法》第67条第2款第(八)项所规定之“持有股份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形,符合“重大事件”要求,进而构成内幕信息[注]陈洁.对违规增持减持股票行为定性及惩处的再思考——以违反证券法第86条权益披露及慢走规则为视角[J].法学,2016,(9):21.。
当前学术界对违规增持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内幕交易争议颇大[注]吴飞飞.违规举牌相关争点回应与规制路径探寻[J].证券市场导报,2017,(9):61.,有学者从法理基础、规范依据和具体操作三个角度有力阐释了不能定性为内幕交易的理由,此处不赘。笔者认为,尽管违规增持与内幕交易都具有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外观,但二者的逻辑基础却是截然不同的:内幕交易制度系以具有公司信息优势的内部人为首要规制对象,要求公司高管、控股股东等内部人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持股权益披露规则”和“慢走规则”则是以不具有公司信息优势的外部投资者为规制对象,要求他们向内部人和其他投资者披露信息[注]项剑,丛怀挺,陈希.股东权益变动规则重构:以控制意图和冷却期为核心[A].证券法苑(第二十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因此,如果以内幕交易定性违规增持行为,无疑是令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格局下,不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与具有信息优势的内部人承担了相同的责任,这显然有违“权责一致”精神。再者,至少就“ST新梅案”而言,原告无法依循内幕交易的规范路径获得救济,因为《证券法》第76条规定的内幕交易民事责任限定于为“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提供救济,亦即,只有那些在内幕交易行为实施期间进行反向操作的投资者才是适格索赔主体。本案中,原告的持股比例始终未改变,这就是说其并未在被告违规行为实施期间进行反向操作,因而,即便原告未撤回损害赔偿诉求,亦注定无从获得救济。
(二)“诱空型”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不能成立
所谓“诱空型”证券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虚假的消极利空信息,或者隐瞒遗漏重大利多信息,诱使投资人在股价相对低位时卖出而遭受损失的行为[注]贾维.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之完善[J].法律适用,2014,(7):17.。该类证券虚假陈述的构成要件、法律责任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付之阙如,部分学者主张以“诱空型”证券虚假陈述定性违规增持行为,认为违规增持系以不作为的方式对其持股权益变动信息予以隐瞒披露或者迟延披露,以期达到在能买卖特定公司股票时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尽管此种虚假陈述行为模式具有非典型性,亦在宏观上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开与公平,微观上损害了交易对手方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故不妨碍虚假陈述的行为定性[注]莫壮弥.试析违反权益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A].金融法苑(第九十三辑)[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张弋羲.超比例增持股票行为的定性探析[A].证券法苑(第二十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以上见解业已取得司法实践的部分回应,如在“韩玉与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即认为,“鉴于京博公司系违反持股量的非例行信息的及时披露义务,构成消极沉默的诱空型虚假陈述”。但原告的损害赔偿诉求并未获得支持,因为“在此类虚假陈述行为中,利好消息即便未披露,也不会诱使投资者做出积极的投资决定”,故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被告京博公司实施的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其投资损失系市场系统性风险所致,亦与被告行为之间不存在损失因果关系[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商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事实上,“诱空型”虚假陈述在行为模式上与内幕交易别无二致,均系以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方式诱使投资者实施股票交易行为,而受困于因果关系认定难题,内幕交易索赔案多年未有成功维权的先例[注]曾洋.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J].法学研究,2014,(6):21.。直至2015年的“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案”,首采“推定因果关系”加以认定[注]曹中铭.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案宣判意义非同寻常[N].上海证券报,2015-10-12.,“诱空型”虚假陈述因果关系认定难题似乎由此而“柳暗花明”了。尽管“推定因果关系”的司法适用目前尚处于“试水”阶段,效果究竟如何尚有待学术探讨和市场实践检验,却无疑有望为“诱空型”虚假陈述的受害投资者开启救济之门,然而,由于“ST新梅案”原告在被告违规增持期间未实施反向股票交易操作,故原告同样不能依照“诱空型”虚假陈述的规范路径获得救济。
三、违规超额增持行为致原告受损法益辨析
承前所述,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以“诱空型”虚假陈述定性违规增持行为,符合特定条件的投资者亦有望循此路径获得损害赔偿救济。然而,如同“ST新梅案”原告的特殊投资者,亦即,因违规增持而丧失公司控制权的投资者则无法享受同等待遇,但其遭受的损失似乎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损失究竟应如何定性呢?
(一)法院见解:控制权不属于法定权益范畴
“ST新梅案”中,原告上海兴盛公司持股比例为11.19%系新梅公司原控股股东[注]虽然上海兴盛公司持股比例仅为11.19%,但新梅公司股权结构比较分散,且新梅公司亦认可上海兴盛公司系其控股股东,故法院认定上海兴盛公司系新梅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斌忠及其一致行动人置持股权益披露规则于不顾,在二级市场“秘密”大量买进新梅公司股票,最终合计持股比例达14.86%,新梅公司控制权在短短数月间即告易主。针对原告上海兴盛公司诉称其控制权丧失的主张,法院认为,“所谓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仅表现为投资者根据其投资比例依法享有的对公司管理事务表决权的大小,并非控股股东依法所应享有的股东权利,”这其实是认为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具有独立价值,因而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权益损失。
法院的前述见解,究其根源,是基于传统股东“同质化”(Shareholder Homogeneity)逻辑假定而以无差异的资本作为公司权利配置的唯一标准,资本多数决原则即是以上权利逻辑的法理表达[注]赵万一,汪青松.股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结构性变革——以股东同质化假定到异质化现实的演进为视角[J].现代法学,2011,(3):19.。显然,资本多数决原则是以抽象的资本平等理念掩盖了不同股东权利义务上实质的不平等,因而不断遭到理论和现实的有力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投资者偏好的差异,认同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中意见分歧(Divergence of Opinion)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种意见分歧系投资者“异质性”(Investor Heterogeneity)的表现类型之一,股东异质性以及不同性质的股东之间关系的处理迅速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注]汪平,邹颖,兰京.异质股东的资本成本差异研究——兼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基础[J].中国工业经济,2015,(9):27.。
(二) 原告损失定性:控制权私人收益损失
尽管上市公司控制权是一定数量股权集合的结果,但这种集合绝非只是股权数量上的简单相加,更是跨越权利性质“临界点”导致权利质变的结果,其成分数量和结构均不同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股权)。这种质变即体现为学者所谓“由一般权利质变为权力化权利”的过程[注]陈醇.权利结构理论:以商法为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控股股东遂享有左右公司经营的优势地位,进而令如何防范控股股东侵蚀中小股东利益成为公司法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原本不符合“委托-代理”模型的“控股股东信义义务”遂应运而生。
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控股股东既然需向其他中小股东承担义务,其亦必享有区别于其他股东的权利和利益,这就是控制权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根据经济学理论,公司控制权的价值可以划分为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两个部分。前者系通过控制权的行使令公司绩效提升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后者系控制权人通过各种方式所获得的无法被所有股东分享的收益[注]Gross man S,Hart O.One share—one vote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20.Issue.3.1988,p.97.。传统理论将控制权私人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但这造成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称为“控制权悖论”[注]“控制权悖论”主要包括:1.控制权收益与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悖论;2.控制权收益与其可持续性实现的悖论;3.控制权收益与市场均衡的悖论。参见刘少波.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J].经济研究,2007,(2):31.。国内有学者进一步将控制权私人收益区分为合理控制权私人收益和超额控制权私人收益两种,前者是指大股东所选择的能使小股东保持沉默来获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它既能给小股东带来更多收益,亦有助于改善公司业绩、提升公司价值;后者则具有侵害性质,它不仅让小股东利益受损,还会摧毁控制权私人收益可持续性的基石,最终导致公司衰败[注]冉戎,刘星.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基于中小股东视角的解释[J].管理科学学报,2010,(6):45.。有的学者认为,控制权私人收益具有“私人信息”特征,因而对于外部股东而言,不仅在法律上不可证实,甚至不可观察[注]Dyck A,Zingales L.,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ournal of Finance,Vol.59.Issue 2.2004,p.126.。后来陆续有学者提出各种间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大宗股权溢价法”[注]大宗股权溢价法由美国学者Barclay和Holderness率先于1989年提出,其采用大宗股权转让价格相对于转让消息公告后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溢价水平来测度控制权私人收益。参见郑志刚,吴新春,梁昕雯.高控制权溢价的经济后果:基于“隧道挖掘”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4,(9):47.,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特殊制度背景,测算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均值为27.9%[注]唐宗明,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4):17;余桂明,夏新平,潘红波.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分析[J].管理科学,2006,(3):29.。
虽然学术界业已公认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客观存在,甚至有可能测算出具体数值,因而将“合理控制权私人收益”纳入“合法权益”范畴加以法律保护似乎并无不妥。但是,前述见解只是基于理论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基于各种现实障碍,目前各国尚无就控制权私人收益提供司法保护的先例[注]武常岐,张林.国企改革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及企业绩效[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49.。尽管当前尚不能对“ST新梅案”被告施加金额确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认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必须承认该案原告确已遭受损失的事实,基于“有损失必有救济”的法理,法律理应为原告提供损害赔偿以外的救济渠道。鉴于表决权是控制权的主要实现方式,一旦限制违规超比例增持部分股票的表决权,违规者的控制权意图即无法实现,因此,限制表决权即成为维护“ST新梅案”利益最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民事责任方式。
四、限制违规超额增持部分股票表决权规范路径检讨
(一)《证券法》第213条的规范属性
如前文所述,限制违规超比例增持部分股票表决权是原告最佳救济途径,其亦提出该项诉求,但却遭法院驳回。法律依据是《证券法》第213条关于“改正前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规定,事实依据是王斌忠已于2015年1月23日补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遂据此认定王斌忠已经履行“改正”义务,故表决权受限的法定事由已消失。
笔者认为,法院适用“改正前不得行使表决权”法律条文有误,该条款不能作为判定可否限制表决权的法律依据,理由如下:
第一,基于法律体系解释角度的分析。第213条规定于《证券法》“法律责任”专章,该章除第231条系刑事责任引致条款外,其余各条款规定的法律责任均系行政责任,涵盖警告、罚款、撤销从业资格、市场禁入、责令关闭、没收非法所得等各种行政责任方式。即便在第213条中,“不得行使表决权”的法律责任亦是与警告、责令改正、罚款并列规定的责任方式。因此,在周遭尽是行政责任的“条款丛林”中,独将“不得行使表决权”理解为民事责任显然欠缺说服力。
第二,基于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区别角度的分析。行政责任的前提是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具有制裁性特征;民事责任的前提是民事主体违反民法上的义务,不具有制裁性特征,而是“原有义务之履行”,使受害人恢复至应然状态即可[注]胡建淼,吴恩玉.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属性[J].中国法学,2009,(1):29.。据此论之,行政责任的制裁属性旨在威慑行政相对人不得从事行政违法行为,因此,行政责任的履行通常带来的是公共利益的改善,而非特定个人利益的改善[注]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亦可能会改善某一具体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从而具有民事性和司法性特征,但ST新梅案中,证券监管部门对王斌忠实施的行政处罚并非行政裁决。。与此相对,民事责任的补偿性特征决定,民事责任的履行会直接为特定受害人带来个人利益的改善。
就“ST新梅案”观察,无端丧失控制权的原告并未因王斌忠履行“改正”责任,亦即补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在个人利益上有任何改善。尽管“改正”责任与罚款责任相结合,无疑能够产生一定威慑效果,从而有助于证券交易秩序的改善,原告亦可成为受益人,但这只是公共利益改善的“外溢性”影响,并不符合民事责任所要求的受害人特定与直接改善个人利益两项特征,故“改正”当属行政责任无疑。至于“改正”前“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规定,则意味着限制表决权旨在确保违规增持者履行“改正”义务,既然“改正”是一种行政责任,用以确保该行政责任履行手段的限制表决权责任,亦应认定为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尽管限制表决权兼具民事责任性质,但法律不可能以民事责任作为确保行政责任履行的手段,故第213条规定的限制表决权在功能上是为了确保行政相对人履行罚款责任的滞纳金,亦应将其界定为行政责任。例如,驾驶人不得闯红灯的义务显然是一项行政法上义务,无论该行为是否导致行人的人身或财产受损,都会引起诸如驾照扣分、罚款等行政责任,不能因为罚款与损害赔偿责任都具有金钱给付的外观,即认为罚款属于民事责任。“ST新梅案”中,如果依照法院的逻辑加以推演,必然会得出“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应取决于是否履行行政责任”的结论,这显然是一种逻辑上的“错位”。
第三、基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行为关系角度的分析。我国早期立法在涉及此类问题时,往往直接以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作为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和定案依据,200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即是典型例证。因学术界普遍持批评态度[注]刘俊海.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执法协调[J].现代法学,2003,(1):36;殷洁.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论[J].法学,2003,(6):42.,201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注]《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即修正了传统安排,赋予原告以直接起诉的权利,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亦不再必然是民事诉讼的定案依据。有学者认为,这是司法审判自主性原理的必然结论,因为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应当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审理,独立对争议案件作出裁判,无需假手他人,更不应受行政机关的拘束[注]何海波.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力[J].中国法学,2008,(2):51.。这就是说,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只是作为一项证据而存在,法院并不承担必须采信的法定义务,否则就无异于是放任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侵蚀。因此,无论证监会是否就王斌忠的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处罚,投资者均享有诉权,法院亦有权依据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审理。易言之,无论王斌忠是否履行“改正”责任,均不能成为判定其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当然亦不能成为判定是否限制其表决权的依据。
(二)限制表决权的现行规范基础
《证券法》第213条的规范属性决定该条款不能作为判定是否限制被告表决权的法律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规范资源对被告“束手无策”。笔者认为,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参照关于限制股东表决权的现行规定,同样可以得出限制表决权的结论,理由如下:
第一,《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第18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可以限制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股东会可以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学术界认为,该规定的合理性在于,股东的权利与其出资是对应的,股东只有履行了其出资义务后方可享有股东权利,如果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存在瑕疵,说明其取得股权的对价不充分,相应地,公司可以对其股权的行使作出限制,甚至予以除名[注]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57.。事实上,“ST新梅案”被告实施违规增持行为给原告以及其他投资者造成的损害[注]鉴于本文系以ST新梅案为分析样本,新梅公司、上海兴盛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前文并未详细分析违规举牌行为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事实上,从原控股股东上海兴盛公司的激烈反应观察,王斌忠所实施的违规举牌行为已构成敌意收购,中外学者大量实证研究均已证实,敌意收购并非总是能带来提升目标公司业绩和股东收益的理想结果,公司控制权转移后业绩下滑、收购方掏空目标公司的实例不胜枚举。Andrei Shleifer and Lawrence H.Summers,Breach of Trust in Hostile Takeovers,Reprinted from Alan J.Auerbach,editor“Corporate Takeovers:Causes and Consequenc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34-35.,又何尝小于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的危害性?既然瑕疵出资、抽逃出资可以构成限制乃至剥夺股东权利的正当性基础,那么限制违规超额增持部分股票表决权又有何不可?
第二,《公司法》第16条第2款、第3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该股东不得参加担保事项的表决。法律之所以在此限制股东表决权,乃为避免股东因个人利害关系而可能牺牲公司利益的流弊,确保股东会决议结果不会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注]王文宇.公司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7.。其实,在公司担保情形下,公司承担的只是一种或然性而非确定性的不利后果,亦即,只有当主债务人未能履行到期债务时,公司才须承担担保责任。何况,如果提供的只是一般保证,主债务届期未能履行,公司还可享有先诉抗辩权。这就是说,在公司最终是否承担不利后果尚不确定时,存在利害关系之股东即不得行使表决权。与此对照,尽管“ST新梅案”被告实施的违规增持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存在测度困难,但却是现实存在的。况且,信息之于证券市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公司控制权因违规举牌而在各方猝不及防之际突然转移,已经令目标公司以及诸多利益相关者陷入不测风险之中。据此,基于“举轻以明重”的法理,既然公司利益处于或然受损状态时即可限制关联股东表决权,那么在公司、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确定受损或者同样处于或然受损状态时,当然亦有充足的理由限制违规超额增持部分股票表决权。
(三)甄别举牌意图并无实益
有学者认为法律不应不加甄别地一概限制违规者超额增持部分股票表决权,因为部分投资者系出于套利目的进行财务投资,只是无意间触发5%的持股权益披露“红线”,而非以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为目的,故前者无必要限制表决权[注]陈洁.对违规增持减持股票行为定性及惩处的在思考——以违反证券法第86条权益披露及慢走规则为视角[J].法学,2016,(9):23.。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证券法》第86条规定于第四章,即“上市公司的收购”一章,持股权益披露规则显然是旨在规制公司收购行为;其次,在“安全”思维的指引下,商法历来强调外观原则的适用[注]冯兴俊.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综述[J].法商研究,2013,(6):112.,至于当事人主观意图如何则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因此,虽然不能排除一部分投资者确系以财务投资为目的,“不经意间”违反持股权益披露规则,但判断纯粹的主观意图显然欠缺可操作性,且该违规增持者即便最初确系财务投资意图,但亦不能排除嗣后转变为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因新梅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原告上海兴盛公司持股11.19%即成为控股股东,如果适逢股权结构更加分散的上市公司,违规增持实施公司收购恐将愈发便利。因此,区分投资意图的主张在实践中并无实益,反可能会徒增法律适用困扰。
五、结论
“ST新梅案”裁判规则客观上诱导乃至于强化了市场主体规避法律的机会主义心理,令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沦为“漂白”违规增持行为的工具。在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炒作盛行、脱实入虚现象日趋加剧的背景下,司法裁判必须准确理解法律精神和市场逻辑,确立限制违规超额增持部分股票表决权民事责任方式,据以关闭“ST新梅案”裁判规则为违规收购开启的方便之门,避免危害各方市场主体利益的资本游戏频繁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