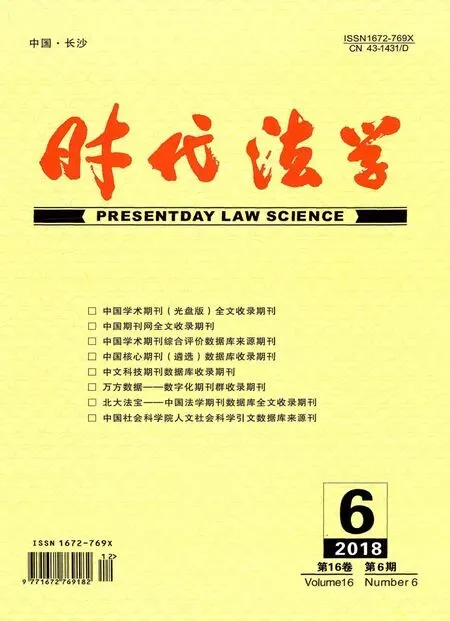检察权的双层权能与效力实现
巩寒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检察权在我国的传统司法实践中被赋予了诸多的权力运用形式,包括法律监督、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批准逮捕、“职务犯罪侦查”[注]伴随2017年11月5日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同职务犯罪侦查相关的大部分权力已完成职能转隶。等,以这些权力形式及其环境要求(包括特定的组织体制和运行原则)[注]所谓权力运行的环境要求是指不同性质的权力运行对组织体制及运行原则等环境的不同要求。为根据,检察权在理论争议中逐渐具备了司法权、行政权、行政司法权、“法律监督权”等不同的权力属性。多数研究者实质上将检察权定性问题看作是检察体制研究的“逻辑起点”[注]陈卫东教授认为,“探讨检察机关的职能以及改革,首要问题就是对检察权的性质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而龙宗智教授在两篇探讨“司法责任制”和“检察权司法化改造”的文章中,也传递出其探求“司法化”本身正是认同了检察权力属性同检察体制改革之间的密切关系。参见龙宗智.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适度司法化改革[J].法学研究,2013,(1),以及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5,(1);此外,刘宗珍博士也认为,“对权力从性质上进行定性将影响权力的特点,进而将影响司法改革的方向。”参见刘宗珍.理解检察权:语境与意义[J].政法论坛,2015,(5).,而所谓“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中回答基本问题的关键概念,其关键性体现为概念对体系本身区别性特征的规定。”[注]周越,徐继红.逻辑起点的概念定义及相关观点诠释[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检察权定性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组织体制和运行原则的区别性特征,例如,行政性权力定性要求“阶层式建构”的组织体系,要求上令下从,讲求效率、服从和管理,遵循官员代换制和职务转移制[注]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司法性的审查起诉以及审批逮捕,则要求体现终局性、中立性特征以及权力主体的独立性地位;而监督权运行则应当以特定的独立性[注]有学者指出,监督权的根本特点在于独立于被监督的权力,其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性质上不同于被监督权力;监督主体对立于监督对象;监督权运行独立于被监督权力。参见夏金莱.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察权与检察权[J].政治与法律,2017,(8).组织结构和单向性[注]“监督模式下权力的结构是单向性的,即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参见夏正林.权力制约中的监督与制衡[N].检察日报,2017-02-22(7).的权利运行为特征。
一、传统检察权定性研究的两个忽视与一个误读
由此可见,检察权定性问题研究确有其关键性和重要性意义,但在笔者看来,围绕权力属性的争议,因过于理论化和模式化,而同检察权运行的复杂实践难以对应。尤其是在我国,检察权除了承担与公诉相关的程序性职能之外,还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在监察体制改革推行之前还承担着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因此,权力定性本身模式化、简单化了的检察权运行研究,并无益于解决检察权运行的实际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权力定性研究忽视检察权存在的必要性和特殊性问题。例如,司法化检察权定性[注]关于检察权或检察官的司法化定性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曾有过短暂的繁荣,谓之“等同法官说”。这一学说面临的问题亦存在于我国检察权“司法性说”中,包括检察体系内的上命下从,法官享有的权力与保障亦不可为检察官所得。因此司法化定性说既不存在理论上的完整性,也缺乏组织体系和运行原则建构的现实基础。可能面临如下问题:在宪法规定的“检察一体”既有体制之下,所谓司法性检察权缺乏权力运行原则和组织体制的保障,此其特殊性不足;其次,现代检察权形成于“诉讼分权模式”[注]台湾学者林钰雄认为,在检察官与法官之间形成彼此节制,可以保障刑事司法权行使的客观性和正确性,而这不构成检察官司法化存在的必要性理由。林所指的节制关系是对“诉讼分权模式”的合理性解释,而此诉讼分权模式不同于所谓检察权的司法化定性问题,诉讼分权模式是近代公诉制度得以延续的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而检察权司法化定性问题探讨的则是我国检察权在行使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审查批捕、提起诉讼等职能时所秉持的角色定位,是“分权”之后何以司法性的问题。下的控审分离,“检察官不是法官,检察机关也不是法院”,并且将“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都等同于“司法化”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后文将对此予以剖析),此其必要性不足。而其行政性定位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如果说侦查权及其运行的环境要求决定了检察权的行政性特点,那么在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之后,是否意味监察监督在实质上承继了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能?由此更进一步的逻辑延伸是,是否意味着公安机关也将以其普通犯罪侦查职能的形式而实质上分享这一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力,可见,由此推导出的逻辑结论是存在问题的。此外,“法律监督权”的称谓本身即是存在问题的。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仅明确了检察机关享有检察权,第129条将检察机关确立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宪法层面并未有“法律监督权”的表述,并且法律监督概念本身是涵盖性的和整体性的[注]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J].法学,2000,(2).,这种定性欠缺“服务于特定组织体制和运行原则”研究上的必要性。因此,对检察权的定性研究也就无助于描述和解决监察改革推进以来的检察权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的问题。
第二,一元化权力定性忽视了检察权体系的多元现状[注]关于检察权力体系的组成存在多种划分角度。例如,“依照权力属性的差异,检察职能被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判断权、追诉权以及监督权”。参见孙皓.论检察权配置的自缚性[J].环球法律评论,2016,(6);依据是否属于监督权力的类型划分,参见夏金莱.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察权与检察权[J].政治与法律,2017,(8).这些划分尽管存在各自角度和参考依据的不同,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是认识到了检察权体系的多元化内涵。。笔者在查阅检察权研究的相关文献时发现,权力定性的关注者多从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的角度切入,并试图用一种权力性质概括检察权的所有功能表现[注]笔者认为这是导致权力性质争议以及诸多问题的根源。检察权不同于审判权、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权(伴随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该权力以归属于监察委员会)运行中相对较单一的功能表现,检察权被赋予了更多性质的职权表现。,而较少关注其差异化权能的具体内容。此外,笔者也注意到,这种“一元化”的研究思路存在于大量的法学体系及概念的研究中,这或许同讲究“集体、一致、统一、和谐的中国‘一元文化’”特点相关[注]孙苗飞.中美传统文化中多元化与一元化特性之比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总之,这种一元化的属性问题研究同检察权力结构的复杂体系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而我国检察权体系构成被认为具有“不同于域外的独特品质,其体系之繁复实在是世所罕见”[注]郝银钟.中国检察权研究[A].刑事法评论(第5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95.。
第三,一元化权力定性与域外检察权审视的符号化误读。我国一元化定性研究伴随着西方“三权分立”称谓或“权力制衡”学说的流传,在本土研究的“忽视”与西方研究的“误读”之间呈现了某种权力模式上的套用和匹配[注]在“忽视”与“误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且这种对应对权力研究格局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具体见于检察权性质的相关研究论述中。笔者在此仅举一例予以说明:传统研究中,学者多从西方“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的格局中,寻求完成对“检察权”的理论定位。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由此造成对域外检察权权力构造的符号化误读。暂且不论,在监察改革推进以来的宪法溯源[注]童之伟教授认为,改革应获得最高权力机关授权,以此赋予改革过程以宪法正当性。参见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J].法学,2016,(12).中,“法律监督机关”的表述被认为是超越了西方经典的“行政权——司法权”的分权理论范畴,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制度安排”[注]袁博.监察制度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未来面向[J].法学,2017,(8).(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元化模式”的另一种展现)。单就对西方检察权的符号化认识而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一元化检察权定性研究造成的理论混淆和误读。在西方社会,检察权并非是非行政即司法的截然二分,检察官或检察机关也并非一种统一的角色定位,尽管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定位于司法机构还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分支以及其他组织体系的差异[注]在西方社会,检察权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中呈现着巨大差异,尤其是相较于法官(司法裁判权)以及警察(行政执法权)而言。,但这种结构定位上的差别并非是决定性因素,法律文化环境的差异也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检察权力的运行。法定主义与权宜主义导致的实践差别要远远超出理论上的预期[注]例如,有学者指出“虽然任职于警察部门,但却属于权宜主义法律观念统摄下的检察官与那些定位于司法系统,但尊奉法律主义的检察官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See Tapio Lappi & Michael Tonry, “Crime, Criminal Justice, and Criminolog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Scandinavia, edited by Michael Tonry and Tapio Lappi. Vol 40 Crime and Justice:A Review of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而案件压力和财政预算的不同,也在影响检察权运行及其职能的实际状况上,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形塑下,正如迈克·通瑞(Michael Tonry)所指出的,警察、法官,乃至矫正(执行)系统人员在法治相对完备的国家大体上是相似的,但检察官却呈现着根本的不同。而不同政治体制、司法体制下的检察权运行的选择差别,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说明了检察权力体系同司法制度体系的迥异选择间存在着密切的形塑关系[注]迈克·通瑞(Michael Tonry)认为,“检察官是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中潜在的最具权力的角色。”联邦法院上诉法官杰拉尔德·林奇(Gerald Lynch)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检察官,而非法官或陪审团,才是事实的核心裁判者(central adjudicator)。典型的如,日本的刑事司法系统就受到了检察官对其行为和工作的组织以及执行方式的强烈形塑。See David T. Johnson, “Japan’s Prosecution System”, Vol. 41 No. 1 Crime and Justice, Prosecutors and Politics: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ugust 2012), pp.35-74.。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涉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权力配置中,检察权是直接影响改革方向与预期的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注]相较于法官(司法裁判权)以及警察(行政执法权)权力运行的固定模式而言,检察官的角色及其权力运行模式呈现了更强的可塑性。。
二、检察权权能研究——双层权能结构
传统检察权定性研究所存在的上述问题促使笔者展开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一方面,套用既有的关于“行政权”、“司法权”以及“法律监督权”的典型模式去认识检察权运行的研究陷入了一种各说各话、各有各理的尴尬处境,所论皆有合理之形,又皆存无法自圆之处;另一方面,伴随宪法溯源,检察权研究被升格到宪法层面、国家政权架构层面。诚然,这一转变在当下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但由此而忽视检察权作为诉讼程序权力本身的技术性特征,似有“夸大其政治性,而忽略其科学性”[注]夏金莱.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察权与检察权[J].政治与法律,2017,(8).之嫌。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研究局面,新的研究起点的选择就变得尤为关键。笔者认为,这个新的研究起点的选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应当避免对权力性质的过度解读,摒弃一元化的研究窠臼;其次,应当从对权力运行的形式要求的关注转向权力的实质内容和效力的考察;第三,应再次尝试在检察权的宪法溯源和域外现状之间,寻求某种技术层面的一致性[注]所谓技术层面的一致性是指非政治性的。就检察权而言,笔者认为《宪法》关于“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是政治性的,这是宪法对于中国检察机关的特别授权。除此以外,检察权本身也同样承担着重要的程序性角色,如提起诉讼、审查起诉等,就这些点而言,检察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技术层面的一致性的,而这是进行相关研究的经验与教训的重要参考。。
综上,笔者认为,“权能”概念在检察权研究中的引入,能够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同时,避免传统定性研究所带来的困扰。首先有必要对“权能”这一概念予以阐释。在查阅的相关资料中,“权能”概念较多的被使用于私法领域。例如已经在民法领域成为通说的观点认为,在大陆法系传统中,物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注]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9.。同样在民法领域,权能被解读为“权利的内容和职能”[注]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232.。方世荣教授进一步将其表述为,权能旨在“揭示权利的具体内容,但在认知角度上不是着眼权利的外在形式,而是强调权利内容不可或缺、能对实现权利的目的发挥特定功能的各种构成。”[注]方世荣.论行政立法参与权的权能[J].中国法学,2014,(3).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权利的性质与其对应的权能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不同性质的权利有不同的权能构造[注]韩松.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J].法学研究,2014,(6).。例如只有具备了所有权的合法形式之后,才能享有相对应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而这些权能依据其不同的构造而发挥独立的功能。当进入公法领域,尽管权能概念的使用较少,但却存在着同私法领域相似的理解角度。丹麦法哲学家阿尔夫·罗斯指出“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的能力。”[注]〔29〕[德]罗伯特·阿列克西.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J].冯威译.比较法研究,2013,(5).或言之,“拥有一项权能意味着拥有某种形式的可能性。”〔29〕由此,可以尝试得出如下结论:检察权权能意味着检察权运行形式的某种可能性。
综上,《宪法》第129条“法律监督机关”的表述,更宜被解释为对检察机关职能上的特别授予,即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特别权能[注]石少侠教授在其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权能”这一概念用来表述检察权同法律监督(权)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将“一元论”观点表述为“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应当统一于法律监督或法律监督权”(参见石少侠:《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对检察权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解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与石教授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尽管检察权与法律监督之间是权力与其特定职能或者说权能的关系,但应表述为“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统一于检察权,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权的特别权能,基于特别授权而获得。”。因此,我国检察权也就具备了双层权能结构,分别是法律监督权能和诉讼权能[注]关于“诉讼权能”的一个大略定义是,以公诉为主的,为推进诉讼进行服务的一系列权力职能的总称。此外在关于检察权的另一种定义中,也可以探求“诉讼权能”的相关表述,例如“检察权是检察机关基于保护公共利益之需要,而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请求及为实现该诉讼请求而行使的一系列权力的总称。”(参见陈冬.监察委员会的设置与检察权的重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尽管这一观点,因其“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性条件不具有特殊性而被指存在问题(“以公共利益为理论基础来界定检察院的法律定位和检察权,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参见夏金莱.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察权与检察权[J].政治与法律,2017,(8).),但笔者认为,“提起诉讼及为实现该诉讼请求而行使的一系列权力的总称”却可以用来恰当的描述“诉讼权能”所对应的权力运行的概念指称。。
(一)检察权的监督权能
《宪法》第129条规定了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有学者以此为据,认为我国检察权在性质上就是“法律监督权”[注]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J].法学,1999,(10).,而这也是定性问题研究中“法律监督权说”的来源,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
首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37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对此,曹建明检察长指出:“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是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曹建明.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N].人民日报,2016-11-23(6).由此可见,“监督”的存在形式包含人大监督、政府监督、监察监督以及司法监督等。而鉴于各个机关在权力类型、权力配置、机构属性方面的不同,监督的存在形式或作用方式必然存在差别。在这个意义上,“监督”是一种综合性的宽泛性的政治定位,“监督”以及“监督机关”更类似于一种职能和地位上的宪法确认,而非具体权力的赋予,也即人大、政府、监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行使其被赋予的通常权力的同时,承担着监督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特别职能,而非特定监督权的赋予。有学者从“刑事公诉具有监督属性角度论证了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制度合理性”[注]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7,(2).,这其实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宪法关于“法律监督机关”的确认,正是基于检察权权力性质本身的职能性定位,而非特定权力的宪法确认。
其次,就我国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与职能配置实践而言[注]例如,《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3条规定了检察院通过两种形式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分别是检察建议和抗诉。,它并不具有服务于“监督”的特别权力形式(相较于域外检察实践而言)。甚至相较于法律便宜主义盛行的西方检察机关而言,我国检察机关在提供“辩诉交易”、“检察程序分流措施(prosecutorial diversion programs)”[注]Tapio Lappi-Seppala, “Penal Policy in Scandinavia.” In Crime, Punishment,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Michael Tonry. Vol. 36 of Crime and Justice:A Review of Research, edited by Michael Ton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等方面的自由裁量空间也十分有限。也即“司法监督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通过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审判、检察职能,依法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行使的权力进行的监督。”[注]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7,(2).
因此,就理论上而言,宪法上的“每个国家机构都有明确的性质与功能”[注]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J].法学评论,2017,(3).应该体现在《宪法》第131条的规定里,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而第129条“法律监督机关”的表述,更宜被解释为对检察机关职能上的特别授予。从实践层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6年和2017年的工作报告[注]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7年3月1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www.spp.gov.cn/gzbg/.中,也分别将“努力增强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及“加强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等作为检察系统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世界范围内的检察实践而言,“监督是各国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不惟我国检察机关独有。”[注]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7,(2).总之,法律监督权能是我国检察权的重要功能,而不是检察权的性质规定,换言之,我国检察机关(检察权)基于宪法特别授权而获得法律监督权能。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权力与权能常常存在着适用上的互换与混同,但就定性与认识问题的特定研究而言,二者的区别却是应当予以明晰的。
(二)检察权的诉讼权能
在世界范围内,检察权在不同权力体制和制度实践中呈现巨大差异[注]检察官在基础环境(包括诉讼模式、法律文化环境、民主责任制),结构定位(司法机构、政府行政分析以及承担特殊目的的政治权力机构),选任、招募和训练等方面存在着根本不同,由此导致了其权力运行方式与机构角色定位的巨大差异。See Michael Tonry, “Prosecutors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Vol. 41 Crime and Justi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4, (August 2012).的同时,也遵循着相似的运行模式。例如,在我国,检察权运行是通过对犯罪的“审查、分析、认定,以决定是否诉诸于审判权来追究某人的刑事责任”的[注]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在英美法系,检察权对应的英文翻译为“Prosecutorial power”。“prosecute”一词的词源意为“follow up, pursue”,在《元照英美法》词典中,其意为:“实行、进行、执行;提起公诉、进行刑事诉讼之意”[注]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09.。追溯较早的16世纪70年代,在英文语境中,它的含义为“带到法庭中来(bring to the court of law)”行“追诉、起诉、告发”之职。而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2-703.中也指出“检察长的唯一权利和义务是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可见“提起诉讼”是检察权力运行的“通行模式”,而这一模式是蕴含于检察权产生的历史基因之中的。
今天,公诉权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注]谢鹏程.论检察权的结构[J].人民检察,1999,(5).。“我国检察机关也是为适应公诉制度的需要而建立的。”当回溯更早时期,公诉制度可被看作是现代检察制度的前身或基石。现代检察制度源于中世纪封建割据时期法国的公诉制度,其优势在于克服了私力诉讼所具有的种种弊端。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公诉制度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废除纠问制度,确立诉讼上的权力分立原则”[注]林钰熊.检察官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6.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由检察官负责包括审查起诉、决定起诉/不起诉、公诉变更、出庭支持公诉和抗诉等在内的现代检察制度体系,以此一方面通过审查起诉、决定起诉/不起诉、批准/不批准逮捕,使得“侦查结果仅有暂定(provisorisch)的效力”,客观上形成对警察活动的节制;另一方面通过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在无控方之起诉,即无法官之裁判(原则之下)……当然成为控制法官裁判入口的把关者。”[注]林钰熊.检察官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诉讼权能是检察权的基础性权能。
由此,检察权运行的基本形式可以概括为“案件的选择与诉的提起”,即通过决定起诉此案而非彼案以表达对特定侦查(警察)活动的支持与否;通过提起此诉而非彼诉、以此罪起诉而非彼罪起诉,从而制约法官的审判权。在某些时期和地区的实践中,搭配特定的刑事实体法案,使得检察官“对起诉罪名的选择权力包含了极大的强迫性”[注]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州,自1975年废除了假释委员会制度之后,针对特定犯罪类型的“强制性最低量性(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制度,以及“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等实体法规定的出台,在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使得检察官对特定起诉罪名的选择直接等同于单边性地决定了犯罪人可能承受的刑罚期限,这在辩诉交易以及提起公诉的过程中,都对嫌疑人或被告人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并在实质上替代了法官的裁判权。,而这被认为“捆住了法官的手并将巨大的权力转移给了检察官。”[注]Albert Alschuler, “Sentencing Reform and Prosecutorial Pow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26:550-577 (197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检察官职位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他必须对案件进行拣选……,而这蕴含了检察官的最具危险性的权力。”[注]Angela J. Davis, “The American Prosecutor:Independence, Power, and Threat of Tyranny”, 86 Iowa L. Rev. 393 (2001). 然而这种所谓的“绝对”也仅是一种表达上的修辞手法。典型的如日本,其战后标榜独立自主的检察体制也正在经历着时代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民意和政治实际上已经成为检察制度不得不考量的重要因素。
综上,检察权的诉讼权能可以概括为“对案件或罪名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我国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改革与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对检察官“拣选案件”、“提起诉讼”、“推进诉讼”的诉讼权力的独立性的保护。例如“主诉、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进旨在摒弃“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内部实行的‘三级审批’的办案机制”[注]陈辐宽.检察改革的问题、使命与前景[J].法学,2015(9).。并且,就我国检察权发挥诉讼监督、侦查监督的具体形式而言,也确实是通过“案件拣选的诉(或不诉)的形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以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注]姜涛.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一个中国问题的思考[J].政法论坛,2015,(6).的职能,这在实质上是扩大并强化了检察权诉讼权能的作用形式及范围。
三、检察权效力实现——以监督与诉讼权能的关系及建构模式为视角
诉讼与监督构成了我国检察权两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权能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蕴含着检察权体系建构与效力实现的根本要求。
(一)诉讼权能的效力——监督乏力的审视与重构
如前所述,诉讼权能是检察权的基石性权能。但在通常的研究中,研究者缺乏对其基石性地位的足够重视,如有的学者将诉讼权能等同于公诉权能,并进而指出“检察权的全部权能在性质上都应当统一于法律监督权”[注]〔54〕石少侠.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对检察权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解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5).。实际上,公诉权仅是法律监督权具体权能之一种。尽管上述认识实现了形式上合乎宪法规范的一致性,但却带来了在司法实践和具体阐释时过于抽象、缺乏操作性的问题,即便其支持者也指出“并不是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监督的权力都被具体化”〔54〕。由此产生的具体问题是:公诉权之外的法律监督权是什么?公诉权之外的监督权实现形式又是什么?带着这一疑问,笔者对现行监督权能的实现途径做了简要的梳理,以期明确其间的问题。
1.监督乏力的规范现状
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涵盖了刑事诉讼程序从立案到执行的整个过程。
在立案环节,对公安机关拒绝执行人民检察院的“通知立案书或者通知撤销案件书”时,检察院有权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但在公安机关仍拒绝纠正时,根据《规则》第560条规定,由检察机关“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协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
在侦查环节,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强制措施运用中的违法行为,依据《规则》第567条、第569条和第570条规定,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在公安机关未回应“纠正违法通知书”时,“敦促公安机关回复。”
在审判环节,除对于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注]抗诉是诉讼权能(公诉权能)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监督职能的重要形式,抗诉本身所引发的原审审级的提升、审判组织的改变展现出了切实的强制性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多样化、强化检察权诉讼权能的运行形式是检察权改革和重构的重要方向。外,依据《规则》第579条、第580条,检察院对于审委会的评议活动和审判活动仅可以“发表意见”或“提出纠正意见”。
在执行环节,对于看守所羁押、执法的监督,见于《规则》第623条、第626条和第630条的规定。相关的监督形式仅包括“提出纠正意见”。另外,对于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规则》第637条、第638条 、第640条、第641条分别赋予了检察机关监督权能以“建议停止执行”,“提出纠正意见”的实现形式。
综上,检察机关的“通知书”、“纠正意见”、“发表意见”、“建议停止执行”、“同公安机关协商处理”等监督形式缺乏必要的拘束力或强制性。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也缺乏进一步的补充性规定。整体而言,检察机关的宪法“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缺乏必要的规范性措施的支撑,就监督效果而言,较为一般。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权能的效力实现方式,但就监督效果而言,不同监督形式之间存在重要不同。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中,便进一步明确了两种主要监督形式的差别,就“检察建议”而言,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其中,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抗诉。可见,检察建议可以看做是初步性的非强制性措施,并不具有一种“监督权”所应当具有的强制力,因此就检察权监督职能的效力发挥而言,仅有抗诉一种形式。
2.监督诉权化的重构设想
就现有检察权监督权能的效力实现方式而言,抗诉以其所引发的原审审级的提升、审判组织的改变等一系列“效果”,展现出了切实的强制性效力。目前,就《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来看,检察院仅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享有抗诉权,而此外的“检察建议”、“意见”、“纠正书”等“监督形式”则明显缺乏必要的拘束力,同“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并不匹配,也难以辅助检察权的效力实现。
因此,从完善检察权监督权能的角度出发,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是扩大检察权抗诉的范围。宜尝试将“检察建议”、“意见”、“纠正书”等作为检察监督的前置措施(形式手段),以其指示受监督主体行为的规范性问题;并将抗诉的提起作为监督的实质性保障手段,在形式手段未能达成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如受监督主体拒绝回复检察意见,拒绝接受检察建议,拒绝回应“违法纠正通知书”,并在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向审判机关提起抗诉。该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就当前的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而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监督诉权(抗诉)化的整体趋势。例如在上述立案、侦查、执行等诸多环节所引发的检察监督情形中,多是因为存在相应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例如“审判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执行活动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而新近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也明确了“行政诉讼监督”的可诉性。此外,这一改革设想也同样涉及到相应实体法的重新修订,以此才能实现对相关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整体性。诚然,抗诉仅是诉讼权能行使的一种方式,在此本文仅以其为例探讨监督权能行使的重构可能性。对监督权能的诉权化重构有着以下优势:
第一,诉讼权能是检察权基石性权能的体现。基于此前的分析,检察权区别于侦查权、审判权,不在于其行政性或司法性的属性之别,也不在于其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性差异[注]有学者指出,一切公权力的行使在本质上均以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和实现为目标。参见胡勇.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再定位与职能调整[J].法治研究,2017,(3).,而在于其权力行使方式的独特性。在我国,检察权以“提起诉讼(公诉)”的方式实现权力效力;在域外,抑或通过案件拣选,将“案件带到诉讼中来”,或者赋予“检察长的唯一权利和义务是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而这种检察权力行使方式的一致性恰恰说明了检察权的区别性(区别于审判权和侦查权)特征所在。因此,对监督权能的诉权化重构,不但合乎检察权运行的内在要求,而且也体现了检察监督的独特性,并因抗诉本身的既有特征而保障了有效性。
第二,可以跳出“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魔咒。一切监督制度设计所面临的根本难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诘问。通过叠床架屋似的机构设置,总会面临对最顶层机构的监督缺位问题,而缺乏顶层机构又意味着监督者本身等级较低的监督疲软问题;此外,内部监督或自身监督又因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而或者形同虚设或者需要借助更加复杂的监督模式和结构设置[注]杨春福.检察权内部监督机制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5).。并且,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低效和财政负担。监督权能的诉权化重构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顾虑。监督权能的诉权化通过将案件“带到法庭中来”接受法庭审判,从而实现了借助现代法庭的更公开的更透明的监督形式。也即,司法审判程序本身的程序特征以及对抗性的结构特点保障了“检察监督”的公正性与客观性。
第三,有效调解案件压力。伴随着审判中心主义,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推行,“监督诉权”改造可能面临的批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案件压力的现实。然而“监督权能的诉权化将导致诉讼量的激增,挤占司法资源”的说法的片面之处在于:首先,“监督诉权(例如,抗诉)”是第二位的、后置的监督措施。其只在“检察建议”、“违法纠正通知书”等形式监督并未得到有效回应之时才发挥作用,是作为所谓“形式监督”的后置威慑性力量而存在的,并不必然导致诉讼量增加。甚至,正因为这种威慑性力量的切实存在将大大提升诸如“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意见”等文书的强制性效力,从而有效威慑、预防并及时矫正潜在的违法行为,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其次,“监督诉权”的建立是配合一整套“诉权体系”的健全而发挥作用的,“抗诉”仅仅是检察权偏向“监督权能”的一种效力实现形式。此外诸如上述“检察程序分流措施”、“检察权的自由裁量”,甚至于大量存在于西方司法实践当中的“辩诉交易”等,都是检察权诉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偏向于“诉讼权能”的组成部分,且可以预想这些诉讼权能形式在检察权运行中的引入,将极大的缓解法庭审判的案件压力,同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纠纷实质性解决等有极大的正面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健全配套的司法制度体系,完善相关的权力和权利保障,摒弃符号化的认识误区,那么哪怕是对相关措施的设计思路的借鉴或参考,都将有益于检察权效力的实现与完善。
(二)诉讼与监督权能关系的再审视
德国刑事诉讼法学大儒史密特言之“不信任,乃最足以形容现代检察官制生成与演变的三字箴言。检察官,乃因对法官及警察的不信任而诞生”[注]〔59〕〔61〕〔62〕林钰熊.检察官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94-95.77-78.。或言之,检察权与生俱有“监督制衡”之基因。
现代检察权自其形成之初即包含了“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59〕的考量。其先分立于“独揽追诉审判大权”之纠问法官,后又为“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创设目的,并辅以“守护法律,保障人权”之任。尽管检察官及检察体制伴随诉讼模式、法律文化环境的迥异,以及定位司法机构、行政分支机构、“自主的刑事司法机关”[注]史密特(Eb. Schmidt)等人以“司法官署”或“自主的刑事司法机关”来定位检察机关,以突出其(行政/司法)双重特性,与此一点,史密特所描述的该种定位,同我国检察机关在“检察一体”原则下,秉持司法机关定位的特征颇多相似之处。等的不同而呈现着巨大的实践差异,但“检察官向来亦居于法官与警察、行政权与司法权两者之间的中介枢纽。”〔61〕这或许可看作迈克·通瑞所谓“根本性不同”之外的“结构性”相似,这种相似亦体现在我国检察权运行之中。“检察官不是法官,但要监督法官裁判,共同追求客观正确之裁判结果;检察官也不是警察,但要以司法之属性控制警察的侦查活动,确保侦查追诉活动之合法性。”〔62〕
检察机关的设置,天然的就不是为追诉犯罪的效率考虑的(显然不设置检察机关,案件直接由侦查程序进入审判程序,更符合经济效率价值的要求),而是为促使案件从侦查机关的追诉向审判机关的裁判过度中,滤去国家暴力机器的实质的以及潜在的威胁,实现公正客观的定罪量刑。
因此,尝试解读检察权监督权能的效力必须首先关注检察权存在的结构性基础,也即权力运行直接所及的两个部位,“警察与法官”。一方面,检察权应监督侦查权启动与运行,以“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靥”;另一方面,检察权应监督裁判权启动与运行,以避免裁断滥权,“保障终局裁判之正确性与客观性。”这是检察权“法律监督权能”运行的根基所在。此外的权能形式的创制与发掘,在形式与结构上必以其为参照。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诉讼分权”、“监督制衡”等概念尽管肇始于欧陆德国法统,却并非西方“权力分立”思想所述的“行政——司法”区分的政治体制一脉,而是基于诉讼活动本身的规律演进,旨在控制警察滥权,以不告不理抑制纠问式审判,以实现保障人权为底线的司法诉讼活动。就此而言,我国司法体系中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建构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监督制衡”的结构特点。检察权处于中间环节,前承侦查权的暴力强制,后启审判权终局权威,因此检察权必须具备相当的“禀赋”,才可以对抗两种颇为强势的权力,而避免陷入警察国或纠问式法官的覆辙。因此,我国《宪法》第129条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对检察权“禀赋”的特别确认。基于此,检察权的诉讼与监督权能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密切关联。对此有学者认为“控诉是手段,监督是目的……由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其目的就是为实现对警察侦查权和法官审判权的双向监督。”[注]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7,(2).然而这种说法在描述两种权能之关联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应当说,诉讼与监督二者并不存在目的与手段上的截然两分。例如在抗诉时,诉讼行为本身即是监督权能的实现过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实质上也是通过“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诉权”而实现对公权力的“法律监督”的。在针对侦查活动的审查起诉时,监督的要求则更多的体现为对“检察官乃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而非政府的传声筒”[注]语出自德国20世纪刑事诉讼法学者史密特(Eb. Schmidt),转引自参见林钰熊.检察官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的角色要求,这是由检察权权力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与其说是权能的特别创制,不如说是对检察权已有权能形式的宪法强化与确认。
因此,诉讼与监督权能的关系更宜表述为,诉讼权能本身即是手段也是目的,而监督权能则需以诉权为载体并有其独立目的,而超越诉权之外的监督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由检察机关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能所面临的批评和争议也揭示了这一点。侦查本身既非诉讼行使也非监督履行[注]有学者指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象应当是公权力,而侦查活动本身是针对公民私人的犯罪行为而进行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行使应当以此为界,否则既成“法律监督泛化”。参见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7,(2).。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不但违背了现代检察制度的创设本意,更会遭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合一的困境。尤其在当前监察改革全面推进的过程中,伴随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部分)转隶,检察机关面临着职能定位与权力结构的调整,检察权的各项权能也同样处在新的创制与发掘之中。事实上,我们更应当注意的是,检察权的效力应当建立在诉讼权能的实现之上,并且只能建立在诉讼权能的实现之上。在宪法“法律监督机关”的整体定位之下,遵循诉讼权能与监督权能的基本关系,在诉讼中发挥监督职能,使监督回归诉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