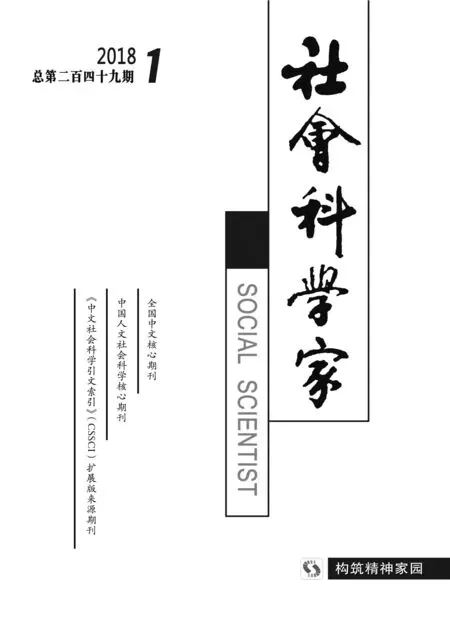正义的中国面孔
——评“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
方旭东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非常高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现在外面风雨大作,其实上海是非常难得这样下雨的。前段时间我们一直盼着下雨。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有贵人来才会下雨。所以,你们是风师雨伯式的人物,才会这样下雨。谢谢你们这些贵人给上海带来这么多的雨水。
言归正传,关于今天的活动,我先大概说一下缘起。近些年来,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刊物、会议了解到,黄玉顺教授这些年一直在做“生活儒学”,我们很感兴趣。生活儒学讨论的这些话题,本身也是很刺激人的一些话题。而且我觉得,黄教授是很有论战色彩的,例如,上次在曲阜,关于“贤能政治”的问题,他跟贝淡宁(DanielA.Bell)两个人就唱了一场对台戏。[1]我们举办这样的小型座谈,相当于沙龙,是因为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国内同辈学者之间,甚至上下两代学者之间,缺乏这样一种形式。西方的学者,一般来说,如果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出来,大家会开一个会,很深入地来讨论。有这样一种机会,我觉得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很好的。而我们华东师大哲学系呢,本身就有一个探究哲学理论的传统。我们系里现在有定期的青年哲学沙龙,我自己以前在系里也组织过哲学俱乐部。我们特别强调要带有批评性,好话不用当面说,背后再去说他好。
今天呢,我就来担任一个相当于报幕员的工作。因为大家都已经认识了,介绍的环节我们就跳过去。之前我跟黄教授一起拟了一个议程,现在我们就按这个议程来,首先请黄教授开个头,做一个引言式的个人观点陈述,然后我们进入逐个发言的环节,最后再请黄教授集中回应一下。①以上三段,是方旭东教授作为这个研讨会的主持人的开场语,今移于此。
一
我们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儒家学说或想法比较多了起来,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有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十多年来,黄教授一直在“生活儒学”上用功,现在这本《爱与思》已经是增补本了。但是,据我的观察,他后来发展出来的东西,尤其是最近几年所深入探讨的形而下的部分,已经不是最初的“爱与思”的框架了,已经超出了这本书的四讲的范围了。我相信,他的这种理论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于原来的“爱与思”的架构了。所以,他这次增补的部分,我觉得是提纲挈领地把他最近几年的思考呈现出来了。前面各位对“爱与思”或者“存在”这个部分讲得比较多。就我个人来讲,他后面发展出来的部分,尤其是最近几年讲的“中国正义论”、“国民政治儒学”这些东西,我更感兴趣一些。所以,我今天要发表的感想,或者说是评论,主要是针对这个部分。
在向黄教授讨教之前,也许我可以先讲讲生活儒学的一些特点,讲讲我对生活儒学的观察。我讲三个意思。
我主要是做宋明理学的。明代的阳明学,王阳明之后主要是所谓阳明后学,王阳明的学生发展出很多流派,诸如:以王畿为代表的现成派,以王艮为首的日用派,以聂豹、罗洪先为首的归寂派,以欧阳德、邹守益、钱德洪为首的修证派。那么,借鉴王门后学的这种分派,我觉得,如果现在要给黄教授的生活儒学来一个命名,也许可以称之为“当下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生活儒学”这个名目似乎还嫌不够鲜明,不够特别。我觉得,黄教授讲“生活”,其实他要突出的就是“当下”、“当下现成”这个意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跟他是有共鸣的。我一直认为,对儒学的理解,不应该有一个现成的框框,好像儒学是一个现成的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黄教授的生活儒学,其实就是非常强调生活就在当下,是特别活的,所以很难用以前的东西来框定。而像牟钟鉴先生,还有我老师陈来先生,他们讲的可能更多的是面向历史的,是就历史本身发挥演绎出来一个东西。而黄教授的讲法,我之所以称之为“当下派”,就是整个进路跟他们的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就黄教授的学源来讲,他以前是在中文系,在训诂方面下过功夫、做过工作。我们这边的刘梁剑教授,他对语言哲学比较感兴趣,专门研究汉语言哲学。所以我猜想,他后面大概会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讨论。我是说,黄教授的这种训诂训练,他原来的这种学术经历,对他的整个写作,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就我所读到的他的中国正义论、国民政治儒学,在所有的关节处、看家的地方,他都是从训诂讲出来的。比如,他关于中国正义论的两个原则(正当性原则与适宜性原则),就是从汉语“义”字的训诂发展而来,他说:“正当”乃是汉语“义”或“正义”的一项基本语义[2],“适宜”也是汉语“义”或“正义”的一个基本语义。[2]每一条都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如果是没做过训诂的人,那在这些地方是不能不服的。这是我的一个观察。运用训诂学或语义学方法做哲学,好像在西方哲学家里,海德格尔也喜欢这么做;在中国,清代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路数。这种路数,也许可以说,更偏于“语学的”(philological)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的”(philosophical),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古典解释学当中“语学的”方法与“哲学的”方法(也就是传统所说的汉宋之争),我借用意大利学者罗伯特·艾科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这个概念,[3]进一步提出,站在汉学或语学的立场,会认为宋学或哲学的解释未免过度;反过来,站在宋学或哲学的立场,会认为汉学或语学的解释未免不足。[4]对语学方法的详细检讨,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展开,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在西方显然是有别于,比如说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则是有别于宋明理学的。
还有,好像刚才也有人提到了,那就是,《爱与思》初版(也就是现在这个增补本的正篇),我觉得现象学的味道太重了,受现象学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而我自己比较偏好分析哲学,所以,现象学的很多东西,我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我在读《爱与思》增补本的时候,经常会在上面打问号:这样讲的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像“爱与思”这个书名,它就是一个诗性的标题,是一个浪漫的标题。这大概是因为四川多才子的缘故吧?像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5],他就拎出“怕”和“爱”两个字。黄教授呢,他拎出“爱”与“思”两个字。这些都是很文艺、很浪漫的词。我觉得,好像一般做学术,不用这样一些词,学术性的语言与诗性的语言可能还是要有所区分吧。不过,我也注意到,黄教授后来讲中国正义论的部分,相对来讲,前面那种诗性的语言就比较少了。
以上是我对生活儒学、对《爱与思》增补本的一些观察。因为我感兴趣的、比较注重的是后面增补的部分,所以,接下来,我想跟黄教授请教的,就是关于“中国正义论”的这个部分。我讲的这些,也许在去年你们开的那个会①指2016年8月20日至21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可能已经有人提出来过了,对黄教授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新鲜的,如果是这样,我要请黄教授以及各位原谅。
二
我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黄教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原则的评价问题。黄教授在书中写道,他的“中国正义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他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特别强调它们其实是纯粹“形式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他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罗尔斯正义论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其实根本就不算正义原则。这个讲法,我初听的时候,就像当年徐爱对王阳明有关“格物”的理解是“初闻而骇”,我是有一些惊骇的。黄教授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实不是真正的正义论,他讲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正义论,因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还不够形式,还是实质的,即已经是一种制度建构。
黄教授主要是从中国文字训诂学的角度来讲的,从“义”字归纳出两条正义原则,一条是正当性原则,一条是适宜性原则;然后又进一步区分时间上的适宜性,空间上的适宜性。确实,他的讲法完全是形式化的,就是说,关于究竟怎么样的制度安排才算是正当的、适宜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他认为,一种真正的普适的正义论、正义原则,只能讲到形式的层面,不能有任何内容的部分,否则就会陷入具体的历史、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文化,就没有普适性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讨论的。我恰恰觉得,要讲正义,就必须要讲到一个实质性的原则。否则,如果只是抽象地讲“正当”、“适宜”,抽象地讲时间上的适宜、空间上的适宜,那是不够的。比如说,“义”本身当然可以训为“正当”,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正当?怎样才叫正当?这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当然,罗尔斯也会讲到抽象形式的层面,比如“无知之幕”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对“正当”的理解都不一样,比如说,穆斯林和美国人都认为做事要正当,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正当的?我们怎么来讲“正当”?还是需要实质的内容的。所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就有实质的内容,比如说minimax原则,即照顾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差别原则”。他的这种处理,不是没有意义的。
三
第二点,是关于“义”与“利”的问题。
我发现,黄教授有一个地方讲得特别好,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他在“仁”和“义”之间插入一个“利”的环节,而且把“利”和“仁”联系起来。他这一套讲法,我觉得至少他自己是把它圆起来了。
确实,要讲“义”,就必须讲“利”,因为“义”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利益问题的嘛。黄教授虽然不同意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原则是正义原则,但是,他不否认罗尔斯的这个观点:什么是正义问题?就是处理有关利益、有关资源分配的问题的嘛。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利”字。我觉得他特别有发挥的是两个地方:第一,他一反传统的讲法,而强调“利”。传统的讲法,好像儒家只讲道义论,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汉书·董仲舒传》。原文“义”作“谊”。。这好像是儒学对“义”的一种更常见的理解。而黄教授注意到,儒家讲“义”,其实跟“利”的关系很大,儒家从来不回避“利”。第二,他有一个提法:“利”是因“仁”而起的,最后又因“仁”而消。我觉得他的这些讲法都是很特别的,我待会儿讨论。
就第一个问题、即“利”的问题来说,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区分。儒家讲的这个“利”字,事实上有两种讲法,它们之间是有一点紧张的。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儒家通常讲的是“正其义不谋其利”。但是,儒家对“利”还有一种讲法,黄教授也引到了,就是《易传》里面讲的:“利者,义之和也。”(《周易·乾文言》)这个讲法,黄教授是比较强调的。
在“义之和”这个意义上、即在“利”的正当性的意义上来讲“利”,这个地方我觉得需要补充一点。我这次读他的书,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中国正义论的一些关节的地方,荀子对他的理论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石的作用,这是我一开始没想到的。但是,其实,在宋代的理学的讨论当中,大家更重视孟子。黄教授也引到孟子,但特别引荀子。而宋儒呢,特别是朱子,他在《孟子集注》里面讲“王何必曰利”的那一段,非常有名。(《孟子集注·梁惠王上》)他那里面就提到了儒家关于“利”的两种理解之间的紧张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稍微有点了解,是因为正好去年我写过文章,讲朝鲜的李退溪,他把朱子讲的这个问题发挥得很大。[6]实际上,李退溪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就搞不懂,说:孔夫子很明确地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尚义”嘛,可是为什么《易传》当中又有“利者,义之和也”这种“利”字有好的意思的讲法呢?这个朝鲜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请教李退溪。李退溪就把朱子在《孟子集注》中的一些讲法、包括《孟子或问》里面、《语类》当中的一些讲法拿出。我感觉黄教授注意得比较多的是“利者义之和”这个方面,而不是传统儒家讲“义利之辩”的那个方面。
我现在的一个基本结论或者说一个基本倾向是:儒家基本上是肯定“义利之辩”的;但是,如何融合不同经典之间关于“利”的不同言说,这还是有解释上的困难的。朱子的讲法,我的理解是,就其思想的倾向来讲,他其实还是要强调维持孟子讲的“王何必曰利”,就是说,如果天下皆言利,那后果很严重。我觉得,就他的思想立场来讲,朱子是强调“利”和“义”之间的这种紧张性,但是,黄教授在他的书里强调了由“利”到“义”的序列,而没有特别关注反过来的情况。
前面讲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是处理利益分配问题的。为什么他的两个原则至少在西方被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恰恰是因为他面对利益冲突,除了恪守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平等的自由原则,还提出了一个最有利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所谓差异原则。而这个差异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调节性原则,它所致力的目标是社会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重新分配。正是在这一点上,罗尔斯与保守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后者以诺奇克为代表,向罗尔斯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凭什么、以什么样的理由去做这种制度调整和重新安排,让社会中一部分人再次让渡一部分权利来周济那些弱势群体呢?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具有实质内容,才会激起反对之声,如果罗尔斯只是提出一些抽象的形式性原则,比如,主张人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恐怕也不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实质性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像黄教授说的他那个正义原则根本不是正义原则;也就是说,仅仅提出来一种纯粹形式性的适宜性原则或者正当性原则,是不解决问题的。
四
还有一点,是关于“仁”与“爱”的问题。
黄教授的一个提法是:是爱导致了利益的冲突。就我的了解来看,至少宋儒就从来不会把“爱”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范畴提出来,作为一个更本源性的东西。在宋儒那里,尤其是在朱子的讲法里面,“爱”这个词不会那么突出。实际上,更本源性的概念是“仁”。我觉得这可能更符合儒学的通常的讲法。
当然,对黄教授来说,这可能并不重要。因为,黄教授可能会说,他讲的“爱”其实就是“仁”。问题是,黄教授理解的“爱”,恐怕不能说就完全可以跟“仁”,尤其是宋明儒学讲的“仁”画等号。比如,黄教授非常强调情感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恰恰就是朱子讲的:“爱”只是“情”。按照朱子,凡是讲到“情”,它都是一种由“性”发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更本源的东西。
也许黄教授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的取向本来就不是要对儒学做一种学术史的研究,而是提出他自己对于儒学的认识,因此,与历史上的儒学观点一致不一致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但是,即便从理论本身来讲,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黄教授已经看到,爱会导致利益的冲突,是因为爱本身是有差等的,而且这几乎就是人的一种自然状况,全人类都是这个样子,美国人也是,中国人也是,肯定是爱自己家人比爱外人多一点。最近网上不是在讨论费孝通当年提出的“差序格局”吗?①由苏力的一篇论文《较真“差序格局”》(《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而引起的讨论。费孝通那时候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现在人们会反问:难道西方人的爱就没有差等吗?其实,正是因为要克服爱的差等性,人类才需要讲“博爱”,才需要讲更高的东西。《圣经》里面不是有“爱邻人”与“爱敌人”这样的诫命吗?②见《马太福音》,5:44。爱自己的家人,这谁都会;但是,爱自己的邻人就很难,爱自己的仇人几乎是impossible的,但正因为难,这才需要去做。对于《圣经》的这条诫命,康德的解释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邻人与敌人不是人们日常所爱好的对象,爱他们是出于责任的表现。[7]黄教授后面也讲:利益的冲突,能够由“仁”来化解。但是,这里的要害,实际上宋明儒学里面也讨论得比较多,就是:从“差等之爱”到“一体之仁”,是怎么出来的?是如何可能的?讲到最后,其实就是:究竟怎么能够用“一体之仁”来消弭“差等之爱”?像程颐就对“一体之仁”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曾经笑问一个主张万物一体的:“他人食饱,公无馁乎?”[8]
这个问题对于儒家来说很严重,因为处理不好“差等”的问题,不仅仅涉及所谓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在当代的语境,还会面临诸如动物权利论者的挑战。实际上,王阳明当年就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一方面,他讲万物一体,讲得非常好,上到天下国家,下到鸟兽、草木,甚至瓦石,他说都可以为一体。[9]另一方面,人家问他,既然如此,“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王阳明回答说:“惟是道理,自有厚薄”,“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这是道理合该如此”。[10]说了半天,该吃动物的时候还是吃,发生危险的时候还是先救自己的亲人,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与“爱有差等”比,“一体之仁”终究还是次一级的原则,在爱有差等面前,一体之仁显得苍白无力。
所以,我很希望黄玉顺教授在这个地方做更多的解释:“利”因“爱”而起,又怎么因“仁”而消?对于我们这些做宋明理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恰恰就是最难理解的地方。
[1]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与贝淡宁教授商榷[J].文史哲,2017(5).5-19.
[2]黄玉顺.爱与思(增补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366;371.
[5]艾科.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4]方旭东.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例[J].哲学研究,2005(2).
[5]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三联书店,1996.
[6]方旭东.递相祖述复先谁——李退溪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J].湖南大学学报,2017(4).
[7]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一)[A].二程集[C].北京:中华书局 2004,2.413.
[9]王守仁.大学问[A].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96.
[10]王阳明.传习录下[A].王阳明全集[C].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