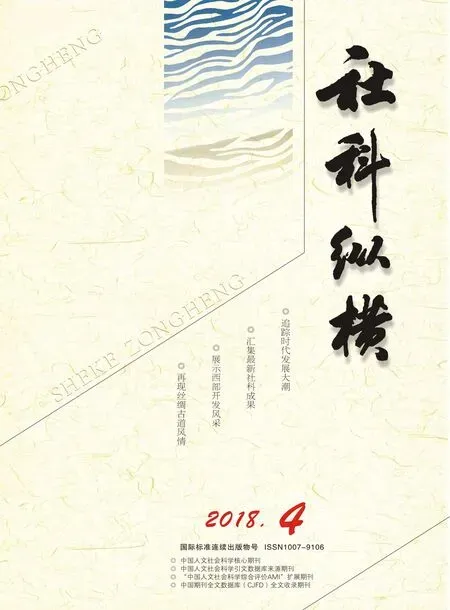弗雷泽和霍耐特关于再分配斗争的比较研究
袁 丽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0)
一、“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的经济不平等
当今社会,随着新社会运动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弱势群体日益关注那些未获得承认或被错误承认的独特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发动寻求主流文化价值模式对其认可和尊重的承认斗争。在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看来,这意味着当今社会呈现出“后社会主义”状况。在《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一书导言中,她描述了这一社会状况的三大构成性特征:一是尽管斗争阵线急剧增加,但缺乏替代现存秩序的任何可信的进步性前景;二是随着“身份政治”兴起、阶级去中心化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相应衰落,以再分配为正义的核心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治想象转向以承认为正义的核心问题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想象;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面对具有攻击性的市场化以及急剧攀升的物质不平等时,平等诉求去中心化。[1](P1-3)可见,“后社会主义”状况下,承认取代再分配成为正义话语的核心,“为承认而斗争”迅速成为政治冲突的典型形式,边缘化或取代以往人们为经济领域的物质和财富的平等分配而进行的再分配斗争,正如弗雷泽所说:“群体身份取代阶级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文化统治取代剥削成为基本的非正义。文化承认取代社会经济再分配成为非正义的矫正和政治斗争的目标。”[1](P11)新社会运动使文化领域的不正义凸显出来,一些弱势群体的独特性或差异没有被主流文化价值模式承认或被错误承认,遭遇了身份贬低或蔑视,因此,“为承认而斗争”在“后社会主义”状况下迅速发展起来。但随着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经验上无数事实都说明经济领域的不公正并没有得到消除,相反进一步加深和扩展。正如弗雷泽看到的:“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发生在一个物质不平等急剧恶化的世界中,……物质不平等在美国、中国、瑞典、印度、俄国和巴西等世界大多数国家正在加剧。同时,它也日益具有全球性,显著地沿着南北分界线发展。”[1](P11)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诸多方面不同意且批评了弗雷泽的观点,但完全赞成她对当今社会经济不平等仍然存在且日益加剧这一判断。霍耐特明确指出:“大多数人口走向日益增长的贫困的趋势、一个无权使用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的新的‘下层阶级’的出现及极少数群体财富的稳定增长——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可耻的表现使得这一点显得自明的:即赋予基本品(essential goods)的公正分配的规范观点以最高的优先性。”[2](P112)可见,弗雷泽和霍耐特在强调对个体或群体独特性的承认时,并没有忽视经济领域物质和财富的分配不正义,他们都承认经济领域不平等的客观存在,因此经济领域的再分配斗争仍然重要,只不过,两者对再分配以及它与承认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已。
二、弗雷泽:承认与再分配“视角的二元论”
当今社会,主流的制度化文化价值模式将某些弱势族群建构为低下、无能且不值得重视的,从而应接受其文化统治,同时不承认或蔑视他们独特的文化产品、价值信念、文化身份等具有的价值,体现为一种文化的不正义。在弗雷泽看来,矫正这种不正义的措施是“文化或象征的变革”,包括“积极地重新评价被蔑视的身份或被污蔑群体的文化产品,承认并积极肯定文化多样性,或改造将改变每个人的社会身份的表述、解释和交流的大规模社会模式。”[2](P13)这些措施不尽相同,前两种意味着肯定个体和群体的独特性,承认并平等地对待彼此间的差异;后一种则是通过改造文化价值模式,来消除或解构现存的差异。不过,弗雷泽统一将它们称之为“承认”,也就是说,文化不公正的矫正方案是承认。与文化领域中体现为文化或象征的不正义不同,经济领域的不正义在于不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得某些弱势群体的劳动成果被他人无偿占有,或将他们限定在不被重视的边缘性工作中,或甚至完全拒绝给予他们有酬工作机会,物质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公。面对经济领域的这些不正义,矫正的方法无疑是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劳动分工的重组、改变财产所有权结构、投资决策制定的程序民主化,或对其他的基本经济结构进行改造。”[2](P13)与对文化不公正的矫正方法一样,经济不正义的这些矫正方法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但弗雷泽统一将他们归于“再分配”这一术语之下,即经济不正义的矫正方案是再分配。
在弗雷泽的理解中,区分经济和文化不正义及与之对应的再分配和承认矫正方案,这只是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一区分只是分析上的,并不代表实际情况。因为,几乎不存在不包含任何文化维度的经济不正义,经济领域并非跟文化无关,而是一个文化工具化和重新意义化的领域,即使是最具物质性的经济制度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意义与规范,受到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在市场经济中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无疑与男尊女卑的思想文化传统有关。同样,也不存在不包含任何经济维度的文化不正义,伴随着不公正的制度化文化价值模式产生的是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举例来说,文化上被建构为低劣、卑贱和不应受到重视的黑人族群在经济领域也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常被限制在辛苦、低报酬、地位低下、卑贱、肮脏、家务性劳动中,与“白人”从事的轻松、高薪酬、地位显贵、白领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管理性工作明显对立;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被剥夺了获得任何有酬工作的机会,被拒绝纳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可见,经济不正义和文化不正义绝非两个封闭的独立领域,它们之间交互重叠、相互作用,彼此纠缠而不能截然分离。相应地,再分配与承认之间的区分也是分析上的,并不意味着实践情况中的绝对分离和对立。因为经济和文化不正义之间的相互纠缠,所以我们在实际矫正这些不正义时同时需要再分配和承认。不仅如此,再分配矫正通常都预设了一个基本的承认概念,比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其政治哲学中宣扬资源平等主义,把平等称为“至上的美德”,在“拍卖”、“保险”和“税收”等概念基础上推出了一种再分配的分配正义。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能要求资源的平等分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获得平等尊重的权利,将平等主义社会经济的再分配建立在对“人的平等道德价值”的同等尊重基础上。[3](P112-151)同样地,承认的矫正有时也预设一个基本的再分配概念,如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在《自由主义、社群和文化》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对社群和文化的自由主义解释,认为“自由主义也包含了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更为广泛的说明——特别是对于个人在社群和文化中的成员身份的一种说明。”[4](P1)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容的,将其主张建立在一个完整的文化结构中要求对基本善进行正义分配的基础之上。可见,经济和文化不正义、再分配和承认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密切的关系,不能被绝对地分离和对立,从这一点出发,弗雷泽批评了“实质的二元论”。因为其将再分配和承认归于两大不同的正义范围,对应着两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前者属于社会的经济领域,对应生产关系;后者则属于社会的文化领域,对应承认关系,两者有明确的界限和作用范围。所以,当我们考虑像劳动分工这样的经济事务时,我们应采取分配正义的立场,关注经济制度和结构对社会参与者相对地位的影响。相反,当我们考虑女性在公共文化中被贬低和蔑视等文化现象时,我们应该采取承认的立场,考察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对社会参与者相对地位的影响。
但我们在强调经济和文化不正义、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交互重叠和相互作用时,又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否认区分两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后结构主义的反二元论”支持者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艾利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等人否认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之间作为二元的划分,在她们看来,深刻地相互关联和构成的文化和经济不可能被有意义地区分;同时,当代社会高度体系化,反对任何一方面的斗争必然会威胁整体,区分承认诉求和再分配诉求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所以,取代将身份和阶级、承认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她们主张解构所有的差别。弗雷泽批评了这一方法,认为它不适合当代社会的理论建构,因为简单地规定所有的不正义以及相应的矫正要求同时是经济和文化的,会模糊实际存在的地位与阶级间的分歧,从而放弃了理解社会现实所必需的概念工具,同时,把当代资本主义当成一个有着完全连锁性压迫的整体系统将遮蔽其实际的复杂性,这一方法远不是努力推进再分配斗争和承认斗争之间的结合,它不可能容纳如何使当前偏离且冲突的两种斗争形式可能被整合和协调这些紧迫的政治问题。[2](P61)
如果说实质的二元论过于强调经济和文化不正义、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区分和差异的话,那么后结构主义的反二元论则过于强调两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两者都具有片面性,因而都不能作为思考当代社会正义问题及建构相应正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于是弗雷泽提出“视角的二元论”(perspectival dualism)。不同于实质的二元论,在视角的二元论下,再分配和承认并不对应于两个独立存在的社会领域——经济和文化;相反,每一实践都必须看成同时是经济的和文化的,从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评估他们其中的每一个,当然不必按同等比例,在更具经济特征的不正义中,我们应更多地采取再分配的方法,反之亦然。也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反二元论,视角的二元论允许我们从理论上区分经济与文化、再分配和承认,进而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它把再分配和承认看成是社会正义的两大基本维度,分别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上独特的方面相关:“承认维度对应于社会的地位秩序,因此对应于这一结构,通过社会地确立的文化价值模式,文化上被定义的社会行动者种类——地位,每一种通过与他者相比的那种相应尊重、声望和尊敬而被区别开来。相反,再分配维度对应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对应于这一结构,通过财产制度和劳动市场,经济上被定义的社会行动者类型或阶级,通过他们不同的资源赋予而被区别开来。”[2](P50)同时,每一维度也对应一个分析上独特的从属或者说不正义形式,“承认维度与根源于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的地位从属一致;相反,分配维度则与根源于经济体制的结构特征的经济的阶级从属一致。”[2](P50)再分配与承认分别对应社会秩序的分析上独特的方面,两者有着不同的作用领域和从属形式;但彼此又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对当今社会正义的实现来说同等重要,不能像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一样简单地将其中的一个还原为另一个。文化主义是将政治经济还原于文化、阶级还原于身份地位的一元社会理论;经济主义则相反,将文化还原于政治经济、身份地位还原于阶级,其共同的问题在于错误地理解政治经济和文化、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关系,不正确地使其中的一个还原于另一个,从而遮蔽了其价值和意义。
视角的二元论既强调经济和文化不正义、再分配和承认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又在分析或理论上将两者区别开来,将其各自对应的社会秩序、作用范围、从属形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论化,这样我们就可以“立即理解他们在概念上的不可还原性、经验上的分歧以及实践中的相互纠缠。”[2](P64)这一方法有助于克服实质的二元论、后结构主义的反二元论、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问题,为思考和解决当代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了合适的方法或概念工具。“视角上被理解的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差异,就不是简单地再生产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分裂,而是为质询、解决并最终克服这些分裂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2](P64)通过视角的二元论,弗雷泽将“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的再分配斗争与承认斗争结合起来,使再分配和承认作为正义的基本维度,共同受制于参与平等的这一规范原则,建构了一种包含经济、文化等多维正义本体的规范一元正义理论,为当代社会正义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三、霍耐特:作为为承认而斗争的分配冲突
在霍耐特看来,当代社会的“承认理论转向”不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回应,即反映了新社会运动中,弱势族群寻求对其独特的价值信仰、生活方式和文化身份承认的要求,而是代表回答一个理论上固有难题的尝试。“不是身份政治诉求的兴起——更不必说多元文化主义的目标——证明了根据承认理论来重铸社会批判理论基本概念的合理性,而是社会不满和抵抗的道德动机的改良的深刻见解。”[2](P125)因此,他反对弗雷泽将承认理论作为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回应,因为在大量的日常斗争中,只有相对可忽略数量的斗争成功获得政治公共领域的关注而被官方承认为“新”社会运动,也就是说新社会运动本身具有偏狭性,遮蔽了大量日常斗争的存在。通过继承和发展青年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承认思想资源,结合乔治·米德(George H.Mead)的社会心理学,霍耐特构建了一种从道德视角剖析社会冲突与变革过程的解释模式,创立了其影响深远的承认理论。在他看来,将社会承认仅限于文化形式是错误的,至少存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三种深植于资本主义道德秩序的承认领域。通过对个人身份形成的历史条件的反思,他提出爱、法律和团结三种承认形式,各自能发展出自信、自尊和自重的实践的自我关系,并分别对应需要原则、平等原则和成就原则三大承认原则。主体的完整性建构和自我实现依赖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如果相互承认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主体就会产生蔑视的情感体验,对应三种承认形式存在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贬黜其生活方式)三类不同的蔑视形式。为减少或消除这些蔑视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个体必然会“为承认而斗争”,蔑视的道德体验构成了社会冲突和变革的根本动力。
我们知道,在前现代社会中,个体的法律承认(即由某些确定权利所保护的作为社会成员被承认的地位)直接与个体由于出身、年龄和职业所享有的社会尊敬相关。个体能合法地支配的权利范围某种意义上直接来自于已确立的声望框架内其他社会成员所赋予他/她的荣誉或地位。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是以荣誉为基础的等级制度,这里的荣誉一词本身是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就其内在本质而言是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个体能否获得荣誉依赖其出身和财产等先天性因素,因此荣誉并非人人都能享有。但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典型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和发展,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传统的荣誉观念失去合法性,个体在法律上应得的社会尊敬不再取决于有着相应荣誉符码的政治等级制度中的成员资格,而是工业化组织的劳动分工结构中的个人成就,成就原则成为社会尊敬分配的规范标准。拥有不同能力和才干的主体对社会的贡献不同,应得的社会尊敬及物质资源也相应不同,由此成就原则为“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提供了道德上能得到辩护的规范资源。个体依据其成就而不是出身、宗教信仰等其它因素而享有社会尊敬及物质资源,这有利于避免强权,体现了合理社会秩序下的平等诉求,具有深刻洞见。但成就原则本身存在问题:一方面,评价标准具有片面性,成就范围的确立依赖以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和男性资产阶级为规范参照点的价值标准,仅仅表达了那些拥有资本和重组社会经济再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精英群体的价值视野;另一方面,评价成就的方式受到有助于决定什么应算作个人努力的表达的陈旧世界观的影响,导致某些人的努力被排除在成就考虑范围之外。比如自然主义的思考方式将本质主义的集体特性归于家庭主妇或母亲这样的亚群体,她们的实践努力不被当作是成就或工作,而仅仅是天生本性的实现,因此不被作为生产性贡献而得到社会尊敬。可见,人们在经济领域中获得的不同的物质资源和社会尊敬不完全反映其努力和所创造的成就,确定什么能算作成就的方式和和评价成就的标准本身就受到诸如资产阶级精英主义和性别歧视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制度化文化价值模式使某些人的努力根本不被当作成就或使其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尊敬。“不仅哪些活动能被评价为‘工作’,并因此是符合职业化资格的;且每项职业化活动的回报应该多高,都取决于深植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的类别形式和评价方案。”[2](P153-154)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领域中为物质资源和财富的平等分配而进行的再分配斗争就是为重新评价主流的成就定义而进行的承认斗争,作为对他们实际成就的蔑视经验的回应,他们试图通过质疑已确立的成就评价模式来争夺更多的社会尊敬和经济分配。
社会尊敬和物质资源不能全部依据成就原则来分配,不仅因为其自身存在缺陷,还因为个体不只是作为生产性的个人也作为拥有同等自治权利的法律个体来参与社会生活。作为法律个体,他/她拥有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同样的自治权利和资格,应受到同等尊重,所以不依赖现实成就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尊敬和经济福利必须得到保证。因为“社会成员只有被保证与收入无关的最低限度的经济资源,才能实际地利用他们受到法律保障的自治。”[2](P149)但在实际过程中,经济领域的物质分配极为不公,某些弱势群体最低限度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机会没有得到保障,无法成为与他者平等的法律个体并享受同等尊重,这会产生剥夺权利的蔑视情感体验,动员起寻求法律上平等对待的社会斗争。
可见,在霍耐特的理解中,物质资源的分配应服从两大基本原则:一方面,较少部分的物质资源应该以社会权利的形式来给作为法律个体的个人以保障;另一方面,更大份额的物质资源应该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原则来分配,按照其成就或贡献大小来给予个体不同的物质资源。也就是说,物质资源的分配应同时实现承认的平等原则和成就原则,从而既保障作为平等法律个体的基本权利,又不至于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淖,阻碍社会竞争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经济领域的不公正使得这两个承认原则都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被指派为‘分配斗争’的社会冲突呈现两种形式,因为他们能够既通过发动合法的争论,又通过重新评价主流的成就定义而发生。”[2](P150)也就是说,“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的再分配斗争一方面为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源和财富的保证;另一方面则为特殊的能力和才干的得到应有的财富分配,既寻求平等的法律承认又要求公正的社会尊敬。这样“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的再分配斗争就被理解为“为承认而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由于承认的平等原则和成就原则没有得到实现而在道德上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冲突。
四、结语
尽管弗雷泽和霍耐特都认为“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经济领域的不公正依旧存在并不断加深,再分配斗争仍有必要,但两者对再分配的理解以及再分配与承认关系的看法大不相同。霍耐特坚持承认的一元论,将再分配斗争理解为承认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由于承认的平等原则和成就原则没有得到实现而在道德上被动员起来的斗争。承认的规范一元论将再分配斗争归属于承认斗争,看到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和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是有深刻洞见的,但也存在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领域的再分配斗争都与要求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对其承认有关。举例来说,工人为避免失业而发动的反对公司为获取更大利润进行合并的罢工运动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承认而斗争,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和作用范围,不能完全还原为承认。不同于霍耐特,弗雷泽认为在重视承认问题时,不应忽视、边缘化甚至替代再分配问题,因为两者交互重叠且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离和对立。但为了更好地解释和解决社会正义问题,她采取“视角的二元论”,在分析上将其区分开来,理论化各自的作用范围、从属形式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把它们看成是正义的两大基本维度。不仅如此,在弗雷泽看来,正义的维度是开放的,更多维度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通过社会斗争而被揭示出来,在后来的著作中她也详细阐述了正义的第三个维度——政治维度。这些多元的正义维度对于正义来说不可或缺且不可相互还原,共同受制于参与平等的规范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正义需要允许社会的全体(成年)成员作为平等的个体彼此相互作用的社会安排,构建了一种多维本体论基础上的规范一元正义理论。这种对正义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深入分析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领域的社会不正义,探讨其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矫正方案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能更好地解释和解决现实社会的不正义,也为当代社会正义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Nancy Fraser,Justice Interruptus: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postsocialist”condition,New York&London:Routledge,1997.
[2]Nancy Fraser,Axel Honneth,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APolitical-PhilosophicalExchange,trans.JoelGolb,James Ingram,Christiane Wilke,London&New York:Verso,2003.
[3]姚大志.何为正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加]威尔·金里卡.应奇,葛水林译.自由主义、社群和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